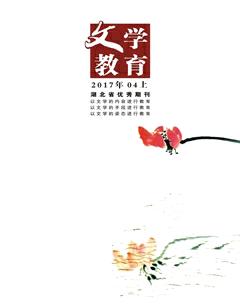淺論蕭紅生命意識變化:從《生死場》到《呼蘭河傳》
張玲
內容摘要:本文主要對蕭紅這位二十世紀三十年代的偉大的女性作家進行分析,分析的依據是《生死場》和《呼蘭河傳》兩部作品,在對這兩部作品進行研究的時候,采用的是女性的思維,在女性的視角下進行分析,從而在《生死場》和《呼蘭河傳》兩部作品的研究中,探析蕭紅作品中生命意識或者是生命意識的改變與轉變。
關鍵詞:蕭紅 生命意識 《生死場》 《呼蘭河傳》
對于一位藝術家來說,藝術家對于生活有著自己獨特的姿態和態度。正像魯迅先生對于國家民性的觀察和鞭撻,冰心先生關于母愛、童真、自然的稱贊類似,蕭紅作為一位有著自己獨特個性的作家,必然是存在這某個貫穿性的包括蕭紅特別的經歷和發現的事物。蕭紅的作品之一的《生死場》被認為是蕭紅來表現愛國情懷和民族之間抗爭的小說,而另一部作品《呼蘭河傳》是以回憶作者童年故鄉和童年生活為主題的抒情散文小說,然而筆者認為,這兩本作品的背后更為深刻的意義和主題卻被小紅隱藏起來,被讀者所忽略,在不斷的閱讀蕭紅作品,進入到蕭紅的作品世界之后,筆者終于對于之前覺得深刻的主題和意義漸漸有所發現和感悟,這種發現和感悟就是蕭紅自身特殊的對待生命的態度和感想以及生命的意識都是從蕭紅作品語言身后表達出來,從而為讀者打開了蕭紅新的世界觀和態度。
一.呈現生命的最真實的樣子
蕭紅作品的《生死場》中,作者用較為樸實的語言描寫了東北人民的生活樸實的狀態。在三十年代的時候東北那時候生活水平較為低下,在極端的貧困窮苦的狀態下,人民對能夠活下來變成了唯一的愿景。“在鄉村,人和動物兩者一起忙著生,忙著死”,蕭紅在這句描寫中,巧妙的以動物作為隱喻,間接的描寫了在那個時代的人生活的不易,生命的重要性自己不了解,同時別人也處處體現了對生命的不尊重,從一個人生到死都沒有注重到生命的重要性。馬克思也曾經說過“人是最直接的自然的存在物”,并且是有生命的的存在事物。《生死場》最多的是從形而下的視角來描寫,表現了人類作為一個有生命力的事物,是有想法的。東北的農村人民的生命是被遏制的,而這種的壓制并不是來源傳統所想的儒家的人倫體制和傳統文化中那些不合理的地方,而是來自直接的貧困以及貧困有關聯系的事物的愚蠢,在作家蕭紅的小說語言中,貧窮和愚昧是于不符合常理的道德更能遏制生命以及歪曲人性的力量。小孩子是人類中生命力最具有活力的一個生命階段,但是在這部小說中也顯示不出來生命的真正價值意義。《生命場》這部小說中不止一次的描述小孩子生命被破壞的的慘無人道的場景,比如說,王婆說:“這村子上哪家養小孩,一旦遇到孩子以后不能養下來,我就去拿著鉤子, 也許用那個掘菜的刀子,把孩子從娘肚里硬攪出來……”小說中的小金枝也因為被貧困而困擾從而暴躁易怒的金枝的父親而摔死,在遠方的呼蘭城中,生命的存在的方式在被動的沒有被尊重的狀態。蕭紅此時此刻完成了對于生命存在意義帶有哲學意義的抽象。
父親死亡,兒子哭泣,兒子死亡母親哭,兄長死了一家人哭泣,家里嫂子死亡,娘家人哭。不管哭了多長時間,不管時間長或者短,總要是到城市外面的,挖個洞把死人埋起來。如果有人問這些人他們的人生這一生為了什么,他們不會對此茫然無知不知道怎么做答,他們會直接毫不猶豫的說人活著就是為了吃和穿,如果繼續問他們,如果人死了呢,他們則會說,人死了就什么都沒有,一生都完了。一年四季,春秋寒冬不停的變換,那是從盤古開天辟地以來就存在的,在惡劣的環境中,如果受得了的自然而然就過去了,受不了的就會隨緣,自然而然,雖然自然而然的結果往往不好,將一個人、一個生命悄無聲息的毫無聲響的把那個人的璀璨的生命帶走,帶離這個世界上。至于那些沒有被帶走的人,則會在人間繼續被惡劣的環境中承受著。人類和動物都是平等的,都是在完完全全的自然的生命的狀態中。人類的生命低賤卑微,沒有任何的價值。蕭紅隱藏在關照生命的表面后,用語言描寫了生命生存最為真是的形態。生活本身的質量等,生活本身的魅力,生活的生命的樸實的美好,這些在蕭紅的作品中都有強而有力的描寫。在這些悲劇生命,生命意識的身后,我們可以從其中發現更多的更為深刻的文化的本質和源泉。作家蕭紅女士對于生命的悲劇意義的領悟已經超過了小說中的呼蘭城或者是東北某個小鄉村,而是擴展到了整個民族的生命的存在形式,傳達了我國中華民族從遠古時代就有的特有的生命的主觀觀念和意識。
二.蕭紅作品中的生命意識
生命意識往往體現在小說中生命的描寫里面,死亡往往是生命的重要的一部分。一位名人曾經說過:“傳統的生活就是生命和死亡之間的存在。”在生命過程中的任何的一個階段,我們都在不可避免的走向死亡,死亡,換一種說法,其實也是生命的另一種延續,一種特殊的生命狀態。所以,生命和死亡知識單純的統一行為的兩個對立面,在形而上的角度上來說,生命和死亡是同樣的一種哲學的問題。作為一個作家來說,張揚生命,追求夢想的一種生命的狀態,一定會考慮到也會描寫到死亡這個對立層面的形態。蕭紅的小說作品都溢滿了厚重的死亡的意識和悲劇的意識。她表現的是美好純粹的生命形態卻被外界的因素而破壞摧殘的悲劇。在《呼蘭河傳》里面,各種形形色色的角色,比如王大姐、紅辮根等,同樣在《生死場》里面打魚為生的漂亮女性月英等等,這些美麗而璀璨富有生命活力的生命卻被沉重的現實生活以及無法避免的命運而破壞從而走向死亡。有的角色作家蕭紅在作品中并沒有正面的描寫角色的死亡,但是卻也間接用周圍人的態度和語言以及外界的環境來做對比,形成一個強有力而又諷刺的對比。
作家蕭紅的用這種方法來描寫死亡,對于讀者來說并不太過于痛苦和哀傷,也不恐怖可俱,而是樸實平平淡淡的,簡略的一句話帶過,往往一句話的描寫中就透露出一個人、一個強健生命的消逝與消亡。類似這種的描寫在蕭紅的作品中多次的出現,在貌似平淡冷漠的描寫中,我們可以讀出作家內心深處的不平靜以及心酸哀傷,生命的悲慘、悲劇感在這種時候悄無聲息的散發出了對逝去生命的哀傷和感概。死亡假使發生在了最具有生命力、生命最為璀璨時期的孩童身上,而且這種悲劇的發生又與他們的父母有著千絲萬縷聯系的時候,在這個時候,死亡的本來的自身的意義便會凸顯明確出來,更加的牽動人心,并且作家在里面隱藏的感情態度以及自身的價值觀念也更加的明確具體。作家作品中不止一次的描寫孩童這種稚嫩生命的死亡和消逝,完成和突顯作家對于生命的悲劇的感概和感嘆,從而完成作家對于生命意義的肯定。死亡狀態的偶然性和殘酷性,正是由于人們對死亡缺少認知而變得過分的沉重。作家蕭紅正是在這種時候,借由這些事情表述了自己對于民族性格的生命的存在的方式,即是將不同方面的原因都黏合在神功的存在的方式中,作家描寫生命的跳動、生命的扭曲、生命的凋零的悲慘的經過,從而完成作家對于完整的生命的狀態的渴求和期盼,激發以及重新塑造一個民族的靈魂的憧憬和心愿。
三.痛苦但倔強的生命力
《生死場》的這部作品描寫的是在日本軍閥的侵略下,趙三、李青山等等這些農民傳統的抗爭,這是被壓抑的生命在外界環境的影響下進行的一次強烈的爆發。生命的高貴以及尊重等等的品質在小說中的一些主要人物的身上得到了充分的散發光芒的體現。
無一例外的,《生死場》中出現的主要角色的這些人物都是痛苦且充滿不幸的,然而他們卻都是熱愛自己生命的人,正是因為他們受到的痛苦越多,他們越能尊重自己的生命,對生命也會產生更多的感概。
在生命的角度和觀念上來說,痛苦和悲劇往往是激發一個生命產生強烈自主意識的前提條件之一,生命的偉大性和主觀意識的生長也只能在強烈壓制的自然或者社會環境的這些力量的對抗中,才能更加的凸顯和明確,它對于生命主題的進步和意志的強化都有著密切而且重要的聯系。雖然蕭紅的作品中這些任務并不一定都具有自覺主觀的生命的意識,但是他們的堅強倔強的生命力卻都是來自生命體的本能的反映。精神的自我安慰的民族的特性減少了人們對生命的悲傷的感覺,從而增加了生命的倔強和頑強,然而這些人物的倔強的生命力是一個民族連續不斷傳承下去的靈魂。
蕭紅的生命意識充滿了對生命的痛苦的感受,痛苦是生命體不可或缺的因素,人類的生命也一定要意識到痛苦的內涵。并且作家在痛苦中表達了生命對不同的目的執念,贊美了生命在承受這些痛苦的頑強。
四.結語
作家蕭紅在一定的水平上,作品對于生命的呈現已經上升到表現人類“類性”的層次。生命的哲學意義一般都是在藝術文化中隱藏著、蘊含著,這是最深刻的也是最基本的。尼采原先說過:“在生命中最為困難的階段上肯定自己的生命,生命的意識也在最高類型的犧牲當中為自己的不可窮盡而歡欣鼓舞。”另一方面,假使尼采的生命意識更深層的表達了外國那種生命的跳動和頑強的話,那么蕭紅的作品的表述就是平淡中的充滿生命活力的倔強的東方的方式,在蕭紅的作品中我們可以看出了中華民族的傳承不斷的民族的靈魂。本文通過對蕭紅的兩部作品《生死場》和《呼蘭河傳》進行深刻的研究和探究,發現了隱藏在蕭紅言語之間那種最為真實的原本生命應該存在的模樣,正是那種平淡的、樸實的。此外從蕭紅的筆下那些悲慘的生命看出蕭紅對于生命的態度,以及對于那種因為外界環境下以不人道的方式摧殘生命、對生命漠視的無奈、憤慨以及心酸。本文希望對喜歡蕭紅作品的人士以及專門研究蕭紅作品的學者提供些許的幫助,幫助讀者更能明白蕭紅隱藏在樸實語言背后所想表達出來的真實含義。
參考文獻
[1]焦玉蓮.生命的悲劇意識──蕭紅《生死場》、《呼蘭河傳》的深層意蘊[J]. 齊齊哈爾師范學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97,06:50-52.
[2]金美英.中韓現代女作家的女性意識比較研究[D].浙江大學,2012.
[3]郭延紅.“生死場”中的生死人生——蕭紅小說的生命意識[D].延邊大學,2004.
[4]王文冰.蕭紅作品悲劇意蘊新論[D].遼寧師范大學,2012.
(作者單位:中國傳媒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