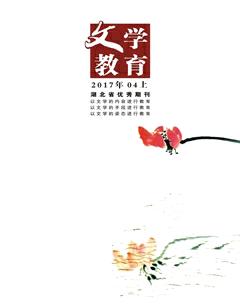嚴歌苓《床畔》中英雄話語權力的建構與瓦解
內容摘要:醫學普遍認為植物人已經喪失了認知能力,自然是毫無話語權力的。英雄,與之相反,在權力體系中,掌握著至高無上的話語權力。嚴歌苓新作《床畔》中的英雄張谷雨,身上兼有著“植物人”與“英雄”這兩個在話語權力體系里截然相反的兩極角色,是如何完成英雄話語權力的建構的?又是如何在一步一步中走向失語的?嚴歌苓的英雄觀忽視了權力對于英雄、正常人的支配與制約,她的“英雄”是依附著權力而生的。
關鍵詞:床畔 英雄 話語權力
英雄張谷雨一直活在護士萬紅、吳醫生、秦政委等人的話語中,至死仍未出場。但這不意味著他沒有話語權力:秦教導員沾著英雄的光“晉級”成秦政委;護士萬紅成為了“普通天使”;張谷雨偏僻貧窮的家鄉則成為了英雄的誕生地:“谷雨村”。這些都是英雄話語權力的體現。
福科認為話語在社會生活中有著結構性的意義,話語的建構與知識、權力都有著密不可分的關系:“權力和知識是直接相互連帶的;不相應地建構一種知識領域就不可能有權力關系,不同時預設和建構權力關系就不會有任何知識。”[1]權力往往是流動的,在傳播中得以擴散,在話語中得到進一步的塑造。
一.話語權力的建構——英雄是如何誕生的
《床畔》第二章開頭寫道:“六月的這個下午,56野戰醫院全體官兵集合到籃球場上開大會。”[2]P13會議的主講人是秦教導員,他告訴大家:“張谷雨通知雖然是個人事不省的植物人,但他的英雄精神將要衡定醫院五百多醫護人員的情操。”[2]P13-14全體大會,是我們日常生活中屢見不鮮的教育手段,通過聚集、演講、研討、表彰、批評等方式,達到某種既定目的。文中的此次會議,我們可以稱之為一場儀式。秦教導員通過開會的方式,在宣傳、歌頌張谷雨之后,賦予了“看護張谷雨”以榮譽和高尚。儀式的主體是包括萬紅在內的所有醫生、護士,儀式的主題是對英雄張谷雨的頌揚,這是一種具有象征意義的、標準化的人類行為。儀式參與的人越多、越隆重,舉行的時間越長,越是可以烘托主題。第五章中,秦教導員的訓斥無疑可以看做是前一次集體大會的延續。當得知胡護士失職之后,秦教導員并不是單獨責罵胡護士,而是開會訓斥集體。通過運用權力,秦教導員把胡護士的錯誤放置在了每一個醫護人員的身上,錯誤程度加重,涉及人員擴大,這一切都是為了烘托儀式的主題——英雄張谷雨。
有無儀式,對于形象的塑造是起著相當關鍵的作用的。嚴歌苓代表作之一《金陵十三釵》中,玉墨等人自愿頂替女學生,赴死亡之約之前,十三個風塵女子把自己裝扮成女學生的樣子,原著一筆帶過,但在張藝謀電影改編后,這一幕恰恰成為了全劇最悲壯、最慘痛的一幕。原因就在于張藝謀把這一瞬間,刻畫成了永恒、具有震撼意義的一個莊嚴儀式,這與福柯把“刑罰”場景看做是權力的彰顯其實是一個道理,定格某個最具包孕性的瞬間,將其發揮到極致。這就是儀式的效果,可以達到一種集體性的、戲劇性的效果。
與《金陵十三釵》電影有所不同的是,《床畔》中的儀式是帶有官方意味的,是官方權力主導下的結果。張谷雨連長為了救兩個年輕的小戰士,負傷變成了植物人,他完成了從一個青年連長到一個全國英雄的身份轉變。在這一轉變的背后,是權力的宣傳與滲透,他背負著儀式,背負著官方權力的運作。
不僅如此,張谷雨的英雄形象也是民間道德的一個組成部分,民眾在接受了英雄典型之后,自覺自愿地完善著英雄形象。萬紅來到張連長的老家時,距離張谷雨從常人變為英雄已經過去六年,但“這個窮鄉僻壤一直為英雄張谷雨驕傲到今天。”[2]p250墻上刷著:“向英雄張谷雨同志學習”,村子也重新命名為:“谷雨村”。新中國成立至今,這樣的情況是農村常態。宣傳標語、宣傳橫幅以其直觀性、大量性在潛移默化中完成官方話語到民間話語的轉移。除了視覺宣傳之外,張谷雨的權力話語還通過“口口相傳”這一最原始的形式完成。萬紅初到醫院,就從胡護士口中感受到了護理英雄的榮譽感,萬紅一而再,再而三的向花生灌輸他的父親是一個英雄的觀念等等,英雄觀念的形成建立在民間窄小而又親密的社會關系之上。作為一個喪失話語權的植物人,張谷雨的英雄話語權力事實上是依附于官方與民間雙重力量誕生的,在這一誕生過程中,每個人都在權力關系內尋找自己的位置和權力的從屬關系。這樣的權力主題在畢飛宇的筆下,有著較為深刻的表現。《玉米》中主人公玉米在經歷了父親失勢,玉秀失貞后,自愿嫁給權力和物質,以此獲得女性的權力。事實上,權力不僅控制我們的政治生活,還在控制著我們的日常生活,正是有了它的介入,英雄才得以占領每一個普通人的日常生活領域。
二.誕生即失語——英雄之后
新的時代呼喚著新的新的倫理秩序,自然也就呼喚著新的英雄。作品《床畔》背景被置于1976年,文革過后象征著的是一個新時代的開始。之前諸如文中提到的董存瑞、黃繼光已經成為了過去式,和平年代,張谷雨這樣舍己為人的英雄才是新時代的典型。英雄往往寄托著我們的理想,承載著新的道德倫理,而這一切已經超出了他們自身所代表的品格,象征著的是民族的典范性。
事實上,普通人一旦成為英雄,就已經被納入權力體系,對他人造成了制約與支配。秦教導員一輩子都在追隨英雄,善于發現第一。“戰爭領袖的追隨者、革命英雄的街頭群眾,嚴重當然不會有正常經濟運作的條件。”[3]秦教導員這樣的政治投機客變成了被權力異化的人;胡護士工作的疏漏被上升到了某種政治的高度;萬紅愛著吳醫生,同時也愛著英雄,她渴望英雄能夠擺脫植物人的身份。她自我賦予的使命感,讓她產生了如果自己不堅守在英雄身邊,英雄就會落寞而逝的英雄就會消失的心理暗示,即使在張谷雨去世之后,她也自愿選擇當“最后一個嬤嬤”。這是權力對于一個善良堅守之人的制約與支配,萬紅并不是嚴歌苓筆下所謂的“英雄”,而是英雄話語權威的犧牲品。
更重要的是,英雄的話語權力也是被不斷制約的。官方體系再不斷塑造新的英雄,“英雄研究生”、“英雄歌星”逐漸替代了張谷雨這類英雄的地位。英雄話語帶有永恒性,但英雄形象確實暫時的。“漸漸地,玉枝覺得她谷雨哥躺的那張白鐵床是艘船,把她撂在岸上,久了,床畔的一切都在流動,流動的一切都在變化。”[2]P73船與河岸象征著兩類人之間的身份對立,象征著秩序和流動的對立,在《床畔》中,面對不斷流動的秩序和規則,萬紅與張谷雨這兩個昔日的英雄,已經成為了權力范圍內的邊緣人。
英雄就算無法維持自己的“英雄”形象,也再也無法回到“常人”。卡萊爾定義英雄:“對他而言,只有真理是存在的,其他的只是影子,騙人的虛空。”[4]如果英雄指的僅僅是忠實,那么就給人們灌輸了一個觀念:只要堅守信仰,抓住機遇,人人皆可成為英雄。這利用的是人們的普遍心理:英雄是在“我們”中產生的,英雄是“可復制的”,追趕的目標近在咫尺。“當代民眾具有把事物在空間上和人性上變得更靠近些的愿望,這與他們通過接受現實的復制品來戰勝每一個現實的獨特性意愿同樣強烈。”[5]但“英雄”與“常人”往往是一對矛盾,當過度拔高了英雄形象之后,人們便無法對英雄產生認同,反而把英雄從“我們”中排除在外,讓英雄變成“他們”。正如《床畔》中,秦政委打算派萬紅去一線,找別人來照顧張連長,萬紅提醒秦政委張連長的英雄身份,但“張連長舍己救人的英雄事跡沒讓這個老首長心生敬意”[2]P206。不是大家健忘,而是眾人對英雄的認同只是短時間內的,是權力壓迫下的被迫認同,張谷雨英雄只活在萬紅那一代人的心中。更富有戲劇性的是,花生將他的爸爸當成了“活玩具”,作者通過兒童視角進行反諷,佯裝無知者,為了說明:變成了英雄的常人已經與自己本身的身份產生了脫節,并再也無法回到常人狀態。由此可見,權力帶來的影響是無法磨滅的。在權力的更迭中,英雄早已被權力打敗,變成被奴役、被支配的符號。
隨著多元、自由觀念的深入,當代英雄不斷被解構,韓東用《有關大雁塔》的呼聲來消解英雄和崇拜,所以在《昨天再會》、《北門口預言》中,“韓少功總是忍不住要講眼光轉到英雄氣概背后,看一看隱藏在英雄氣概背后的猥瑣。”[6]面對英雄價值觀的崩塌,嚴歌苓試圖重建英雄,起人們對英雄的關注,為英雄招魂。但為什么嚴歌苓筆下的英雄形象如此迅速的被建構,又如此迅速的喪失?這與嚴歌苓的英雄觀有關,劉禾在研究五四時期國民性討論時稱:“我們的困難來自語言本身的尷尬,它使我們無法離開有關國民性的話語去探討國民性(的本質),或離開文化理論去談論文化(的本質),或離開歷史敘事去談歷史(的真實)。”[7]如果我們無法離開英雄話語去討論真正的英雄,那么英雄也不過是權力掩蓋下的假象。
參考文獻
[1]米歇爾·福柯:《規訓與懲罰》,劉北成,楊遠嬰譯,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6,第29頁
[2]嚴歌苓:《床畔》,長江文藝出版社,2015
[3]馬克思·韋伯《學術與政治》,錢永祥等譯,廣西師范大學,2010,第210頁
[4]托馬斯·卡萊爾:《英雄與英雄崇拜》,何欣譯,遼寧教育出版社,1998,第165頁
[5]瓦爾特·本雅明:《機械復制時代的藝術》,李偉,郭東譯,重慶出版社,2006,第6頁
[6]林建法等:中國當代作家面面觀,復旦大學出版社,2010,第637頁
[7]劉禾:《跨語際實踐——文學,民族文化與被譯介的現代性》,宋偉杰等譯,2002,第103頁
(作者介紹:曹婷,南京師范大學強化培養學院文科強化班學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