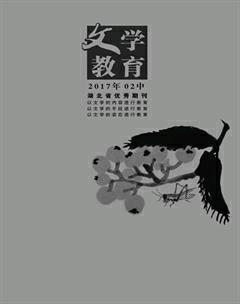女性思維中的“男權意識”
內容摘要:在小說《我不是潘金蓮》中,李雪蓮的形象不能簡簡單單的被解讀為對男權的反抗和對話語權的爭取,她的形象具有另外一層深層內涵。具體來說,李雪蓮堅持二十多年的告狀,她最終的目的是為了洗刷丈夫對自己的污蔑,表面上她為了維護自己的“權利”和“尊嚴”不懈努力,實際上她更深深的陷入男權意識。李雪蓮的形象既有對女性思維中的“男權意識”揭示,也有對女性的自我奴化現象深層剖析,以及對權利文化的整體批判和斯德哥爾摩情結現象的深層探究。
關鍵詞:李雪蓮 “男權意識” 自我奴化 權利文化 斯德哥爾摩情結
劉震云作為80年代新寫實小說的開拓者和領軍人物,他的作品對新時期文學的影響是巨大的。1987年創作的《塔鋪》是他的成名作,之后的作品《新兵連》和《一地雞毛》以新寫實手法寫出士兵人生和官場的另一面;90年代以來他的創作轉向故鄉系列小說,《故鄉天下黃花》、《故鄉鄉土流傳》以及《溫故一九四二》《手機》等故鄉小說揭示了中國現當代鄉村歷時的面貌;新世紀以來,他的長篇小說《一腔廢話》《一句頂一萬句》、《我叫劉躍進》等,寫出了當代人生存的悲哀與困境。
《我不是潘金蓮》出版于2012年。2016年9月改編為同名電影上映(馮小剛執導,范冰冰主演),引起強烈反響。小說從李雪連與丈夫秦玉河的假離婚說起。李雪蓮意外懷了二胎,為了逃避懲罰,和丈夫假離婚,沒想到弄假成真,秦玉河最終和另一個女人結婚。秦玉河不僅不答應復婚,而且還污蔑李雪蓮是潘金蓮,李雪蓮為了洗刷屈辱,證明自己的清白,堅持了二十年告狀。李雪蓮最終因為秦玉河的死亡而放棄告狀。
李雪蓮堅持二十年上訪倔強的給自己正名,她的形象既有對女性思維中的“男權意識”揭示,也有對女性的自我奴化現象深層剖析,以及對權利文化的整體批判和斯德哥爾摩情結現象的深層探究。
一.女性思維中的“男權意識”
潘金蓮是中國古代極具反叛性特征的女性形象之一,她不在乎所謂的封建倫理道德(“三從四德”、“男尊女卑”、“夫為妻綱”等),為了滿足自己的欲望,勇于追求自己的情欲,不斷挑戰封建倫理綱常。在劉震云眼中,李雪蓮與潘金蓮具有相似性:一方面她們都是反叛者角色,另外一方面她們最終都以失敗告終。不同之處在于,潘金蓮所反叛的是封建倫理道德秩序,而李雪蓮的叛逆是為了解脫丈夫秦玉河強加給她的冤屈,她堅持二十多年的告狀的最終目的就是證明:我不是“潘金蓮”,徹底清洗丈夫對他的誹謗。
李雪蓮的人生價值觀和潛意識里:潘金蓮是淫蕩、惡毒、不守婦道的代名詞,潘金蓮竟然毒死了自己的丈夫武大,又與西門慶風流快活,她完全沒有羞恥之心,她是一個有著深重罪孽的女性。李雪蓮被丈夫污蔑為潘金蓮,于是她想通過告狀的方式來證明自己并不是壞女人,但是她的一系列行為卻是在男權制社會認證自己的“身份”,李雪蓮堅持二十年的告狀源于男權社會和男權意識對她的影響和壓迫,肉體上的壓迫可以反抗,精神上的壓迫則根深蒂固。從古至今,男性一直處于主導地位,幾乎各個方面,女性都是處于男性的從屬地位,女性在潛移默化中不斷的接受男性所規定的道德秩序與倫理準則,因此具有了女性思維中的“男權意識”。在人類主導的社會中,一切政治、經濟、宗教、法律、道德等都是為主流意識形態服務的,而男性話語又恰恰是社會中的主流。劉震云把李雪蓮放在這樣的社會環境中,從某種意義上來說,也就為她的悲劇命運埋下了伏筆。在這個過程中,李雪蓮獨立人格完全喪失,所有的內心欲望被深深地遺忘,她的生存狀態完全受制于男權社會。她蜷縮在男權世界的陰影里,雖然經過幾次痛苦的掙扎,但最終還是看不到太陽。傳統文化的很多觀念禁錮了她的思想,壓抑了她的欲望,李雪蓮一次次的狀告無果,表明了傳統男權文化對女性生存的強大殺傷力。李雪蓮告狀的最終目的是想成為男權世界觀中的完美女性,她就是要維護自己的名譽,捍衛自己的清白,但她的行為不可避免的陷入了男權思維,最終還是深陷男權所設定的牢籠中,她不得不成為社會和男權意識所賦予她的女性角色,成為男人眼中的“女人”,這進而說明她更加的依附于男權。可以說,李雪蓮的一生從來就沒有按照自己的意愿過自己的生活,因為作為一個女人,她從來就沒有得到過屬于自己的真正的女性地位,從到至尾被污蔑為“蕩婦潘金蓮”。李雪蓮其實想成為的是男人眼中的好女人,并且這種觀念伴隨和控制著她的一生。
二.自我奴化意識
自母系氏族社會解體后,女性主體地位逐漸下降,男性在政治、經濟等各個方面處于主導地位,女性慢慢成為男性的從屬。伴隨這男性和女性之間的不平等關系,女性屈服于男性權威,結果是:女性的內在主體力量持續變弱,自己的主體意識喪失,漸漸成為男性的附庸,變成男人的奴隸,家庭地位一落千丈,無法擺脫男性的強權壓迫。在這部小說中,李雪蓮不斷受丈夫秦玉河的壓迫,不斷被奴化,漸漸陷入自我奴化的怪圈之中。李雪蓮希冀本身有自力更生的能力,但時刻受到秦玉河與各種官員的逼迫:丈夫拋棄自己和孩子,敗壞她的名譽,害的她差點自殺,孤苦無依的情況下選擇告狀卻又受各層官員的推三阻四,無人關照。她始終不能將成為完全獨立的一個人,她告狀,為恢復自己的名譽不辭辛苦,但最終淪為男權與社會壓迫的犧牲品,她不得不依賴與秦玉河與各級官員,完全喪失了自身的主體意識和主體地位,不斷走向自我奴化的深淵。
女性自我奴化的過程其實是從內心接受了自己比男人低一等的現實。當女性行為和話語權由男人決定時,女性永遠生活在男性話語權的陰影當中。女性行為的設定完全由男性控制,男性把自己的思想強加于女性,進一步泯滅女性的主體意識,使女性失去獨立思考的能力,使女性一直處于從屬地位,并在不知不覺中令女性成為了男性的奴隸。受丈夫秦玉河的影響,李雪蓮的精神世界扭曲、變形,削弱了自我力量,她泯滅了自我發展的意識,完整人格和自由精神的發展也遭到破壞,終其一生無法擺脫自我奴化。從狀告丈夫秦玉河到告倒一批又一批的官員,她一生的目標為自己正名—“我不是潘金蓮”,最終因丈夫的意外去世而變得無足輕重,歷經痛苦掙扎、理想最終幻滅。她要求為自己正名,希望恢復自己名譽被官員無一例外地拒絕,在現實世界中掙扎、苦斗,撞得頭破血流,甚至犧牲了青春。故事的最終結局是李雪蓮一生都活在男性為她所設置的觀念牢籠中。
父權制替代母權制以后,女性地位在家庭中的逐漸失去主導地位,財產由男性掌控,男性可以支配女性的一切,女性成為男性的附屬,甚至成為能男性的奴隸,長期受制于男性。自五四之始,要求女性自由解放的呼聲在中國越來越高漲,時至今日,透過女主人公李雪蓮的境遇,我們不得不再一次思考當代女性的現實處境問題。為了保住丈夫的工作,李雪蓮即使意外懷了二胎,想通過假離婚的方式逃避懲罰,丈夫秦玉河假戲真做,導致李雪蓮被拋棄,并且的污蔑她也說是潘金蓮。秦玉河當著許多朋友的面羞辱她,污蔑她是潘金蓮,不遵守三從四德,沒有羞恥心。這一指責的原因竟是當年成親時,李雪蓮不是處女。在男權制度依然盛行的今天,李雪蓮顯然是無辜而又弱小的。當男人可以不顧道義良知胡作非為時卻還在要求女人的貞操與婦道,這是女性的可悲,也是現實的可憎。女性自我奴化的思維如同一條沉重的鐵鏈拴在幾千年封建社會女性的身上并延續至今,女性自身失去了個性和主體意識。
三.權利文化對女性的壓迫
權力,是劉震云小說的主題之一。縱觀劉震云的小說,無論是他早期的《塔鋪》還是90年代末的《故鄉面和花朵》,小說的主題一直沒有間斷對權力的探索。
劉震云的小說具有權力自覺的權力批判意識,通過人生的眾生相揭露社會的黑暗,并且展現了畸形權力扭曲人性的悲劇。劉震云始終深入剖析權力給人類精神帶來的災難,展示權力對人精神的茶毒和心靈的栽害,無情地撩開權力文化的面紗。李雪蓮堅持二十年的告狀無果源于權力對她的無情摧殘和壓迫。小說中,作品中的官員說是要為人民謀利益,實際上他們只關心自身的仕途,這些人高踞社會上層,無視李雪蓮的一次次狀告,他們是玩弄權力、玩弄人民,以滿足個人欲望的小人。這部小說無不揭示著官員對底層人民的欺壓,剖露出權力對人的壓迫。
主人公李雪蓮為了糾正一句話,為了證明自己不是“潘金蓮”,而堅持了二十年的上訪路,其實主人公李雪蓮的要求并不高,只是想通過告狀來證明離婚是假的,想恢復自己的名譽。她只想要一個能相信她,肯傾聽她的人。但是在李雪蓮告狀的過程中,董憲法、荀正義、史為民、蔡富邦為了保護自身的利益,極盡所能,或恐嚇,或欺騙,或威脅,濫用手中的權力,極力推三阻四,不想攤上這一個“燙手的山芋”,甚至動用暴力手段,在勸阻無效的情況下,把她關進看守所,逼得李雪蓮走投無路想要自殺。到最后,李雪蓮也沒有擺脫權利對她的壓迫,一步步被權利所掌控、迷失了人生的方向、失去了活下去的信心。通過對李雪蓮這一人物形象的靈魂透視,作者表現出對當下中國中國權力文化的深刻探究,在此反思的基礎上,劉震云對官場和官員腐敗的種種丑惡現象以及權力文化籠罩下的官員種種丑陋行為進行了揭示和批判。在對權力文化批評和反思的同時,劉震云通過這部小說向我們提出了著一個問題:中國自古就重視權力的運作,無論國家權力還是地方權力,都是統治階級統治被統治階級的尚方寶劍。在物欲橫流、價值觀念錯位、精神世界迷失的社會環境中,人們瘋狂的追逐權利,為了權利不惜刀劍相向,不顧他人死活,最終,人們應該走樣擺脫權利文化的桎梏呢?就像小說中的李雪蓮,她作為生存的個體,蕓蕓眾生的一員,終其一生都活在權利文化的陰影之下,官員對她的壓迫對她生活和命運帶來了痛苦和磨難。我們看到,弱小的人肉軀體在強大官場權力面前的無能為力,權力是控制人們的祛碼。有了權力,便可以把自己的意志強加在他人的身上。權力打破了李雪蓮原有的平靜生活,她失去了自我與自由,不再對生活充滿美好的憧憬。在這部小說中,所有的人不知不覺都被權利所掌控,所奴役。權利變成了官員作威作福的工具。
四.斯德哥爾摩情節
斯德哥爾摩綜合癥(Stockholm syndrome),又稱斯德哥爾摩癥候群,是指犯罪的被害者對于犯罪者產生情感,甚至反過來幫助犯罪者的一種情結。這一詞起源于瑞典,1973年8月,瑞典斯德哥爾摩的一家銀行突然闖入兩名全副武裝的劫匪。劫匪扣押了4名銀行職員作人質,與警察對峙了6天之久。6天后,警方設法鉆通了保管庫,用催淚瓦斯將人質和劫匪驅趕出來,狙擊手同時作好了危急情況下擊斃劫匪的準備。然而,離開保管庫后,3名人質反而將劫持者圍了起來,保護他不受警方的傷害。被警方營救出來后,人質非但沒有控訴綁架者,相反卻為劫匪辯護,對警察的調查取證工作也采取堅決不合作的態度,致調查取證工作困難重重。這些人質之所以表現出如此怪誕的行為,是因為他們患上了一種心理疾病。從此,人們把這種心理疾病命名為“斯德哥爾摩綜合征”。按照心理學分析,斯德哥爾摩綜合癥是一種病態的心理。
小說中李雪蓮與丈夫秦玉河也有著這種類似的“綁架”與“被綁架”、“施虐”與“被施虐”的關系。通讀小說,我們會驚訝的發現,李雪蓮對秦玉河的愛,絕不是正常的男女的情感,而是一種病態、的畸形的情感。李雪蓮長期經常遭受丈夫的精神暴力,被秦玉河誣陷為“潘金蓮”但她沒有選擇徹底離開,對丈夫心存幻想并有依賴情緒,她沒有選擇結束這種虐待關系,陷入了“綁架者”迷戀“被綁架者”、“施虐者”迷戀“被施虐者”的怪圈中。在李雪蓮和秦玉河的關系中,我們可以看出,秦玉河是傷害李雪蓮最深的人,也是對李雪蓮感情踐踏得最狠的人。李雪蓮中途本有過放棄告狀的打算,準備找秦玉河和解,但是喝酒上頭的秦玉河當著眾人的面說:“你是李雪蓮嗎,我咋覺得你是潘金蓮”。“李雪蓮如五雷轟頂。如果不是伸手能扶著墻,李雪蓮會暈倒在地上。她萬萬沒想到,秦玉河會說出這種話來。今天之前,她折騰的是她和秦玉河離婚真假的事情,沒想到折騰來折騰去,竟折騰出她是潘金蓮的事。”為什李雪蓮受盡了丈夫的折磨,但在心理上對秦玉河依然有強烈的依戀?第一個原因是受封建禮俗和道德觀念的影響。古代封建社會李雪蓮一直處于弱者的地位,她依賴于丈夫秦玉河,對丈夫有著從一而終的依賴性。在李雪蓮與秦玉河感情中,李雪蓮從始至終都依戀于,秦玉河,她陷入了一種思維陷阱,找不到其它出路。在男性占有絕對話語權的時代條件下,她對愛情與婚姻的認識和理解上有某些局限,對丈夫具有一定的依賴性。第二個個顯而易見的原因是,對于李雪蓮來說,離開自己曾經愛過或仍然愛著的人,是一件非常困難的事情;而且李雪蓮為了這個家庭付出了太多的心血,她犧牲了自己青春,也沒有盡到一個當母親的責任,自己的兒子從小到大無人照顧,正是因為過于傾入了過多的心血,才越難做出選擇離開秦玉河。因此李雪蓮對壓迫殘害自己的丈夫不但不恨,反而對秦玉河產生了依戀的情緒和依賴的情結,李雪蓮陷入瘋狂與糾纏中,李雪蓮面對丈夫秦玉河的污蔑和背叛,她為了自己的愛情,倔強的要給自己討個說法,為了證明自己的清白,犧牲了青春,疏忽了孩子,荒蕪了天地,花光了所有的積蓄,到最后卻換來了狀告無果,孤老終生。這只能說明李雪蓮患上了愛情斯德哥爾摩綜合癥。
五.結語
這部小說具有自覺的文化批判意識。劉震云一方面透過官場的眾生相揭露官場的黑暗,另外一方面也展現了權利文化扭曲人性的悲劇,在《我不是潘金蓮》這部小說中劉震云著力刻劃了李雪蓮這一犟女形象, 并賦予這個形象以較高的社會價值和文學價值。他對女主人公精神世界進行發掘,展示了她的痛苦、抗爭,更重要的是在女性的男權意識、女性自我奴化、權利文化的整體批判以及斯德哥爾摩情節等問題上進行了深刻的探索,劉震云以人文關懷的態度關注當代社會現實,深入分析社會現實問題,對人們具有一定的啟示和引導作用。
參考文獻
①劉震云.《我不是潘金蓮》,《長江文藝出版社》P64,2012年9月
②《京華時報》,《劉震云小說探討荒誕底線》,2012年8月
③高翔.《反叛潘金蓮的反叛—我不是潘金蓮的解讀》,《名作欣賞》2014.1月
④高芳艷.我不是潘金蓮中李雪蓮人物形象的女性主義解讀,《文本分析》,2014.4
⑤倪素平.《對我不是潘金蓮中李雪蓮的人物形象解讀》,《短篇小說》,2014.9
⑥劉震云.《潘金蓮是前所未有的女性形象》,鳳凰網,2012年9月
(作者介紹:鄭稚丁,中南民族大學文學與新聞傳播學院2015級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