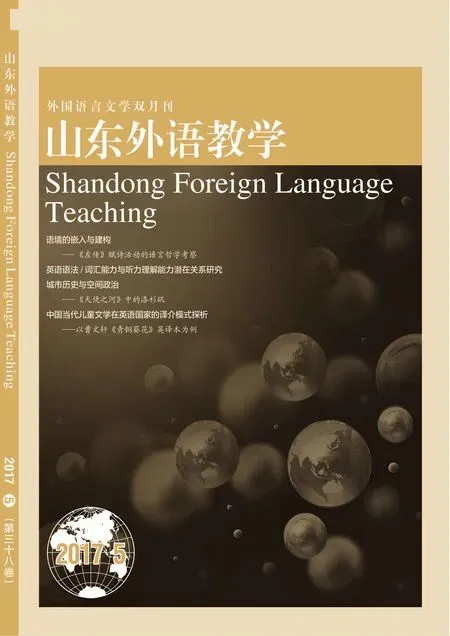城市空間與生存張力:解析賴特《局外人》
龐好農
(上海大學 外國語學院, 上海 200444 )
城市空間與生存張力:解析賴特《局外人》
龐好農
(上海大學 外國語學院, 上海 200444 )
賴特的《局外人》講述了美國黑人生存空間、空間遷移和空間重構等方面的故事,其筆下的城市空間成為物理空間、精神空間和社會空間的有機統一體。他借助于“公眾空間”、“職場空間”、“空間重構”等概念界說了城市空間的物質性、社會性和精神性,展現了非裔美國城市自然主義小說的空間詩學。賴特從城市空間遷移、生死空間遷移和種族空間遷移三個方面描寫了芝加哥和紐約的城市空間里黑人和白人對自身身份的困惑和迷茫,同時還揭示了空間變換后的身份焦慮感和惶恐感。在社會空間視角導向下,賴特展現了因空間重構而產生的道德倫理危機,顯示出熱愛生活和國家的人文情懷。
理查德·賴特;《局外人》;城市空間;生存張力;道德倫理危機
1.0 引言
理查德·賴特(Richard Wright,1908-1960)是美國20世紀中期的著名作家。他的文學作品主要描寫了19世紀末至20世紀中期的美國種族問題,揭露了種族歧視和種族偏見對黑人的重大傷害。不少文學評論家認為,賴特的文學作品促進了主流社會對黑人文化的認知,使黑人問題第一次得到主流社會的理性直面。因其對現代黑人小說發展的巨大貢獻,他被學界譽為“美國黑人小說之父”。除《土生子》(NativeSon,1940)和《長夢》(LongDream,1958)外,《局外人》(TheOutsider,1953)是賴特的另外一部優秀作品。該小說以美國20世紀三四十年代的種族形勢為背景,描寫了城市黑人知識分子的生存窘境和不懈抗爭,揭露了種族主義、專制主義和存在主義社會環境里的生存危機和信仰危機,表明種族偏見占主導地位的社會環境制約了黑人青年生存和發展的城市空間。社會非理性促使個體非理性惡行的出現和發展,導致黑人青年從個人空間的自發捍衛者發展到存在主義式唯我論的自覺奉行者,給社會、家庭和自我造成難以挽回的損失。
美國學界把《局外人》視為非裔美國城市自然主義的重要作品。古納爾德(Jean-Francois Gounard)(1992)、法布爾(Michel Fabre)(2008)等認為這部小說體現了賴特的作家使命,揭露了黑人青年在信仰危機中的唯我性癲狂;菲爾格爾(Robert Felgar)(2000)和波奇馬拉(Anna Pochmara)(2011)等認為這部小說的自然主義視野生動地再現了美國黑人的生存困境;辛格(Amritjit Singh)(1995)和曲塞(Steven C. Tracy)(2011)等認為這部小說是芝加哥黑人文藝復興的代表性作品之一,與薩特存在主義思想有著密切關聯,揭示了無限追求對人性的扭曲。國內學界也對這部小說表現出濃厚的興趣,楊昊成(2010)等認為在《局外人》里,賴特的寫作超越了種族局限性,表明他已經從早期的馬克思主義狂熱信徒轉為理想幻滅后的尼采主義者。其實,《局外人》呈現出很強的空間布局意識,展現了賴特的空間思維脈絡。賴特從多維度描寫黑人青年在種族主義社會環境中的空間變遷和人格演繹,各種空間的形成和變化直接預示和再現了黑人的生存危機和種族困境。法國思想家亨利·列斐伏爾(Henri Lefebvre)“以‘三元辯證法’為哲學方法論基礎,分析了城市空間的三種形態,即自然空間、精神空間和社會空間,認為城市空間是自然空間、精神空間和社會空間的三維統一體”(高春花,2011:31)。他的理論有助于闡釋這部小說的空間問題。因此,本文擬采用列斐伏爾空間理論的基本原理,從三個方面探析《局外人》中城市空間與生存張力的內在關聯:社會空間的排斥性、空間遷移的非理性和空間重構的冷酷性。
2.0 社會空間的排斥性
社會空間是一種物質產物,與其他物質要素有著密切的關系,主要涉及一定社會語境里人際關系和身份認同問題。人際關系和社會生態賦予社會空間以形式、功能和意義。因此,社會空間“不僅是社會結構布展的某種場面,而且是每個社會在其中被特定化的歷史總體的具體表達”(牛俊偉,2014:143)。由此可見,社會空間與政治有著密切的關聯。巴米·沃夫說,“社會構成空間在政治上絕不是中性的,通常會充滿斗爭和沖突,因此,每一個空間秩序都會反映出社會利益,空間關系可能會因服務于權力而被扭曲”(Warf,1993:111)。的確,在一定社會形態里,社會空間結構通常會形成以權力為中心的運作原則,突出社會空間的公眾性和排斥性。因此,筆者擬從公共空間、職場空間和家庭空間三個方面,探究賴特在《局外人》里所描寫的社會空間里的生存張力。
隨著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結束,黑人的人權意識和平等意識日益增強,為美國民權運動的來臨打下了良好的社會基礎。美國城市空間的社會化狀況越來越表明現有公共空間的狀態和氛圍還嚴重滯后于社會發展。賴特在《局外人》里揭露公眾空間的敵意性、狹隘性和奸詐性。在芝加哥城里,城南地區是黑人聚居區,居住環境惡劣、社會治安失控、色情場所泛濫;在白人生活或工作區,黑人為白人當奴仆或從事白人不屑為之的工作。白人把黑人視為下等人或道德品質低下者。郵局秘書芬奇借錢給克洛斯時充滿蔑視地說,“你們黑小子在城南地區制造了不少麻煩,你們每晚都沉溺于酒色之中吧!”(Wright,1991:440)他把所有的黑人想象成色情場所的常客。此外,賴特還描寫白人與黑人的疏離性。克洛斯在火車上看到黑人列車服務員鮑勃(Bob)為乘客的杯子倒開水時,一名白人婦女無意中一揮手打翻了鮑勃手上的開水茶壺,導致她自己被燙傷。那名白人婦女把所有責任都歸咎于鮑勃,聲稱是鮑勃導致了這個事件。其實,她本人才是這個事件的主要責任人。如果她不去揮那一下手,就不會碰到開水壺,也就不會發生這個事件。車廂里有名白人牧師是整個事件的目擊者,但出于對黑人的敵意,他不愿站出來為黑人說一句公道話。他的不作為導致鮑勃被公司開除了公職。最后,賴特還描寫了公眾空間的欺詐性。黑人大媽凱瑟(Cathie)是一名身世凄苦的寡婦。騙子懷特(White)和密爾斯(Mills)為了詐騙凱瑟的財產,哄騙她賣掉現有的房子去炒房地產,這個陰謀差一點使善良的凱瑟大媽陷入破產的陷阱。這些白人騙子的陰險和貪婪是這個詐騙事件的源頭。
職場空間指的是勞動者為謀生而勞動的區域。賴特在這部小說里描寫黑人青年克洛斯(Cross)在芝加哥郵局的工作場所。克洛斯是郵件分揀員,每天都要分揀成千上萬的信件,枯燥而無聊。他的三個朋友布克(Booker)、喬(Joe)和品克(Pink)都是郵局的工作人員,對工作沒有熱忱,上班盼望下班,一下班就一起到酒吧去。黑人的職場空間猶如玻璃天花板,所以他們不論工作多么努力,為單位做出的貢獻有多大,仍然不可能得到升遷的機會。他們的生活猶如一種“社會死亡”,整日到處游蕩,尋歡作樂。職場空間的無前途,導致黑人過著行尸走肉般的生活。在當時的社會環境里,不論多么聰明,多么勤奮,黑人都無法獲得與白人平等的升遷機會,顯示了黑人的政治、經濟和文化地位的低層次固化。
賴特在這部小說里描寫得最好的社會空間是家庭空間。主人公克洛斯的道德淪喪引起家庭空間的張力劇增。由于職場空間的無前途性,克洛斯把自己的追求轉向吃喝玩樂。他干了兩件讓妻子格萊迪絲(Gladys)傷心無比的事:一是當格萊迪絲因生小孩住院時克洛斯在家里招妓,被格萊迪絲撞見;二是克洛斯勾引未滿16歲的黑人少女朵特(Dot)。克洛斯對格萊迪絲妻子身份的踐踏導致他與家庭空間的疏離。為了懲罰克洛斯的出軌行為,格萊迪絲勒令他馬上去辦三件事:(1)簽字把房子轉讓給格萊迪絲;(2)簽字把汽車轉讓給克萊迪絲;(3)找郵局財務部賒賬800美元。格萊迪絲的三個指令剝奪了克洛斯的財產權,使他陷入職場空間的債務危機。她還以聯合朵特指控他強奸少女為要挾,以經濟手段緊縮他在家庭的生存空間。此外,克洛斯在家庭生活中的不端行為和好色品行也受到其母親達蒙(Damon)的強烈譴責。達蒙年青時曾遭花花公子騙財騙色,所以對玩弄女性情感的行為痛恨無比。總之,克洛斯在家庭空間里遭到來自三個方面的壓力:格萊迪絲的索賠、朵特的逼婚和母親達蒙的指責。這三股壓力猶如三股絞索套在克洛斯的脖子上,迫使他一步一步地討厭和遠離家庭空間,以逃離自己的家庭空間為最大愿望。賴特通過對家庭空間的描寫探討了性別問題、人格問題和家庭經濟責任問題。正如伊麗莎白·海耶斯所言,“住宅是性別政治和階級斗爭的舞臺。對于黑人女性來說,種族政治當然也通過住宅來上演的”(Haynes,2004:671)。住宅在黑人社會生活中起著主要作用,精神壓力會極大地壓縮他的生存空間。
因此,賴特在這部小說里所描寫的公眾空間、職場空間和家庭空間是社會空間的主要表現形式,也是城市居民每天都要去的空間。個體生活與社會空間融合后便會產生精神和社會特質,與社會語境和人際交往有機結合,產生獨具特色的空間意義。賴特強調社會空間與人的特質、社會特性、社會結構和倫理道德觀等有著密切的關系,認為城市空間的社會性、種族性和個體性造就了人們各自的生存空間。挑戰社會倫理底線的行為必然會引發人際關系張力和身份認同危機,縮小或毀滅自我的生存空間。
3.0 空間遷移的非理性
空間遷移是空間變化發展的一種表現形式,指的是在一定語境下人從一個空間轉移到另一個空間的行為或過程。“人們通常借助空間轉移方式來追求自己的財富夢和政治野心,實現自我身份的轉變,但通常會困于非此非彼的閾限空間”(趙莉華,2011:2)。賴特在《局外人》里描寫黑人在美國社會所經歷的空間遷移,展現了空間遷移的理性和非理性。因此,筆者擬從城市空間遷移、生死空間遷移和種族空間遷移等方面來探究賴特在這部小說里所揭示的空間遷移與人性演繹。
城市空間遷移指的是人們從一個城市遷徙到另一個城市的過程。城市是人類文明發展到一定程度后形成的產物,可以視為一種人為的空間結構和社會形式。城市的空間特性不同于一切自然屬性的事物。其實,“城市空間的出現是對自然空間的一種侵犯和掠奪,城市符號象征著對自然的征服。這種對自然的消滅和抹殺給都市人帶來不可磨滅的影響,生活在城市中的人,也逐漸壓抑和褪去自身的自然屬性,從而導致人格的不健全和身份感的異化”(李圣昭、劉英,2014:57)。賴特在這部小說里描寫了兩個城市空間遷移的事件:克洛斯事件和鮑勃事件。芝加哥地鐵顛覆事件為克洛斯的城市空間遷移提供了機會。在芝加哥城市空間里遭遇了生存困境的克洛斯,無法解決自己與原配妻子克萊迪絲和情人朵特之間的關系,克萊迪絲的拒不離婚和朵特的堅決要結婚把克洛斯推到了難以消解的兩難境地。地鐵顛覆后的新聞報道把克洛斯列入了死亡者名單。對芝加哥城市空間徹底失望的克洛斯,借此機會,默認了報上錯誤消息,悄然前往紐約,去開辟自己的第二個城市生存空間。克洛斯是帶著追求更好生活的美好愿望去進行自己的城市空間遷移的。在這部小說里,賴特還描寫了一個被迫的城市空間遷移的故事。鮑勃因在列車上為顧客摻開水時燙傷了一名女顧客而被鐵路公司解雇,他是一名美國共產黨員,擔任列車行李工工會的負責人,因此,他利用職務之便,組織工人們起來抗爭,但遭到美國共產黨中央負責人反對。但鮑勃不顧組織原則,繼續組織罷工。因此,美國共產黨組織負責人吉爾(Gil)秘密向紐約警察局告發,指認鮑勃是來自西印度群島的非法移民。最后,鮑勃被驅逐出境。這個事件使鮑勃與妻子和家人分離,使其家庭陷入了解體的危機。賴特以此揭露了美國共產黨組織的非人性和機械性對黑人生存空間的限制或毀滅。
在這部小說里,賴特還描寫了生死空間遷移的故事。生和死是人生的兩大節點,其轉換必然導致當事人命運的改變。賴特講述了克洛斯和杰克的生死空間遷移。地鐵顛覆事件后,克洛斯的母親、妻子、孩子、情人、朋友和單位領導都認為克洛斯遇難了,因為警察從一名死者身邊找到了克洛斯的身份證明。其實,這個證明是他逃離現場時不小心遺落在事故現場的。這樣,在這些人心目中,克洛斯就是“另一個世界”的人,但出于對家人和朋友的思念,克洛斯在地鐵傾覆事件后不久偷偷地跑到家附近,偷窺他們的生活狀況。在小說末尾部分,克洛斯被捕,艾利檢察長找到他的家人。當家人得知克洛斯還活著的消息時,其母親達蒙被活活嚇死;妻子格萊迪絲覺得難以置信。這是虛擬生死空間的現實版再現。克洛斯在生活中奉行唯我主義理念,只愿接受共產黨組織給他帶來的福利待遇,但拒絕加入共產黨。此外,他漠視黨組織紀律,涉嫌謀殺美國共產黨的兩名中央委員。因此,美國共產黨中央主要負責人布里明(Blimi)指派了兩名特工蒙特斯(Mentis)和亨克(Hunk)去追殺克洛斯,最后把正要跨入出租車逃跑的克洛斯當街擊斃。克洛斯的人生歷程演繹了生死空間的瞬息遷徙,揭示了存在主義者對無限權力的追求必然會導致自己命喪于其他存在主義者之手的悲劇。
種族空間的遷移是這部小說描寫的另一個亮點。賴特通過白人檢察官艾利(Eli)之口,揭示了種族空間遷移的窘境:在文化移入中,黑人學習和繼承了白人文化的精髓,同時也接受了白人的價值觀和世界觀;但黑人還是被白人社會視為局外人和他者。由于不利社會環境對黑人生存空間的擠壓,黑人難以真正融入白人社會。黑人接受白人空間之后時常會與現實白人社會的諸多方面發生沖突,白人文化的排斥性和種族主義者的敵意使黑人種族空間的遷移困難重重。賴特關于種族文化空間遷移問題的描寫旨在展現黑人對不合理社會制度的反感、憤怒和抗爭。在《長夢》里,為了在紐約地區開展“抵制白人房東種族歧視”的運動,吉爾故意安排黑人克洛斯到自己家居住。吉爾的房東是白人種族主義者赫恩頓(Herndon)。赫恩頓討厭白人吉爾和黑人克洛斯的親密交往,特別不能容忍一個黑人居住在他的房子里。克洛斯從自己的黑人城市空間搬入白人的城市空間,引起和激化了黑人和白人之間的種族矛盾。克洛斯作為一個種族自尊心極強的青年一代黑人,一方面痛恨赫恩頓之類的白人種族主義者,另一方面也痛恨把自己當作棋子的吉爾類白人唯我論者。因此,當吉爾和赫恩頓發生肢體沖突時,克洛斯無情把兩人都打死了,并偽造了兩人互毆而亡的假現場。種族問題是一個敏感的社會問題,故意安排或設置的種族空間遷移是種族主義的另類表現形式,必然會傷害黑人的自尊心,激起黑人的抗爭。
總之,賴特從城市空間遷移、生死空間遷移和種族空間遷移三個方面描寫了芝加哥和紐約城市空間里的黑人和白人對自身身份的困惑和迷茫,同時還揭示了空間變換后的身份焦慮感和惶恐感。在無法認清自己身份的情況下,處于空間遷移中的人依然渴望同化,也渴望異化,而美國種族主義現實中的個體身份也在自行經歷著同化與異化,演繹了個體與群體間的斗爭與妥協。
4.0 空間重構的冷酷性
一般來講,城市空間的建構形式和生態狀況對都市人的身份建構有著重要的影響。城市在空間上的密集和消費文化的盛行在一定程度上對個體身份產生同化作用, 而城市的結構布局、社會階層的分化、水陸交通的發展及其對自然生態的破壞則對個體身份產生異化影響。隨著美國社會的發展,種族平等、人權平等和性別平等的社會呼聲越來越強烈。自我空間的重構成為美國城市空間變遷的最為顯著的變化之一。自我空間的政治屬性、社會屬性和文化屬性的功能日益顯現。“空間一方面為權力、利益、理念等要素提供發生場所,另一方面也遮蔽和固化了城市擴張、人口流動、產業結構調整等現象背后的社會分層、權力沖突、利益爭奪等深層制度化的社會問題”(鐘曉華,2013:14)。賴特在《局外人》里展現了自我空間重構在人物塑造和主題思想的深化方面獨特貢獻。因此,筆者擬從四個方面來探析這部小說關于空間重構的方式與策略:空間重構中的詭計、空間重構中的殺戮、空間重構中的自我克制和空間重構中的虛擬性。
賴特在這部小說里描寫主人公克洛斯采用詐死、借尸還魂和盜用出生證等手段進行自我空間的重構。克洛斯本是芝加哥郵局職員、格萊迪絲的丈夫、達蒙太太的兒子、三個兒子的父親和少女朵特的情人。在家庭空間和公眾空間的擠壓下他難以正常生存下去,于是就在芝加哥地鐵車禍事件中詐死。后來,在墓地中偶遇萊昂內爾·萊恩(Lionel Lane)的墓碑,就臨時決定冒用他的名字,并到市政廳辦理了萊恩的出生證明復印件。從此他就獲得了萊恩的合法身份。萊恩父母的離世使萊恩的身世更加無法查證,使克洛斯借尸還魂的詭計得以成功。此后,克洛斯就以“萊恩”的身份生活在紐約,參與了共產黨組織的不少社會活動,與白人少婦愛娃(Eva)墜入情網。他通過自我空間重建的方式開始了自己的第二人生。
《局外人》還描寫個人空間重構過程中的血腥性和殘酷性。克洛斯是一個極端的存在主義者,以自我為中心,采用消滅一切不利因素的手段來保全自我的生存方式。芝加哥地鐵車禍發生后,他被一具尸體壓住右腿。為了取出自己的腿,他不惜用磚頭敲碎死者的頭。當他決定以詐死為手段來掩蓋自己的身份時,他在旅館偶遇以前的好朋友喬。為了防止喬泄露他還活著的消息,就用啤酒瓶敲碎了喬的頭,然后把他的尸體推到樓下。克洛斯把自己的個人空間重構視為改變人生的決定性手段,把一切可能威脅其身份重構的人視為自己的最大敵人。在小說的末尾部分,克洛斯潛入約翰·希爾頓(John Hilton)的家,發現他在柜子里藏有克洛斯殺死吉爾和赫恩頓的血帕,認為約翰是在暗中搜集他的犯罪證據,并以此為要挾,迫使克洛斯成為其奴仆。奴仆身份會使克洛斯喪失自己的個性空間和基本人格。因此,約翰所保留的證據成了克洛斯必殺他的理由。存在主義式的唯我論者使克洛斯變成濫殺無辜的惡魔。個性空間的建立并沒有給他帶來渴望的幸福和自由,反而使他一步一步走向嗜血的深淵。
為了不在外界的誘惑中失去自我,克洛斯自覺地抵御了女色和黨派的誘惑。當克洛斯剛從地鐵車禍事件中幸免于難時,他接受了白人妓女詹妮(Jenny)的性服務。之后,詹妮對克洛斯產生了愛意,打算和他建立固定的情人關系,并隨他浪跡天涯。但克洛斯不愿再次陷入婚姻陷阱,于是以撒謊的方式擺脫了詹妮的糾纏。之后,克洛斯去紐約的路上,投宿到一家旅店。女店主海蒂(Hattie)對年輕英俊的克洛斯一見鐘情,頻施秋波。為了克制自己對女色的生理欲望,克洛斯帶上行李不辭而別,再次逃離女色誘惑。此外,對黨派組織,他也一直持回避態度,擔心加入黨派組織后個人空間發展會受到各種限制。不論共產黨負責人吉爾怎么勸說,他都拒絕加入。克洛斯不愿讓自己的個人空間受到任何組織和他人的約束,認為對女性和組織的沉溺必然導致自我的喪失和個性空間的毀滅。
賴特還在這部小說里描寫了虛擬的精神空間。克洛斯是一名大學肄業生,但在黑人中是難得的高學歷知識分子。在現實生活中,他不但以自我為中心,而且還時常把自己裝扮成上帝。克洛斯在幾十層樓高的辦公室里向窗外扔錢幣,引起不少人在樓下瘋搶。望著樓下搶錢的人群,克洛斯哈哈大笑道,“說實話。我想我要笑死了”(Wright,1991:373)。在此刻,克洛斯覺得自己像“上帝”,在自己的精神空間里成了至高無上的主。由此可見,克洛斯想以撒錢的方式來滿足自己的個性欲望,實現自己濟世救民的政治幻想,從而重建自己的個性空間。
在《長夢》里,美國社會個性空間的重新建構是個人活動空間的重新組合;由種族利益和政黨利益而形成的空間形態會造成人際關系的分割和分散。城市空間的重構是城市居民日常生活場景中的真實過程,是具體行動者能動性的產物,同時又直接影響著人的行為、生活方式及價值觀。空間重構的實施行為和捍衛自我的人生追求在存在主義思想的催化下會導致生存空間的壓縮和倫理空間的毀滅。
5.0 結語
《局外人》描寫了美國黑人的生存空間、空間遷移和空間重構,使城市空間成為物理空間、精神空間和社會空間的有機統一體。賴特借助于“公眾空間”、“職場空間”、“空間重構”等概念界說了城市空間的物質性、社會性和精神性,展現了非裔美國城市自然主義小說的空間詩學,從空間角度顯示了賴特對美國種族問題的獨特見解和思考。賴特從美國政治、經濟、文化、道德、倫理等層面描寫了黑人的民族主義思想,弘揚了黑人的民族精神,強調了城市生存空間與黑人意識形態的密切關系。賴特認為,城市空間對個體身份的同化與異化作用正時時刻刻地發生在城市人身邊。在社會空間的建構過程中,不同種族的人們人格平等,不同主體的碰撞和互動有助于逐步接受彼此的文化習俗和價值觀,達到種族關系和人際關系的和諧。互相信任是社會空間理性建構的基礎,主體間的換位思考和平等交流是社會空間不斷融合的核心;賴特倡導在相互尊重、平等友善和認同多元價值的基礎上實現各民族文化的差異性并存和多元化發展。賴特關于空間問題的描寫拓展了美國黑人城市自然主義小說的主題空間,為非裔美國小說在20世紀七八十年代的大發展打下了良好的社會基礎。
[1] Fabre, M.RichardWright:Books&Writers[M]. Jackson:University Press of Mississippi, 2008.
[2] Felgar, R.StudentCompaniontoRichardWright[M]. Westport, Conn: Greenwood Press, 2000.
[3] Gounard, J. F.TheRacialProblemintheWorksofRichardWrightandJamesBaldwin[M]. Trans. Joseph J. Rodgers, Jr. Westport, Conn: Greenwood Press, 1992.
[4] Haynes, E. T. The Named and the Nameless: Morrison’s 124 and Naylor’s “the Other Place” as Semiotic Chorae[J].AfricanAmericanReview, 2004,38(4):669-681.
[5] Pochmara, A.TheMakingoftheNewNegro:BlackAuthorship,Masculinity,andSexualityintheHarlemRenaissance[M]. Amsterdam: Amsterdam University Press, 2011.
[6] Singh, A. Richard Wright’sTheOutsider: Existentialist Exemplar or Critique?[A].TheCriticalResponsetoRichardWright[C]. (ed.). Robert J. Butler. Westport, Conn: Greenwood Press, 1995.124-143.
[7] Tracy, S. C. (ed.).WritersoftheBlackChicagoRenaissance[M]. Urbana: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2011.
[8] Warf, B. Review of the Production of Space[J].JournalofRegionalScience, 1993,33(1):111-112.
[9] Wright, R.TheOutsider[M].LaterWorks:BlackBoy(AmericanHunger),TheOutsider[C]. (ed.). Arnold Rampersad. New York: Literary Classic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91.367-841.
[10] 高春花. 列斐伏爾城市空間理論的哲學建構及其意義[J]. 理論視野,2011,(8):29-32.
[11] 李圣昭,劉英. 城市空間與現代性主體——從空間理論角度解讀《嘉莉妹妹》[J]. 安徽文學,2014,(3):55-58.
[12] 牛俊偉. 從城市空間到流動空間——卡斯特空間理論述評[J]. 中南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4,(2):143-147.
[13] 楊昊成. 超越種族的寫作:理查德·賴特作品的精神實質[J]. 外國文學研究,2010,(6):126-129.
[14] 趙莉華. 空間政治:托尼·莫里森小說研究[M]. 成都:四川大學出版社,2011.
[15] 鐘曉華. 社會空間和社會變遷——轉型期城市研究的“社會—空間”轉向[J]. 國外社會科學,2013,(2):14-21.
(責任編輯:任愛紅)
UrbanSpaceandExistentialTensionAReviewofRichardWright’sTheOutsider
PANGHao-nong
(SchoolofForeignLanguages,ShanghaiUniversity,Shanghai200444,China)
InTheOutsider,RichardWrightmakesurbanspaceintoanentityofphysicalspace,spiritualoneandsocialoneinthedepictionofblackAmericans’existentialspace,spacetransferenceandreconstructionofspace.Basedontheconceptsofpublicspace,workingspaceandreconstructionofspace,heillustratesthephysicality,socialityandspiritualityofurbanspaceandunfoldsthespatialpoeticsofAfricanAmericanurbannaturalisticfiction.Fromtheperspectivesofurbanspacetransference,lifeanddeathspacetransferenceandethnicspacetransference,hedelineatestheblackandthewhite’spuzzlementandperplexityintheurbanspacesofChicagoandNewYork,disclosingtheanxietyandterrorrelatedtotheiridentity.Viewingfromtheangleofsocialspace,herevealstheethicalandmoralcrisescausedbythereconstructionofspaceanddemonstrateshumanisticmoodsintheloveofhislifeandmotherland.
RichardWright;TheOutsider;urbanspace;existentialtension;ethicalandmoralcrises
I106
A
1002-2643(2017)05-0073-07
10.16482/j.sdwy37-1026.2017-05-009
2017-06-20
本文為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非裔美國城市自然主義小說之性惡書寫研究”(項目編號:14BWW074)階段性成果。
龐好農(1963- ),男,漢族,重慶人,教授,博士生導師。研究方向:美國文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