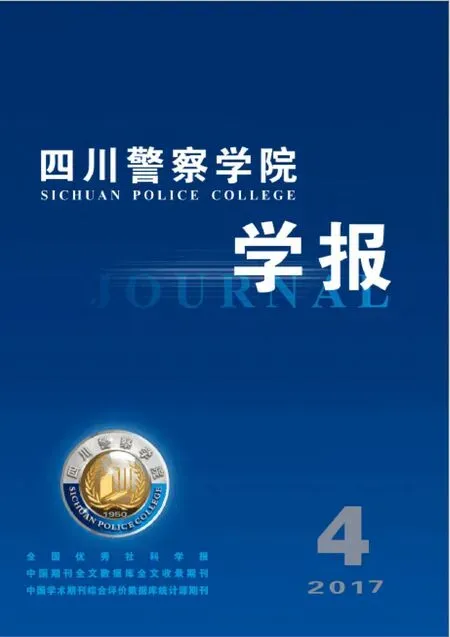“互聯(lián)網(wǎng)+公共圖書館”的版權(quán)保護困境及突破
張 力
(西南政法大學(xué) 重慶 401120)
“互聯(lián)網(wǎng)+公共圖書館”的版權(quán)保護困境及突破
張 力
(西南政法大學(xué) 重慶 401120)
數(shù)字化在大大拓展圖書館復(fù)制、傳承與傳播人類精神文明成果的同時,也改變了傳統(tǒng)版權(quán)法運作所依賴的“以人就書”的作品信息傳播模式,從而引起來自版權(quán)法調(diào)整方法的調(diào)整,以在圖書館的公益性,與版權(quán)保護之間求得新的平衡。圖書館合理使用對其已不適用,法定許可使用也存在諸多限制,第三方在圖書館數(shù)據(jù)平臺上的侵權(quán)行為也可能牽涉到圖書館的相關(guān)責任。為兼顧版權(quán)方、作品使用方、網(wǎng)絡(luò)信息服務(wù)提供方之三者利益,公共數(shù)字圖書館應(yīng)當對作品作出適當審查與分類,拓展授權(quán)渠道合法獲得相應(yīng)版權(quán)和鄰接權(quán),避免因遺漏或不當行為引發(fā)的侵權(quán)責任。
互聯(lián)網(wǎng);公共圖書館;版權(quán)保護
數(shù)字文獻信息資源的擁有量和利用水平,已經(jīng)成為當前評價一個國家或地區(qū)信息基礎(chǔ)水平的重要標志。我國數(shù)字文獻建設(shè)與利用的基礎(chǔ)較為薄弱,但近年來隨著“互聯(lián)網(wǎng)+”建設(shè)的突破而呈現(xiàn)快速發(fā)展,后來居上的態(tài)勢。不容忽視的是,當今數(shù)字文獻建設(shè)與利用體制(也稱為“數(shù)字圖書館”),始終伴隨著“網(wǎng)絡(luò)版權(quán)侵權(quán)”的高度法律風險。這一風險自北京海淀區(qū)法院判決“中國數(shù)字圖書館有限公司侵害陳興良版權(quán)案”敗訴以后,更是日益“無差別”地由商業(yè)數(shù)字圖書館擴散至公益性數(shù)字圖書館領(lǐng)域,甚至形成“數(shù)字圖書館規(guī)模、公共性與法律風險成正比”的所謂“數(shù)圖版權(quán)悖論”(本文中版權(quán)與著作權(quán)同義)。這尤其值得引起正大力發(fā)展公共數(shù)字文獻建設(shè)的圖書館界的注意[1]。
一、“互聯(lián)網(wǎng)+公共圖書館”事業(yè)發(fā)展的理想化法律環(huán)境
(一)互聯(lián)網(wǎng)技術(shù)對公共數(shù)字圖書館事業(yè)帶來的機遇與挑戰(zhàn)
在互聯(lián)網(wǎng)環(huán)境下,數(shù)字圖書館服務(wù)的提供方,既包括不以營利為目的的公益性數(shù)字圖書館,也包括商業(yè)性的網(wǎng)絡(luò)信息服務(wù)主體,例如中國知網(wǎng)(CNKI)、萬方等商業(yè)性數(shù)據(jù)庫,百度文庫、騰訊空間、新浪微博等數(shù)據(jù)平臺。對于網(wǎng)絡(luò)信息服務(wù)提供方,維持一定的用戶訪問構(gòu)成其存續(xù)的基本理由。“公益性數(shù)字圖書館,是指由國家投資興辦的,只追求社會效益,以服務(wù)于社會公共利益為生存目的的數(shù)字圖書館”[2]。公益性數(shù)字圖書館建立的初衷即是為滿足和實現(xiàn)公眾的閱讀和學(xué)習權(quán)、促進知識的傳播和文化的發(fā)展。數(shù)字化在大大拓展圖書館復(fù)制、傳承與傳播人類精神文明成果能力的同時,也極大的沖擊甚至改變了傳統(tǒng)版權(quán)法運作所依賴的“以人就書”的作品傳播模式[3]。從而必須對其與傳統(tǒng)版權(quán)法之間的整體關(guān)系加以重述。
2000年8月,世界圖書館界的代表組織“國際圖書館協(xié)會聯(lián)合會”(簡稱“國際圖聯(lián)”)的“版權(quán)與其他法律事務(wù)委員會”,向聯(lián)合國教科文組織提交了《國際圖聯(lián)關(guān)于數(shù)字環(huán)境下版權(quán)的立場》的報告等一攬子文件,強調(diào)其事業(yè)在互聯(lián)時代面臨的新挑戰(zhàn)。該文件批評上世紀90年代以來,不斷擴大的版權(quán)技術(shù)保護措施對讀者合理使用信息及學(xué)習權(quán)的嚴重威脅;同時痛陳,本應(yīng)促進信息的無障礙溝通的互聯(lián)網(wǎng)信息技術(shù),卻越來越多的被版權(quán)人、鄰接權(quán)人用以構(gòu)筑公眾與數(shù)字化信息之間的技術(shù)壁壘,且獲得法律的認可。例如版權(quán)人單方給定在線點擊使用許可合同,對數(shù)字化信息復(fù)制的直接禁止與限制,進而是將許可與收費捆綁,成為對公眾中的弱勢群體接觸所急需知識信息的經(jīng)濟壁壘。尤其讓人憂慮的是,在傳統(tǒng)背景下令圖書館界引以自豪的,面向社會公眾的無償(至少是非贏利的)出借等方式的信息傳播服務(wù),在數(shù)字化背景下正越來越多的受到圖書館無法控制的,版權(quán)人、鄰接權(quán)人操縱的,通過圖書館向社會公眾收費(多有贏利目的)而有償“出售”信息的新傳播方式的替代,等等[4]。
(二)國際圖書館界希望獲得的法律支持
針對上述問題,“國際圖聯(lián)”重申在版權(quán)人與讀者間維持版權(quán)平衡的重要性,以及圖書館在這一維持機制中發(fā)揮的重要作用,并提出了關(guān)于版權(quán)保護與限制的觀點與措施,以期在新世紀的頭十年中,初步建構(gòu)起國際化的數(shù)字化圖書館信息服務(wù)的合法性基礎(chǔ)[5]。為此需要在法律上獲得一系列針對版權(quán)人的數(shù)字化權(quán)利行使方式的限制,同時擴大公共圖書館在代表“社會公共求知權(quán)權(quán)”的方面的活動自由與法律責任豁免:
1.力求免費獲得與傳播數(shù)字化信息;
2.圖書館應(yīng)進一步發(fā)揮促進信息資源共享的中介作用;
3.限制在線點擊合同與反復(fù)制保護技術(shù);
4.圖書館不承擔侵犯版權(quán)的間接侵權(quán)責[5]。
二、數(shù)字化公共圖書館中的版權(quán)保護困境
距離國際圖聯(lián)正式公布立場已經(jīng)過去了十六年。該立場在國際圖書館界、知識界與社會公眾中均產(chǎn)生了廣泛影響。于此同時,這一立場與關(guān)于數(shù)字時代版權(quán)保護的國際公約與國內(nèi)法的傳統(tǒng)立場之間的分歧甚至沖突也日益凸顯,從而形成了某種新的版權(quán)保護困境。
(一)與部分國際條約的出入
《世界知識產(chǎn)權(quán)組織版權(quán)條約》(WCT)將過去作品發(fā)表權(quán)、出版權(quán)與復(fù)制權(quán)的數(shù)字化整合成新的權(quán)利形式——“公共傳播權(quán)”,從而將版權(quán)保護向數(shù)字環(huán)境延伸,但又在WCT第10條針對上述權(quán)利進行了限制。WCT認為“數(shù)字化”并未根本改變版權(quán)法的價值取向與技術(shù)特征,也并未自動帶來互聯(lián)網(wǎng)環(huán)境下的知識共有公用。國際圖聯(lián)在這里犯了以偏概全的錯誤——對WCT中的“數(shù)字化沒有什么不同”的法律意義進行了不當?shù)臄U大性解釋。這樣得出的數(shù)字環(huán)境下的圖書館使用與傳播館藏信息的行為模式,同樣應(yīng)適用傳統(tǒng)時代“圖書館合理使用”的結(jié)論,就喪失了邏輯前提與合法性基礎(chǔ)。
(二)與部分國內(nèi)法的沖突
美國《千年數(shù)字化版權(quán)法》。相對于美國1995年《版權(quán)白皮書》將網(wǎng)絡(luò)瀏覽形成的暫時復(fù)制作為版權(quán)項下復(fù)制權(quán)內(nèi)容的規(guī)定,《千年數(shù)字化版權(quán)法》對該問題未為規(guī)定,這對圖書館及起所代表的讀者群是有利的。如果版權(quán)人不能通過復(fù)制權(quán)控制讀者在瀏覽圖書館提供的數(shù)字化作品時,有關(guān)作品暫時“復(fù)制”進入讀者終端系統(tǒng)的“行為”,就不能認為有關(guān)瀏覽行為,以及圖書館對有關(guān)瀏覽行為的支持(將作品數(shù)字化與上載到自己的網(wǎng)站)行為侵害了版權(quán)。但是,“該法卻明確要求對數(shù)字環(huán)境下的圖書館在傳播信息過程中的合理使用地位進行嚴格而分段的評估,并將圖書館在數(shù)字環(huán)境下的合理使用,限制在了館內(nèi)網(wǎng)際傳播的狹小空間范圍內(nèi)”[5]。
歐盟《關(guān)于協(xié)調(diào)信息社會版權(quán)與鄰接權(quán)某些方面的指令》對數(shù)字化圖書館有利的是,“指令”第5條第1款的規(guī)定,某些暫時性復(fù)制被排除在復(fù)制權(quán)的范圍之外。同時,“指令”第5條第3詳細列舉了15種可以就復(fù)制權(quán)、向公眾傳播權(quán)和向公眾提供權(quán)的免責情形,其中即包括為了研究或個人學(xué)習的目的,通過設(shè)在圖書館、教育機構(gòu)、博物館和檔案館的終端,向公眾中的個人傳播或提供其收藏的作品和其他受保護客體[5]。然而,這種版權(quán)限制的限度止于“設(shè)在圖書館等公益機構(gòu)內(nèi)”的態(tài)度,也是非常明確的[6]。
我國法律界的態(tài)度與美國、澳大利亞基本相同——數(shù)字化引起了圖書館法律地位的不同。
綜上,根據(jù)WCT及其指導(dǎo)下的主要實施法,傳統(tǒng)時代圖書館相對自由的傳播館藏信息的權(quán)利,同時也是對著作權(quán)保護的限制,在數(shù)字環(huán)境下正受到日益明顯的立法限制。一個至少對于圖書館傳播館藏數(shù)字化信息這一問題,數(shù)字化引起了著作權(quán)人、圖書館、社會公眾在作品保護與限制問題上原有利益平衡的打破,與新的平衡的建立。
三、數(shù)字化公共圖書館傳播自由加以法律限制的原因
問題的關(guān)鍵是,對作者而言,公共圖書館與信息的商業(yè)傳播人(如作者、出版商)間的區(qū)別,到底有多大?
事實上,一直以來對“公共圖書館對作者作品的使用,與公眾對圖書館館藏作品的使用都應(yīng)是無償使用”的另眼相待,特別關(guān)照的態(tài)度早已發(fā)生了變化。也就是說,在傳統(tǒng)環(huán)境下,圖書館資料出借與復(fù)制行為的法律性質(zhì)已經(jīng)發(fā)生了嬗變。“上世紀70年代以來,一些國家(如荷蘭、澳大利亞等)將大規(guī)模的個人目的的少量復(fù)制,由過去的合理使用轉(zhuǎn)歸法定許可,并向集中提供這種服務(wù)的機構(gòu)甚至復(fù)制設(shè)備制造者征收版稅,再容這些機構(gòu)將之作為成本而最終轉(zhuǎn)嫁到個人復(fù)制者頭上”[5]。
另一方面,商業(yè)模式對數(shù)字化公共圖書館的滲透,也是數(shù)字化公共圖書館傳播自由須加以法律限制的關(guān)鍵性因素。長期以來,數(shù)字化公共圖書館建設(shè)受制與巨大的前期成本,日益高昂的版權(quán)索賠風險,而常常被假設(shè)為入不敷出,存在強大的財政依賴。這又提高了社會對公共政府部門相對不足的文化事業(yè)財政預(yù)算投入,逼迫公共圖書館事業(yè)巨大赤字的“開源節(jié)流、自行解決”的種種灰色行為模式容忍度:例如向數(shù)字文獻讀者的收費程度逐步超過基本成本維持、為讀者代收版權(quán)使用費等等公益性范疇,而具有了自收自營的營利性特色。但而今,這種容忍度正逐步被擴張到嚴重侵害作者版權(quán)財產(chǎn)利益的傾向。這是因為,一來對公共圖書館事業(yè)的公共財政支持近年來已大幅提高,基本運營之成本早已不是問題。更重要的是,公共圖書館基于前期建設(shè)積累的海量文獻數(shù)據(jù)庫,已日益發(fā)展出分類精細檢索、搜集、查重等云數(shù)據(jù)技術(shù)能力,從而發(fā)展出具有廣闊市場前景的衍生與增值信息市場。僅以我國最大的學(xué)術(shù)文獻平臺“中文知網(wǎng)”為例,其海量數(shù)據(jù)庫事實上已常態(tài)性的與各類經(jīng)營性或非經(jīng)營性主體構(gòu)成聯(lián)合關(guān)系,為其有償提供論文學(xué)術(shù)不端的網(wǎng)絡(luò)監(jiān)測比對服務(wù),收取高昂的適用費,由此形成了巨額收入,早已突破其非營利性范疇。衍生市場的巨大收益建立在前期作者文獻極其廉價甚至無償?shù)臄?shù)字化建設(shè)的基礎(chǔ)上,對此,廣大文獻作者理應(yīng)參與衍生增值收益的分享。而數(shù)字圖書館事業(yè)的運營主體的公司化,也在佐證著這一判斷。雖然公司必須以營利為目的,但公司法的調(diào)整方法本身就承認了所調(diào)整主體的強大的營利潛力與訴求的的合法性。那么,公司化的公共數(shù)字圖書館就更難以證明代表廣大讀者,集中對作者文獻合理使用的合理性與合法性。
四、互聯(lián)網(wǎng)圖書館版權(quán)保護困境的突破
國際圖聯(lián)的理想也許過渡超越了版權(quán)法的歷史發(fā)展程度:任何時代的作品傳播者在最能涉及作品商品化的,聯(lián)系作品最終使用者的場合,都較之作者擁有更強的對傳播事業(yè)的控制力、創(chuàng)造力及牟利能力。這使版權(quán)在語源(copyright)及利益歸屬上一開始“既不是作者的權(quán)利,也不是不依賴于王室的權(quán)利,而是統(tǒng)治者授予的作為對印刷商的賞賜的獨占性特權(quán)”[7]。雖然這在1710年英國《安娜女王法》頒布而引發(fā)的出版商還權(quán)、還利于作者的,版權(quán)“回歸”運動以后有了決定性扭轉(zhuǎn),但作品傳播者基于社會分工及信息統(tǒng)治的政治需要,而取得對傳播業(yè)手段的優(yōu)勢壟斷地位,使我們在探討作者對信息的壟斷與信息共用的公益價值間沖突的協(xié)調(diào)時,應(yīng)以作者——弱者——為思考基點。三百年來,無論作者對作品壟斷能力的消長,上述傳播能力的不同并無實質(zhì)變化。而每當傳播技術(shù)革命的時代,保障作者利益的手段與方法,標準與幅度的調(diào)整,將成為那一時代版權(quán)法制演進的最為重要的課題之一。圖書館界在質(zhì)疑當代信息中介傳播商業(yè)主體的“惟利是圖”,令圖書館運營成本負擔日重的同時似乎忘記了,它所代表的圖書館,特別是新興的數(shù)字化圖書館不也是某種傳播主體嗎,如果關(guān)于“數(shù)字化沒有什么不同”的公益性訴求,最終帶來的僅僅是其自身對于其他傳播主體的競爭優(yōu)勢乃至逐步替代的結(jié)果,而把作者撇在一邊,這與當代已經(jīng)普遍存在的,各類商業(yè)、準商業(yè)中傳播主體傾軋作者階層的狀況相比,就真的沒有什么不同了。故圖書館界的立場也應(yīng)改弦更張,以更符合法制社會要求的面貌,指引各國圖書館事業(yè)的發(fā)展[5]。
(一)作品的審查與分類策略
從法律權(quán)屬角度來看,數(shù)字圖書館面對的海量作品可以被分為已過版權(quán)期限作品、所有權(quán)明確的版權(quán)作品、所有權(quán)不明的版權(quán)作品的三類。數(shù)字圖書館應(yīng)當先行的首要工作,就是按照上述標準對作品進行區(qū)分。
對于已過版權(quán)期限作品,數(shù)字圖書館只要澄清該作品已處于公共領(lǐng)域,同時注意保護作者的署名權(quán)、修改權(quán)、保護作品完整權(quán)等人身性權(quán)利,就可以無障礙地獲取和使用——既無須向版權(quán)人及相關(guān)權(quán)利人取得授權(quán)、支付報酬,也幾乎不會涉及侵權(quán)的法律風險。基于此優(yōu)勢,各國公共數(shù)字圖書館都非常重視公有領(lǐng)域的資源開發(fā)。以意大利國家圖書館為例,其于2010年與谷歌達成一項圖書掃描協(xié)議,將館藏的1870年以前出版并進入到公有領(lǐng)域的圖書交由谷歌公司進行掃描數(shù)字化處理,其中包括伽利略手稿、草藥文稿等珍貴文本,極大地促進了意大利文明的保存與文化的傳播[7]。我國國家圖書館也一直注重開發(fā)進入公共領(lǐng)域的古籍文獻,截止2013年底古籍文獻數(shù)字資源已經(jīng)超過6萬種。
對于所有權(quán)明確的版權(quán)作品,數(shù)字圖書館一方面應(yīng)當澄清版權(quán)持有人(包括作者、出版者、有權(quán)傳播者等),從而實現(xiàn)這些作品的數(shù)字化檢索。另一方面,由于這些作品內(nèi)容的復(fù)制與傳播需要得到作者的授權(quán),所以不可以直接進行數(shù)字化處理并向公眾開放,但卻不妨礙數(shù)字圖書館提供檢索服務(wù)以及在一定程度上進行的有限數(shù)字展示。
對于所有權(quán)不明的版權(quán)作品,目前我國尚未有成型的處理方法。然而,“孤兒作品”的處理并非小事,它關(guān)系到私人利益與版權(quán)法固有的公共利益平衡問題。如何處理孤兒作品,應(yīng)該由法律來規(guī)定,而非由法院或某一組織單獨決定。就未來立法走向看,可以參考美國《2008孤兒作品法案》和谷歌修訂版和解協(xié)議(Amended Settlement Agreement,以下簡稱ASA)中的孤兒作品版權(quán)策略。其基本思路是設(shè)立一個獨立的受托人對孤兒作品進行統(tǒng)一管理。該受托人要有足夠的代表性,能為一切所有權(quán)不明作品的權(quán)利人主張權(quán)益,因此極有可能由版權(quán)集體管理組織擔任。確立受托人后,還需制定孤兒作品的認定方法與作品許可費用的處置規(guī)則。作品信息經(jīng)受托人公布之后,一定年限內(nèi)若無人認領(lǐng)則可認定作品為孤兒作品,相關(guān)費用由受托人代為保管并可從中抽取一定比例用于合理而勤勉地搜索權(quán)利人。屆時,數(shù)字圖書館就孤兒作品的版權(quán)授權(quán)與使用問題,可直接與受托人商談。在此之前,對于孤兒作品,數(shù)字圖書館很難獲得合法而正當?shù)氖褂脵?quán),因此只能如同上述所有權(quán)明確而又未能獲得作者授權(quán)的版權(quán)作品一樣,標示已有的相關(guān)權(quán)利信息,并至多進行有限的數(shù)字展示。
(二)針對數(shù)字化圖書館建立簡便的授權(quán)許可與計價體制
“首先,圖書館可以與版權(quán)集中管理機構(gòu)協(xié)商,爭取為讀者取得合理使用地位;其次,在對版權(quán)人付費總量相對恒定的情況下,允許數(shù)字化圖書館面向讀者實行區(qū)分性收費標準,對不同用戶發(fā)放含不同收費標準的網(wǎng)絡(luò)閱讀磁卡;再次,對作品信息的經(jīng)濟價值加以區(qū)分;最后,還應(yīng)當發(fā)展數(shù)字化圖書館的自主版權(quán)”[5]。
(三)建立健全版權(quán)信息管理系統(tǒng)版權(quán)信息管理系統(tǒng)
其本身的主要目標是實現(xiàn)館藏作品信息、授權(quán)信息和合同信息三位一體的登記、版權(quán)代理與管理[8]。實行“中國版本圖書館—國家數(shù)字圖書館—中國版權(quán)保護中心”統(tǒng)一管理模式[9]。在此基礎(chǔ)上提供和開展相關(guān)信息的查詢、檢索和統(tǒng)計服務(wù),建立各種資源間的版權(quán)關(guān)聯(lián),以及版權(quán)與館藏資源間的授權(quán)關(guān)系,同時與數(shù)字圖書館的其它業(yè)務(wù)功能和系統(tǒng)間保持順暢的數(shù)據(jù)交換關(guān)系[10]。其所涵蓋的信息內(nèi)容包括以下幾方面:其一,版權(quán)作品信息,包含該作品的唯一標識符、作品名稱、責任人、出版信息等。其二,作品授權(quán)信息,包含授權(quán)使用的地域范圍、時間期限、所獲權(quán)利種類(復(fù)制權(quán)、信息網(wǎng)絡(luò)傳播權(quán)等)、授權(quán)類型(專有使用授權(quán)、非專有使用授權(quán)、轉(zhuǎn)授權(quán))、授權(quán)用戶范圍、提供服務(wù)方式等。其三,相關(guān)合同信息,包含合同編號、名稱、主體、類型、時間、變更與續(xù)約狀況等。其四,系統(tǒng)接口信息,包含各采集系統(tǒng)、組織系統(tǒng)、發(fā)布服務(wù)系統(tǒng)、館藏管理系統(tǒng)中輸入和輸出的緩存數(shù)據(jù)。其五,系統(tǒng)維護信息,包含系統(tǒng)配置信息與用戶管理信息、日志統(tǒng)計信息等。
版權(quán)信息管理是貫穿于數(shù)字圖書館建設(shè)和利用數(shù)字文獻全過程的基礎(chǔ)性措施,也是整個數(shù)字圖書館運行的法律支持與核心構(gòu)件。其信息系統(tǒng)的健全與準確性,是發(fā)生法律風險后迅速作出反應(yīng)的前提。本文中所提及的版權(quán)聲明、合理注意義務(wù)等法律措施,也依托于這種信息管理手段。舉例來說,圖書館對作品進行推薦、排名、選擇、編輯、整理、修改等都須依靠版權(quán)信息,在判別無權(quán)利瑕疵或侵權(quán)嫌疑的前提下才得以安全實行。否則,極易被認定為“知道”侵權(quán)事實而與直接侵權(quán)人承擔連帶責任。又如,圖書館可以通過信息管理監(jiān)控本館IP流量情況,當發(fā)生異常時可以及時采取凍結(jié)IP賬號、“通知移除”等程序來減小侵權(quán)行為的負面效應(yīng),避免承擔侵權(quán)責任的法律風險。
[1]王斌英.信息資源共享模式下數(shù)字圖書館版權(quán)問題研究[J].蘭臺世界,2016,(10):95-97.
[2]趙 媛.數(shù)字圖書館法律問題研究[M].成都:四川大學(xué)出版社,2009:5.
[3]賴文智.圖書館與著作權(quán)法[M].臺北:臺北益思科技法律事務(wù)所,2002:163.
[4]胡大琴.數(shù)字圖書館版權(quán)問題應(yīng)對策略探討[J].數(shù)字圖書館論壇,2014,(3):55-60.
[5]張力.數(shù)字化沒有什么不同?——評國際圖聯(lián)(IFLA)關(guān)于數(shù)字環(huán)境下版權(quán)的“千年立場”[J].情報資料工作,2006,(3):33-36.
[6]Fion Macmillan.The digital copyright deadlock[J].The Australian Library Jouranl,2000,May:113-118.
[7]江向東.歐盟99/100指令對圖書館公共借閱活動的影響[J].圖書館雜志,2003,(9):67-70.
[8]王 衛(wèi),等.版權(quán)代理模式下數(shù)字圖書館版權(quán)保護問題策略研究[J].圖書情報工作,2013,(2):38-41.
[9]陳艷紅.數(shù)字圖書館版權(quán)問題的自律措施及建議[J].管理工程師,2015,(6):13-16.
[10]呂淑萍,等.圖書館數(shù)字資源版權(quán)管理實踐與案例[M].北京: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13:156.
On the plight of copyright protection for public library in the “internet+”era and its solution
ZHANG Li
Digitization is of great help to copy,inherit an d spread human spiritual civilization achievements.Meanwhile,it also changes the book-oriented information dissemination mode which the traditional copyright law operation relies on,which causes adjustment of copyright law to achieve balance between the public welfare of the library and copyright protection.The reasonable use of the library is not applicable to it,and there are many restrictions on the use of statutory license.The infringement made by the third party on the library data platform may also involve the relevant responsibilities of the library.Considering the interests of copyright owners,product users and the cyber-information service providers,public digital library should make a proper work review and classification mechanism,and expand the authorized channel to obtain corresponding copyright and neighboring right,so as to avoid tort liability caused y omission or misconduct.
the internet;public library;copyright protection
DF523.1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4-5612(2017)04-0001-06
(責任編輯:賴方中)
重慶市教委軟科學(xué)研究計劃項目《重慶市數(shù)字文獻建設(shè)與利用中的版權(quán)管理策略》(KJ080106)
2017-04-17
張 力,(1976- ),男,重慶人,博士后,西南政法大學(xué)比較私法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博士生導(dǎo)師,研究方向:比較民法學(xu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