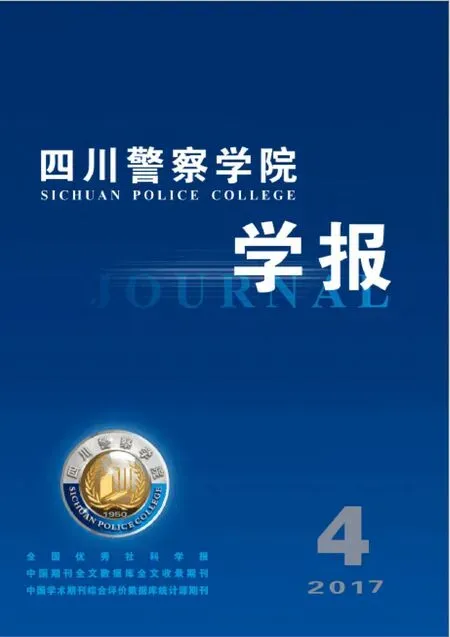現實與重構:“中國式”的未成年人刑事和解制度
王 統
(山東大學 山東濟南 250100)
現實與重構:“中國式”的未成年人刑事和解制度
王 統
(山東大學 山東濟南 250100)
世界范圍內未成年人犯罪率上升和犯罪低齡化問題已經成為危害社會安全的突出問題。當前我國社會處在轉型期,未成年人犯罪問題日漸突出,需要發揮未成年人刑事和解制度的作用。在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中要引入區別于成年人的刑事和解制度,并構建“中國式”的未成年人刑事和解制度。“以和為貴”一直是我國傳統文化和傳統道德的精髓,這種“和”理念更應貫穿于“中國式”未成年人刑事和解的整個過程。
未成年人;刑事和解;制度構建
一、問題的提出
我國新《刑事訴訟法》規定了當事人刑事和解制度,它是一種與傳統刑事訴訟模式相抗衡的非訴處置犯罪的機制。近些年,未成年人犯罪刑事案件頻現,未成年人犯罪也已經在世界范圍內成為公認的社會問題,預防和減少未成年人犯罪已經成為各國共同的討論熱點。而刑事和解制度作為一種非訴的制度,旨在實現未成年犯罪人和被害人雙方利益的最大化[1],所以在未成年人犯罪處置機制中引入刑事和解這一制度是世界各國的通識。本文通過梳理法條時發現,在我國司法理論中,很少有關于未成年人刑事和解制度專門化、規范化的研究。處于轉型期的中國雖然認識到了這一重大社會問題,我國在2013年頒布的新《刑事訴訟法》中新設特別程序一章,用24個條規規定了4個特別程序,其中第一個就是未成年人犯罪案件訴訟程序,但新《刑事訴訟法》由于剛剛頒布,對于未成年人刑事和解制度相關立法難免還不完善。其中,“未成年人犯罪案件訴訟程序”專章并沒有特別規定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和解程序,僅用第276條簡單規定直接適用“當事人和解的公訴案件程序”相關條款。一般來說,相較于成年人,未成年人生理、心理各方面尚未發育成熟,加之未成年犯罪人大多是偶犯和初犯且主觀惡性和社會危害程度較小,所以針對未成年人犯罪,在司法制度上應更多是推崇區別于成年人犯罪的人性化、輕刑化的處罰制度,而不應該如法條規定那般直接、簡單。
由于立法不完善,使得未成年人刑事和解操作起來并非法條規定的如此簡單,在各地司法實踐中也是做法不一,爭議不少。未成年人刑事和解制度中的爭議問題主要可歸結為以下幾個方面:
首先,適用的案件范圍有限。未成年人由于自身心智尚未完全成熟,很容易一時沖動而走上犯罪道路,未成年人犯罪所觸及的案件范圍也是五花八門。其次,適用的階段不明確。在我國的現行法律法規中,并未賦予公安機關主持未成年人刑事和解案件的權利。該規定僅僅指明了公安機關可以主持制作和解協議書,但卻沒有給公安機關到底能否主動促成刑事和解的這一疑問一個明確答案。這其實也是涉及到了公檢法三機關在刑事和解制度,特別是未成年人刑事和解制度運行中的角色定位問題。再次,監督的力度不足。一個制度的良性運行必然需要強大監督機制支持。刑事和解要求加害人和被害人雙方以非訴的方式解決刑事案件。雖然未成年人一直以來受到國家和法律的保護,但我們不能忽略未成年加害人的行為仍是犯罪行為,所以司法機關必須對這一制度進行嚴格的控制和監督。最后,和解的其他爭議點的歸納。據現行的法律法規并沒有規定刑事和解的主持人,在不同階段由公檢法三大司法機關做未成年人刑事和解主持人是否真的合適?設立專門的調解機構是否更加理想呢?達成未成年人刑事和解的過程中,是否也應該賦予律師在場的權利呢?倘若加害方的未成年人家庭著實沒有賠償能力并因此導致被害方家庭生活十分困難,這種情況下,國家司法救助制度是否是給當事人雙方打開了另一扇窗?
二、“中國式”未成年人刑事和解制度構建的必要性分析
刑事和解制度這一概念是20世紀中葉從英美等發達國的司法實踐中衍生而來的,是恢復性司法的重要內容。刑事和解也可以稱為被害人犯罪人的和解、被害人犯罪人的會議或恢復性司法對話等。它的基本內涵是:犯罪發生后,加害真心悔過并積極認罪,經調停人的幫助,與被害人直接溝通、共同協商,解決糾紛。西方少年法庭制度是未成年人刑事和解制度的起源,由于政治、經濟、文化、歷史等各方面原因,西方國家對于未成年人犯罪刑事和解的研究領先于我國。刑事和解制度本身又具有妥善、積極解決矛盾與糾紛的社會功能,使得未成年人刑事和解這一制度在西方廣泛發展。隨后,世界各國也紛紛著手于未成年人司法制度的探究。雖然各國對于未成年人刑事和解制度的規定各有不同,但總體來看是兩個模式:一個是國家主導模式,它以德國、法國為代表的歐洲大陸法系國家為典型;另一個是社會主導模式,則是以芬蘭、加拿大等國家為典型代表。
國家主導模式的未成年人刑事和解制度主要是國家的立法機關經正式立法程序,制定具有國家強制色彩的相關法律法規,將未成年人刑事和解制度正式納入國家刑事司法體系并明確規定此制度運行適用的條件、適用的范圍、適用的程序以及相應的法律后果等[2]。社會主導模式的未成年人刑事和解制度就是指對適用于未成年人的刑事和解并沒有正式的規范性依據,而是靈活地依靠社區自治、地區自治來指導未成年人刑事和解的實踐。未成年人刑事和解制度的突出特點是未成年犯罪人與被害人可以協商,達成和解協議,并且協商結果對案件處理能夠產生一定的影響。但是,未成年人刑事和解并不能完全等同于民間“私了”,而是國家處理犯罪的一種特殊的方式[3]。基于此,構建“中國式”的未成年人刑事和解制度,仍然是以“國家主導模式”為主。
綜上,立法和司法上,在我國未成年人犯罪中適用刑事和解這一舉措仍處于摸索階段。吸收借鑒國外未成年人刑事和解運作模式的優點,堅持“國家主導模式”為主,從未成年人和解制度適用的案件范圍、適用的階段以及監督機制上進行本土化的設計,構建“中國式”的未成年人刑事和解制度已迫在眉睫。
三、大勢所趨:“中國式”的未成年人刑事和解制度構建
(一)案件范圍的構想:不再單純以“刑法分章節的方式”限定
刑事和解作為一種解決糾紛、分流案件的方式,案件范圍要有限制。我國刑事犯罪主要可分為三大類,刑事和解的進行必須得到被害人同意,所以在案件沒有明確的被害人,刑事和解根本無法達成。所以一般認為刑事和解著重適用第一類犯罪。過去未成年人犯罪主要是盜竊等侵財型犯罪為主,但是目前未成年犯罪類型已經向多元化趨勢發展。我國未成年人犯罪的類型明顯增多,如計算機、金融、涉毒、賣淫等犯罪日漸增多,這就造成了各地司法在實踐中處理未成年人刑事和解案件范圍往往比《刑事訴訟法》規定的范圍更廣些的局面。
筆者愚見,“中國式”未成年人刑事和解適用的案件范圍仍需以有明確直接被害人的犯罪類型為主,但可以考慮不完全以“刑法分章節的方式”[4]來規定。本文更贊同,把未成年人刑事和解適用的范圍規定在有明確被害人案件的同時,還應根據未成年人所犯罪行的社會危害程度以及其悔罪表現來確定是否適用刑事和解制度,甚至對一些嚴重的未成年人刑事犯罪也可以有限度的適用刑事和解。未成年人心智不成熟,易沖動,犯罪的主觀惡性、客觀行為的惡劣程度以及帶來的社會危害性往往小于成年人,所以對未成年人適用刑事和解適用范圍的態度應該更寬容。
(二)適用階段的設計:貫穿于整個刑事訴訟過程
2013年新《刑事訴訟法》規定了當事人和解的公訴案件在偵查、審查起訴、審判階段三階段可以適用刑事和解程序。筆者認為,既然針對未成年犯罪人的刑事和解制度旨在最大限度地教育、挽救涉罪的未成年人,幫助他們回歸校園,重返社會,那么我國未成年犯罪人的刑事和解貫穿于刑事訴訟整個過程更為合適。換言之,未成年人刑事和解可適用于立案、偵查、審查起訴、審判和執行五大階段。在刑事訴訟任一階段,只要未成年人犯罪符合刑事和解的條件且未成年加害人和被害人有自愿和解的意向,就可以相應的啟動未成年人刑事和解程序。
第一,作為刑事訴訟的首要階段,立案和偵查階段是相對其他后續階段,對不履行和解協議這一行為救濟更為廣泛,所以筆者認為在立案、偵查階段只要犯罪案件符合刑事和解啟動的條件,雙方就可以在偵查人員的組織下提起和解,達成和解協議。偵查機關可以就此終結訴訟活動,撤銷案件并且也沒有必要再移送到檢察機關。同時可以引入檢察機關對和解案件的監督,從而更加確保和解結果公平公正。第二,審查起訴階段是刑事訴訟的關鍵階段,在我國各地司法實踐中,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在這一階段適用刑事和解的案例也是最多的。因為經過偵查機關的細心偵查,搜集整理證據,未成年人的犯罪事實已基本清楚、證據也已經固定下來,同時未成年犯罪人經過自己的反思及司法機關工作人員和家人的耐心勸導逐漸穩定心神,認識到了自己的錯誤。此階段更有利于未成年人刑事和解的開展。具體操作上,檢察機關在受理偵查機關移送的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后,經過審查符合刑事和解條件的,可以由當事人雙方或檢察機關啟動未成年人刑事和解程序。檢察機關可以在啟動未成年人刑事和解程序的同時設置一定的考察期,在未成年犯罪人成功度過考察期后正式作出不起訴的決定。第三,未成年人犯罪在審判階段是否適用刑事和解,一直以來備受爭議。2013年新《刑事訴訟法》規定了當事人公訴案件的和解可適用于審判階段,鑒于此,我國針對未成年人犯罪的刑事和解也完全可以適用于審判階段。案件進入了審判階段也就意味未成年犯罪人馬上要被追究刑事責任,這也是未成年犯罪人真誠悔罪求得被害人原諒以從輕處罰的最后機會。由于這一階段已案件事實清楚,證據確鑿充分,未成年人已經明確構成犯罪了,所以此階段的未成年人刑事和解主要作為適用緩刑或從輕減輕的量刑條件更為合理。第四,隨著審判終結合議庭作出最終裁判,刑事和解也應畫上一個句號。但由于我國未成年犯罪人的家庭、教育以及社會文化等種種原因,當事人雙方在立案偵查、審查起訴、審判階段沒能達成刑事和解的,在執行階段也應當給予未成年犯罪人刑事和解最后的機會。未成年犯罪人如果能夠真誠悔悟,認真服刑,改過自新,在積極賠償的同時取得被害人的諒解,那么這時的刑事和解協議完全可以作為對未成年犯罪人給予減刑、假釋的依據。
“中國式”未成年人刑事和解應當貫穿于整個刑事訴訟過程的目的不僅僅在于預防和減少未成年人犯罪,更重要的是最大限度地挽救未成年犯罪人,幫助他們樹立正確的價值觀和人生觀,健康成長,早日回歸校園,走向社會。
(三)監督機制的建立:實現從制度啟動到后續的全方位監督
我國各地未成年人刑事和解的司法實踐蓬勃發展,但目前我國新《刑事訴訟法》還沒有專門關于未成年人刑事和解的條文,所以部分地方司法機關零星地對未成年人刑事和解做出了規定。這些地方“立法”雖然規定了未成年人刑事和解適用條款,但由于自身法律位階較低、約束力小,公檢法擁有較大的自由裁量權,司法難以操作。人民檢察院是國家的法律監督機關,監督我國的未成年人刑事和解的運行這一重擔,自然也應由檢察機關主要來承擔。“中國式”未成年人刑事和解的構建,完善相應的監督機制非常重要,具體而言:
一是對制度的啟動進行監督。啟動未成年人刑事和解程序的前提是案件符合刑事和解的條件。對未成年人刑事和解適用的監督要從和解啟動就開始。無論和解在哪一階段啟動,檢察機關都應嚴格監督未成年人刑事和解案件能否啟動或者和解的啟動是否合法,是否有金錢、人情等社會因素介入以促成未成年人刑事和解的啟動。二是對和解過程的進行監督。如前文述,“中國式”的未成年人刑事和解貫穿于刑事訴訟全過程,那么不同適用階段也應配有相應的監督措施。為了確保監督的效果,最理想的狀態是檢察機關深入參與每一個未成年人刑事和解案件。例如:首先,立案及偵查階段。檢察機關可以派員監督偵查機關處理未成年人刑事和解的全過程。其次,審查起訴階段。這一階段的監督只依靠檢察機關自身監督管理部門是遠遠不夠的,還應在完善內部監督機制的同時,利用外部力量對未成年人刑事和解進行監督。再次,審判階段。此階段檢察機關主要監督法院因刑事和解而做出從輕或減輕處罰的相關依據是否正當、合法。檢察機關認為未成年刑事案件的和解不符合相關規定的,可以提出檢察建議或直接啟動審判監督程序。最后,執行階段。“中國式”未成年人刑事和解之所以可在執行階段適用,主要考慮未成年犯罪人的家庭狀況、受教育程度、社會文化等因素對犯罪人的影響以及未成年犯罪人的悔罪表現,從而給原本已經終結的訴訟程序開一扇小窗監,因此階段督應主要側重于審查未成年犯罪人及家屬提供的信息是否屬實,被害人在此階段愿意參與和解的具體原因,以及對未成年犯罪人悔悟程度。三是對和解后續的進行監督。對未成年人刑事和解后續的監督,一方面對刑事和解協議的履行情況監督,實時監督當事人雙方有無反悔情況;另一方面,把未成年犯罪人置于社會中對其進行改造和矯正是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刑事和解制度的重要特點之一也是重要的意義所在。
(四)制度的完善:幾個細節的再思考
除上述愚見外,在此,最后本文還想對其他幾個問題求教于各位同仁:
其一,在全國各地未成年人刑事和解的實踐中,大部分是由不同階段的辦案機關主持和解,而設立專門的調解機關則是西方國家的一貫做法。筆者認為,為保證和解程序更加公正、合理,“中國式”的未成年人刑事和解,也應當學習借鑒以德國等國家主導模式的做法,設立專門的調解機構,而不應再有司法機關本身主持和解。其二,“中國式”未成年人刑事和解完全可以賦予律師在場權利。從我國的司法實踐來說,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以及被害人之間往往缺少溝通平臺,并且他們在司法機關面前也常常表現得很敬畏,不敢表達自己內心的真實想法,律師作為其委托的人,能夠充當他們之間的溝通使者[5]。辯護律師在場,可以幫助雙方在和解過程中提出更合理更理性的和解意見,同時也能夠有效避免被害人漫天要價等現象。其三,把國家司法救助制度靈活運用到未成年人刑事和解中是刑事和解本土化的另一有力舉措。我國在2014年頒布的《關于建立完善國家司法救助制度的意見(試行)》中明確把刑事案件被害人因加害人死亡或無賠償能力而造成生活困難的作為國家司法救助的對象。筆者認為,國家司法救助制度完全可以作為“中國式”未成年人刑事和解下對被害人的救濟措施。當加害人確實無能力賠償時,由加害人申請國家司法救助,由國家向被害人先行墊付賠償金,加害人通過勞動等在一定時期內償還國家。
四、結語
在世界范圍內,未成年人犯罪問題已經成為各國普遍關注的社會熱點問題。未成年人犯罪低齡化和多元化趨勢也越發明顯。未成年人作為一個特殊的群體,需要當代社會的特殊保護,尤其需要區別于成年人的社會制度和司法制度的特殊保護。古以來,儒家都主張,“禮之用,和為貴”。“以和為貴”一直是我國傳統文化和傳統道德的精髓,這也與刑事和解所體現的“恢復性司法”共通。在我國,這種“和”理念更應貫穿于“中國式”未成年人刑事和解的整個過程。在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中引入區別于成年人的刑事和解制度,構建“中國式”的未成年人刑事和解制度,不僅使得被害人的精神利益和物質利益得以恢復,有利于加害的未成年犯罪人再社會化,同時更是有利于對訴訟程序繁簡分流,最大限度地節約訴訟資源、提高訴訟效率。
[1]肖晚祥,張 果.刑事和解的困境與出路[J].法律適用,2010,(4).
[2]黎 莎.兩種模式下的西方未成年人刑事和解制度特征解讀[J].公民與法:法學版,2010,(5):34.
[3]孫 勤.刑事和解價值分析[M].北京:中國人民公安大學出版社,2009:111.
[4]田文昌.新刑事訴訟法熱點問題及辯護應對策略[M].北京:中國法制出版社,2013:277.
[5]岳禮玲.刑事審判與人權保障[M].法律出版社,2010:121.
Reality and Reconstruction:Chinese-style System of Victim-offender Mediation for the Juvenile
WANG Tong
All around the world,the rising juvenile crime rate and the decreasing age of criminal offenders have become the problems which endanger society safety.The juvenile crime is becoming increasingly prominent in the transformation of Chinese society.Therefore it is necessary to function the Chinese-style system of Victim-offender Mediation(VOM)for the juvenile,which is different from the VOM for the adult and blends with the idea that harmony is a virtue,the essence of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and morality,in the meditation process.
juvenile;VOM;system construction
DF7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4-5612(2017)04-0049-05
(責任編輯:吳良培)
2017-04-26
王 統,(1993- ),女,山東青州人,山東大學法學院法學碩博連讀生,研究方向:刑事訴訟法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