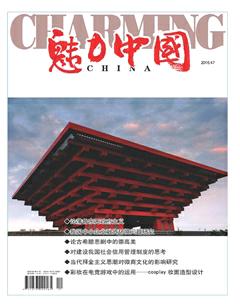論王夫之的道統(tǒng)與治統(tǒng)
謝階玉
摘要:在王夫之的學(xué)術(shù)思想中,“道統(tǒng)”和“治統(tǒng)”是兩個(gè)很重要的概念。“道統(tǒng)”思想由來已久,王夫之在前人已有成就的基礎(chǔ)上,又有所發(fā)展,提出“圣人之教,是謂道統(tǒng)”,并認(rèn)為應(yīng)以“明倫”和“察物”為“道統(tǒng)”基本內(nèi)容的總綱。對(duì)于君主政權(quán)的合法性來源問題,王夫之反對(duì)傳統(tǒng)的“正統(tǒng)論”而提出“治統(tǒng)說”,認(rèn)為“天子之位也,是謂治統(tǒng)”。王夫之還強(qiáng)調(diào)“治統(tǒng)”應(yīng)該是對(duì)人民有利的,為了使人民過穩(wěn)定生活、免受戰(zhàn)亂之苦,改朝換代亦無不可。這對(duì)于一個(gè)封建士大夫來說已是一種極大進(jìn)步。在王夫之看來,“道統(tǒng)”和“治統(tǒng)”是唇齒相依的關(guān)系,兩者相結(jié)合才能達(dá)到平治天下。
關(guān)鍵詞:王夫之;道統(tǒng);治統(tǒng)
王夫之是我國(guó)古代杰出思想家之一,他的政治思想融哲學(xué)、史評(píng)、政論為一體,尤其在政治哲學(xué)方面博采眾長(zhǎng),獨(dú)放幽馨。但由于過去學(xué)界對(duì)其思想的不重視,導(dǎo)致其很多作品遭到破壞或遺失。幸運(yùn)的是自19世紀(jì)20年代以后學(xué)界開始重視王夫之思想,在眾多學(xué)者的努力下,許多遺失的作品被找回,并整理與出版。這為以后的研究工作帶來了很大的幫助。在王夫之的政治思想中,他的“道統(tǒng)論”和“治統(tǒng)說”是不容忽視的,特別是他的“道統(tǒng)”和“治統(tǒng)”合一的觀點(diǎn)。
一、道統(tǒng)的傳承與批判
中華道統(tǒng)思想由來已久,最早可以追溯至伏羲,由周公、孔孟等圣人傳承。《孟子·公孫丑下》:“五百年必有王者興,其間必有名世者。”[1]敘述了堯、舜、湯、文王、孔子的傳承脈絡(luò)。唐韓愈則作《原道》,正式提出傳道譜系,建立起真正的道統(tǒng)論。宋儒在韓愈的基礎(chǔ)上對(duì)道統(tǒng)論作進(jìn)一步的發(fā)展,朱熹更是將韓愈儒家仁義之道的思想正式定名為“道統(tǒng)”。到了王夫之,許多學(xué)者認(rèn)為王夫之對(duì)傳統(tǒng)儒家道統(tǒng)論,特別是對(duì)宋儒道統(tǒng)論持否定態(tài)度。其實(shí)不然,筆者認(rèn)為王夫之更多的是對(duì)傳統(tǒng)儒家道統(tǒng)論的一種批判繼承。
那么,何為“道統(tǒng)”。王夫之說:“圣人之教,是謂道統(tǒng)。”意思是孔孟之道,亦即禮仁政治的基本原則,就是道統(tǒng)[2]。因此,王夫之又把“道統(tǒng)”成為“儒者之統(tǒng)”。“道統(tǒng)”的基本內(nèi)容又是什么呢?王夫之在《讀通鑒論》中寫道:“若夫百王不易、千圣同原者,其大綱,則明倫也,察物也;其實(shí)政,則敷教也,施仁也;其精意,則衹臺(tái)也,躋敬也,不顯之臨、無射之保也;此則圣人之道統(tǒng),非可竊者也。”[3]從這一段話中可以看出,王夫之認(rèn)為“道統(tǒng)”主要包含三方面的內(nèi)容,分別是:(1)明倫,察物;(2)敷教,施仁;(3)衹臺(tái),躋敬。三項(xiàng)基本內(nèi)容,每項(xiàng)都有自己的內(nèi)涵和思想,但以“明倫”和“察物”為總綱。“明倫”“察物”,指明于人倫、察于庶物。具體說來是察于萬物之情,達(dá)于萬物之理,明與人倫之愛敬,知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zhǎng)幼有序、朋友有信。[4]很多學(xué)者據(jù)此認(rèn)為這是王夫之對(duì)傳統(tǒng)儒家道統(tǒng)論的一種顛覆。其實(shí),我們?nèi)绻軌蛴靡环N客觀的心態(tài)來品讀王夫之的著作,以及聯(lián)系孔孟之道的話,就會(huì)發(fā)現(xiàn),王夫之的“道統(tǒng)”恰恰是對(duì)傳統(tǒng)儒家道統(tǒng)論的繼承,王夫之所認(rèn)為的“道統(tǒng)”三項(xiàng)基本內(nèi)容,其實(shí)就是孔孟之道。王夫之認(rèn)為,作為“儒者之統(tǒng)”的道,首先是人道,人道來自于人性,其內(nèi)容體現(xiàn)為孔孟所反復(fù)倡揚(yáng)的仁義禮智信之道,他認(rèn)為“性存而后仁、義、禮、知之實(shí)章焉”。[5]所謂的顛覆,不過是對(duì)宋儒道統(tǒng)論的一些不足、缺陷所做的一些反思、修正而已。宋儒的道統(tǒng)論在發(fā)展的過程中,一些理學(xué)家與理學(xué)學(xué)派為了提高本學(xué)派及其宗師的地位,“道統(tǒng)”就與他們的“單傳”、“心法”聯(lián)系起來。王夫之乃是對(duì)這種做法持否定態(tài)度。[5]王夫之在《讀四書大全說》卷9中寫道:“古今此天下,許多大君子或如此作來,或如彼作來,或因之而加密,或創(chuàng)起而有作,豈有可傳之心法,直指單傳,與一物事教奉持保護(hù)哉。”[6]由此可見,王夫之所要否定的乃是這種狹隘心態(tài)的道統(tǒng)論。
王夫之非但沒有否定宋儒的道統(tǒng)論,反而認(rèn)為道統(tǒng)正是在宋儒這得到繼承和弘揚(yáng)。“自周子出,而始發(fā)明圣道之所由,一出于太極陰陽人道生化之始終,二程子引而伸之,……故朱子以格物窮理為始教”[7]。他認(rèn)為宋儒周、程、張、朱真正繼承并弘揚(yáng)了“道統(tǒng)”。而在這些大儒中,王夫之備為推崇的是關(guān)學(xué)張載。他認(rèn)為張載所講的“道”既是太虛陰陽屈伸的天道,又是人治存神盡性、明誠(chéng)立禮的人道,這種天人合一、明體極用之道才是儒家道統(tǒng)所堅(jiān)守的道。[5]王夫之在道統(tǒng)譜系中肯定張載高于程朱,是因?yàn)樗J(rèn)為雖然程朱在傳承孔孟道統(tǒng)方面功勞很大,但程朱之學(xué)未能極道之用,因此認(rèn)為其在道統(tǒng)譜系中的地位在張載之下。
二、治統(tǒng)說的創(chuàng)立
在封建政治領(lǐng)域,最核心的問題就是君主統(tǒng)治權(quán)的“合法性”來源問題,而在這個(gè)問題上最流行的觀點(diǎn)就是“正統(tǒng)論”。正統(tǒng)論認(rèn)為,“必有所承以為統(tǒng),而后可以為天子。”歷代封建統(tǒng)治者為了證明自己建立政權(quán)的合法性,紛紛提出或采用各種神秘的學(xué)說以證明其政權(quán)的“正統(tǒng)”性。在這些學(xué)說當(dāng)中,影響最顯著的乃是戰(zhàn)國(guó)時(shí)期鄒衍提出的“五德終始說”。而王夫之則對(duì)這些正統(tǒng)論學(xué)說進(jìn)行了批判,認(rèn)為這些不僅不能夠證明君主政權(quán)的合法性,反而成了君主暴政、夷狄亂華,把天下變成他們“一姓之私”的借口。在他看來,“以天下論者,必循天下之公,天下非一姓之私也。”[3]因此,王夫之提出了“治統(tǒng)說”。“天下所極重而不可竊取者二:天子之位也,是謂治統(tǒng);圣人之教,是謂道統(tǒng)。”[3]所謂治統(tǒng),即君統(tǒng)、帝統(tǒng)、帝王之統(tǒng)。治統(tǒng)是治平天下一般原則的實(shí)施和運(yùn)作,其傳承者必須居天子之位。[2]所以王夫之又把“治統(tǒng)”稱為“帝王之統(tǒng)”。
王夫之認(rèn)為“帝王之興,以治相繼”,繼而指出:“商、周之德,萬世之所懷,百王之所師也。柞已訖而明徑不廢,子孫不可替,大公之道也。秦起西戎,以詐力兼天下,蔑先王之道法,海內(nèi)爭(zhēng)起,不相統(tǒng)一,殺掠相尋,人民無主,漢祖滅秦夷項(xiàng),解法網(wǎng),薄征搖,以與天下更始,略德而論功,不在湯、武之下矣。漢柞既終,曹魏以下二百余年,南有司馬、劉、蕭、陳氏,皆竊也,北有五胡、拓拔、宇文,皆夷也。隋氏始以中原族姓一天下,而天倫絕,民害滋,唐掃群盜為中國(guó)主,滌積重之暴政,予兆民以安,嗣漢而興,功亦與漢坪等矣……唐之既亡,朱溫以盜,朱邪、桌披推以夷,劉知遠(yuǎn)、郭威鎖鎖健兒,瓜分海內(nèi),而僅據(jù)中州,稱帝稱王,賤于垂尉,至宋而后治教修明,賢君相嗣,以為天下君師。于是周、漢與唐,猶手授也。”[3]由此可知,王夫之認(rèn)為治統(tǒng)應(yīng)該具備以漢族為君主、統(tǒng)一、祚久三個(gè)條件,其實(shí)質(zhì)也突出了“治”。秦、隋雖然統(tǒng)一了天下,君主又是漢族,但他們“殺掠相尋”“天倫絕,民害滋”,而且政權(quán)持續(xù)時(shí)間短,因此王夫之認(rèn)為秦、隋應(yīng)該被排除在治統(tǒng)之外。而商、周、漢、唐、宋、明這六朝做到了“前有所承則后有所授”“德足以君天下,功足以安黎民,統(tǒng)一六宇,治安百年,……合乎人心之大順”[3],因此屬于治統(tǒng)。
王夫之的“治統(tǒng)”還有一個(gè)很明顯的特定,就是他的民族主義思想。他認(rèn)為“治統(tǒng)”應(yīng)該掌握在本民族,而不能為“夷狄”所掌握,即否定少數(shù)民族在中原建立政權(quán)。如果“治統(tǒng)”掌握在異族的手中,天下將大亂。他指出:“治統(tǒng)之亂,小人竊之,盜賊竊之,夷狄竊之,不可以永世而身;其幸而數(shù)傳者,則必有日月失軌、五星逆行、冬雷夏雪、山崩地坼、雹飛水溢、草木為妖、禽蟲為蠥之異,天地不能保其清寧,人民不能全其壽命,以應(yīng)之不爽。”[3]因此,他把元朝排除在治統(tǒng)之外,認(rèn)為宋亡以后,天下處于“無統(tǒng)”狀態(tài)。王夫之這種民族主義思想,在當(dāng)時(shí)有一定的現(xiàn)實(shí)意義。王夫之處于明末清初的動(dòng)亂時(shí)期,社會(huì)矛盾非常復(fù)雜。滿族推翻漢族的統(tǒng)治,在中原建立起少數(shù)民族政權(quán),民族矛盾空前激發(fā)。王夫之作為愛國(guó)主義分子,參加過幾次抗清運(yùn)動(dòng)。因此,王夫之絕不會(huì)把清朝列入他的“治統(tǒng)”范圍。同樣,他必然將非漢族政權(quán)的元朝的統(tǒng)治列入亂世。
王夫之還強(qiáng)調(diào)“治統(tǒng)”應(yīng)該是對(duì)人民有利的,他指出:“天下者,非一姓之私也,興亡之修短有恒數(shù),茍易姓而無原野流血之慘,則輕授他人而民不病。”[3]天下不是君主一個(gè)人的私有財(cái)產(chǎn),朝代的更替有一定的定數(shù)。為了使人民免受戰(zhàn)亂之苦,繼續(xù)過穩(wěn)定的生活,把政權(quán)交給另一個(gè)漢族政權(quán)亦無不可。他甚至還說:“茍有知貴重其民者,君子不得復(fù)以君臣之義責(zé)之,而許之以民主可也。”[3]即如果有尊重人民、重視人民利益的人,便可以推舉其為民之主。在這一點(diǎn),王夫之的“治統(tǒng)說”與黃宗羲的治天下“不在一姓之興亡,而在萬民之憂樂”的政治思想是極為相似。[8]雖然王夫之的政治思想始終都沒有擺脫君主政治的思想,但對(duì)于當(dāng)時(shí)的社會(huì)、對(duì)于一個(gè)封建士大夫來說,強(qiáng)調(diào)君主要作民之主,已是一種極大的進(jìn)步。
三、道統(tǒng)和治統(tǒng)合一
有學(xué)者認(rèn)為“道統(tǒng)”和“治統(tǒng)”體現(xiàn)了儒家士大夫與君主之間一種緊張的關(guān)系。而王夫之認(rèn)為,商、周、漢、唐這些“治統(tǒng)”君主之所以能夠平治天下,在于他們奉行“道統(tǒng)”,即“儒者之統(tǒng)”。因此,“道統(tǒng)”和“治統(tǒng)”不僅不沖突,反而應(yīng)該相伴而行,合而為一。“儒者之統(tǒng),與帝王之統(tǒng)并行于天下,而互為興替。其合也,天下以道而治,道以天子而明;及其衰,而帝王之統(tǒng)絕,儒者猶保其道以孤行而無所待,以人存道,而道可不亡。”[3]在王夫之看來,“道統(tǒng)”和“治統(tǒng)”互為唇齒。“治統(tǒng)”是“道統(tǒng)”的現(xiàn)實(shí)基礎(chǔ),“道統(tǒng)”是“治統(tǒng)”的內(nèi)在依據(jù)。[4]如果君主以孔孟之道治理國(guó)家,可致太平盛世,天下得治。而儒家學(xué)說也會(huì)因此得到繼承和發(fā)展。此所謂“治統(tǒng)”興則“道統(tǒng)”顯;反之,“治統(tǒng)”絕則“道統(tǒng)”隱。[4]但是王夫之又指出“道統(tǒng)”具有相對(duì)獨(dú)立性,即使“帝王之統(tǒng)絕”,儒者也會(huì)自覺地承擔(dān)起傳承“道統(tǒng)”的歷史使命,此所謂“以人存道,而道不可亡”。而只要“道統(tǒng)”不絕,“治統(tǒng)”就有復(fù)興的希望。在反抗清朝、恢復(fù)明朝統(tǒng)治的希望破滅后,王夫之隱居衡陽石船山,潛心注釋儒家經(jīng)典,以傳承“道統(tǒng)”自任,就是為了等待“治統(tǒng)”的接續(xù)。
人們?cè)谘芯客醴蛑淖髌窌r(shí),可以看到一個(gè)似乎矛盾的地方。即王夫之一方面猛烈地抨擊君主專制統(tǒng)治,揭露和批判了歷代君主的殘暴、自私、專橫,甚至提出“一姓之興亡,私也,而生民之生死,公也。”[3]“茍有知貴重其民者,君子不得復(fù)以君臣之義責(zé)之,而許之以民主可也。”[3]等反君主專制的言論。這些言論成為了近代民主思潮的先聲。另一方面,他又沒有否定君主專制制度,只是否定“舍君天下之道而論一姓之興亡”,即否定將“一姓之興亡”作為“治統(tǒng)”的根本,而不否定“君天下”的君主專制制度。他認(rèn)可的“明王”就是這種君主政治的典范,即“明王之涖臣民也,定尊卑之秩,敦忠禮之教,不失君臣之義”。[5]這兩方面看起來很矛盾,但以他的道、治合一論來看,這其實(shí)并不矛盾。王夫之提出“天下所極重而不可竊取者二:天子之位也,是謂治統(tǒng);圣人之教,是謂道統(tǒng)。”[3]這首先肯定了君主的權(quán)力和地位。但要達(dá)到平治天下,就要遵循“道”,以君主政治權(quán)力為核心的“治統(tǒng)”必須受到“道統(tǒng)”的制約,以孔孟之道來治理天下。王夫之提出:“復(fù)有賢子孫相繼以飾治,興禮樂,敷教化,存人道”[3]“道相承也”,表達(dá)的就是這種思想。
王夫之曾提出“君、相、諫官”三者“環(huán)相為治”的權(quán)力制衡觀念,“宰相之用舍聽之天子,諫官之予奪聽之宰相,天子之得失則舉而聽之諫官;環(huán)相為治,而言為功。”[9]王夫之意識(shí)到君主擁有至高無上的政治權(quán)力,如果沒有監(jiān)督,君主很有可能按照自己的意志行使權(quán)力,而不是“道統(tǒng)”。為了使君主權(quán)力的行使受到“道”的制約,王夫之認(rèn)為應(yīng)該設(shè)立“諫官”一職以監(jiān)督君權(quán)。可以說王夫之看到了君主專制制度的嚴(yán)重弊端,“環(huán)相為治”的權(quán)力制衡思想充滿了政治智慧,這一思想使“治統(tǒng)”在“道統(tǒng)”的制約中更好地發(fā)揮作用。
參考文獻(xiàn):
[1]楊伯峻譯注:《孟子譯注》,中華書局2008年第1版。
[2]劉澤華、葛荃主編:《中國(guó)古代政治思想史》(修訂版),南京大學(xué)出版社2001年第2版。
[3][清]王夫之著、舒士彥點(diǎn)校:《讀通鑒論》,中華書局2013年第3版。
[4]彭傳華:《正統(tǒng)、道統(tǒng)、治統(tǒng)——王船山對(duì)于政權(quán)合法性來源的思考》,南昌大學(xué)學(xué)報(bào)(人文社會(huì)科學(xué)版)第44卷第2期2013年3月。
[5]朱漢民:《王船山的道統(tǒng)、治統(tǒng)與學(xué)統(tǒng)》,北京大學(xué)學(xué)報(bào)(哲學(xué)社會(huì)科學(xué)版)第50卷第1期2013年1月。
[6][清]王夫之著:《讀四書大全說》,中華書局2011年第1版。
[7][清]王夫之著:《張子正蒙注》,中華書局2011年第1版。
[8]蔡克驕:《王夫之的“治統(tǒng)”和“道統(tǒng)”》,衡陽師專學(xué)報(bào)(社會(huì)科學(xué)版)1987年第4期(總第31期)。
[9][清]王夫之著、王嘉川譯注:《宋論》,中華書局2008年第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