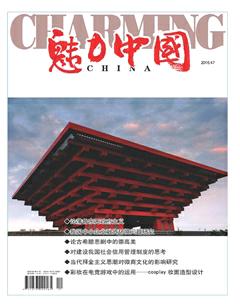中國書法藝術淺談
摘要:書法是中國的國粹,究竟何為書法,各家說法不一。本文擬從以下幾個方面探討漢字書法的特性: 一,漢字的實用美與藝術美;二,漢字結構造型、點畫動勢、用筆節奏的特點與古埃及象形文字的圖案性和具象性的區別;三,書法與文學的關系;四,漢字線條本身的形式美及與西方藝術美的不同
關鍵詞:中國書法;結構造型、象形文字;點畫動勢
書法是中國的國粹,究竟何為書法,各家說法不一。有人說書法是用毛筆寫漢字的藝術,這就把硬筆書法、甲骨文、鐘鼎文排除在外。硬筆書法是硬筆寫的,甲骨文、鐘鼎文是刻鑄的,但我們無論如何無法否認它們當中都有書法美,尤其是甲骨文和鐘鼎文中那種因刻鑄所產生的獨特的美。把它們的美排除在書法之外,很難自圓其說。
有人說漢字的書法藝術在于漢字具有象形性,但象形性只是六書造字法之一,其它還有指事、會意、形聲、轉注和假借,而且其象形性隨著文字的發展變遷以及幾次的漢字簡化,越來越弱。實際上,現在漢字的象形性遠比古埃及象形文字弱,而抽象性卻很強。所以,象形性不能看作書法美的根基。古埃及象形文字也有象形性,也有獨特的美,如果象形性是漢字書法美的根基,那么古埃及象形文字的美為什么就不能也算作書法美?
我認為,漢字的書法藝術在于結體的點畫之間有一種造型的“勢”,它使線條之間產生動態的呼應和彼此牽引呼喚的動勢,結果使抽象的漢字具有了形象性。而且,點畫之間這種造型的“勢”給線條和用筆創造了充分表現的舞臺。也就是說這種“勢”及其所造就的抽象的點畫之間的動態象形,加上刻寫人的用筆個性和風格才是漢字書法藝術性的根基,至于是毛筆寫的,還是硬筆寫的,還是刻鑄的并不是關鍵的因素。當然用毛筆書寫,更容易寫出不同的筆意,使藝術性更充分地體現出來。
從造型角度來看,古埃及的象形文字實際上是一種圖案式的符號,它可以加以描摹,但它不能像漢字那樣從用筆上來“寫”出點畫的筆勢。甲骨文、金文,盡管是刻鑄的卻有“用筆”的感覺。
漢字書法美不在形體的描摹和具象,而在于上文所說的點畫之間的“勢”,在于點畫之間的呼應和用筆產生的節奏感。在西方古典繪畫中,線條是再現物象和人物的手段,不是獨立的審美對象,無所謂美與不美。在中國書法和繪畫中,線條不只是手段,還是目的,也就是說,線條除了用來描摹物象、人物,構架漢字外,其自身就呈現獨立的形式美,成為獨立欣賞的對象,只是書法比繪畫更充分體現這一點。在漢字書法藝術中,線條有自身的“質感”,而在西方繪畫中線條被消解在物象或人物中。
但是,書法藝術無論如何也不能脫離漢字這個載體,否則,無論其中有多少書法的形式美,都不能算作書法。以此類推,山水畫中的皴法具有線條的審美特質,但離開山石之形,其皴法線條再美也不能算作山水畫。中國繪畫中線條的審美特性還只是半獨立的,而書法藝術中的線條之美的獨立性比繪畫就更進了一步。
書法離不開成千上萬漢字先天具有的筆畫造型和動勢,你想甩開現成的漢字,想另創一套自編的線條,以求其抽象美作為一種新的書法藝術,那只是癡人說夢、想入非非的扯淡。
中國書法藝術是純粹的“為藝術而藝術”或純粹的“有意味的形式”,換句話說,書法藝術不是像西方藝術那樣借用線條、色彩、構圖逼真地表現宗教、神話和歷史等強烈而且明確的“文本內容”,而是表現筆墨線條本身的“形式美”,盡管文字的含義對欣賞筆墨線條的“形式美”有一定的影響,這種影響與其說是“實的”,不如說是“虛的”,從每種意義講,可能是一種含糊的“心理作用”。
書法的另一個特點是純藝術與實用的界線難以劃分。書法藝術本源于實用,離不開文字,文字是文化中最實用的東西。最早的書法是在抄寫和記錄過程中逐漸總結出的一些工藝性的經驗:如何把字寫得更清晰好認,更精致、工整、漂亮,從而也更具有實用性。
在實用的工藝美之外,慢慢創造出抽象線條的形式美,如用筆產生的筆法、筆勢、筆意及其韻致,從而產生一套復雜的書法藝術的森嚴法則。
書法美有不同的層次:低級層次講究實用的工藝美,即工整、易識、精致、漂亮、規范。這是純實用的層次,所追求的美是工藝性的,不是純藝術性的;中級層次除追求工整、規范、精致、實用外,又萌生了對筆法技巧、筆墨趣味,對于線條的形式美的感悟,但只能刻意求之,不能得心應手,不過無論如何,在這個層次上書法藝術產生了;高級層次雖然不一定完全擺脫實用,但對于筆法、筆勢、筆意,已胸有成竹,并能揮灑自如地操縱線條,不受實用和規范約束,達到抒情寫意的目的。。
這高級層次,就是純書法藝術的本質特點。
書法還和文學有千絲萬縷的聯系,它最初產生于抄寫產生的銘文、文告、經籍、碑文、書信,等等,其中任何一樣都與文學相關聯。
我們欣賞書法時,不用先搞懂文字內容,可以直接欣賞書法的形式美,但這并不等于說文字內容與書法毫不相干。文字內容引發的情感一定程度影響對書法的欣賞。最典型的例子是顏真卿的“祭侄稿”。當你不了解“祭侄稿”的內容,不了解當時的歷史境況,仍然可以欣賞“祭侄稿”,欣賞它的“意不在書”,天機自動,欣賞“無意於佳乃佳,不求工而自工”的自然境界。但當你了解那一段悲慘的歷史,并讀完“祭侄稿”,知道此文是顏真卿在其侄子被俘,慘遭殺害后寫就,你無意間會發現“祭侄稿”中有怒氣、有悲憤、有極度的痛苦和悲懣激昂之情。
西方人欣賞中國書法困難重重,其原因在于西方藝術中沒有中國書法的形式美。如:通過有意識地協調和控制掌、指、腕、臂,融入書寫者對書法美的感悟和經驗而產生的筆力;通過提、按、頓、挫、轉、折、方、圓等用筆的起伏而產生的節奏感; 通過中鋒用筆所形成的沉著渾厚的立體感。
達芬奇的 “蒙娜麗莎”是西方藝術的“明星”,對畫中美麗女子的神秘微笑的詮釋,眾說紛紜,莫衷一是。那微笑表現的是少女初嘗世俗性生活的甜美而產生的竊喜,抑或是對世俗生活的揶揄?微微上翹的嘴角到底表現什么情感?我們可以欣賞女子豐滿而韻味十足的身姿、姣好的面容和柔軟而富有彈性的手指,但我們無論如何不會欣賞其中的筆觸、筆墨、筆意和筆勢,以及線條的形式美。我認為在西方印象派之前,西方繪畫中基本上不表現形式美。西方人習慣于表現和欣賞形象和色彩的逼真。直到印象派之后,尤其是后印象派之后,西方人才對線條和色彩的純形式美有所醒悟,而這種西方藝術中的形式美也不同于中國書法中的形式美。
中國一些書法評論家認為中國書法中的韻律感、節奏感在表現人的情感方面不亞于,甚至勝于音樂,我認為這實在是夸張得有點離譜。書法的抒情手段依靠的是線條的種種變化——提按、疏密、向背、起伏、疾澀、縱斂等等,總之,是通過造型時對線條意態形象的傾向,聯想生活中具象的情境、氛圍。在這兒抒情依舊是心理上一種含糊的類比。所謂“龍跳天門,虎臥鳳閣”,“公孫舞劍”之類,無非是對“勢”的一種想象啟迪,是線條在時間中的揮動,定形于空間的框架,從而引動視覺上的感悟,而音樂是通過旋律、節奏等音樂手段和不同樂器的音色將人的情感如鏡般反映出來,也就是說音樂和情感之間有比較具體的對應關系,而書法卻不能。
參考文獻:
[1]啟功 著 啟功給你講書法[M].北京.中華書局.2005-10-1。
[2]邱振中 著 書法 北京 .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2009-1-1。
作者簡介; 劉清浩,1957,男, 山東青島人,教授, 研究方向:中西文化文化藝術比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