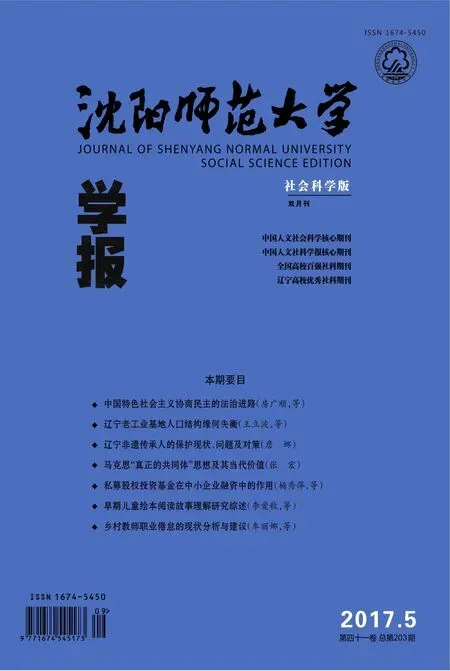產學合作的政治經濟學分析
許悅雷
(遼寧大學 日本研究所,遼寧 沈陽 110036)
產學合作的政治經濟學分析
許悅雷
(遼寧大學 日本研究所,遼寧 沈陽 110036)
產學合作是推動創新發展的關鍵。因此,對于產學合作的深入研究在我國當前生產力水平不高、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背景下具有舉足輕重的作用。運用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協作理論、生產力—生產方式—生產關系理論、生產關系—分配理論對產學合作的定義、產學合作形成的原因、產學合作的特點、我國產學合作的特質、產學合作的利益分配及產學合作的作用進行綜合分析的基礎上得出結論:社會主義的產學合作應該具有與資本主義產學合作不同的特質,應該大力推進我國產學合作及創新的發展,逐步構建具有中國特色的產學合作利益分配機制是重中之重。
產學合作;政治經濟學;創新;利益分配機制
一、產學合作的內涵
西方學術界對產學合作的研究已有較長的歷史,它主要是指為了促進知識和技術的交流和交換,高等教育體系的任何部分與產業間的互動[1]。實際上,產學合作是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協作”理論的進一步延伸和發展。馬克思認為,“許多人在同一生產過程中,或在不同的但相互聯系的生產過程中,有計劃地一起協調勞動,這種勞動形式叫作協作。……在這里,結合勞動的效果要么是個人勞動根本不可能達到的,要么只能在長得多的時間內,或者只能在很小的規模上達到。這里的問題不僅是通過協作提高了個人的生產力,而且是創造了一種生產力,這種生產力本身必然是集體力”[2]。
從馬克思關于“協作”的內涵界定中可以得出,協作是一個“生產過程”,是相互聯系的同一生產過程或者是不同的生產過程。產學合作從本質而言,也是一種“生產過程”,是知識和技術的生產并運用的過程。產學合作既可以是知識和技術的雙向轉移,也可以是雙方同時對科技的研發。經由產學合作生產過程生產出來的“產品”由企業投入到市場,在資本主義社會,這種產品是為了賺取剩余價值;在社會主義社會,這種產品是為了滿足廣大人民群眾的消費需求,即使用價值。總體說來,產學合作的產品通常是企業核心競爭力的外在表現,是價值實現的載體,是企業創新的集中體現。這種創新通常會帶來企業的個別勞動時間低于社會必要勞動時間,從而為企業帶來較大的利潤。從社會整體而言,這種創新有時甚至會帶來生產方式的變革,極大地促進生產力的發展。
在馬克思“協作”的內涵界定中,“計劃”是另一個關鍵性詞語。馬克思指出,“一切規模較大的直接社會勞動或共同勞動,都或多或少地需要指揮,以協調個人的活動,并執行生產總體的運動”[2]367。這也就是說,“計劃”一詞本身就具有管理思想的存在,實際上馬克思很早就已經意識到協作中是需要管理、需要指揮的。產學合作中,根據勞動對象的性質,要么是單方管理,要么是產學雙方共同管理以協調產學合作中的各個環節和各種矛盾。馬克思協作的概念是在“生產過程中”定義的,因此本身就是一個動態的概念,這與蒂斯(Teece)[3]提出的動態能力或是動態管理能力有異曲同工之妙。根據蒂斯關于動態能力的定義,可以把產學合作動態管理能力定義為,產學合作主體對各自內外部具有競爭優勢的資源進行整合或配置以適應不斷變化的外部環境的能力。由此可見,依照馬克思的定義,產學合作的本質是一種生產力,這種生產力靠單個勞動或單個組織是很難實現的。很多國家似乎都已認識到這種“新的生產力”的重要性,在美國、日本、新加坡和歐洲各國,產學合作都有著實質性的增加,并且對本國創新活動及經濟的發展起到了巨大的作用。產學合作已被廣泛認為是提升企業創新能力的重要因素[4],是發展創新型國家的關鍵。企業和大學已經成為國家創新體系的主要參與者,產學間知識的廣泛轉移影響著國家創新體系的發展[5]。這也就是說,產學合作創造的“集體力”在當今世界的作用不可忽視,是“協作”的進一步發展及表現形式,本身就是一種生產力。
二、產學合作的原因
在《資本論》中,馬克思依次分析了簡單協作、工場手工業時期及工廠(機器)時期的協作。馬克思指出,“許多力量融合為一個總的力量而產生的新力量”[2]362,這表明協作生產力產生的根源在于“結合勞動”。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特點就是同一個資本同時雇傭較多的工人。“較多的工人在同一時間、同一空間,為了生產同種商品,在同一資本家的指揮下工作,這在歷史上和邏輯上都是資本主義生產的特點”[2]358。在簡單協作的生產過程中,“雖然協作的簡單形態本身表現為同它的更發展的形式并存的一種特殊形式,協作仍然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基本形式”[2]372。這表明簡單協作形態能夠形成的原因就在于同一資本雇用了較多的工人,換句話說,只有較多的工人或人的集合才有可能產生簡單協作。到了工場手工業時期,協作也發生了一定程度的變化,“一方面,它以不同種的獨立手工業的結合為出發點,這些手工業非獨立化和片面化到了這種程度,以致它們在同一個商品的生產過程中成為只是互相補充的局部操作。另一方面,工場手工業以同種手工業者的協作為出發點,它把這種個人手工業分成各種不同的特殊操作,使之孤立,并且獨立化到這種程度,以致每一種操作成為特殊工人的專門職能”[2]375。這也就是說,工場手工業時期的協作逐漸演變為以分工為基礎,“分工的產生導致了勞動工具的分化和勞動工具的專門化,這是工場手工業的特征”[2]378,但工人依舊是生產的主體,勞動資料的運動仍然以工人為出發點。但到工廠時期,卻發生了本質上的變化,生產過程演變成為工人跟隨勞動資料的運動。這種根本性的轉變表現在,協作是以勞動資料技術體系上的分工為基礎,工人已經成為機器的附屬物,正如馬克思所說,大工業階段“勞動過程中的協助性質,現在成了由勞動資料本身的性質所決定的技術上的必要了”[2]423。通過上述馬克思對不同時期協作的分析可以發現,只有人的集合或“結合”才會產生協作,才會產生新的力量,單靠生產資料本身是無法產生協作的。在資本主義社會,協作的異化會提高勞動生產率,但這種勞動效率的提高是以工人成為機器的附屬物為前提,是為資本服務的,是奉獻給資本的免費午餐;勞動者也只是赤裸裸地變為可變資本,無法享有這種由于協作而帶來生產效率提高所惠及的產品。
知識經濟的今天,產學合作更集中于新科技的研究和開發,以突破性創新為根本目標[6]。產學合作演變的根本原因是由創新或開放式創新的本質所決定。開放式創新是有目的使用知識的流入及流出以加速內部創新、擴大外部市場的過程。總體說來,開放式創新有兩個特點,一是滲透式的創新流程,二是企業與外部環境的互動。開放式創新就是要把外部創新資源引入企業內部并進行商業化。換句話說,開放式創新的本質必然要求企業與外部“有計劃”地互動,以尋找外部的創新性資源。大學是知識儲備的地方,是創新的源泉,其所生產和儲蓄的知識恰好是企業所需的外部創新資源。大學的這些有益知識可以推動企業創新的發展,進而促進經濟和社會的發展。因此,大學是創新的發源地,在創新的發展進程中發揮著不可替代的作用。20世紀90年代,美國產學合作取得了較大成功,產生了廣泛的示范效應。部分國家和地區都在參考美國的成功實踐,把大學定義為創新體系中的關鍵部門,積極建立本國的創新激勵體系[7]。有的學者認為,產學合作產生的直接原因是產學雙方主體面臨的壓力所造成的。企業所面臨的壓力主要包括快速的科技發展、更短的產品周期、全球性競爭加劇所帶來的環境變化[8]。大學所面臨的主要壓力有不斷增加的新知識、成本上升的變化及資金問題,這些問題對大學產生了巨大的資源壓力,迫使大學與企業合作。另外,大學還面臨要成為經濟增長引擎的社會壓力。這些壓力不斷刺激產學雙方主體開展產學合作的意愿,這種產學活動的展開客觀上也會不斷提升全社會的創新能力及經濟競爭力[9]。
此外必須注意的是,產學合作的形成除了上述原因外,也需要一定的物質基礎。馬克思指出,“協作工人的人數或協作的規模,首先取決于單個資本家支付多大資本量來購買勞動力”[2]366,“較大量的生產資料集聚在單個資本家手中,是雇傭工人進行協作的物質條件,而且協作的范圍或生產的規模取決于這種集聚的程度。”[2]367-369這表明,協作或者說產學合作能夠形成的物質基礎之一是企業必須具有大量的資本。一方面是由于復雜勞動有著更高的價值,另一方面是由于創新或產學合作本身就具有不確定性,創新生產過程本身就需要大量的資本。物質基礎之二是復雜勞動愿意并能夠參與到產學合作中去,這與物質基礎一相比更為重要。只有具備了這兩個物質基礎,產學合作才有可能形成。
三、產學合作的特點
產學合作的一個特點是會帶來生產資料使用方面的節約。產學合作中“生產資料使用方面的這種節約,只是由于許多人在勞動過程中共同消費它們”[2]361。也就是說,在產學合作中由于復雜勞動的協作會產生生產資料如研究儀器、設備、材料等方面的節約,這種節約一方面會相對減少生產資料對最終產品的價值轉移,另一方面會改變產品中資本不變組成部分和可變組成部分的價值比例關系。
產學合作的另外一個特點是大學的研究成果太過于“胚胎化”,需要后續的進一步研發。據調查,產學合作中大多數大學的研究成果都處于概念和產品的原型上,能夠馬上進行商業化運作的只占12.3%[10]。這也就意味著,由于大學的創新成果太過于“胚胎化”,很難順利地整合到企業內部、真正成為企業創新的直接推動力,大學的創新都需要進一步研發才能具有實用性。
四、我國產學合作的特質
我國的產學合作與資本主義有著不同的特質。在資本主義社會,“一旦從屬于資本的勞動變為協作勞動,這種管理、監督和調節的職能就成為資本的職能。資本家的管理不僅是一種由社會勞動過程的性質產生并屬于社會勞動過程的特殊職能,它同時也是剝削社會勞動過程的職能,因而也是由剝削者和他所剝削的原料之間不可避免的對抗決定的。如果說資本主義的管理就其內容來說是二重的,那是因為他所管理的生產過程本身具有二重性:一方面是制造產品的社會勞動過程,另一方面是資本的價值增殖過程,這樣,資本主義的管理就其形式來說是專制的”[10]367-369。這也就是說,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決定了必然是勞動從屬于資本,因此,產學合作的生產關系是不平等的生產關系,是帶有剝削性質的生產關系,勞動的管理異化成為資本的職能。
在我國的產學合作中,勞動或者說復雜勞動至少和資本之間是平等的生產關系,產學合作的管理過程體現了復雜勞動和資本自由意志相結合的過程,中間的調節、管理等職能是勞動和資本平等溝通、協調的體現。產學合作的管理是一種社會化生產的過程,也是體現“創新是引領發展的第一動力”的過程。在這樣一個過程中,與資本主義不同,復雜勞動者的技能也會得到提升,體現了人的充分發展。更為重要的是,在這個生產過程中,復雜勞動并不在資本的支配之下,也要參與剩余價值的分配。因此,我國的產學合作就其管理形式而言是民主的,是雙方意志的充分體現。
關于產學合作創新體系的建設,我國出臺了一系列重要文件,如《國家中長期科學和技術發展規劃綱要(2006—2020年)》指出,我國國家創新體系的重點和特色是建設以企業為主體、產學研相結合的技術創新體系。因為只有以企業為創新主體,才能堅持技術創新的市場導向,有效整合產學研的力量,切實增強國家競爭力。2015年3月,《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深化體制機制改革加快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的若干意見》提出,要完善企業為主體的產業技術創新機制,市場導向明確的科技項目由企業牽頭、政府引導、聯合高等學校和科研院所實施。鼓勵構建以企業為主導、產學研合作的產業技術創新戰略聯盟。2015年10月,《中共中央關于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三個五年規劃的建議》又提出,要強化企業創新的主體地位和主導作用,支持創新型領軍企業和科技型中小企業的形成和發展。從上述的這些重要文件可以得出,我國產學合作技術創新體系的特點是以企業為主體。但現實情況是,在我國的創新體系中,企業的研發能力過弱。根據《中國科技統計年鑒》的數據顯示,2004年一定規模以上有研發活動的工業企業比例為6.2%,到2012年僅上升為13.7%。我國大部分企業都沒有足夠的研發能力,如果僅靠企業自身研發,很難解決復雜的技術問題。另外,這樣一種過弱的研發能力也很難使企業從外部獲取創新資源,把大學研究成果商業化。就我國企業創新現狀而言,企業無法單打獨斗,企業必須積極參與產學合作以彌補自身科研能力較弱的缺陷。也就是說,在產學合作的過程中,企業要把外部大學的創新資源很好地整合到企業內部,充分發揮大學作為創新源泉的作用。在這樣一個過程中,產學合作雙方的協作和溝通尤為重要。
五、產學合作的利益分配
“雖然協作的簡單形態本身表現為同它的更發展的形式并存的一種特殊形式,協作仍然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基本形式”[2]372,“資本主義的協作形式一開始就以出賣自己的勞動力給資本的自由雇傭工人為前提”[2]371。這表明在資本主義社會,由于勞動在資本的支配之下,產學合作的利益分配必然是有利于資本的分配,或者說是資本對勞動的無償占有。與此不同,社會主義的產學合作絕對不是復雜勞動出賣給資本的過程,而是復雜勞動與資本有機融合的過程。在這樣一種有機融合中,真正創造價值的只有復雜勞動。產學合作本身是一個非常復雜的生產過程,一方面,在這個過程中會凝結比一般社會產品更多的復雜勞動;另一方面,產學合作產品的個別勞動時間會低于社會必要勞動時間,因此,產品本身就具有更高的價值,產學合作的產品在一定時間內會有較高的利潤。盡管如此,產學合作是在兩個極不相同的世界展開,生產過程極其復雜,大學和企業之間也存在不同的利益、目標、限制和激勵。這些不同會導致產學合作雙方嚴重的沖突、誤解和不信任,進而會減弱雙方參與產學合作的動機及滿意度,降低產學合作的效率[11]。
馬克思認為,“人的奮斗所爭取的一切都同他們的利益有關”,按照這樣一種說法,成功產學合作的充分必要條件就是必須保障產學合作雙方各自適當的利益分配。這是產學合作得以維持的基礎和底板。從本質而言,利益分配指的就是馬克思所說的分配關系,即“所謂的分配關系,是同生產過程的歷史規定的特殊社會形式,以及人們在他們的生活的再生產過程中互相所處的關系相適應的,并且是由這些形式和關系產生的”[12]998。產學合作的普遍發展不得不說是知識經濟的產物,在創新驅動成為發展主題的今天,各個國家都在舉全國之力進行創新。在我國產學合作的過程中,產學雙方主體是獨立、平等、互惠的生產關系,基于這樣一種生產關系,雙方的分配關系就應該是平等、共贏的關系,利益分配時就應該遵循共贏原則、協商原則、彈性原則和滿意度原則。就如同馬克思所指出的一樣,生產關系決定分配關系,“分配關系本質上和生產關系是同一的,是生產關系的反面”[12]993。由于產學合作的生產關系是一種平等的生產關系,是一種合作共贏的生產關系,因此,產學合作的分配關系必然要體現出這樣一種的生產關系。當分配關系不適應于生產關系的發展,兩者矛盾積累到一定程度的時候,必然導致產學合作生產關系的瓦解、產學合作聯盟的解體。
我國處于并將長期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社會生產力水平不是很高,也不是單一的公有制經濟結構。產學合作的利益分配也要按照我國基本的收入分配制度執行。2015年,《中共中央關于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三個五年規劃的建議》指出,“堅持居民收入增長和經濟增長同步、勞動報酬提高和勞動生產率提高同步,持續增加城鄉居民收入”“完善市場評價要素貢獻并按貢獻分配的機制”。馬克思也指出,“勞動生產率不僅取決于勞動者的技藝,而且也取決于他的工具的完善程度”[2]378。因此,在我國的產學合作利益分配的過程中,一方面要考慮復雜勞動的勞動生產率情況,另一方面也要考慮資本對產品的貢獻度情況。只有平衡好兩者的關系,才能構建出合理的產學合作利益分配機制。
(一)產權
產學合作中利益分配的核心是產權的歸屬問題。產權是指以法律的形式保護發明、品牌、設計和創藝。產權實際上是法律層面的用語,財產關系是生產關系的法律表現,“這種具有契約形式的法權關系,是一種反映著經濟關系的意志關系。這種法權關系或意志關系的內容是由這種經濟關系本身所決定的”[13]。這也就是說,生產關系決定產權結構。由于在產學合作的生產過程中,大學主要提供復雜勞動(人力資本),企業主要提供資本,這樣一種平等的生產關系就已經決定了產學合作的產權必定是共同所有。共有產權將會給產學合作雙方提供共同探索產權的壟斷權利,也就是共同控制剩余價值的索取權。這與資本主義社會“奇異的結果”有著本質上的不同——“產權在資本方面辯證地轉化為對他人產品的權利,或者說轉化為對他人勞動的產權,轉化為不支付等價物便占有他人勞動的權利,而在勞動能力方面則辯證地轉化為必須把它本身的勞動或把它本身的產品看作他人財產的義務”[14]。在實踐中處理產權問題時,以下因素必須考慮:雙方提供的資源狀況、研究進行的地點、雙方提供的資金比例、人力資源對研究成果的貢獻等。為了確保產學合作的順利進行,需要建立清晰、透明的產權政策,清晰的利潤分配比例及利益沖突解決方案,明確大學和企業各自的權利和義務。另外,由于美國、日本等發達國家在產學合作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果,因此,借鑒這些發達國家的利益分配方式也有一定的必要性。
盡管在理論上,產學共有專利是最佳選擇,根據我國《專利法》也應該是產學共有產權,然而由于產學合作的復雜性,特別是涉及向第三者轉讓的問題時,在實際的操作中會遇到很多困難,因此,共有專利是次優選擇,有可能的話,企業都希望回避[15]。實證分析發現共有專利的比例與其市場表現呈反向關系[16]。在美國,產學共同研究時,一般都避免產學共有產權,往往是大學擁有專利權,企業可以獲得壟斷實施權或比其他企業有利的一般實施權。在英國的產學實踐中也盡可能回避共有產權,大學可以單獨擁有產權。因為專利權的共有將會阻礙商業化或技術轉移,大學承擔基礎研究的任務往往會同時與幾個企業合作,專利的共有會妨礙大學從事基礎研究。從整體看,英國共有專利的比例從1997年起10年間,大約從32%減少到13%。我國在處理產學合作產權問題時,一方面可以借鑒國外的經驗和做法;另一方面,也要應根據具體情況確定是否需要共有產權。
(二)分配機制
產學合作進行的最普遍方式是技術許可或轉讓,雙方通常在技術許可協議中規定利益的具體分配方式。專利技術許可協議最主要的項目是專利使用費和固定費用[17],具有較高商業價值的協議應該包括專利使用費,具有較低價值的發現協議應該含有固定費用[18]。創新越是“胚胎化”,就越應該在專利協議中規定專利使用費。因此,最佳的技術許可協議不能單靠一次性支付,如固定費用和研究資助基金,還應該包括某種基于產出的支付,如技術使用費。
此外,在實際的利益分配中,大學擁有產權并獲得企業中的股份,企業可以使用大學產權的權利的做法非常普遍。美國技術管理協會(AUTM)早在1995年的報告中就已經提到了這樣的趨勢。股份可以為大學提供獲得企業未來收益的機會,股份使得大學也成為企業主人,與企業形成聯盟,實現共同的商業化目標,與企業一起共同索取剩余價值。大量的證據顯示,大學在進行技術許可時采用的是股權、技術使用費和固定費用的形式[19]。對美國知名的研究型大學調查顯示,23%的技術許可中包含股份。在這些基于股份的協議中,79%包括專利使用費,67%包括一次性使用費[20]。盡管調查的大部分都是以專利使用費為基礎的協議,但對股權使用的趨勢一直在增加。1992年,40%的大學開始使用股權方式,到2000年,這個比例達70%。研究顯示,產學合作經驗豐富的大學更愿意使用股權方式[21]。從長期而言,基于股權的協議比固定費用和專利使用費更能為大學帶來更多利潤[22],即大學會獲得更多的剩余價值。
通過以上論述可以得出,符合我國現階段特點的產學合作分配機制應該有兩個選項,一是產學共有產權,二是大學擁有產權,企業在一定時間內獲得產權的壟斷或非壟斷使用權。對產學合作雙方主體而言,大學獲取剩余價值的最佳方式是股權或技術使用費的比例形式,盡量不要采用一次性支付。
六、產學合作的作用
產學合作對創新意義重大,創新的首要任務是加速產學間知識的轉移和商業化的成功[23],創新也會引起生產方式的變革。“生產方式的變革,在工場手工業中以勞動力為起點,在大工業中以勞動資料為起點”[2]408,在知識經濟中則是以創新為起點。習近平總書記在講話中多次提到了創新的重要性,他指出“創新是引領發展的第一動力。必須把創新擺在國家發展全局的核心位置,不斷推進理論創新、制度創新、科技創新、文化創新等各方面創新,讓創新貫穿黨和國家一切工作,讓創新在全社會蔚然成風。”這表明,我國應該把產學合作放到國家的戰略高度,必須積極以產學合作推動創新的發展。
實際上,我國產學合作的現狀卻并不樂觀。根據中國社會科學院的研究,從基礎研究到產品開發,中國90%的科技成果死亡。根據清華大學和復旦大學等國內20所大學發布的“大學科技成果轉化的探索與實踐”課題研究報告顯示,中國每年產生的6 000至8 000件科技成果中,實現真正意義的成果轉換不到10%。企業往往說大學的研究缺乏實用性,大學往往說企業缺乏長期眼光。產學雙方只有滿足一定利益條件的時候才會產生知識轉移的意愿。這意味著在產學合作的生產過程中,不僅僅是企業,大學也必須參與到剩余價值的分配中,否則大學不會有動機參與產學合作。根統計,中國科研能力的40%集中在大學,30%集中在社會科學院,企業科技能力較弱,創新能力低下,很多企業公司內部沒有設立研究所。由于科研能力發展的不平衡,知識轉移就很難進行。但從另一個角度而言,這樣一種科研能力發展不平衡的現狀也為產學合作提高了一定的客觀條件和必要性。要實現建立以企業為主體產學合作技術創新體系的戰略目標,我國大學就必須在產學合作中發揮創新源泉的重要作用。就如同有學者指出的一樣,除了教學和科研外,大學的“第三任務”—商業化必須對創新有重要貢獻[24]。產學合作會帶來創新,創新會引起生產方式的變革,進而會推動生產力的發展。
歸根到底,產學合作是協作的進一步發展和表現形式,產學合作本身也會產生一種生產力。馬克思說“這種生產力是由協作本身產生的。勞動者在有計劃地同別人共同工作中,擺脫了他的個人局限,并發揮出他的種屬能力”[2]366。在我國經濟新常態和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背景下,大力促進產學合作的發展,以產學合作推進創新及經濟的發展十分必要。產學合作所帶來的生產力在推動科技進步的同時也會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充分實現人的自由。
[1]Bekkers R,Freitas I B.Analysing knowledge transfer channels between universities and industry:To what degree do sectors also matter[J].Research Policy,2008,37(10):1837-1853.
[2]馬克思.資本論: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362.
[3]Teece D J,Pisano G,Shuen A.Dynamic Capabilities and Strategic Management[M]//Dynamic capabilities and strategic management.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9:509-533.
[4]Dyer J H,Kale P,Singh H.When to ally and when to acquire[J].Harvard Business Review,2010,82(7):109-115.
[5]Chen K,Kenney M.Universities/research institutes and regional innovation systems:The cases of Beijing and Shenzhen[J]. World Development,2007,35(6):1056-1074.
[6]Mora-Valentin E M,Montoro-Sanchez A,Guerras-Martin L A.Determining factors in the success of R&D cooperative agreements between firms and research organizations[J].Research Policy,2004,33(1):17-40.
[7]HülsbeckM,LehmannEE,StarneckerA.PerformanceoftechnologytransferofficesinGermany[J].TheJournalofTechnology Transfer,2013,38(3):199-215.
[8]Barnes T,Pashby I,Gibbons A.Effective University-Industry Interaction:A Multi-case Evaluation of Collaborative R&D Projects[J].European Management Journal,2002,20(3):272-285.
[9]Perkmann M,Tartari V,Mckelvey M,et al.Academic engagement and commercialisation:A review of the literature on university-industry relations[J].Research Policy,2013,42(2):423-442.
[10]Thursby J G,Jensen R,Thursby M C.Objectives,characteristics and outcomes of university licensing:A survey of major US universities[J].The Journal of Technology Transfer,2001,26(1-2):59-72.
[11]DasTK,TengB.Betweentrustandcontrol:Developingconfidence in partner cooperation in alliances[J].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1998,23(3):491-512.
[12]馬克思.資本論:第3卷(下)[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998.
[13]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102.
[14]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455.
[15]Hagedoorn J.Sharing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an exploratory study of joint patenting amongst companies[J].Industrial and Corporate Change,2003,12(5):1035-1050.
[16]Belderbos R,Faems D,Leten B,et al.Technological activities and their impact on the financial performance of the firm:Exploitationandexplorationwithinandbetweenfirms[J].JournalofProductInnovationManagement,2010,27(6):869-882.
[17]Macho-Stadler I,Pérez-Castrillo D.Incentives in university technology transfers[J].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Industrial Organization,2010,28(4):362-367.
[18]Macho-StadlerI,Pérez-CastrilloD.Contratsdelicencesetasymétried’information[J].AnnalesDéconomieEtDeStatistique,1991(24):189-208.
[19]Savva N,Taneri N.The Role of Equity,Royalty,and Fixed Fees in Technology Licensing to University Spin-Offs[J]. Management Science,2014,61(6):1323-1343.
[20]Jensen R,Thursby M.Proofs and Prototypes for Sale:The Licensing of University Inventions[J].American Economic Review,2001,91(1):240-259.
[21]Feldman M,Feller I,Bercovitz J,et al.Equity and the technology transfer strategies of American research universities[J]. Management Science,2002,48(1):105-121.
[22]Bray M J,Lee J N.University revenues from technology transfer:Licensing fees vs.equity positions[J].Journal of Business Venturing,2000,15(5):385-392.
[23]Arundel A,Geuna A.Proximity and the use of public science by innovative European firms[J].Economics of Innovation and New Technology,2004,13(6):559-580.
[24]Larédo P,Mustar P,Elgar E.Research and innovation policies in the new global economy an international comparative analysis edited by[J].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2003,41(3):941-942.
Analysis on Industry-University Cooper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olitical Economy
Xu Yuelei
(Institute of Japanese Studies,Liaoning University,Shenyang Liaoning 110036)
Industry-university cooperation is key to promote innovation and development.Therefore,the in-depth study of industry-university cooperation in the context of China’s current level of productivity is not high,the supply side of the structural reform is very important.The use of Marxist theory of political economy,the theory of productivity,production-production relations theory,production relations-distribution theory of the definition of industry-university cooperation,the reasons for the formation of industry-university cooperation,the characteristics of industry-university cooperation.Based on the comprehensive analysis of the role of industry-university cooperation and the role of industry-university cooperation,it is concluded that the industry-university cooperation in China should have different characteristics with the capitalism,and should promote the cooperation and innovation.It is of utmost importance to gradually construct the mechanism of benefits distribution of industry-university cooperation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ndustry-university cooperation;political economy;innovation;benefit distribution Mechanism
F06
A
1674-5450(2017)05-0068-07
【責任編輯:李 菁 責任校對:張立新】
2017-03-27
許悅雷,男,遼寧大連人,遼寧大學副研究員,主要從事政治經濟學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