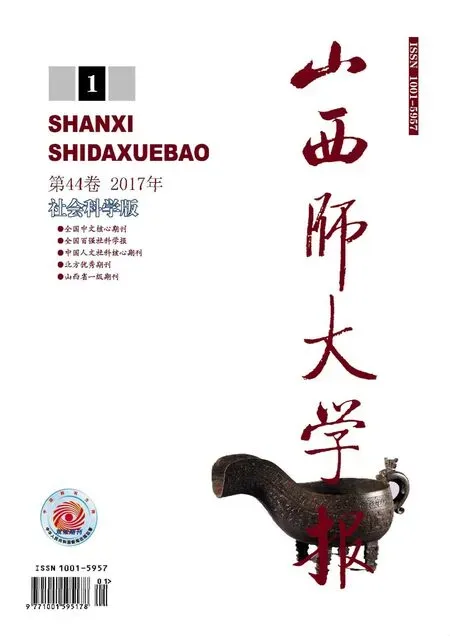反窺“疏離型”幸福的形態變化
——以“獲得感”為詮釋語境
張方玉,楊偉榮
(曲阜師范大學 馬克思主義學院,山東 曲阜 273165)
中國文化中有一個重要的傳統,這個傳統就是求一種境界,這種境界是“即世間而出世間”的。體現在人生幸福方面就是一種幸福智慧,這種幸福智慧著重體現在富有彈性的人生邏輯之中:經世—憤世—厭世—避世—玩世—順世。經世到順世在禮崩樂壞、秩序失衡中產生裂變,疏離情緒隨之產生,但順世到經世又會在安定繁榮的社會和諧中完成統一,彈性智慧也由此顯現。得意時以“用世”,失意時以“用生”,從而使個體得以在各種人生矛盾中應付裕如。如此形成一個完整意義上的“文化機制”,“疏離型”幸福就是在這種文化機制中成長的中國人所特有的幸福形態。伴隨著中國社會由古代農業文明向現代工業文明邁進,“疏離型”幸福經歷了由傳統形態向現代形態的轉變。面對物質文明的飛速發展,人生的幸福、快樂非但沒有隨著物質文明的發展而增加,反倒是成比例失落。“倉廩實”“衣食足”與“識禮節”“知榮辱”并沒有呈現出應有的進階關系,逐物拜金的誘惑,精神世界的失落,一味的物質追逐反而引發了人們對社會的疏離和與幸福的距離。這種疏離和距離也導致人們對幸福的理解出現偏差,無論是曾經的精神超越,還是現在的物質追求,都是人們渴望實現幸福的條件,如今卻轉變為支配、統治人本身的異己力量。這種層次斷裂下的“疏離”也讓幸福變得越來越缺乏“觸摸感”,但這并不意味著幸福的缺失。疏離的幸福形態,或者說是幸福的疏離性質,只是使得“疏離型”幸福作為一種特殊的幸福形式,在當下呈現出了一種不同于以往的幸福氣象。習總書記提出的“獲得感”一詞,是人們在疏離之余重新認識幸福定在的關鍵,也是新時期詮釋幸福的全新語境。其形態變化不是由物質追逐再倒回精神尋求的簡單復歸,而是經過“否定之否定”之后的再次升華。追求“疏離型”幸福的路徑也需要在此基礎上實現一種綜合型的超越。
一、“內向用力”到“外向用力”的轉變
無論是對于個人還是國家社會,追求幸福的基本路徑大致分為內向用力和外向用力兩種。內向用力強調內在精神追求,即通過智識探求增強認識、提高修養以調整自身心態,培養自我德行,提升自己的境界和智慧。中國傳統文化是以道德為本的文化:“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為本。”以“修身為本”即以道德為本。[1]以修身為本的傳統中華文明要求人們內向用力,誕生的自然也是注重精神追求的思想體系和倫理結構。傳統中國人受中國傳統文化滋養,特別是儒、釋、道三位一體的文化結構影響,信仰“天人合一”,追求“成賢成圣”的終極關懷和理想人格。外向用力則注重外在物質索求,這種“物質”既指財產、物資等有形物,也包含權利、榮譽等無形物,即希望通過更多的物質獲取來改善自己的生活狀態。現代工業文明激勵人們外向用力,積極從事物質生產與創造,激勵各種競爭,依靠科技進步與經濟增長來改變具體的生活內容和生活方式。毫無疑問,這是現代化發展的根本標志,是推動古代文明向現代文明過渡的重要力量。在人類文明演化的過程中,就伴隨著幸福追求理念和實現路徑的轉變,即“內向用力”到“外向用力”的轉變。
“統治我們這個龐大的帝國,專靠嚴刑峻法是不可能的,其秘訣在于運用倫理道德的力量使卑下者服從尊上,女人聽男人的吩咐,而未受教育的愚民則以讀書識字的人為楷模。”[2]21正是這一“秘訣”使得中國古代社會只有讀書人才能進入社會頂層階級,而這一頂層精英階級多以孔孟門人自居,尊崇孔孟之道。這就決定了中國古代的社會精英階層大都以成賢成圣為終極關懷和內在目標,“修身成圣”成為他們內向用力以實現超越的基本方法,具體的實現路徑就是“窮理盡性以至于命”。而“窮理盡性”的一個關鍵要訣就是無欲,“無欲則靜虛,靜虛則明,明則通”,[3]260因此,修身就是要摒棄一切不合天理的欲望。中華文明中這一“內向用力”的傾向,有效約束了人們的物質貪欲和征服性技術的發展,且承繼了幾千年。與此迥異的西方文明以“外向用力”為傾向,逐步發展為近代工業文明,致力于財富的創造和征服欲的滿足,當這種征服欲擴展到中國的時候,則讓中國人看到了西方工業文明的強大,也激發了中國人內心的向往,加之擺脫民族危機的歷史重任,中國人開始了由“內向用力”到“外向用力”的歷史性轉變。這一轉變經歷了從器物到制度,再到觀念的深入過程。從西方列強入侵的鴉片戰爭開始,中國人就不斷被近代工業文明成果刺激著神經,船堅炮利輕而易舉攻破清政府的防線,在西方列強的武力威逼和東漸西學的逐級滲透下,以內圣外王之道為意識形態核心的傳統文化失去了其“內向用力”整合社會秩序的作用。面對東西方發展水平的巨大差異,中國不得不進行痛苦的轉型,中國人希望通過借鑒學習來擺脫民族落后與危機,并以此填補內心的缺憾和差距。
對近代中國來說,這種轉變不算是一個民族內部自然和諧的文化發展,而是在外部暴力壓制下的強迫性改造。這一轉變是中國人面臨亡國滅種危機下的救亡圖存行為,因此,必然會牽動人們深層次的民族情結,導致情感、信念、實踐行為等一系列方式的變化。而每一個部分的改變都可能與固有文化結構存在一定沖突,這種沖突會因為現實社會危機與民族矛盾的加劇,使得客觀現實與主觀情感之間產生背離,表現在個人的社會理想方面,就是對人對事、甚至整個社會的疏離。這種結構型的轉變在中國近代的傳統舊式文人身上有著深刻的體現。20世紀初是中國知識分子由傳統型向現代型轉變的時期,他們的思想中或多或少都會呈現出疏離的性質與特點,這是“內向用力”到“外向用力”轉變導致的必然結果。盡管新中國的成立足以讓所有人歡欣鼓舞,但社會轉型仍在繼續,影響也隨之不斷擴大。
從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經過改革開放到今天,中國人用了半個多世紀的時間,完成了從以道德為本的文化到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文化轉變,這一轉變不但改變了社會經濟和政治結構,也引起了國民價值觀的改變,人們由傳統意義上的精神價值至上向現代理念的物質利益推崇轉變。而夾雜在經濟體制和政治體制改革中的這種“價值觀的改變”,在西方所謂“物質主義現代化”的影響下也悄然發生了“裂變”。這一裂變的過程表現為,一部分人被欲望的強大力量所驅使,由對物質價值的合理重視激化為對物質利益的瘋狂追逐。這種欲望的洪流不僅流向物質領域,還注入人們的精神世界。有錢人越來越多,可抑郁癥患者也越來越多。誰都不能否認中國人的生活水平和質量越來越高,同樣,誰也都不敢斷言中國人過得越來越幸福。內在的失落與空虛作為一種信號,顯露出人們對“外向用力”路徑已漸生疏離,但人們對幸福生活的追求卻不會停止,于是人們開始重新思索傳統文化孕育的“內向用力”在現代化的“外向用力”過程中該有的地位和價值。
二、“外向用力”到“內向用力”的復歸
20世紀以來,許多經濟學家利用各種統計和計算方法研究各個國家人們的幸福感,他們得出一個所謂的悖論:“當一些國家在物質上變得更加富裕,也變得更加健康時,其平均的幸福感水平并不會提高。”[4]18現代化所倡導的“直觀性真理”開始被越來越多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人們所質疑:科技的進步、財富的增長使得繁重的手工作業和體力勞動被大量的機器或技術載體所替代,為什么現代人卻沒有從前幸福?其實這一結論在哲學領域并不算什么悖論,古代哲學家們早就揭示過人的物質生活質量與人的精神苦樂之間的關系。人不同于動物的一個重要之處在于,人不會只追求肉體感官的滿足和愉悅,人會有物質以外的精神追求與享受,人是一種會追求無限意義的有限存在,因為人會受文化的熏陶成為意義價值的追求者,或者說是一種文化動物,而不再是單純的自然動物。這就決定了一個人的精神和信仰會影響甚至決定他的苦樂感受。子曰:“賢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論語·雍也》)自我成長訴求和生活質量的表達開始受到普遍的注意和重視,西方也由此提出了“后物質主義”的概念。許多西方學者都認同,現代化這一曾經產生巨大影響的概念已經開始逐漸淡出于時尚,但“修正版”的現代化概念需要繼續發揮重要作用。“修正版”的現代化概念其實就是“后物質主義”的概念,這標志著西方發達國家的主流價值觀開始出現由物質主義向后物質主義的轉變。這似乎是一種由“外向用力”到“內向用力”的實質性復歸,但在清華大學哲學系的盧風教授看來,這只是一種形式上的復歸,實質上人們并沒有認清物質主義和后物質主義的實質。因為過于樂觀地預計了現代化的后果,所以也就過于簡單地判斷了人類由物質主義向后物質主義的超越。[5]言外之意就是,所謂的物質生活簡樸的后物質主義并沒有超越物質主義的價值觀,這只能算是物質主義的一種新發展或新形態。
事實也的確如此,當下物質主義仍是許多人所謂的對“人生意義”的深刻理解,因為他們認為自己也是在追求更高的生活質量的,消費主義人生觀和價值觀就是一例。但這一價值觀已經不同于以往的消費主義,它的確被附加了許多后物質主義因素。這著重體現在現代人的消費態度或者說消費目的,在很大程度上已經不是為了滿足自身純粹的生理需要,而是突出在表現自我或展現自我價值上。人們因為可以消費不同等級的商品,或者享受不同檔次的服務,而被分屬到不同的階級或階層。人們所謂的自我價值和自我實現活動,就是通過這些檔次和品牌加以標識。這相當于告訴每一個人,只有多賺錢、占有更多的財富,才能獲得更多的標簽和肯定。但不要忘記,激勵人們永不休止地追逐金錢和財富的同時,也在消泯著“知足常樂”這一最簡單而最可靠的幸福道理。享樂主義的實質是造成對幸福誤解的最直接原因。
長期以來對“終極關懷”和“人生智慧”的領悟,使中國人更清楚地認識到物質生活享受與精神生活幸福之間的關系。鄧小平也正是對此看得清楚,所以他最早指出,要在特別注意建設物質文明的同時,注重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由此可見,從“以道德為本”到“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價值觀轉變,并不是要道德“退居二線”,相反,是要求更重視道德。因為,如果人的欲望不能受到合理的規范和正確的引導,那么物質利益的追求必然會在物質領域和精神領域同時掀起“波瀾”,這一波瀾的最終結果就是物欲的釋放變得徹底而肆無忌憚,而這也是精神文明全面崩潰的邊緣。因此,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如何協調發展一直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重要方面。尤其是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不斷發展,如何以超越的人文精神去規范和調控物質欲望的追求,充分體現著中國人的智慧。因為這種調控既不是宏觀的,也不屬于微觀的,既不是強制性的措施,也不像“看不見的手”。作為一種“軟調控”,我們需要將人的欲望轉化成經濟建設的動力和成就,這種成就是特殊意義上的最高實在,但卻不是普遍意義上的“終極實在”。中國古代倡導的“終極關懷”是古代中國人所追求的人生終極意義,然而卻對現實的“最高實在”缺乏合理的認識,這是由一定歷史條件造成的歷史局限性。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現代化建設不能走西方“破裂性”現代化的老路,要體現傳統中華文明的“連續性”,這一“連續性”體現在經濟發展的可持續性以及精神追求的極高明狀態中。體現并堅持這種“連續性”才能使“外向用力”到“內向用力”的幸福追求路徑不至于成為一種簡單機械的“倒退”,而是一種以走向未來為目的的“復歸”。
三、“獲得感”語境下的內外超越
(一)“內外兼修”的人生智慧。傳統中國人“內向用力”的基本方法即是儒家所倡導的修身,佛家講的修行,道家則稱為修養。無論是修身、修行還是修養,僅僅是方式方法的差異而已,本質上都是對個體自我境界的提升。這種提升不單是格物致知的過程,更是生命智慧和生活智慧基礎上人生智慧的凝練與升華。對于個體來說,生命智慧是一種建立合理的生命秩序、賦予生命以自力更生的旺盛生命力的智慧。對于社會和國家來說,生活智慧是一種建立合理社會關系、賦予世俗生活以超越性價值意義的智慧。[6]187現代社會的進步與人際關系的發展,不會允許一個人隨便“隱于世外、超脫自在”,如此獨有生命智慧而拋卻生活智慧并不現實,也不應該。因為這不是追尋個人幸福的最佳方式,個人幸福的獲得是絕對不可能脫離社會、集體而存在的。就算得到,也會轉瞬即逝,不能長久,不能算是真正的幸福,最終必然會由“出世轉入即世”。當然也不可能飽享生活智慧而缺失生命智慧,一個缺乏真正的安身立命智慧的人不會有多幸福,因此,追求幸福生活的根本是要實現生活智慧與生命智慧的有機統一,其現實的實現方式就是在“內向用力”和“外向用力”之間保持一種平衡。歷史已經證明,一味地“內向用力”或者一味地“外向用力”,都不可能真正幸福。如果說,科技進步和經濟增長的“外向用力”改變了我們生活的具體內容,就認為人們的幸福感會隨之不斷增加,這是不準確的。因為,它在消除某一特定生活內容的痛苦與失落的同時,人們又會產生其他種種的無聊與寂寞。就像空調能解除人們夏季的炎熱難耐,卻又會產生身體長時間限居室內的苦惱和積聚濕熱的苦痛。同樣地,如果說人生必然苦樂相伴,那么認為修身、修行、修養等“內向用力”的方式必然增加一個人的快樂也是沒有道理的。快樂不能等同于幸福,提升自我境界、增強自我智慧只是讓一個人保持一種更和諧的生命狀態,這種狀態會使人的心情對于外界造成的紛擾做出“適當的回應”,不會隨意趨向于任何一個極端。這是一個人生活幸福的保證,卻不是一個人增加快樂的砝碼。因此,現代人的生活就是用一種“內外兼修”的智慧實現一種“雙向用力”的平衡。
(二)“獲得感”指向的幸福調節。無論你是知識分子,還是工人、農民,都是作為一名社會成員的社會性個體而存在。所以你就必須參與到社會協作與競爭中去,整體的協作與激烈的競爭要求你必須要具備較強的工作能力和交際能力,這樣你才能保證有一份穩定的工作和合法的收入,才能在社會群體中生存下去。這是作為一個生存個體所必須具有的“外向用力”的能力。然而,一個人不可能只作為一個“社會普遍物”而存在,每個人又都是一個具有獨特性的個體,內心會有外界他人所無法觸及和不可理解的東西,即自身作為有限性個體的無限性追求。人永遠有欲求,卻不可能你想要什么就會有什么,這個社會或他人也不可能永遠按照你所希望的那樣存在和發展,這就決定了在追求的實現過程中必然會遭受挫折、承受委屈、甚至接受“不公”。[7]如果你缺乏應對外在的一種積極的生活態度和高明的人生狀態,那么,產生生活乏味、意義失落甚至社會疏離的情緒也就在所難免。如果這時候一個國家或一個社會也不能幫助社會成員獲得一種張力來保持“內向用力”與“外向用力”之間的平衡,那么這種幸福缺失感與層次斷裂感就會愈演愈烈。當人民生活貧困、社會物質匱乏時,就必須激勵人們積極“外向用力”,從事社會生產,創造物質財富,改善物質生活條件。而當社會財富不斷增加、人們生活水平不斷增長的時候,唯利是圖、為富不仁、處窮不義等社會現象的出現就會激化社會矛盾,這種時期注重“內向用力”的人本來就少,如果國家和社會還一味鼓勵和崇尚“外向用力”,惡就會變成“理所當然”,善則成了“背道而馳”。人們的疏離激化到一定程度,社會自然也無法保持穩定與和諧。
中國社會正處在一個混合期,也是一個過渡期。人們已經強烈感受到社會普遍“外向用力”所帶來的經濟增長和財富積累,但同時,人們也看到了經濟增長速度過快造成的財富積累比例失衡。失衡的任何一方都對幸福的認識產生了偏差,或者被金錢刺激、麻痹了神經,把實體快樂當作幸福,或者被忙碌消磨、抽離了感官,視幸福為虛幻。無論哪一種都是對幸福的誤解,能夠被分類和量化的感官快樂不同于幸福,它讓人產生的是刺激感和愉悅感,這或許會發展成為一種滿足感,但絕不會成為一種“獲得感”,因為過于短暫,轉瞬即逝。被虛化和抽象的幸福失去了觸摸感,就等于幸福失去了定在,無法體現“獲得感”的幸福同樣不是真正的幸福。這是“外向用力”與“內向用力”嚴重不平衡導致的兩種不同性質的幸福“假象”。“獲得感”的意義可以幫助人們消除這種假象,重新感受幸福的實在。通過感受這種實在來引導人們保持“內外平衡用力”,這是國家角度對社會與個人發展完善的一種平衡,是一種“軟調控”的功能發揮,也是國家保障發展穩定、人民幸福和諧的一種方式。習近平總書記講人民群眾的“獲得感”是改革的“試金石”,要讓人民群眾有更多的獲得感。雖然在改革的前提下定義,但“獲得”的對象已然超出了物質財富的范疇,包含精神境界的豐富和提升。“獲得”是增加“獲得感”的前提,卻不是“獲得感”的關鍵。因為“獲得感”雖然以實際獲得為基礎,但又不是等量的,有時甚至不是正相關的。“意義獲得感”與“實在獲得感”共同構成了“獲得感”的完整內容。可擁有、可支配、現實可見,是“實在獲得感”的特點。可回味、可預見、深切可感則突出了“意義獲得感”的不同。沒有獲得,“獲得感”當然是一句空話,但也絕非獲得越多,“獲得感”就越強。以羅納德·英格爾哈特為代表的許多西方學者都認同滿足感的邊際效用遞減原理,正如吃第一口美食時候的滿足感很高,但隨著繼續吃,滿足感就會遞減,有的學者稱其為“饜足效應”。這就決定了無論獲得的對象是什么,“獲得感”不會一直隨著量化的增加而不斷增強。“意義獲得感”的補充可以緩和這種物質“饜足感”,從而使人們對“獲得感”的把握具有了實在性和超越性的雙重意義。這就必然指向“內向用力”和“外向用力”的雙向平衡,從而發揮國家和社會層面對幸福的調節作用。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成就不斷,過程突顯出利益與競爭角色的極端重要性。因為催生各種勞動與創新的精神動力已經由早期的“社會主義覺悟”變成了當下的“物質主義追求”。這種物質主義的精神和追求是“外向用力”的力量擴展,是推動現代社會物質繁榮的重要動力。但這種擴展力量不是極度無限的,因為滿足人們消費心理的物質性財富和征服性技術,并沒有使人們的生活越來越幸福,反而造成了越來越大的生活落差和意義缺失,并逐漸發展為一種個體的疏離情緒和社會的疏離氛圍。但絕不可以說現代性的信仰就注定缺失幸福,積極尋找“內向用力”的思想升華和精神填充是獲得充實感與獲得感的精神路徑。如果將積極改變現狀、追求幸福美好的努力過程稱為超越,那么,努力平衡“內向用力”和“外向用力”的“內外兼修”智慧就是一種內外超越,這一幸福追尋過程就可以稱之為“疏離型”幸福的實現。由古代農業文明向現代工業文明的轉變需要“疏離型”幸福的實現,按照盧風教授的觀點,由現代工業文明向未來生態文明的超越,同樣也需要“疏離型”幸福的實現。就當下的中國來講,這一幸福的實現尚處在一個過渡的進程之中,而“獲得感”的提出和把握是推動這一進程發展的重要理念,這也讓這一時期的“疏離型”幸福呈現出具有中國特色與傳統人文精神的形態。
[1] 盧風.當代中國人價值觀的改變與經濟發展[J]吉首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1997,(1).
[2] 黃仁宇.萬歷十五年[M].北京:中華書局,1982.
[3] 朱貽庭.中國傳統倫理思想史[M].上海: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15.
[4] 卡蘿爾·格雷厄姆.這個世界幸福嗎[M].施俊琦譯.北京:機械工業出版社,2012.
[5] 盧風.超越物質主義[J].清華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6,(4).
[6] 樊浩.倫理精神的價值生態[M].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1.
[7] 盧風.幸福、修身與內向超越[J].唐都學刊,2016,(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