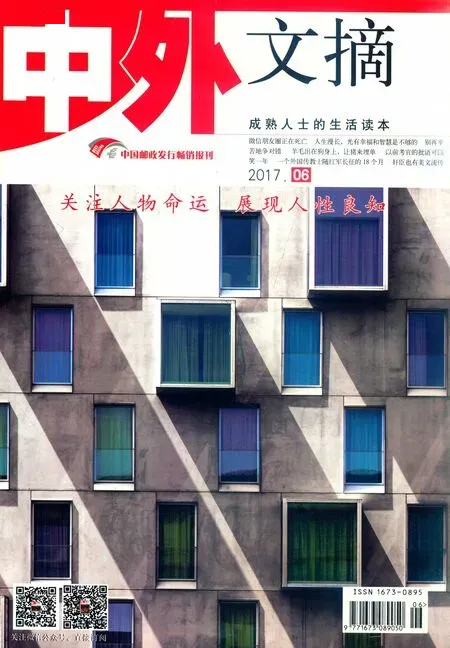夜型人如何自我辯護
□ 張 靜
夜型人如何自我辯護
□ 張 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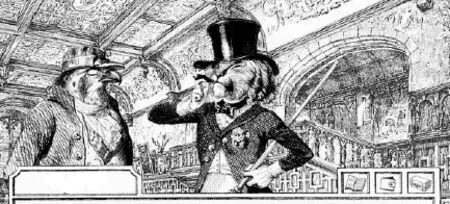
萬達集團董事長王健林11月30日的行程被公布后,許多年輕人開始反思自己荒廢的青春。
4點起床,4點15分至5點健身,接著是半小時早餐,7點已經從雅加達飛往海口。
按照工作時間分類法,王健林是不折不扣的“晨型人”。在傳統看法中,這種生活方式往往與美德掛鉤。
美國建國元勛本杰明·富蘭克林有句名言:
Early to bed and early to rise,makes a man healthy,wealthy,and wise.
早睡早起使人健康、富裕又明智。
富蘭克林在政治、物理、出版等多領域都頗有建樹,這位發際線高企的智者認為,早睡早起可以改善人的精神面貌,甚至改變性格。
中國思想家朱熹也在《朱子家訓》里吩咐:黎明即起,灑掃庭除,要內外整潔,既昏便息,關鎖門戶,必親自檢點。
相比之下,晚睡晚起的“夜型人”——俗稱“夜貓子”,經常面臨“自制力缺乏”“欲望過于強盛”等指控。
晚睡不總是沉溺于欲望
一種常見的說法是,夜型人大多道德墮落。夏商朝桀紂兩位暴君,徹夜沉溺于酒色,最終亡了國。白居易則用“春宵苦短日高起,從此君王不早朝”的詩說明,唐玄宗因貪戀女色晚睡,影響了工作。
和古代君王的聲色犬馬不同,如今許多年輕的夜貓子不是重度酗酒者,也并非性誘惑過多而不愿早睡。畢竟“賢者時間”是入睡的絕佳時刻。事實上,不少晚睡的年輕人都是單身。
晚睡并非對工作不負責
有傳統觀念認為,晚睡將導致次日工作效率低下。對于遵循常規社會工作時間的人來說,的確有道理。
不過在現代社會,部分工種的工作時間富有彈性,從事這些工作的人晚睡的幾率更高,編劇、藝人、記者和程序員當中就有不少夜貓子。有些工種則必須早起,早班出租車司機、中小學教師等工作,多由晨型人把持。
在富蘭克林時代,晚睡的人要耗費蠟燭或燈油,成本昂貴。如今電費顯然不成問題,如果工作時間自由,白天和夜晚開工并沒有優劣之分。
《紐約客》曾報道過一系列關于睡眠與道德感的研究,研究者分別在早晨和晚上測試人們考試作弊的幾率,結果顯示,早晨作弊的人更少。然而經過更嚴密的控制變量后,喬治城大學Sunita Sah教授發現,的確早上作弊的人少,但那是在被調查者原本就是晨型人的前提下;而夜型人在晚上道德感更強,也更少作弊。
熬夜一度是美德
不少領導人是夜型人,毛澤東要靠安眠藥入睡,一般午后才起床。熬夜是他年輕時養成的習慣。小學語文課文《八角樓上的燈光》里,描寫了他在井岡山革命時期,深夜挑燈寫作的場景。
周恩來的晚睡也被寫入教科書,“公雞喔喔喔地叫明了,周總理又工作了整整一夜。”作家何其芳感嘆,“這就是我們的總理。他是多么勞苦!”
不過,依靠藥物的睡眠質量不高,長期睡眠時間過短有害健康。習近平總書記就告誡年輕干部不要熬夜:
“那個時候我年輕想辦好事,差不多一個月大病一場。為什么呢?老熬夜。經常是通宵達旦干。后來最后感覺到不行,這么干也長不了。先把自己的心態擺順了,內在有激情,外在還是要從容不迫。”
至于藝術家和創作者,大可以在飽睡的基礎上,靈活選擇工作時間。
夜型人可能與生俱來
的確有些人夜晚生龍活虎,白天昏昏欲睡,朝九晚五的上下班制度對他們而言簡直是噩夢。有種說法是,睡眠類型與生俱來。
時間生物學教授Till Roenneberg認為,每個人都有自己獨特的睡眠類型,由體內固有的生物鐘控制,不能單純靠意志力調節。如果持續違背生物時鐘,可能增加患肥胖癥、糖尿病等疾病的風險,并且容易抑郁。
“基因說”似乎是為夜型人的最佳辯白。然而,沒有跡象表明有哪個想不開的基因會控制人們的睡眠時間。最直接的反例是,老子是晨型人,兒子卻是夜型人。
比如早晨四點起床的王健林,有個中午起床的兒子。從王思聰微博來看,下午一點以后,才是他發微博的正常時間。
(摘自《博客天下》2016年第1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