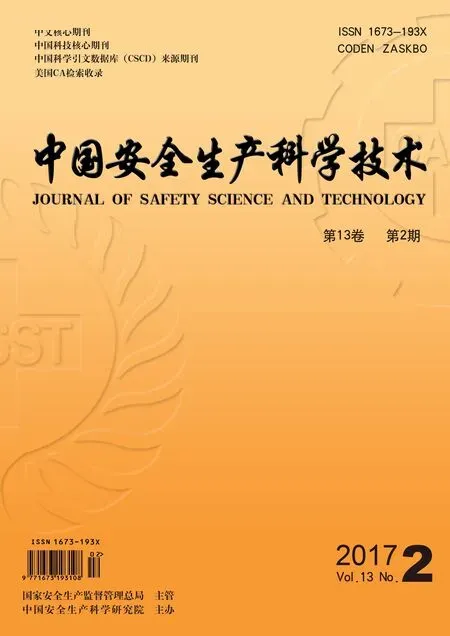管理者的威權領導風格對礦工安全行為的影響研究*
王 丹,宮晶晶
(遼寧工程技術大學 工商管理學院,遼寧 葫蘆島 125105)
0 引言
安全問題一直是困擾我國煤礦經濟發展的重要問題。2016年5月安監局等8個部門下發《關于加強全社會安全生產宣傳教育工作的意見》,指出90%以上的事故是由人的不安全行為造成的,而礦工不安全行為的多發性和難以預防性更是煤礦生產事故發生的重要致因因素。因此,礦工不安全行為管理是預防和控制煤礦生產事故的根本途徑,也成為職業安全領域的熱點研究問題之一。管理者作為企業制度與安全文化的傳導者,其言行對基層礦工有著深刻的影響,管理者能通過改善領導風格而改變員工的工作行為[1],合適的領導風格能夠激勵員工更加努力自覺地提升安全績效[2]。可見,在井下工作情景中,為使礦工安全工作行為融入到企業運行中,管理者領導風格對礦工工作行為的影響研究顯得尤為重要。
由于領導風格是鑲嵌在特定文化中的現象,于是,鄭伯塤結合華人組織特點提出家長式領導,包含威權領導、德行領導與仁慈領導三個維度[3],其中威權領導作為家長式領導最具文化特色的領導風格,是中國企業領導風格的基礎和核心。煤礦企業管理人員大多出身于工科,往往忽視礦工行為方面的柔性管理,現場調研也發現了煤礦生產現場管理者的威權領導風格表現明顯[4],為此重點研究威權領導風格。
管理者是下屬形成關系自我概念的重要人物之一[5],下屬對管理者的認同影響著下屬的工作效率和組織運行效能[6],因而下屬對管理者的認同成為影響下屬態度和行為的重要因素。但是煤礦企業礦工對管理者的認同在二者的工作互動過程中發揮的影響效果沒有得到學者的關注。同時,學者在深入研究后發現,在日常管理中存在著面對同一種領導風格不同的下屬會產生不同反應的現象。于是,2007年Kark和Dijk首次運用調節焦點理論對這一現象進行探索性研究,指出領導風格對員工行為的影響研究中應該更多地關注員工個體的心理機制[7]。該研究雖彌補了以往對心理狀態的忽視,但還存在一些可完善之處,即:以往更多關注促進型或規避型某一類型的調節焦點,或是某一主體自身的調節焦點,而很少研究組織環境中管理者和下屬間的調節焦點適配[8],更忽視該變量在領導風格與員工行為之間影響的強弱,因而近年來學者呼吁對領導風格影響效果進行考察時要更多地考慮邊界調節[9]。煤礦特有的組織架構中,有礦長,安全、機電等副礦長,以及隊長(區長)、班組長等,不同層次的管理人員擔負的責任和行使的職能有所不同。雖然煤礦企業各層級管理人員都有入井工作次數的不同要求,與基層礦工都能有所接觸,但現實中隨著級別提高,與礦工接觸的機會逐漸減少。為此,重點研究與礦工緊密接觸的中、基層管理者的威權領導風格對礦工安全行為的影響,并探討礦工對管理者的認同在二者間的中介效果,以及管理者-礦工調節焦點適配在礦工對管理者認同和礦工安全行為影響中的調節效應。該研究成果不僅為礦工安全行為的研究和調節焦點的研究提供新的研究視角,也為提升管理者的管理能力提供方法依據。
1 研究假設的提出
1.1 威權領導風格對礦工安全行為的影響:礦工對管理者認同的中介作用
雖然煤礦開采工藝和機械化程度均有所提高,但粗放型管理仍然普遍,所以威權領導風格在煤礦企業具有深刻的文化積淀。威權領導風格體現管理者個人權威以及對礦工的支配,要求礦工無條件服從,并對礦工設置嚴厲的懲罰和高績效標準,主要由專權、隱匿、嚴峻和教誨這四個方面構成[10]。專權是管理者認為自己應具有絕對權威和對礦工有絕對控制的行為;隱匿是管理者為了保護自己的權威形象而和礦工保持距離,以對自己的行為有所隱藏;嚴峻是指管理者對礦工嚴格要求,以期望達到高績效標準的行為;教誨是管理者對不遵守紀律和犯錯誤的礦工進行嚴厲批評,并讓礦工按照自己的要求進一步完成任務。
礦工安全行為是指礦工在安全生產過程中嚴格遵守安全操作規程、法規等行為表現,從安全服從行為和安全參與行為兩個方面體現[11]。其中:安全服從行為是礦工嚴格遵守規章制度、依照安全流程規定進行工作的程度;安全參與行為是礦工幫助工友提高工作主動性以及在井下自覺提升安全行為的程度,該行為對礦工不直接產生工作職責上的產出,但是有助于企業安全生產水平的提升。
認同是一種非常普遍而又極其重要的社會現象,個人認同是1958年Kelman提出的,指個體將某個人的信念、形象當作自我參考或自我定義的內容時,會對此人產生認同感[12]。從1990年之后,學者逐漸關注組織中下屬對領導者的認同,并取得了一定成績,比如:Chen等證實了變革型領導與下屬對領導者的認同有正向影響關系,而且變革型領導可通過認同來間接影響下屬的行為[13];李磊和尚玉釩等研究發現下屬對領導者認同度高時,變革型領導才會對下屬創造力有更大的影響[14],等等。相關研究表明領導者與下屬之間在價值觀、態度等某一方面的相似會對彼此關系及行為產生影響。本研究中礦工對管理者認同是指礦工和管理者有相似特質時,會以管理者的表現進行自我定義,并使自己的表現盡量貼近管理者要求。
一般情況下,管理者并不能夠直接決定礦工的工作行為,而只是通過自己行為對礦工工作行為選擇實施一定的影響。威權領導風格對員工工作行為的影響效應已經得到初步證實[4],而Walumbwa又進一步證實領導風格會通過下屬對主管的認同來間接影響下屬的組織公民行為[15]。既然領導者是員工形成自我概念的重要影響人之一[9],那么員工對領導者的個人認同也會成為影響員工態度及行為的重要因素。由此推斷,當礦工認知到管理者和自己有相似的特質時,會引導礦工更多的正向行為。為此,本研究試圖探討礦工對管理者認同在威權領導風格與安全行為之間可能的中介作用,并提出如下假設:
H1:威權領導風格對礦工安全行為有正向影響關系;
H2:威權領導風格與礦工對管理者認同有正向影響關系;
H3:礦工對管理者認同與礦工安全行為有正向影響關系;
H4:礦工對管理者認同在威權領導風格與礦工安全行為間起著中介作用。
1.2 調節焦點適配在礦工對管理者認同和礦工安全行為間的調節效應
調節焦點理論是個體從自身的心理情境出發解釋行為傾向的理論,對員工自身行為有較強的解釋力[16]。該理論把個體在實現目標過程中的動機分為促進型調節焦點和規避型調節焦點,前者指個體會以積極的方式追求目標和自我的成就,對于正向結果較為敏感;后者指個體以避免或預防犯錯的方式來達到目標,比較關注義務和職責,對于負向結果較為敏感。個體促進/規避型調節焦點的差異并非追求不同結果,而是在追求同一結果時有不同的動機,進而采用不同的方式。調節焦點會長期存在于個體的人格特質中,但也可以通過短期的誘發方式引導。Brockner和Higgins指出,在組織環境下,管理者是塑造和影響下屬工作情境性調節焦點的關鍵因素,管理者可通過言語使用、給予反饋和樹立榜樣等方式激發下屬的促進/規避型調節焦點[17]。于是,2000年Higgins依據個體不同調節焦點的心理特征又提出要關注調節焦點適配[18],調節焦點適配是個體實施追求目標的方式與調節焦點傾向的一致性,目前主要從調節焦點傾向與個體行為方式選擇之間的適配、調節焦點傾向與特定情境的適配、以及組織情境下領導風格與下屬調節焦點傾向的適配等方面進行研究[19-21]。根據相似吸引理論,如果領導者和下屬的調節焦點具有相類似,說明二者調節焦點適配,則雙方會很容易地建立情感聯系。所以說,當管理者和員工的調節焦點適配時會伴隨有正確的感覺,這種感覺可增強個人行為的動機和信心,而調節焦點不適配則可能中斷其策略并降低其動機。基于此,提出以下假設:
H5:管理者與礦工間的調節焦點適配,在礦工對管理者認同和礦工安全行為間具有調節效應;
H5a:管理者與礦工間的促進型調節焦點適配,在礦工對管理者認同和礦工安全行為間具有調節效應;
H5b:管理者與礦工間的規避型調節焦點適配,在礦工對管理者認同和礦工安全行為間具有調節效應。
此外,參考2004年Preacher提出的條件性間接效果[22],進一步提出如下假設:
H6:管理者與礦工間的調節焦點適配度會強化礦工對管理者認同的中介效果;
H6a:管理者與礦工間的促進型調節焦點適配度會強化礦工對管理者認同的中介效果;
H6b:管理者與礦工間的規避型調節焦點適配度會強化礦工對管理者認同的中介效果。
綜合以上研究假設,構建理論模型如圖1所示:

圖1 理論模型 Fig.1 Theory modeling
2 研究方法
2.1 研究對象與調查過程
由于國有煤礦企業間的管理水平差異不大,安全管理方式類似,所以為了保證研究結果的普適性,調研對象均來源于國有煤礦企業的一線員工。調查問卷利用安全會議、培訓等時間發放,并采用管理者與礦工配對的方式避免同源偏差的影響。在發放問卷之前,明確告知該調查為匿名調查并僅供學術研究之用,問題回答無對錯之分,并承諾對填寫信息保密,發放問卷后均對各題項進行了宣讀和解釋。問卷發放620份,回收有效問卷544份,有效回收率為87.74%。
2.2 測量工具
問卷中變量的測量利用Likert5點計分法,要求測試者按照每項表述的認可程度依次從“5-非常同意”到“1-非常不同意”中作出選擇,問卷題項采用中性語言進行描述,并隨機排放。選取人口統計學變量年齡、學歷、管理者和礦工共事時間作為控制變量。
威權領導風格(WLF)的量表主要參考鄭伯塤[3]開發的家長式領導量表的威權領導分量表,并根據調查對象特點加以適當修改,共5個題項,如“管理者要求工友服從他的領導”。該量表的信度為0.77。
礦工對管理者認同(RT)的測量參考Kark (2003)編制的個人認同量表[7],該一維結構量表廣泛應用于測量個體在行為、觀念等方面與領導一致性的感知程度,在測量下屬對領導個人認同問題上具有良好的適用性。基于此,采用該量表并結合礦工語境修正問項,最終得到7個問項,如“我和管理者在處理事情時的解決方法上很相似”。該量表信度為0.75。
安全行為(AX)的測量借鑒Vinodkumar[23]開發的員工行為量表,安全服從行為設計了“遵守操作規程或標準”、“使用安全防護品”等6個問項,安全參與行為設計了“工作中與管理者溝通安全問題”、“提醒工友安全工作”等5個問項。該量表的信度0.81。
調節焦點采用Higgins[18]開發的量表進行測量,該量表在高危行業中應用效果較好[24],量表包含促進型調節焦點和規避型調節焦點兩個測量維度,每個維度均有6個題項,如“我通常考慮如何取得好的成果”、“我通常會擔心不能完成我的工作目標”。該量表由礦工和管理者共同填寫,量表的信度為0.68。本研究主要測量管理者和礦工之間的促進型/規避型調節焦點適配性(CTJ/GTJ),所以在數據處理時用管理者和礦工的調節焦點量表12個題項相減的平方來測量管理者-礦工間的調節焦點適配程度,所得的分值高表明適配程度高、分值低表明適配程度低。
3 研究結果
3.1 樣本分析
最終的544份有效問卷中,礦工問卷339份,管理者問卷105份。性別均為男性;年齡:21~30歲占19.4%,30~40歲占29.4%,40~50歲占41.8%,50~55歲占10.4%;學歷:高中及以下學歷的占67.81%,大專以上學歷占32.19%;礦工和管理者共事時間(少于1年的樣本沒有考慮):共事3年以下占58.6%,3~5年占23.2%,5~10年占16.1%,超過10年占4.3%。
3.2 假設檢驗
首先,采用Pearson法進行相關分析。變量間的相關系數、平均數和標準差如表1所示。從結果中可以看出,威權領導風格、礦工對管理者認同和安全行為之間均有顯著的相關關系(在P﹤0.01時,β值分別為0.423,0.165,0.152),說明假設H1~H3得到初步支持。

表1 描述性統計和相關系數 Table 1 Descriptive statistics and correlation coefficients
注:*表示P﹤0.05,**表示P﹤0.01,***表示P﹤0.001(下同)
其次,進行礦工對管理者認同在威權領導風格與安全行為間中介效果的檢驗。盡管Baron和Kenny提供的方法在中介分析時普遍采用[25],但是更應采用在直接分析中的間接作用來檢驗中介效果。為此,使用Preacher和Hayes建議的方法進行中介效應檢驗[26],結果如表2所示。從分析數據看出,假設H4得到了檢驗,說明礦工對管理者認同在威權領導風格與安全行為間有完全中介作用;假設H1~H3得到了進一步的證實,表示威權領導風格與礦工對管理者認同和安全行為均有正向影響關系,礦工對管理者認同對安全行為有正向影響關系。

表2 中介效果分析Table 2 Mediating effect analysis
最后,對管理者-礦工間的調節焦點適配程度在管理者認同與安全行為間的調節效應進行檢驗。采用Baron和Kenny建議的階層回歸分析方法,先控制人口統計學變量后,依次引入自變量和調節交互變量來預測因變量,若交互變量對因變量的預測仍然顯著,則表示有顯著調節效果。分析結果如表3所示。

表3 調節效應的回歸分析Table 3 Regression analysis of moderating effects
表3表明:管理者-礦工間的促進型調節焦點適配在礦工對管理者認同和安全行為間有顯著的調節效果(β=0.184,P﹤0.001);管理者-礦工間的規避型調節焦點適配在礦工對管理者認同和安全行為間也有調節效果(β=0.137,P﹤0.001),但是顯著性水平低于促進型調節焦點適配,表明當管理者與礦工的促進型調節焦點高適配或規避型調節焦點高適配,礦工對管理者認同與安全行為間有較強的正向影響,假設H5a和H5b均獲得驗證。同時,為了直觀表示調節焦點的調節效應,用調節焦點適配的標準化均值、均值±1個標準差來對H6進行驗證,得到圖2和3。從圖中可以看出,促進型/規避型調節焦點適配度高和低的不同情況,會加強或降低礦工對管理者認同在威權領導風格與安全行為之間的中介效果,該結果支持了假設H6a和H6b。

圖2 促進型調節焦點的調節效應Fig.2 The moderating role of promotion regulatory focus

圖3 規避型調節焦點的調節效應 Fig.3 The moderating role of prevention regulatory focus
4 結論
1)威權領導風格是影響礦工安全行為的重要情境因素,對礦工安全行為有正向影響。該結果說明特定情境下消極領導風格對組織績效也有積極影響,這可能是由于調研對象的特殊性所致,低素質、低就業能力的礦工多終身工作于煤礦中,對管理者的威權領導風格方式已經麻木或習慣,因此威權領導風格對礦工安全行為有一定促進效果。
2)威權領導風格會通過礦工對管理者認同正向影響安全行為。該結果表明煤礦企業情境下管理者與礦工間的“上尊下卑”和高依賴度關系,使礦工對管理者的認同程度成為考量礦工安全行為的重要因素。因此,管理者要想提高安全管理效率,必須與礦工保持溝通、交流,增加礦工對管理者的認同。
3)調節焦點適配在礦工對管理者認同和安全行為之間有調節效應。當礦工-管理者之間的調節焦點適配度高時,會使礦工對管理者認同和安全行為之間的中介效果更加顯著,說明管理者在實踐中應該注意礦工的調節焦點傾向,盡量使自己的管理方式與礦工調節焦點傾向相符合。
[1]Larsson S,Pousette A,Torner M.Psychological climate and safety in the construction industry-mediated influence on safety behavior[J].Safety Science,2008,46(3):405-412.
[2]Einarsen,S.,Aasland,M. S.,& Skogstad,A.Destructive leadership behavior: A definition and conceptual model[J].Leadership Quarterly,2007,18(3):150-158.
[3]鄭伯塤,林姿葶.家長式領導與部屬效能:多層次分析觀點[J].中華心理學刊,2010,52(3):1-23.
ZHENG Boxun,LIN Ziting.Paternalistic leadership and employee effectiveness: a multiple-level-of-analysis perspective[J].Chinese Journal of Psychology,2010,52(3):1-23.
[4]王丹,宮晶晶,郭飛.安全管理者的威權領導對礦工安全行為的影響研究[J].中國安全生產科學技術,2015, 11(1):121-129.
WANG Dan,GONG Jingjing,GUO Fei.Study on influence by authoritarian leadership of safety manager to safety behavior of miners[J].Journal of Safety Science and Technology,2015,11(1):121-129.
[5]Kark R,Shamir B.The Dual Effect of Transformational Leadership: Priming Relational and Collective Selves and Further Effects on Followers[A].In:Avolio BJ,Yammarino FJ (Eds),2002:67-99.
[6]Walumbwa,F.O.Wang,P.WangH.,Schaubroeck,J.,Avolio,B.J.Psycholgical processes linking authentic leadership to follower behaviors[J].The Leadership Quarterly,2010, 21(1):22-36.
[7]Kark,R.,Dijk,D.V.Motivation to Leader,Motivation to Follow:The Role of the Self-Regulatory Focus in Leadership Processes[J].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2007,32(2):500-528.
[8]Brown,A,L.,Zimmerman,R.D.,Johnson,E,C.Consequences of individuals fit at work:A meta analysis of person-job, person-organization, person-group,and person-supervisor fit[J].Personnel Psychology,2005,58(2): 281-342.
[9]Brown,M.E.,&Trevino,L.K.Ethical leadership:A review and future directions[J].Leadership Quarterly,2006, 17(6):595-616.
[10]Farh,J.L.,&Cheng,B.S.A cultural analysis of paternalistic leadership in Chinese organization[J].Indigenous Psychological Research in Chinese Societies, 2000,13(6) :127-180.
[11]曹慶仁,李凱,劉麗娜.煤礦安全文化對員工行為安全影響作用的實證研究[J].中國安全科學學報,2011, 21(4):121-129.
CAO Qingren,LI Kai,LIU Lina.Empirical study on impact of coalmine safety culture on miner's safety behavior[J].China Safety Science Journal,2011,21(4):121-129.
[12]Kelman,H.C.Compliance,identification,and internalization:Three processes of attitude change[J].The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1958,2(1):51-60.
[13]Chen,Y.R.,Peterson,R.S.,Phillips,D.J.,Podolny,J.M.,&Ridgeway,C.L.Introduction to the special issue: Bringing status to the table attaining,maintaining and experiencing status in organizations and markets[J].Organization Science,2012,23(2):299-307.
[14]李磊,尚玉釩.基于調節焦點理論的領導對下屬創造力影響機理研究[J].南開管理評論,2011,14(5):4-11.
LI Lei,SHANG Yufan.The research on the mechanism of leaders’ influence on followers’creativity based on regulatory focus theory[J].NANKAI Business Review,2011,14(5):4-11.
[15]Walumbwa,F.O.,Mayer,D.M.,Wang,P.,Wang,H.,Workman,K.,&Christensen,A.L.Linking ethical leadership to employee performance:The roles of leader-member exchange,self-efficacy,and organizational identification[J].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and Human Decision Processes, 2012,115(4):204-213.
[16]Higgins,E.T.Beyond pleasure and pain[J].American Psychologist,1997,5(2):1280-1300.
[17]Brockner,J.Higgins E.T.Regulatory focus theory:implications for the study of emotions at work[J]. Organizecision Behavior&Human Decision Processes,2001,86(1):35-66.
[18]Higgins,E.T,Friedman,R.S,Harlow,R.E.Achievement orientations from subjective histories of success:Promotion pride versus prevention pride[J].European Journal Social Psychology,2000,30(1):1-23.
[19]Higgins,E.T.Making a good decision:Value from fit[J]. American Psychologist,2000,55(3):1217-1230.
[20]Resick,C.J,Hargis M.B,Shao P,Dust S.B.Ethical leadership,moral equity judgments,and discretionary workplace behavior[J].Human Relations,2013,66(7):951-972.
[21]Pham,M.T,Avnet T.Ideals and oughts and the reliance on affect versus substance in persuasion[J].Journal of Consumer Research,2004,30(4):503-518.
[22]Preacher,K.J.,Hayes,A.F.SPSS and SAS procedures for estimating indirect effects in simple mediation models[J].Behavior Research Methods,2004,36(4):717-731.
[23]Vinodkumar M.N,Bhasi M.Safety management practices and safety behaviour:Assessing the mediating role of safety knowledge and motivation[J].Accident Analysis and Prevention,2010,42(6):2082-2093.
[24]蘭國輝,張學森等.班組長領導方式對礦工安全行為的影響效應研究-基于調整焦點理論[J].中國安全生產科學技術,2016, 12(3):175-161.
LAN Guohui,ZHANG Xuesen.et al. Study on effect utility to safety behaviors of miners by the leadership styles of team leader-based on adjusting focus theory [J].Journal of Safety Science and Technology,2016, 12(3):175-161.
[25]Baron,R.M,Kenny,D.A.The Moderator-Mediator Variable Distinction in Social Psychological Research: Conceptual, Strategic and Statistical Considerations[J].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1986, 51:1173-1182.
[26]Preacher,K.J&Haves,A.F.Asymptotic and resampling strategies for assessing and comparing indirect effects in multiple mediator models[J].Behavior Research Methods,2008,40(3):879-8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