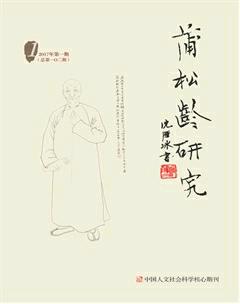《聊齋志異》中的女性與科舉
陽達++徐彥杰
摘要:《聊齋志異》中描寫了許多有關女性與科舉的故事。這些女性不僅為士子們進京應試提供了物質上的支持,還通過各種方式幫助他們及第。盡管有些是虛構的情節,表達了蒲松齡一種美好的想法,但也反映出現實中的女性在士子登第過程中的作用。特別是隨著明清科舉文化影響的擴大以及女性文化水平的提高,很多女性對科舉較為關注,而女性與科舉也由此成為明清小說中的重要題材。
關鍵詞:聊齋志異;女性;科舉
中圖分類號:I207.419 文獻標識碼:A
《聊齋志異》歷來被視為反對科舉制度的經典之作,如《葉生》《于去惡》等篇目揭露了士子登第的艱難,也暴露了科舉取士存在的弊端。但蒲松齡在某些篇目中又肯定了科舉的價值和合理性,如《封三娘》《青娥》《胡四娘》等,這些故事的主角基本上都是女性,男性反倒成為了配角。小說中的女性為士子的及第創造了諸多條件,反映了蒲松齡“另類”的科舉觀。
一
據筆者統計,《聊齋志異》中有關女性與科舉的篇目約三十余篇,如《阿寶》《紅玉》《鳳仙》等都是膾炙人口的名篇。其中女性的角色與作用各有不同,或是妻子勸導丈夫刻苦攻讀,或是母親勸誡子孫獲取功名,或是其他女性以局外人的身份幫助士子及第。
在這些短篇小說中,士子們大多出身貧寒、頗有才華卻不懂營生,而他們的妻子則是家境優越、聰慧勤勞或擁有仙術。她們不僅支持士子們進京趕考,而且在物質上予以了很多的支助。《阿寶》中的阿寶就是出自富商之家,家庭財富可以“與王侯埒富” ① ,而且“姻戚皆貴胄”。阿寶嫁給孫子楚后,帶來了豐厚的嫁妝,“小阜,頗增物產”,使日常生活得到了很好地改善。雖然孫子楚不事生產,只顧研讀圣賢之書,但是,“女善居積,亦不以他事累生”。在阿寶的精心打理下,不光“家益富”,孫子楚更是順利通過鄉試,并高中進士。《胡四娘》中的程思孝也是“家赤貧,無衣食業”,后來得到胡銀臺的賞識,不但將女兒許配給他,并且分給他們房子居住,“供備豐隆”。同時,胡銀臺還幫助他進了縣學,后來程思孝因故沒有參加鄉試,胡四娘便又鼓勵程思孝爭取考試的機會,“四娘贈以金,使趨入遺才籍”。
另外,胡銀臺的愛妾及三女兒也“賂遺優厚”。盡管程思孝此次考試名落孫山,但由于四娘等人給予了足夠的考試費用,“囊資小泰”,才使得他還有機會到京城再次應試,“連戰皆捷”。假設沒有胡銀臺的提拔以及胡四娘等人的援助,程思孝很難在科舉路上取得成功。可以說,這不單單是一個女性的付出,差不多整個家庭都在資助程思孝。
為了能讓士子更好地攻讀舉業,有些女性更是包攬了所有的家務和農活。馮相如亦是貧寒士子,“憂貧乏,不自給”。紅玉就勉勵馮生專心備考科舉,“但請下帷讀,勿問盈歉,或當不殍餓死”,并且身體力行地從事農業生產,“遂出金治織具;租田數十畝,雇傭耕作。荷镵誅茅,牽蘿補屋”。同時,積極幫助馮相如恢復生員身份,“是科遂領鄉薦”(《紅玉》)。還有一類女性則是利用士子們的思念之情,鞭策他們刻苦學習,如鳳仙。鳳仙曾留給書生劉赤水一面鏡子,“欲見妾,當于書卷中覓之;不然,相見無期矣”“因念所囑,謝客下帷。一日,見鏡中人忽現正面,盈盈欲笑,益愛重之。無人時,輒以共對。月余,銳志漸衰,游恒忘返。歸見鏡影,慘然若涕;隔日再視,則背立如初矣:始悟為己之廢學也。乃閉戶研讀,晝夜不輟;月余,則影復向外。自此驗之,每有事荒廢,則其容戚;數日攻苦,則其容笑。于是朝夕懸之,如對師保”。也就是說,假如劉赤水想在鏡中見到鳳仙,必須要勤奮攻讀經書。在這種近似游戲的督促中,劉赤水“一舉而捷”(《鳳仙》)。與此類似的還有《書癡》中的紗剪美人,她為了糾正書生郎玉柱讀死書、死讀書的習慣,也是通過這種若隱若現的方式進行激勸,“‘君所以不能騰達者,徒以讀耳。試觀春秋榜上,讀如君者幾人?若不聽,妾行去矣。郎暫從之。少頃,忘其教,吟誦復起。逾刻,索女,不知所在”。除此,紗剪美人還鼓勵郎玉柱四處交友,為他在社會上贏得了很好的聲譽。郎玉柱本來就熟讀儒家經典,只是學習方法不當,因此多年未能中第。經過紗剪美人的修正以及社會關系的處理,郎玉柱不久便鄉、會試聯捷。可以看出,紅玉、鳳仙以及紗剪美人在士子們登第過程中起著重要作用。雖然這三個人都非現實中的人,但多少反映了科舉社會中女性對于男性以及整個家庭的付出。特別是士子們赴京應試,他們的妻子更是要承受更大的生活壓力。
《聊齋志異》中還有一些故事如《邵九娘》《細柳》《任秀》等,則講述了另一類女性對士子登科的作用,即母親的科舉教育。任秀在其父去世之后,不只荒廢了學業,家里也是一貧如洗。盡管入了縣學,但“佻達善博”,毫無上進之心,某次歲試列居四等。按照清代的考試規則,生員在四等以下要受處罰,甚至黜退。其母多次告誡,乃至“憤泣不食”。在母親的規勸與情感的感染下,“于是閉戶年馀,遂以優等食餼”。任秀后來不單入監讀書,并且通過經商富甲一方(《任秀》)。相比而言,細柳對兩個兒子的教育更加科學有效。繼子(高生前妻所生)長福,由于母親早逝,又加之父親高生的離世,內心受到了極大的創傷,“嬌惰不肯讀,輒亡去從牧兒遨”。細柳多次嚴加管教,甚至進行鞭打,都未能改變長福的習性。于是,細柳便調整了教育方法:首先,并不強迫長福讀書,但必須與其他人一起勞動,“貧家無冗人,便更若衣,使與僮仆共操作。不然,鞭撻勿悔”。于是,長福便與奴仆一起早出晚歸做農活。結果長福無法適應這種體驗式的生活,但細柳并沒有當即答應長福的要求。然后,繼續讓長福體味生活的艱辛,“殘秋向盡,桁無衣,足無履,冷雨沾濡,縮頭如丐”。作為一個后母,如此對待繼子,必然遭到了鄰居們的指責,但細柳并未放在心上。長福因受不了煎熬也離家出走,但沒過幾個月又因無法生存而返家。之后,長福又托人向細柳求情,細柳先讓長福認識到自己的錯誤,但還是沒有馬上讓他讀書,“既知悔,無須撻楚,可安分牧豕,再犯不宥”。最后,經過旁人的勸解,長福才得以從師讀書,“勤身銳慮,大異往昔,三年游泮”。盡管細柳看起來類似現在的虎媽教育,但這種層級式的方法卻取得了較好地效果,并且在她的親生兒子長怙身上也得到了驗證。長怙心性愚鈍,“讀數年不能記姓名”,細柳并未要求他在學業上有所作為,而是“令棄卷而農”。但長怙好吃懶做、游手好閑,細柳也是通過這種曲折的教育方式,使得長怙迷途知返、經商創業,積累起巨額的財富。此時,長福也通過鄉試,三年后又進士登第(《細柳》)。即便在今天看來,這種欲擒故縱的方式代替了傳統的棍棒教育,遠比強迫硬塞更有成效。可以說,細柳的因材施教、循循善誘,成就了兩個兒子的美好前程,也達成了自己的人生理想。
當然,還有一類女性與前面兩種類型不同,她們與士子并無直接關系,而只是在其中起著牽線搭橋的作用,如《封三娘》。為了促成范十一娘與孟安仁的結合,封三娘扮演著紅娘的角色,不但力勸范十一娘私贈金釵作為信物,并且在其去世后又用仙藥救活。孟、范兩人最后得到了家族的認可,而孟安仁鄉、會試也是連傳捷報。青梅最初也是極力撮合阿喜和張生,但由于張生家境貧寒,阿喜及其父母并未同意這樁婚姻,最后青梅才自薦嫁入張家,而后張生也得以授官(《青梅》)。
由上可以看出,這三類女性對士子們的登第都有著直接或間接的作用,實際上反映了蒲松齡對處在科舉社會中女性生存狀況的關注。或者說,小說中描繪的各類形象就是現實中的女性在科舉考試過程中默默付出與犧牲的真實寫照。
二
文學作品中描寫女性與科舉的題材早在唐代就已大量出現,如《鶯鶯傳》《李娃傳》《霍小玉傳》等。這些故事一般發生在士子登科前后,只是此時的女性在其中所起的作用不大。《李娃傳》中雖寫了李娃在科舉上對鄭生有所幫助,但更多的是個人的一種贖罪,也并非作者強調的重點。相比而言,這些女性反倒成為受傷害的對象,如崔鶯鶯、霍小玉。當然,唐代傳奇中也有一些神話傳說,如《柳毅傳》就描敘了柳毅應試下第后與龍女結好的故事,其中虛幻的內容與構思與上述《聊齋志異》中的有關狐女篇目多有相似。
女性真正成為科舉文學作品中的主角則是在元代,如《西廂記》《陳母教子》《曲江池》《荊釵記》《琵琶記》《漁樵記》等劇目都大量描寫了女性與科舉的情節。《曲江池》中的鄭元和就是在李亞仙的救助下一舉登第,并且較好地緩和了家庭矛盾。《荊釵記》中的錢玉蓮在物質上對王十朋就有很大的幫助,特別是王十朋缺少上京應試的資費,錢玉蓮便主動回家借錢,“官人,此系是前程之事,況兼官府催行,雖則家道艱難,如何辭免?可容奴家回去,懇告爹娘,或錢或銀,借些與官人路上盤纏” [1] 243 。當初錢玉蓮沒有遵從父母的意愿下嫁給王十朋就已遭到后母的羞辱,但為了能夠湊足費用,錢玉蓮只能放下尊嚴向父親求助。應該說,王十朋高中狀元離不開錢玉蓮的大力幫襯。《琵琶記》中的趙五娘也是在科舉社會中被忽略的一個經典形象。蔡伯喈進京應試之后,趙五娘獨自扛起打理家庭的重擔,照料年邁的雙親。“奴家自從丈夫去后,屢遭饑荒,衣衫首飾盡皆典賣,家計蕭然。爭奈公婆死生難保,朝夕又無可為甘旨之奉,只得逼邏幾口淡飯。奴家自把細米皮糠逼邏吃,茍留殘喘,也不敢交公公婆婆知道,怕他煩惱” [2] 117 ,災荒讓貧苦的生活更加艱難。特別是公婆去世后,趙五娘又面臨著巨大的生計難題。對于一個弱女子來說,早已超出本能承擔的范圍。高明便在作品中設計用天神幫助了趙五娘,但如果這些事情發生在現實生活中,那么一切就會變得更為艱難。實際上,這一系列的事件本該由蔡伯喈來承擔。由此可見,士子進京后家庭中會發生許多難以意料的事情,而女性則代替他們履行了職責。特別是單親家庭,作為母親的責任就更加重大。不僅要維系整個家庭的正常運作,而且還要肩負教育子女的責任。《陳母教子》中的馮氏則是通過早期的科舉教育,讓陳氏三兄弟都名列三甲。可以說,在很長一段時間以來,我們大多只看到士子金榜題名的光環,卻難以看到這些女性為此所做的貢獻。元代文人著力突出了女性的作用以及在科考中的重要性,對明清文人的創作多有啟發,特別是如《聊齋志異》等以女性為主要描寫對象的作品應該受到了更多的影響。
因此,類似的題材在明清文學中更加豐富,甚至許多作者安排了女性參加科舉考試的情節,如《同窗友認假作真 女秀才移花接木》中的聞蜚娥就是女扮男裝考取了秀才(《二刻拍案驚奇》)。徐渭的《女狀元》更是將黃崇嘏描繪成才華橫溢且精通政事的優秀人才,并且一舉奪魁。在這些作品的影響下,“女扮男裝”考科舉就成為清代小說中一個突出的現象,《聊齋志異》中的顏氏即是一例。顏氏非常支持丈夫攻讀舉業,不僅時刻陪讀和監督,還親自做出表率,“朝夕勸生研讀,嚴如師友。斂昏,先挑燭據案自哦,為丈夫率,聽漏三下,乃已”。只是這個讀書人文運不濟,多次被宗師黜落。為了增強他的自信心以及展示個人的能力,顏氏便請求女扮男裝去應考。于是,顏氏被裝扮成丈夫從小就分離的弟弟,兩人一起學習備考。外人看到顏氏的作文,“瞲然駭異”;加之儀表舉止得體,“由此名大噪,世家爭愿贅焉”。大概是外界的刺激和內心的激勵,某生和顏氏都順利通過了科試。至少說,顏氏的鞭策還是起到了一定的效果。只是某生鄉試失利,而顏氏則連中舉人、進士。顏氏的成功無疑是對士子們的一種諷刺,但也只是蒲松齡的一種遐想。而抱有這種想法的小說家卻大有人在,如《儒林外史》中熱衷于科舉的魯小姐、《再生緣》中高中狀元的孟麗君等。也許,《聊齋志異》也為這些作品提供了一些思路和想法。
可以說,女性與科舉的題材是伴隨著科舉的出現而產生,并且在不同的時代而更顯多樣化。相比而言,《聊齋志異》也呈現出了別樣的風貌,即蒲松齡摻入了大量的狐鬼形象,以一種非現實的方式助力士子登第,如前文提及的紅玉、鳳仙等。即便這些女性都是虛幻的想象,但蒲松齡還是賦予了她們勤勞善良的品德,如青梅為了幫助張生中舉,也是通過刺繡賺取生活費用,“得資稍可御窮。且勸勿以內顧誤讀,經紀皆自任之”。其他女性如胡四娘、邵九娘等,莫不如此。這些女性親自勞動致富的描寫在其他的作品并不多見,這不但代表了蒲松齡的理想,也是封建社會中優秀勞動婦女的化身。
三
《聊齋志異》中還描寫了不孝女、悍婦妒妻等其他女性形象,蒲松齡都進行了批判和否定;但在涉及女性與科舉的作品中,他大多持著肯定的態度。這些小說中沒有士子的負心,也較少有女性的薄情,更多的是她們默默地付出和無私的奉獻。所以,她們大多能以較好的方式結局。這既體現了蒲松齡辯證的婦女觀,其實也折射了個人的凄苦內心與坎坷境遇。
蒲松齡從十九歲便開始參加科舉考試,在縣、府、道三試中都名列第一,但自順治十七年(1660)初次鄉試后,卻屢試失利。康熙二年(1663)、康熙五年(1666)、康熙十一年(1672)、康熙十七年(1678)、康熙二十六年(1687)、康熙二十九年(1690)、康熙四十一年(1702),蒲松齡都曾應試,都因各種原因未能中舉。直至康熙四十九年(1710),七十一歲的蒲松齡才在青州的歲貢考試中順利出貢,并獲得“儒學訓導”一職。由此可以看出,蒲松齡一生都是功名蹭蹬。所以,在他取得科名之后,也是頗有感觸,“落拓名場五十秋,不成一事雪盈頭。腐儒也得賓朋賀,歸對妻孥夢亦羞” [3] 641 (《蒙賓朋賜賀》)。詩中概述了五十年來在科場中的坎壈,既感慨自己一事無成,也表達了他對家人的歉意。正是因為蒲松齡在現實中遭遇了太多的挫折,于是就想通過一種虛幻的方式來彌補內心的遺憾,而“紅袖添香”則成為較為理想的方式,“清貧的文士被社會所拋棄,但美貌女子向他們敞開了懷抱,他們失去了科場,卻在情場上能獨領風騷……現實的不滿在非現實中得到了滿足,失落的價值通過虛幻的方式得以補償” [4] 188 。因此,《聊齋志異》中抒寫了許多狐女通過各種方式幫助士子們及第的故事。實際上,小說中也寄托了蒲松齡的一些期望和美好的想法,特別是士子們在科舉場上的成功讓蒲松齡多少得到了些許慰藉。
文學作品中所寫的女性對科舉的重視以及被世人忽略的作用,其實在現實生活多有實例,《唐摭言》《宋人軼事匯編》等史料中就記載了許多相似之事,明清時期則更多。清代著名女詩人席佩蘭就積極支持丈夫孫原湘的科舉活動,“養親課子君休念,若寄家書只寄詩” [5] 478 (《送外入都》)。詩中訴說了兩人難以割舍的情感,并明確表示自己承擔照顧家庭、教育子女的責任,讓丈夫安心的去參加考試。當孫原湘考場落敗,席佩蘭又寫了一首長詩安慰,“君不見杜陵野老詩中豪,謫仙才子聲價高。能為騷壇千古推巨手,不得制科一代名為標。……作君之詩守君學,有才如此足傳矣。閨中雖無卓識存,頗知乞憐為可恥。功名最足累學業,當時則榮歿則已,君不見古來圣賢貧賤起” [5] 446 (《夫子報罷歸詩以慰之》),開導丈夫不要過于在意功名,應該注重個人的才學與品行。當孫原湘鄉試中式后,席佩蘭又寫了《賀外省試報捷》一詩慶賀。孫原湘在嘉慶十年(1805)終于高中榜眼,肯定是離不開席佩蘭的鼓勵與勸導。再如八旗名媛汪太君,在丈夫去世之后,獨自教育三子成才。“惟望三子學業有成,勉強延名師,截所居斗室之半為家塾;鬻衣飾、市經書,楮墨、饔飧、修脯備極誠敬。已而貧益甚,漸不能支,命負笈就外傅;又不能,乃躬自課督,風雨篝燈,聲淚俱下。其后并無賃屋資,棲身靡所;因賃地結篷編籬為屋以居;或晨炊不繼朝夕。教諸孤,感動奮發讀書,立志無替祖父家聲。諸子偶失學嬉游,則號泣搶地痛刻責,如不欲生;皆哀懼,長跪請改,然后已” [6] 4374 (藍鼎元《貞節汪太君傳》),可以看出,即便是在最窮困之時,汪太君依然沒有放松對三子舉業的監督。在汪太君的感染與引導下,大兒子逢泰和小兒子滿保同年中舉,并先后考中進士,二兒子元旦后來也通過了鄉試。毫無疑問,三個人的榮譽都歸結于汪太君艱辛的付出。由此可知,母親在單親家庭中的教育角色就顯得非常重要。她們指引兒子走上科舉之路,不僅是為了讓他們能有更好的發展前景,也很好地維護了個人及整個家族的榮耀。特別是在富貴官宦之家,假設沒有科名的支撐,家族的利益及威望都會受到影響,甚至由此走向了衰落。所以,王定保很早就道出了科舉取士的社會意義,“草澤望之起家,簪紱望之繼世。孤寒失之,其族餒矣;世祿失之,其族絕矣” [7] 97 。《聊齋志異》中的細柳及任秀之母等女性,也無不鼓勵著后嗣去奪取功名;而這些士人科舉及第后,也帶來了家族的興旺。從某種程度上來說,小說中的事例既是對現實的客觀描繪,也反映了當時夫貴妻榮、子榮母貴的社會心態。
值得指出的是,隨著明清時期人們思想觀念的改變,女性與男性的交往漸漸增多,在文人們的指引下,她們的文化水平得到了很大的提高,不僅能夠寫出了大量的優秀作品,而且通過結社的方式表達了參與社會活動的愿望。特別是男性對科舉的癡迷與狂熱,必然也吸引了女性的關注。有些殷實的家庭開設家塾,讓子女共同學習,多少也會接觸到一些科舉的內容。加之嫁入夫家,受科舉興家等思想的影響,必然也會支持丈夫或后生去應試。因此,她們當中的某些人在科舉方面應該也多有研究,只是沒有機會上場展示才華。《萬歷野獲編》中就記有“婦人能時藝”一條:“山陰張雨若(汝霖)駕部,曾為余言:同里孫司馬樾峰,以甲戌舉南京第一人,而少時師傅,惟其長嫂所授,即冢宰清簡公嫡配,而俟居(如法)刑部之母夫人也。性嚴而慧,深于八比之業,決科第得失如影響,故樾峰受其教以取大魁。” [8] 595 所以,這些人便將自己的學習心得與男性分享,期望他們能夠金榜題名。《聊齋志異》中的顏氏之所以能夠通過科舉考試,也是因為從小就受到了良好的教育,“父在時嘗教之讀,一過輒記不忘。十數歲,學父吟詠,父曰:‘吾家有女學士,惜不弁耳”。某些女性從場外人的角度去審視舉業,或許能夠更清醒地把握八股文的規律,在寫作技巧等方面有著獨到的見解,因而給予士子們較大的啟發。蒲松齡等小說家注意到了這種現象,并將此編成了小說素材,女性也就成為明清科舉文學中不可或缺的角色。或者說,“女性從科舉的旁觀者,變成科舉活動的外圍參與者,乃至通過對男性才能的肯定獲得了與科舉評判相似的權力。這既顯現了女性在小說所描繪的科舉社會中絕非是可有可無的一個群體,同時也為女性在有關科舉的小說中頻頻露面提供了更多的合理性” [9] 145 。
總的來說,《聊齋志異》中敘寫女性與科舉的故事,既反映出了蒲松齡對她們的肯定和認可,也表達了自己對科舉的一種憧憬。通過對這些女性角色的論述,我們可以明顯地感覺到女性也是科舉考試過程中的重要參與者,而這些問題卻往往被忽略,也就難以發現女性在科舉社會中應有的價值。
參考文獻:
[1]王季思.全元戲曲[M].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9.
[2]高明.元本琵琶記校注[M].錢南揚,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3]蒲松齡.蒲松齡集[M].路大荒,整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4]袁世碩,徐仲偉.蒲松齡評傳[M].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05.
[5]胡曉明,彭國忠.江南女性別集初編[M].合肥:黃山書社,2008.
[6]錢儀吉.碑傳集[M].北京:中華書局,1993.
[7]王定保.唐摭言[M].北京:中華書局,1960.
[8]沈德符.萬歷野獲編[M].北京:中華書局,1959.
[9]葉楚炎.科舉與女性——以明中期至清初的通俗小說為中心[J].首都師范大學學報,2009,
(6).
On the women and imperial examination of Liao zhai zhi yi
YANG Da XU Yan-jie
(East China Jiaotong University College of Liberal Arts,NanChang 330013,China)
Abstract: Liao zhai zhi yi described a lot of the stories about women and imperial examination. These women not only provided material support for scholars to take the imperial examination,but through a variety of ways to help them to pass the imperial examination. Although some are fictional plot which expressed Pu Songling's an idea,but also reflected the role of women in the process of imperial examination. Especially with the impact of imperial examination and improvement of women's educational level in the Ming and Qing,many women paid attention to the imperial examination,and the women and imperial examination also became an important theme in the novels of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Key words: Liao zhai zhi yi;women;imperial examination
(責任編輯:朱 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