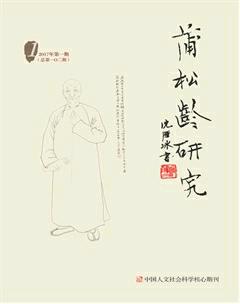《聊齋俚曲集》并列連詞“合”、“和”連接非名詞性詞語考察
摘要:不少人認為,現代漢語中并列連詞連接非名詞性詞語是歐化語法現象,其實,近代漢語中有不少并列連詞連接非名詞性詞語,《聊齋俚曲集》也有,既有連詞“和”,更有連詞“合”。并列連詞連接非名詞性詞語是漢語固有的語法現象而非歐化語法現象。
關鍵詞:聊齋俚曲集;并列連詞;合/和;非名詞性詞語;歐化語法現象
中圖分類號:I207.37 文獻標識碼:A
一
不少學者認為,現代漢語中并列連詞“和”等連接非名詞性詞語是歐化語法現象。如刁晏斌的《初期現代漢語語法研究》 [1] 、王希杰的《修辭學導論》 [2] 等,尤其是賀陽的《現代漢語歐化語法現象》 [3] 。賀陽說,舊白話小說只發現3例“和”連接非名詞性成分,僅占“和”用例總數的0.4%,這3例是指《三國演義》、《西游記》、《紅樓夢》,并說這3例中,連接謂詞的2例都出現在詩歌這種特殊的語體中。 [3]158 賀陽還說:“從這些考察結果來看,并列連詞‘和字一般只連接名詞性詞語,這在舊白話小說中應該是一條較為嚴格的限制。” [3]158 賀陽又說:“五四以來,連詞‘和的連接功能有了擴展,連接的成分不再僅限于名詞性詞語,而是擴展到謂詞性詞語,副詞性詞語,甚至擴展到小句。” [3] 158
但也有學者并不認同這些看法。劉堅等的《近代漢語虛詞研究》舉有唐詩中的例子,有“生和出”、“醉和吟”, [4] 200 劉堅等又舉有宋金元的例子如“愁和悶”、“是和非”、“暖和飽”、“深和淺”、“似和不似”、“多和少”、“存和亡”、“英和烈”等。[4] 201 席嘉的《近代漢語連詞》認為并列連詞“和”出現于唐五代時期,這一時期主要連接名詞性成分,偶見連接謂詞性成分,甚至有連接主謂短語的例子,如:
(1)骨瘦和衣薄,清絕成愁極。
(宋·黃載《孤鸞》)
(2)一霎風狂和雨驟,柳嫩花柔,渾不禁僝僽。
(宋·李石才《一籮金》) [5] 32
以上可見,從唐到宋短短的時間內,“和”連接的成分就有很大的擴展,從謂詞性單音節成分發展到有謂詞性短語。
鐘兆華的《近代漢語虛詞研究》也舉有“和”連接謂詞性成分的例子,又有擴展。例如:
(3)可剉細草和烝豆來,我欲飽食而死。
(宋·洪邁《夷堅丁志》卷13)
(4)皇甫殿直把送柬帖兒和休離的上件事,對行者說了一遍。
(元·無名氏《簡帖和尚》)
(5)一只手揪住這廝潑毛衣,使拳捶和腳踢。
(元·無名氏《盆兒鬼》第3折)
(6)王臣乃將樊川打狐得書、客店變人詒騙,和夜間打門之事說出。
(明·馮夢龍《醒世恒言》卷6) [6] 90-91
以上又可見,從宋發展到明代,“和”連接的成分又有很大的擴展,尤其是例(6),主謂短語更復雜。還有例(3)出自文言筆記,更是特殊,更有價值,連文言筆記都有“和”連接謂詞性成分,可見這種用法的成熟性。例(5)是雜劇,例(6)是白話小說,與唐代的詩歌相比,文體也有了擴展。
到了明清的戲劇與白話小說,“和”連接謂詞性短語的例子更多。(以上可參看崔山佳的《漢語歐化語法現象專題研究》 [7] )
因此,以上的許多例子,較賀陽 [3] 所舉的3部作品一是時間要早得多,二是比例也要高得多,三是文體也更多,并非只有詩、詞,而是有戲曲、有白話小說,甚至有文言筆記。因此說,賀陽 [3] 等認為“和”連接非名詞性詞語是歐化語法現象并不符合漢語事實,是經不起推敲的。
現代漢語方言中也有“和”連接非名詞性詞語的用法。例如:
(7)人問:“做啥行當?”“吃和玩。”
(《分壽命》,《中國民間文學集成浙江省·寧波市·奉化市故事歌謠諺語
卷》第5頁)
(8)這樣,人的壽命三加四加,加到了八十歲,一到廿年是天帝給的,專門吃和玩。
(《分壽命》,見同上,第6頁)
(9)縣官搖搖頭說:“頂窮。”又笑了笑說:“本官也有一首,吟一吟讓三位見笑:千里來做官,為的吃和穿,路上有包袱,孝敬禮當然。”
(《三個秀才拾包袱》,見同上,第315頁)
(10)我勸青年們,忍耐性要強,夫妻之間,朋友同事,有事共商量,切不可罵和打,傷傷和氣難得收場,噯噯呀。
(《勸人五更調》,見同上,第435頁)
(11)夫妻無限恩和愛,那知樂極有悲來。
(《白娘娘十二月花名》,見同上,第454頁)
上例的“恩”算是名詞,但“愛”是動詞。
(12)我夫長城無音訊,不知死活與存亡。
(《十二個月孟姜女》,見同上,第455頁)
上面有的是故事,有的是歌謠。例(12)的連詞是“與”。
劉月華等的《實用現代漢語語法》也說到“和”等連接形容詞或動詞。又分三點,第3點是:“和”也可以連接具有并列關系的謂語動詞,這時后面通常有共同的賓語、補語,或前面有共同的修飾語,使并列的動詞和形容詞成為一個句子成分,而不是并列的謂語或兩個句子,而且所連接的動詞和形容詞必須是雙音節的。[8]318-319
其實,我們所舉例子中,動詞或形容詞也可以是單音節的,古今都是如此,而且古代的例子中,單音節的比例更大。
賀陽說“歐化語法現象的特點”有三點,其中第三點是“歐化只限于書面語”。[3]32-34 賀陽說:
語法的歐化是基本上只影響漢語的書面語,還是能夠深入到漢語的口語,這方面的事實對認識歐化語法現象和間接語言接觸的特點都有重要的意義。王力(1943:334)認為,歐化語法現象往往只出現在漢語書面語中,口語中是不大說的,所以多數的歐化語法現象只是文法上的歐化,而不是語法上的歐化。Kubler(1985:19)的看法與王力不同,他認為漢語語法的歐化已對漢語口語產生很大影響。不過,他的看法令人懷疑,因為他所說的口語未必等于王力和我們所理解的口語。在我們看來,區分口語和書面語的關鍵因素并不在于話語所憑借的物質條件不同,而是正式程度的差異。正式程度很高的口頭表達,如演講和報告,就與書面幾乎沒有什么差別;正式程度很低的書面表達,如口語化的小說和劇本,又與口語十分接近。所以我們所說的口語并不等于口頭表達,而是指正式程度較低的語體,這種語體的典型樣式就是日常生活口語,特別是日常生活對話。Kubler(1985)顯然沒有做出這樣的區分。[3] 33-34
按照賀陽 [3] 的說法,上面浙江寧波奉化的民間文學如故事與歌謠應該屬于口語語體,如例(7)中的“吃和玩”就是對話。針對這種語法現象,賀陽 [3] 陷入“兩難”境地,要么承認歐化語法現象已經進入“口語”,也就是承認Kubler(1985)的看法,要么承認漢語中的“和”連接非名詞性成分不是歐化語法現象,而是漢語固有的。因此,賀陽 [3] 上面的說法同樣是不確切的,不符合漢語事實的。
張斌主編的《現代漢語描寫語法》說,“和、跟、與、同”作為連詞,主要連接的是體詞性成分。也可以連接謂詞性成分,但連接謂詞性成分往往是有條件的:(1)謂詞性成分充當主語、賓語和定語,表示指稱義、修飾義等非陳述義。(2)當謂詞性成分用“和”連接充當謂語時,前后必須有其他成分,不能是光桿謂語。[9]208
這也就是說,即使在現代漢語中,并列連詞“和”等連接名詞性成分也是主要功能,而連接非名詞性成分是次要功能,古今都是如此。這也從另外角度證明,并列連詞“和”等連接非名詞性成分不是“歐化語法現象”,而是漢語固有的語法現象。
二
《聊齋俚曲集》有很高的文學價值,也有很高的語言價值。查“中國知網”,以“聊齋俚曲集”在“篇名”中搜索,就有45篇論文,據初步統計,文學只有3篇,版本、校點等5篇,文化1篇,語言(語音、文字、詞匯、語法等)36篇。以“聊齋俚曲集”在“博碩士”中搜索,有12篇論文,其中文學只有1篇,語言有11篇。由此可見,文學等還大有課題可研究,就是語言研究也大有余地。本文這里以連詞“合”和“和”連接非名詞性成分來展開。先看“合”連接非名詞性成分。例如:
(1)老婆子死去了,冷合熱自己熬,肚里饑飽誰知道?
(《聊齋俚曲集·墻頭記》第1回)
(2)方且早晚冷和熱,怎么好向媳婦言?這里許多不方便。不如我自己另過,饑合飽與您無干。
(《聊齋俚曲集·墻頭記》第1回)
(3)早合晚沒甚么孝順,但只是不敢辭勞。
(《聊齋俚曲集·墻頭記》第3回)
(4)兒婦雖然端相著做,可還不知窄合寬,穿上可教旁人看。
(《聊齋俚曲集·墻頭記》第3回)
(5)老頭子瞎發威,不論個是合非,他不過比我大幾歲。
(《聊齋俚曲集·墻頭記》第3回)
(6)這樣福合佛一樣,不知好合歹,拿著當尋常;只等的歪揣貨兒話出,這才把君子想。
(《聊齋俚曲集·姑婦曲》第1回)
(7)叫聲賢妻,叫聲賢妻:想想從前我好癡,遇著這樣人,辨甚么非合是?
(《聊齋俚曲集·姑婦曲》第3回)
(8)惟有后娘最無情,打兒不管輕合重,你滿心里無干系,不知達達心里疼;心里疼,待做聲,未曾開口笑顏生。
(《聊齋俚曲集·慈悲曲》第1回)
(9)他是姓張,好合歹是您的令郎。
(《聊齋俚曲集·慈悲曲》第3回)
(10)有錢不怕無衣穿,怎奈腰中無有錢,肚里無食偏要死,窮人論不的熱合寒,窮人論不的熱合寒,行路難,起倒一身隨處安。
(《聊齋俚曲集·慈悲曲》第6回)
(11)如今他既把家歸,把家歸,倒也免了是合非,爹爹呀,不必還把神思費。
(《聊齋俚曲集·翻魘殃》第8回)
(12)你在繡房縱然閑,縱然閑,不少綾羅緞匹穿,我兒呀,到那里要知勤合儉。
(《聊齋俚曲集·翻魘殃》第8回)
(13)你可打量肥合瘦,咱倆做成你可穿,我可去找找針合線。
(《聊齋俚曲集·翻魘殃》第9回)
(14)病重不顧羞合恥,逢人告訴一大篇,要想得個昆侖手,竊取紅綃到枕邊。
(《聊齋俚曲集·丑俊巴》)
(15)丑合俊聽你胡吧,好合歹全在你自家,老子娘也替你定不的價。
(《聊齋俚曲集·禳妒咒》第5回)
(16)你就辨辨是合非,他也沒拿著打牙槌。
(《聊齋俚曲集·禳妒咒》第10回)
(17)我不能替他認過,好合歹著他自受。
(《聊齋俚曲集·禳妒咒》第12回)
(18)長合短,小弟也不敢與聞。
(《聊齋俚曲集·禳妒咒》第12回)
(19)慶兒郎聰明,媳婦美合順,不聞吵罵聲,還有什么憂心病?
(《聊齋俚曲集·禳妒咒》第13回)
(20)分開圖免是合非,還捱一棍才解了圍。
(《聊齋俚曲集·禳妒咒》第13回)
(21)終果定不就兇合吉,破上我就去替他,低著頭就把主意拿。
(《聊齋俚曲集·富貴神仙》第2回)
(22)遠合近全不知,生與死不能料。
(《聊齋俚曲集·富貴神仙》第4回)
(23)要知道兇合吉,只在這二月半。
(《聊齋俚曲集·富貴神仙》第4回)
(24)我那兒,我那兒,并不識模樣瘦合肥。
(《聊齋俚曲集·富貴神仙》第9回)
(25)真合假,可以不用證見證。
(《聊齋俚曲集·磨難曲》第9回)
(26)家里未知兇合吉,破上一死無大差。
(《聊齋俚曲集·磨難曲》第6回)
(27)要知吉合兇,明年二月里看。
(《聊齋俚曲集·磨難曲》第9回)
以上“合”連接的是形容詞,是單音節形容詞。涉及的形容詞有:冷-熱、熱-寒、饑-飽、早-晚、窄-寬、是-非、好-歹、輕-重、勤-儉、肥-瘦、羞-恥、丑-俊、長-短、兇-吉、遠-近、真-假。共有16對反義形容詞,應該還算是豐富的。
也有連接雙音節形容詞的,例如:
(28)不求他賢良合孝順,但望安分不生殃,這等就滿了老父賬。
(《聊齋俚曲集·禳妒咒》第12回)
也有連接形容詞短語的,例如:
(29)日頭歪,日頭歪,分不出青紅合皂白。
(《聊齋俚曲集·翻魘殃》第8回)
“青紅”和“皂白”分別是聯合式的形容詞短語。
(30)人都說這一次沒了老子,倒省了許多吵合鬧。
(《聊齋俚曲集·翻魘殃》第1回)
(31)靜悄悄,靜悄悄,密密的滿天星亂搖,總像屋里沒有人,并不聽的說合笑。
(《聊齋俚曲集·翻魘殃》第2回)
(32)兄忽然上了嫖合賭,賣了地土輸老婆,原來自己惹的禍!
(《聊齋俚曲集·翻魘殃》第9回)
(33)娘子推卻,娘子推卻,家里莊田雖不多,儉省著吃合穿,可到也夠俺過。
(《聊齋俚曲集·富貴神仙》第9回)
(34)路上行人多凄涼,暫時不知死合亡;鄉里人民都散盡,城里大板大比糧。
(《聊齋俚曲集·磨難曲》第1回)
(35)張逵不在家,生合死不知他。
(《聊齋俚曲集·磨難曲》第15回)
(36)還包著,還包著,家里莊田雖不多,減省著吃合穿,這可也到還能過。
(《聊齋俚曲集·磨難曲》第19回)
(37)遠方人死合生,口里巴無足憑,這卦兒單看前應。
(《聊齋俚曲集·磨難曲》第24回)
(38)全不顧生合死人皆怕,到處得了勝,就說是通家。
(《聊齋俚曲集·磨難曲》第29回)
(39)把架子兩列開,用幫手的不成才,咱就單戰個勝合敗。
(《聊齋俚曲集·磨難曲》第34回)
(40)照照菱花看看影,叫聲薄命的小怨家,幾時捱夠打合罵?
(《聊齋俚曲集·增補幸云曲》第11回)
以上“合”連接的是動詞,單音節動詞。涉及的動詞有:吵-鬧、說-笑、嫖-賭、吃-穿、死-亡、生-死、勝-敗、打-罵。上面成對的動詞又有幾種類型,如“死”與“亡”是同義并列。“生”與“死”、“勝”與“敗”是反義詞,這表示的不是并列關系,而是選擇關系。好多是相關的動詞并列,如“吵”與“鬧”、“說”與“笑”、“嫖”與“賭”、“吃”與“穿”、“打”與“罵”。從兩者的意義類型來看,比形容詞要復雜。
(41)海參切成四瓣兒,鮑魚切成薄片兒,皮鲊切成細線兒,鯉魚成個正面兒,蔥絲切成碎段兒,花椒研成細面兒,包了剁了細餡兒,蒸合壓了餅沿兒,稀爛的豬頭還帶蒜瓣兒。
(《聊齋俚曲集·禳妒咒》第24回)
上例“合”連接兩個動詞,還帶了時態助詞“了”,更帶了賓語“餅沿兒”,這是非常罕見的用法。
(42)人家沒了父合母,哥哥還把兄弟教,娶媳婦合費錢合鈔。
(《聊齋俚曲集·翻魘殃》第3回)
(43)不望他封妻合蔭子,只望他殿試早回朝,來家合咱打馬吊。
(《聊齋俚曲集·禳妒咒》第30回)
上面2例“合”連接的是動詞短語,是動賓式短語。例(42)中的“合”連接的是“娶媳婦”和“費錢合鈔”,其中“錢合鈔”中的“合”連接的是兩個名詞。例(43)中的“合”連接的是“封妻”和“蔭子”。
(44)粉頭也有公合母。耕地的牛兒都會飛,堪合王龍是一對。
(《聊齋俚曲集·增補幸云曲》第19回)
上例“合”連接的是區別詞。
上面例子中,“合”連接的是同一詞性,也有連接的不是同一詞性的,例如:
(45)王成說雖是真,但沒有錢合銀,官府一聲要夾棍。
(《聊齋俚曲集·寒森曲》第4回)
上例中的“錢”是名詞,但“銀”是區別詞,但區別詞也是非名詞性成分,因為它是從形容詞分出來的。
(46)你自有結發的恩合愛,這露水頭的夫妻嗄相干?
(《聊齋俚曲集·富貴神仙》第6回)
上例中的“恩”是名詞,但“愛”是動詞。
(47)相思里又打上愁合悶。
(《聊齋俚曲集·磨難曲》第19回)
上例“和”連接的是動詞“愁”和形容詞“悶”。
從上面眾多的例子可以清楚地看出,《聊齋俚曲集》中連詞“合”連接非名詞性詞語是比較多的,種類也多樣,特別是例(41),“蒸合壓”處于謂語位置上,后面還帶了賓語,這更是難得的例子。因為此前我們發現的例子,都是處于主語或賓語的位置。還有“合”也有連接短語成分,也是很有價值的。總之,《聊齋俚曲集》中的連詞“合”是比較成熟的用法,并非作者一時心血來潮。也充分證明,并列連詞連接非名詞性成分不是“歐化語法現象”,而是地道的漢語用法。
席嘉說,在清代白話小說中還有一個“合”字,功能與“和”大致相同。“合”本來是入聲字,在近代漢語時期入聲韻尾消失,遂與“和”同音,加上其表示“合并”的意思也與“和”相近,便被作為“和”表示并列關系的另一種寫法。《紅樓夢》中“和”與“合”都可以作并列連詞和引入伴隨對象的介詞,“和”作并列連詞333例,“合”18例。《醒世姻緣傳》中這兩種功能多用“合”,少用“和”,《兒女英雄傳》中一律用“合”。[5]33
《醒世姻緣傳》中也有“合”連接2個動詞的例子,如:
(48)晁夫人說:“有合沒,待瞞得住誰哩?……”
(《醒世姻緣傳》第57回)
向熹的《簡明漢語史》說:“合,連接兩個并列的名詞或名詞性詞組,相當于‘和。” [10]437 其實,與“和”一樣,“合”也有連接動詞、形容詞等的,只是使用頻率遠遠不如“和”。但也不是例外現象,是對連詞“和”的類推。
因此,賀陽 [3] 等認為連詞“和”連接非名詞性成分是“歐化語法現象”的說法是不符合漢語事實的。不用說連詞“和”(我們發現有超過100個“和”連接非名詞性的例子),就是連詞“合”也有連接非名詞性詞語的用法。連詞連接非名詞性成分是漢語固有的語法現象。
三
《聊齋俚曲集》也有用連詞“和”連接非名詞性成分的,例如:
(1)方且早晚冷和熱,怎么好向媳婦言?這里許多不方便。不如我自己另過,饑合飽與您無干。
(《聊齋俚曲集·墻頭記》第1回)
(2)官不論是和非,聽的人說個賊,總像犯了他祖宗的諱。
(《聊齋俚曲集·磨難曲》第1回)
(3)知道咱苦和甜,全憑那上下官,朝廷好那里撈著見?
(《聊齋俚曲集·磨難曲》第1回)
上面例子“和”連接的是形容詞。下面1例“和”連接的是動詞,例如:
(4)好似死囚上殺場,人人保不住存和亡。
(《聊齋俚曲集·磨難曲》第2回)
《聊齋小曲》中也有“恩和愛”的說法,例如:
(5)二人恩和愛,鐵馬響一片。
(《聊齋小曲·尼姑思俗曲》)
上例中的“恩”是名詞,但“愛”是動詞。
“和”連接形容詞、動詞時,好多是表示選擇關系,而非表示并列關系。席嘉說如下的例子中的“和”連接“肯定-否定”對立的內容,也可以理解為有選擇義,但“和”的基本功能還是表示并列關系,選擇只是一種語境意義。例如:
(6)雪似梅花,梅花似雪。似和不似都奇絕。
(呂本中《踏莎行》) [5] P33
又如:
(7)如今入舍,俺為親舅,恣情終日打和拷。
(《劉知遠諸宮調》1)
(8)嬌聲重問,我兒別后在和亡。
(《劉知遠諸宮調》11)
(9)稱鱉氣,吃和不吃,也即由伊。
(《劉知遠諸宮調》11)
楊永龍等的《〈劉知遠諸宮調〉語法研究》認為例(7)中的“打和拷”表示并列關系,而例(8)中的“在和亡”、例(9)中的“吃和不吃”2例,“和”所連接的兩項“在”與“亡”、“吃”與“不吃”之間不能同時存在,是二選一的關系。[11]179 我們認為此說法確實有道理。楊永龍等又一次說,連詞“和”除了表示并列關系外,也可以用于表示選擇關系。所以,表示選擇關系的“和”義同“或”。 [11]180 所以,我們以為,例(6)中的“和”的確是表示選擇關系,這不是一種語境意義,而是一種語法意義。
鐘兆華在“并列連詞‘和”這一節的最后明確指出:
連詞“和”使用之初,是以連接并列的名物詞的。在唐、宋及以后的使用中有所發展,用以連接形容詞、動詞及動詞短語,表示并列關系。[6]92
這里,鐘兆華 [6] 92 認為“和”連接形容詞、動詞時,仍表示并列關系。
北京大學中文系1955、1957級語言班的《現代漢語虛詞例釋》只說到“聯合結構”:“‘和也可以連接并列的動詞或形容詞,但這樣構成的聯合結構,自己不能直接充任謂語。” [12]237 《現代漢語詞典》(第5版)“和”作連詞時,注釋是:“表示聯合;跟;與:工人~農民都是國家的主人。”只說“表示聯合”,沒有明確說明表示選擇。 [13]551 而第6版“和”義項三是連詞:“表示并列關系;跟;與:工人~農民都是國家的主人。”義項四也是連詞:“表示選擇關系,常用在‘無論、不論、不管后:不論參加~不參加,都要好好兒考慮。” [14]524 第7版注釋同。[15]526
呂叔湘主編的《現代漢語八百詞》說到連詞“和”時,第2點是:“表示選擇,相當于‘或。常用于‘無論、不論、不管后。”例如:
無論在數量~質量上都有很大的提高|不管是現代史~古代史,我們都要好好地研究下去|去~不去,由你自己決定 [16]266
上面例子中有“去和不去”,這與例(6)中的“似和不似”、例(9)中的“吃和不吃”一樣,都是表示選擇關系,都不是語境意義,而是語法意義。同時,“和”表示選擇關系更多地出現在連接兩個反義的形容詞和動詞。侯學超的《現代漢語虛詞詞典》在說到連詞“和”第二大點時說:1.跟“無論”等連用。多用于三項中的末項前。2.單用。用得少。[17] 273-274
但我們發現,近代漢語中有許多例子的“和”在表示選擇關系時,一般不用于“無論、不論、不管”后面。如上面所舉例子中除例(2)有“不論”外,其余都未用。
雷文治主編的《近代漢語虛詞詞典》認為作選擇連詞時的“和”音讀作“huò”,通“或”,意為“或者”,例子即為例(6)。 [18]292 我們以為,這也是一種看法。但所舉例子一是偏遲,二是未舉連接反義形容詞和動詞,似是不足。
參考文獻:
[1]刁晏斌.初期現代漢語語法研究[M].修訂本.沈陽:遼海出版社,2007.
[2]王希杰.修辭學導論[M].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0.
[3]賀陽.現代漢語歐化語法現象[M].北京:商務印書館,2008.
[4]劉堅,江藍生,白維國,曹廣順.近代漢語虛詞研究[M].北京:語文出版社,1992.
[5]席嘉.近代漢語連詞[M].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0.
[6]鐘兆華.近代漢語虛詞研究[M].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0.
[7]崔山佳.漢語歐化語法現象專題研究[M].成都:巴蜀書社,2013.
[8]劉月華,潘文娛,等.實用現代漢語語法[M].增訂本.北京:商務印書館,2002.
[9]張斌主編.現代漢語描寫語法[M].北京:商務印書館,2010.
[10]向熹.簡明漢語史[M].北京:商務印書館,2010.
[11]楊永龍,江藍生.《劉知遠諸宮調》語法研究[M].開封:河南大學出版社,2010.
[12]北京大學中文系1955、1957級語言班.現代漢語虛詞例釋[M].北京:商務印書館,2010.
[13]中國社會科學院語言研究所詞典編輯室.現代漢語詞典(第5版)[K].北京:商務印書館,
2005.
[14]中國社會科學院語言研究所詞典編輯室.現代漢語詞典(第6版)[K].北京:商務印書館,
2010.
[15]中國社會科學院語言研究所詞典編輯室.現代漢語詞典(第7版)[K].北京:商務印書館,
2016.
[16]呂叔湘主編.現代漢語八百詞[M].增訂本.北京:商務印書館,1999.
[17]侯學超編.現代漢語虛詞詞典[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
[18]雷文治主編.近代漢語虛詞詞典[M].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
(責任編輯:譚 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