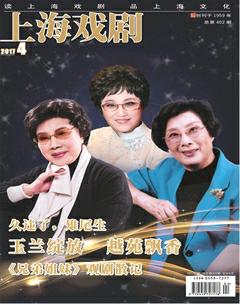迪倫馬特的本土化回歸
李容
作為20世紀最重要的劇作家,弗里德里希·迪倫馬特曾使瑞士戲劇保持了在國家文化中的上升地位,而在上世紀80年代——那時外國劇團來華演出并不多,但外國戲劇的文本介紹卻風靡中國,迪倫馬特和法國存在主義大師讓·保羅·薩特一樣受到中國劇壇的特別青睞,他的主要劇作,如《物理學家》《老婦還鄉》《天使來到巴比倫》和《羅慕洛斯大帝》等為國內一線劇院和一流導演競相搬演,甚至他的小說代表作《法官與劊子手》《隧道》也被改編為話劇。如果說,薩特是以其深刻的哲理來感染和教化當時喜歡思考、追求變革的一代觀眾,迪倫馬特則以其黑色幽默的荒誕性與瞬息萬變的時空感以及悲喜交替的劇情,向中國觀眾展現了別樣的舞臺魅力。那時,中國的戲劇理論還相當幼稚,凡國外非現實主義的戲劇作品被統稱為“荒誕派”,事實上,薩特將其作品視為“境遇劇”,而迪倫馬特把自己的戲劇定義為“悲喜劇”,這才是非常精準的自我定位。
然而,進入90年代以后,人們對迪倫馬特戲劇的熱情被無形地消磨了——當然,不僅僅是迪倫馬特,包括薩特都受到了冷遇。中國與世界戲劇的交流曾有十年的斷層,話劇隨之也步入低谷,一直到十年后才重新回暖。在這漫長的休眠期,善良而善忘的中國觀眾也就把曾給他們帶來悲歡與思考的迪倫馬特和薩特等一并給淡忘了。
由于中國戲劇在其回暖過程中主要是借助于自產自銷的“白領戲劇”“搞笑戲劇”來預熱的——“近朱者赤,近墨者黑”,觀眾習慣了這種“一次性消費”的觀劇定勢后,已沒有興趣在劇場中再花時間對人生和命運去作多余的思考。所以,盡管迪倫馬特的戲劇十分注重用厚實的笑料來鋪墊殘酷的結局,卻由于東西方的文化差異使人們把起碼的認知當成了“燒腦”,而把審美的樂趣當作雞肋都給扔了。
讓人欣喜的是,近期在上海戲劇學院黑匣子上演了由年輕的戲劇人夏天珩執導的迪倫馬特的二幕悲喜劇《流星》,把這位曾經在中國享譽一時的世界重量級的劇作家重新拉回人們的視線。
《流星》講述了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施威特求死不得而讓人啼笑皆非的故事,對照原著,我們可以發現演出本中的大量臺詞都有了本土化的代入。這種本土化改編還摻和進了原先的人物設計中。其實在上世紀80年代排演的迪倫馬特的戲劇大多原計原味,當時剛剛改革開放,西方的歷史和現狀對長期封閉的群體有新鮮感,因此人們愿意通過戲劇的模式加以解讀。改革到今天,很多西方風物已讓人們產生審美疲勞,互聯網時代催生了新事物,更使大家無暇顧及過往和歷史。迪倫馬特是管窺社會發展的文學大師,他筆下反映的永遠是現代社會長期存在的現象和弊病,他劇作的高明之處正是凌駕于時代之上,但他的作品展現的畢竟是瑞士當地的風土人情,這和東方的生活狀態迥然不同,因此本土化的改編勢在必行。例如原著中出現的“救世軍”如果照搬過來一定會引起困惑,這就容易造成對迪倫馬特的誤解。編導聰明地把“救世軍”置換成一群操著方言的陜北農民,他們的樸實愿望就是為了通過讓孩子們上大學而改變命運,不惜大鬧葬禮企圖摸一摸施威特的遺體來啟蒙益智。改編的臺詞顯然更貼近受眾群的現實生活,有明確的指向性,加上令人捧腹的小品式表演效果,因而獲得了劇場內心領神會的一片掌聲。
這樣本土化的例子在編導中不勝枚舉。再如畫家胡格,是經過演員創造在全劇改動最大的人物。原著中的畫家,只是推動劇情的一個符號,沒有性格化的連貫動作。演員覺得不過癮,表演總是顯得生硬。在劇情高潮處一直達不到理想狀態。導演與演員商量后,試著推翻了之前的設定,讓他演繹了一個將藝術作為生存目的卻又迷失了生活真諦的邊緣人。演員還結合了自身情況,融入上海方言,不斷制造符合人物性格的種種笑料。這樣一種神經質的藝術青年,其實在上戲的環境里比比皆是,從而增加了觀眾的認同感和親切感。還有那個“處處有人”的保安,本來是個過場人物,但在我們身邊也是司空見慣的,他們并不甘于小人物的身份,常常動用一切“有人”的關系鼓吹著保護別人,然而這個當口又往往是他們自己最缺乏安全感的時候。演員憑借著個人對生活的細致觀察,通過即興夸張又拿捏自如的表演,活生生將一個“紙片人”變成一個真實存在的無厘頭的“社會關系戶”。
另外,諸如“靠賣考研答案發家”“你是哪個學校的?——我不能在這兒說!”這些排練時隨機產生的包袱和本土化的加詞,與在場觀眾的生活閱歷有諸多相似,自然是“笑果”連連。尤其是那個幫閑評論家對施威特作品的過度解讀,一定程度上已經成為出版商授意的消費宣傳,而施威特的輕易點破,不僅打了評論家的臉,更是妙語連篇,展示出主人公不同常人的聰慧。編導站在迪倫馬特的肩膀上的二度創作不乏神來之筆——“那王八蛋欠我錢,我找不到他,就把他寫死了”“那天鋼筆壞了,一甩,正好6個點” ——這些看似胡編亂造的創作因由,據說取材于導演自己的創作經歷,真是“得來全不費功夫”。
本土化的改編,目的當然是讓戲更好看,這在孟京輝的戲劇中有過先例,如他改編的達里奧·福的《一個無政府主義者的意外死亡》,就是對原著的一次本土化的擴充。改編的難度在于收放自如,這個“收”,是對原著精髓的深刻理解,萬變不離其宗,精髓是根本,根本不能丟,丟了根本,就不是迪倫馬特的《流星》了。盡管《流星》并非迪倫馬特的上乘之作,但他作品中深刻的人文主義是一脈相承的,迪倫馬特對物欲橫流的世界充滿憂患,野心和貪念的洪水無時無刻不在沖擊著人們心靈的道德高地。人們的無知和狂妄在自已的生存空間中塞滿了笑料,而這些無盡的笑料必然引出一個殘酷的結局。這是迪倫馬特劇作的一個基本態度。然而,即便是黑暗世界的一片絕望,迪倫馬特依然會點亮人性的光彩,《流星》的升華之處是妓女奧爾加的為情自殺。在諾姆森夫人不正經的敘述的背后,是奧爾加——唯一對施威特無所求的人的一片赤誠。在這顆愛心被無情踐踏后,奧爾加選擇自殺,而施威特對世界的認知再一次崩潰。諾姆森夫人毫不避諱家丑,甚至張揚自己的妓女身份,看上去喜劇效果十足,背后卻是殘酷的人生。奧爾加以出賣肉體為生,因奉獻感情而死,施威特以出賣靈魂為生,又尋求肉體上的死亡。兩人的對比是極大的諷刺。“奧爾加愛上了我,就可以不再做妓女,而我,卻被他們綁著手腳,隨著車輪滾動永遠停不下來。”“我能有今天靠的不是真才實學,是坑蒙拐騙。沒人愿意揭穿我,因為他們要靠我掙錢,靠我做政績,拆穿了我,他們就什么都沒了。”時代的進步,卻掩蓋不了人類自身的愚昧和自私。
蕓蕓眾生都想從施威特身上瓜分名利,他主宰不了自己的生死。可是前仆后繼的掙扎卻只換來自身的毀滅。施威特成為諾貝爾文學獎得主的光芒閃耀的那一瞬間,便被拉入一片深淵。朋友也好,陌生人也罷,無一不對他虎視眈眈,施威特拼命掙扎,始終抓不住真實,絕望而無力。天下人皆為名利往,只要施威特這樣的人存在于世就永不停歇。在無數笑料鋪陳之后,一陣敲門聲帶著自私的欲望將《流星》推向悲情的結尾。
由上海滑稽劇團的導演虞杰扮演的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施威特灑脫自如、桀驁不遜、目空一切,在表演分寸上掌握得極為精準。我尤其注意到他十分講究眼光的運用:對畫家胡格的蔑視;對牧師的審視;對奧古斯特的打量潛藏著克制的欲念;對特蕾西的乜斜掩飾著粗鄙的本性……導演出身的虞杰顯然在人物的理解和塑造上層次更為分明。其他每個角色扮演者的努力也顯而易見,他們雖然還夠不上“資深演員”,但根據他們各自對人物的準確發揮,卻夠得上“精彩紛呈”這四個字的點評。據說,上戲黑匣子的這一版《流星》的排演過程也很有意思:召集演員基本靠“騙”,占據排練廳幾乎靠“搶”,排練時間完全靠“擠”,演出費用悉數靠“掏”——由導演自掏腰包交制作人“摳門”作業,而全劇組則憑著“摯愛戲劇”的一腔熱情,全身心地無私奉獻。排除這些黑色幽默的“悲劇”因素,演出獲得了滿滿的喜感,整場演出效果奇佳,每一個笑點都有完滿的反應,本土化內容的成功代入使觀眾感同身受。
這一版《流星》在劇本的內涵把握上與迪倫馬特一脈相承。主創對原劇本大刀闊斧地進行改編,同時又抓住了迪倫馬特悲喜劇的精髓。全劇的包袱抖得酣暢淋漓,絲毫沒有過火之嫌。這一版《流星》有別于上世紀對迪倫馬特劇本演出的照本宣科,而是開辟了一條新的道路,巧妙地將其本土化,把握劇本精髓的同時融入了自己的理解,避免了將迪倫馬特戲劇從主流戲劇越推越遠的尷尬境地,是值得贊揚的。由此我想到,我們不妨把迪倫馬特的重要作品全都找回來,把《老婦還鄉》《物理學家》《羅慕洛斯大帝》和《天使來到巴比倫》都找回來,再加上全新的包裝、全新的詮釋和演繹,一定能熱身市場,取得遠比當年更好的商演價值與社會效果,讓迪倫馬特“光榮回歸”上海的舞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