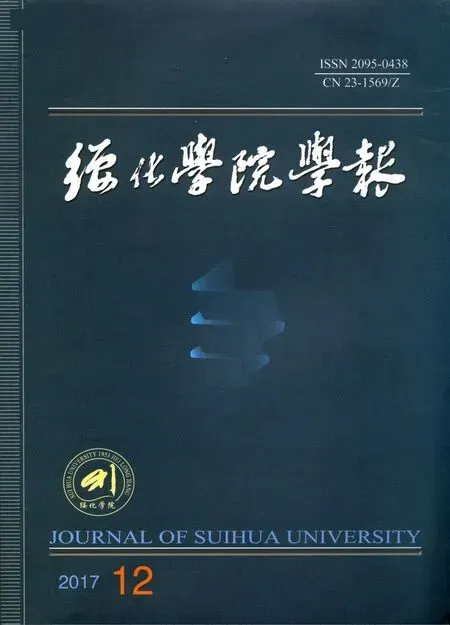沈從文物質文化史研究中方法運用及書寫體例的抒情特質
吳 丹 吳有麗
(吉首大學文學與新聞傳播學院 湖南吉首 416000)
沈從文物質文化史研究中方法運用及書寫體例的抒情特質
吳 丹 吳有麗
(吉首大學文學與新聞傳播學院 湖南吉首 416000)
通過文本細讀,可以發現在物質文化史研究方面,沈從文運用文圖互證的研究方法,這種研究方法可以說是對“二重證據法”的發展。沈從文對文字的遮蔽與局限性的認識與反思,與他采取這種研究方法是有聯系的。同時,沈從文運用綜合分析的治學態度,與中國傳統的不受現代學科體制限制的治學方法有相通之處。沈從文延續“有情”的書寫,使得筆下的紋案、器物變得生動可感、充滿生命力。
沈從文;物質文化史;文圖互證;綜合分析能力;抒情
一、“圖文互證”法以及對文字局限性的認識
沈從文在物質文化史領域的研究方法是以文見物、文圖互證。在對文獻、實物、圖案的對比研究中,沈從文發現物本身的歷史性以及物之間相互的影響和關聯。同時,通過對物的研究,發現物與文化的關系、與人的關系。有論者指出,沈從文物質文化研究的方法與王國維“兩重證據法”是密切關聯的[1]。然而二者又存在差異。沈從文對文字的遮蔽與局限性的認識與反思,與他采取“圖文互證”的研究方法密切相關。
王國維的“二重證據”法對沈從文的研究方法是有影響的。沈從文寫道:“王靜安先生對于古史問題的探索,所得到的較大成就,給我們樹立了一個新的工作指標。證明對于古代文獻歷史敘述的肯定或否定,都必需把眼光放開,用文物知識和文獻相互印證,作新史學和文化各部門深入一層認識,才會有新發現。”[2](31卷,P321)《古史新證》里提出的“二重證據法”是要運用地下之新材料,補正紙上之材料,偏重于利用出土材料來解讀紙上材料,如用甲骨卜辭證實《史記》殷商世系,用卜辭證明晚出的《山海經》《楚辭·天問》等“所言古事,亦有一部分之確實性”[3](P53),而“二重證據法”其地下之材料在今天看來恐怕主要仍然是甲骨、金文[4]。有論者認為沈從文的“圖文互證”一方面是與王國維的“二重證據法”一脈相承,另一方面是對“二重證據法”的修正、補充和發展[5](P28),是有道理的。
綜觀沈從文的物質文化史研究,他的方法是將文獻、文物、圖像三方面結合在一起的。有論者認為,沈從文的研究方法正是上世紀年代以來學界所廣泛提倡的“三重證據法”,“將出土實物、出土文獻與傳世文獻三者有機結合進行互證研究,在文獻研究和考古研究方面開創的嶄新的研究方法”[6]。例如談到瓷工藝研究,沈從文認為:“從書本和實物兩者間切實研究,分別提出報告和結論,才能薈萃處理”[2](28卷,P52),“讓文物、圖像、文獻三結合,作點綜合分析工作,有系統整理出來”[7](21卷,P305)。在沈從文這里,實物包括出土之文物和工藝品,實物的造型之美、圖案之美是沈從文關注的重點。從造型與圖案的發展變遷不僅可以得到歷史性的發展印象,也可以得到共時性的比較。因此,在沈從文經緯編織中,“物”的范圍已從傳統的金石之器擴展到諸多器物上,研究的對象不僅包括文字,而且包括器物的造型、紋案。“圖文互證”的研究方法,是與沈從文對文字的遮蔽作用和局限性認識是相關聯的。
我國歷有“敬天惜字”的傳統,焚燒字紙成了一種禮儀,說明文字早已被人賦予了非常神圣的意義[8]。中國儒家學派有“崇文抑畫”的傳統,如果將圖像放在“文以載道”的歷史語境中,由于它的虛指性,顯然不能和語言命名相提并論,難以成就“文”一樣的“載道”偉業[9](P28)。文字在中國歷史中無疑是精英文化的凝聚,而文字之外的“無名”歷史是被忽略的。沈從文曾經發現,通過文字可以連接歷史,那么,“歷史”在沈從文的觀念里是什么呢?“一本歷史書除了告訴我們些另一時代最笨的人相斫殺以外有些什么?但真正的歷史是一條河。從那日夜長流千古不變的水里石頭和沙子,腐了的草木,破爛的船板,使我觸著我們平時所疏忽了若干年代若干人類的哀樂!”[7](11卷,P188)“歷史書”作為特定時代下的產物,記載更多的是朝代遞嬗、政權更替,而豐饒人類歷史的文化以及真正的人生,卻在另外一本大書里。作為人類心智外化的文字、器物、圖案,在沈從文“有情”的關注下,具有別樣的意義。對無名款的民間工藝品的注目,可以說是對“無名”歷史的發現。沈從文對文物和工藝美術滿懷熱忱,而器物的制作者將自己的情感心智體現為器物的形態、圖案之美,這些是不被包含在傳統的研究視野中的。沈從文對器物觀看的角度,在某一方面是顛覆傳統的價值秩序,而企圖起到“價值重估”的作用。對“物”的重新發現在沈從文的前半生已經表現出來,發展到后期,便是他自己所說的“從文物出發,來研究勞動人民成就的‘勞動文化史’、‘物質文化史’,及以勞動人民為主的‘新美術史’”[7](27卷,P245)。
文字不僅具有遮蔽作用,同時,也有自身的局限,在文學創作中,沈從文已經感覺到文字自身的局限性。對文字局限性的認識與他對圖像的重視是密不可分的。在《湘行書簡》中,沈從文面對“如畫”的風景,想將風景的形色用文字向新婦一一描繪,可他發現他描繪不出自然的聲音、顏色。“這里小河兩岸全是如此美麗動人,我畫得出它的輪廓,但聲音、顏色、光,可永遠無本領畫出了。”[7](11卷,P119)“在先一時我以為人類是個萬能的東西,看到的一切,并各種官能感到的一切,總有辦法用點什么東西保留下來,我且有這點自信,我的筆是可以作到這件事情的。現在我方明白我的力量差得很遠。”[7](11卷,P119)面對可見可聽的自然,文字作為表達媒介是有局限性的,于是沈從文用畫筆來畫。文字書寫之外,呈現出他畫筆下的風景。圖畫在沈從文這里,成為文字之外的另一種有效的表達媒介。翻閱沈從文1949年之后的信件,也可發現許多他對風景、器物的小畫。因此,沈從文在物質文化研究中采用“圖文互證”的研究方法是有跡可循的。“文字是固定的,死的,甚至是不可信的。而物是實在的,又是在不同地域不同時間在不斷發展變化的,所以用來研究它的發展和成就”,“得到十分明確的認識和結論”[7](24卷,P464)。“文獻”作為文字,在文物研究上是有局限的,將文獻與文物與圖案結合起來,可以補足文字的局限性。
沈從文的這種結合文獻、實物,重視文字、圖案的研究方法與他重視的綜合分析能力是有關聯的。
二、“綜合感知能力”和綜合文物研究
沈從文運用聯想的方法,將器物的發展與歷史連接起來的研究方法,與他在文學創作方面所用的方法具有相通性。沈從文在給家人的信中多次提到“綜合分析能力”,這種綜合分析能力反映了他的治學態度。而這種方法又是與中國傳統的不受現代學科體制限制的治學方法有相通處。可以說,沈從文的綜合分析能力,使得他在文獻、實物、圖案中看到關聯,不僅從對物的體悟中發現制物者的情感,也讓他發現物的歷時性演變以及共時性的相互影響。這種“綜合分析能力”直接影響到書寫體例。
沈從文將自己物質文化史研究的工作稱為“綜合文物研究”[7](20卷,P301),而他所用的“圖文互證”的研究方法,他認為是建立在綜合分析能力之上。之所以稱之為“綜合”,可以從沈從文研究對象的選擇上、研究方法的運用上找到內在理路。沈從文認為自己埋頭于“花花朵朵,壇壇罐罐”之中,而這些都是雜文物。翻閱沈從文的物質文化史卷,可以發現這些雜文物的具體所指。這里的“雜”,是相對于傳統的金石之學以及同時代的學院派考古學而言。而在研究方法的選擇上,沈從文有一套自己的治學方法,即“圖文互證”。沈從文在研究中,從實物出發,“給材料排排隊”,結合文獻,“物”的歷時性的發展以及共時性的影響逐漸清晰明確。在這一過程中,涵蓋了歷史學、文學、工藝美術、圖案學等等方面的知識,可謂廣而博。沈從文在這種治學方法下,將目光投入到人類文化諸方面,且寄予了文化理想——即希求文化的發展,包括歷史學、文學、美術、電影、戲劇、工藝品生產等方面。
1975年,年過古稀的沈從文,在家書中寫道:“大致是經過了自我學習,總覺得從生物學和人類學來看,人這一萬年以來,大致只充分發展了人對付人的機能,把對付自然的嗅覺、聽覺和不能理解的一些鳥獸蟲魚的敏感慢慢的全失去了。”[7](24卷,P277)在這里,沈從文一方面強調運用聽覺、視覺、嗅覺對自然的觀察能力,“多識于鳥獸草木之名”(《論語·陽貨》),一方面將這種能力與“綜合分析能力”并舉。而這種綜合分析能力首先又是建立在對自然的觀察能力之上,且與聯想能力、記憶力相關聯。因此可以說,沈從文的這種“綜合分析能力”一方面來源于對自然的感知,一方面來源于他學習過程中逐漸形成的治學觀念。
沈從文喜愛美術和音樂,都從對自然的觀察開始。同時,他所受的文化影響也是這種“綜合分析能力”生長的土壤之一。沈從文并未受過系統的學院訓練,因此可以避免概念的先入為主。因此,沈從文能自由地在文學、美術、音樂之間暢游,不受“概念”的束縛。綜合分析能力可以說既是對學科界線的突破,又是對人自身感知能力的注重。錢穆曾說:“中國古人并不曾把文學、史學、宗教、哲學各別分類獨立起來,無[毋]寧是看重其相互關系,及其可相通合一處。因此中國人看學問,常認為其是一整體,多主張會通各方面而作為一種綜合性的研究。”[10](P4)在這樣一種世風學風之下,讀書人對各種學問多兼而治之。沈從文的治學態度是游離于現代學科分類制度之外的,這從他給年青人的信中可見出。“我覺得學專業能深入,有必要,但業余不妨放寬范圍,各方面去接觸,至少文化各部門能做廣泛接觸,生命會充實得多。和各種人事接觸,也有同樣好處。也有這種可能,即另外一種業余注意到一定時候,成就卻會比原有專業的還大一些”,“沒有更大的綜合各部門成就能力知識,新的斷代史、通識、文化史......通寫不好的。”[7](21卷,P427)可以說,沈從文的綜合感知能力、分析能力構成了他的治學態度,這種態度來自于前半生對生命的思考,體現在文學創作中;他后期轉向物質文化研究,延續了這一治學原則。在綜合分析能力的觀念下,沈從文形成了以文見物,文物互見的研究方法。他強調文獻、實物、美學意義、現實意義之間的融會貫通。
李之檀認為,沈從文有能力編寫《中國古代服飾研究》一書,正是因為他有在多個學科領域的知識,知識的廣泛性,與綜合文物研究的能力分不開。“沈先生不僅懂得美術,而且懂得文學,他看了很多古代文獻,還重視對圖像的觀察,同時也非常關心考古發掘的成就。知識的廣泛性使他能夠編寫這本書,并達到一個很高的高度。”[11](P294)這種綜合分析能力使得沈從文能發現物之間的關聯性,因此能作出許多預見性的推論,而且這些推論許多都被不斷出土的文物而證實。1958年,沈從文看到一堆帶孔的小方玉片。據他推測,這是漢代服飾一種,應該是金縷玉衣。這種葬服20多年后經被發掘出來,和他的推測一樣。
那么,這種“綜合分析能力”是如何在沈從文的物質文化史研究的書寫中得到具體的體現呢?
三、綜合分析的治學態度對書寫體例的影響
沈從文的綜合文物研究視野以及綜合分析能力的研究方法,影響到物質文化史研究的書寫方式以及體例選擇。聯想與記憶力,在沈從文的綜合分析能力占據重要位置,這都直接影響到體例選擇與書寫方式。
首先,聯想和比較的方法是沈從文綜合分析能力的重要一環。沈從文運用聯想和比較的方法,結合文獻和實物對圖案作細致生動的描寫。沈從文不僅發現花紋自身的歷史演變過程以及每個時代不同的呈現特征,也發現花紋之間的相互影響,同時,綜合分析的能力,使得他發現花紋與文化、美學、文學等方面的聯系。例如在《中國古代服飾研究》一書中的《戰國青銅壺上采桑、習射、宴樂、弋獵紋》[2](32卷,P70)一文,并非是對服飾的直觀分析,而是采用綜合分析的方法,涉及到古代生活、文化的諸多方面。沈從文用文獻互證的方法,分析了一個戰國青銅壺上的采桑、習射,宴樂,用矰繳弋獵天空鴻雁的圖案。首先,從圖案分析入手,由此涉及到古代生活各方面的問題。從《左傳》《國語》《爾雅》等文獻,可得知高級絲織物已成為貴重商品以及蠶的種類和培養狀況,這些都與當時的紡織技術有關聯。沈從文認為青銅壺上所見的采桑圖像,是極早有關蠶事生產圖像之一,或本于《詩經》“女執懿筐......爰求柔桑”語意而作。這樣,文學又與圖像發生聯系,由圖像可知文學中具體形象所代表。分析習射和宴樂的形象,采用文圖互證的方法,涉及到了古代生活、文化諸方面的問題。而且,這種通過聯想的對比分析方法,不僅僅體現在《中國古代服飾研究》一書中,其他關于物質文化的著述中也是貫穿這一研究方法的。例如,從銅鏡的實物中,發現紋案的美感,除此之外,紋案中的扇子式樣又對研究扇子實物的歷史有用。
其次,記憶力也是沈從文綜合分析能力的重要因素。聯想的研究方法使得記憶更加深刻,記憶力的發展又與沈從文的呈散文的物質文化史書寫相關聯。沈從文綜合實物、文獻、紋案的研究方法,使得他能通過聯想加深記憶。他常說這些花花朵朵,壇壇罐罐在自己大腦褶皺中無從忘記。這種通過聯想得來的記憶力影響到行文體例。在時代動蕩中,沈從文的研究資料經常散落——要么被抄走,要么被借走,下放干校時,他希望著手研究工作,但手邊竟“無一本書,無一圖像”[7](22卷,P465)。沈從文不得不憑借綜合感知能力得來的聯想、記憶進行書寫,“也居然還能全憑記憶回想,寫成兩個約五百個圖的文章”[7](22卷,P465),在極端孤寂中,“僅憑記憶,寫寫陳列中諸文物問題,性質與《談文字》相近,方法多用敘事散文,重在它的發展和聯系。”[7](22卷,P501)
這些因素,都影響到沈從文物質文化史研究的書寫體例。沈從文說《中國服飾史研究》“內容卻近似風格不一分章敘事的散文”是有原因的。《中國古代服飾研究》在香港出版之后,沈從文認為并“不算是什么‘中國服裝史’,書店為宣傳說是‘史’,不足信。只是個帶試點性資料圖書”[7](26卷,P339),沈從文寧愿稱其為“服裝資料”。“本來只是本試點資料,書店中卻宣稱為‘中國服裝史’,不免使得我感到狼狽”[7](26卷,P349)。黃裳認為:“象這樣的著作,過去的學人是常常稱之為‘札記’的,水平高的就會成為小型論文的集合體。其間發生了有機的聯系,得到貫通,就自然形成完整論著雛形。”[12]
再次,沈從文的綜合分析能力體現在物質文化史研究的著述中,表現為抒情的寫作方式。在書寫方面,沈從文“說明本重在釋疑理惑,為減少過于枯燥起見,又間或略作抒情敘述。”[2](30卷,P241)。汪曾祺說到沈從文的轉業:“他搞的文物工作,我真想給它起一個名字,叫作‘抒情考古學’”[13](P191)。黃裳認為:“作者研究的對象時服飾,這就要求將形態萬方、彩色斑斕的實物用文字再現在紙上。需要散文家的出色才能,不只是忠實的再現,還得寫出事物活潑的情趣。”[12]湖北江陵馬山楚墓發現一批古絲綢織物,沈從文對龍鳳大花紋彩繡衾被紋樣作了分析。對花紋作細致生動的描繪,紋樣似乎變得富有生氣。沈從文的“有情”關注,得以在對“紋”的體悟與書寫中得到延續。“有情”的關注,使得筆下的紋案、器物變得生動可感、充滿生命力。
至此,沈從文通過對文字遮蔽性和局限性的認識,采取文圖互證的方法,運用聯想、記憶、對比的綜合分析方法和抒情筆觸,完成了對“花花朵朵,壇壇罐罐”的抒情寫作。
結 語
1949年,沈從文試圖在新的社會尋求新生。他“試一試把自己當成一株蘋果樹”,接枝、移植到新社會的土壤之中。他意識到“蘋果樹”可能枯萎、被砍伐,但也希求移植后的“蘋果樹”“重新移植,結點對下一代還有益的果子”[7](27卷,P6、7)。雖然土壤不同,氣候有別,“蘋果樹”卻依舊有自身的生命連續性。在研究方法方面,沈從文運用以文見物、文圖互證,這種研究方法可以說是對“二重證據法”的發展。沈從文對文字的遮蔽與局限性的認識與反思,與他采取“圖文互證”的研究方法是密切相關的。同時,沈從文運用綜合分析的治學態度,與中國傳統的不受現代學科體制限制的治學方法有相通處。正是通過綜合分析,運用聯想、記憶等方法,沈從文延續“有情”的書寫,使得筆下的紋案、器物變得生動可感、充滿生命力。
[1]張新穎.“聯接歷史溝通人我”而長久活在歷史中——門外談沈從文的雜文物研究[J].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2012(6):7.
[2]沈從文.沈從文全集(28-32 卷)[M].太原:北岳文藝出版社,2009.
[3]王國維.古史新證[M].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1994.
[4]李銳.“二重證據法”的界定及規則探析[J].歷史研究,2012(4):120.
[5]畢德廣.以“物”見“文”:沈從文文物研究的成就和意義[D].曲阜:曲阜師范大學,2008.
[6]張鑫,李建平.沈從文物質文化史研究與三重證據法的理論與實踐[J].吉首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2(6):28.
[7]沈從文.沈從文全集(1-27卷及附卷)[M].太原:北岳文藝出版社,2002.
[8]趙憲章.文學和圖像關系研究中的若干問題[J].江海學刊,2010(1):185.
[9]趙憲章.語圖傳播的可名與可悅——文學與圖像關系新論[J].文藝研究,2012(11):28.
[10]錢穆.中國學術通義·四部概論[M]//羅志田.近代中國史學十論.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3.
[11]王亞蓉.沈從文晚年口述(增訂本)[M].北京:商務印書館,2014.
[12]黃裳.沈從文和他的新書——讀《中國古代服飾研究》[J].讀書,1982(6):48-50.
[13]汪曾祺.晚翠文談新編[M].北京:三聯書店,2001.
I207.6
A
2095-0438(2017)12-0049-04
2017-08-16
吳丹(1991-),女,土家族,湖南張家界人,吉首大學文學與新聞傳播學院2015級碩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文藝美學、中國現當代文學。
湖南省2016年研究生科研創新項目(CX2016B622)。
[責任編輯 王占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