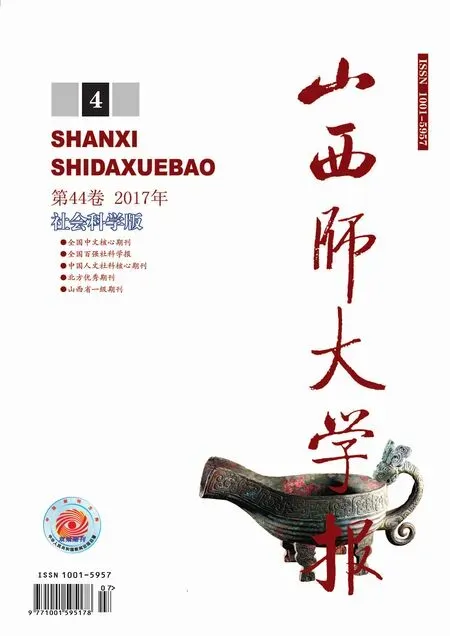略論西方哲學(xué)的兩條思想之路:從本原出發(fā)與通向本原之路
宋清華,張?zhí)鹛?/p>
(河南科技大學(xué) 馬克思主義學(xué)院,河南 洛陽(yáng) 471003)
西方哲學(xué)是一種溯本追源的理論,這是自古希臘哲學(xué)以來(lái)就確立起來(lái)的傳統(tǒng),也是整個(gè)西方哲學(xué)的根本脈絡(luò)。這種傳統(tǒng)無(wú)疑是由古希臘最先確定的,在教父哲學(xué)、中世紀(jì)哲學(xué)的神學(xué)理論中得到進(jìn)一步發(fā)展,而近代哲學(xué),從笛卡爾哲學(xué)強(qiáng)調(diào)要尋求一個(gè)“不可動(dòng)搖之根基”,到德國(guó)古典哲學(xué)探討“最高原理”,都滲透著這種追溯本原的精神。
西方哲學(xué)的這種溯本追源的精神最初是由古希臘七賢之一的泰勒斯開(kāi)啟的,然后在其他哲學(xué)家那里進(jìn)一步發(fā)揚(yáng)光大,但真正將其明確地概括出來(lái)的則是柏拉圖。柏拉圖認(rèn)為,哲學(xué)的道路有兩條,即通向本原之路和回到本原之路。亞里斯多德明確指認(rèn)了這一點(diǎn),他說(shuō):“我們不要忽略,在從始點(diǎn)出發(fā)的論據(jù)同走向始點(diǎn)的論據(jù)之間存在著區(qū)別。這個(gè)問(wèn)題是柏拉圖正確地提出的。他經(jīng)常發(fā)問(wèn):正確的推理應(yīng)當(dāng)是從始點(diǎn)出發(fā),還是走向它?”[1]10對(duì)此,柏拉圖在其著作里做了許多探討,為以后西方哲學(xué)的發(fā)展定下了基調(diào),以至于幾乎所有的哲學(xué)家都在不同程度上受到這一思想的影響,或至少運(yùn)用這一方法從事哲學(xué)研究。
一、古希臘時(shí)期對(duì)本原問(wèn)題的求索——從本原出發(fā)之路
西方哲學(xué)史家康福德認(rèn)為,哲學(xué)的史前史應(yīng)該從神話(huà)開(kāi)始。他說(shuō):“在絕大多數(shù)有關(guān)起源的問(wèn)題中,歷史讓我們失望;我們尋找的有關(guān)傳統(tǒng)的早期聯(lián)系的因緣隱藏在史前的黑暗中。”“當(dāng)我們將它作為一種需要追問(wèn)的現(xiàn)象并將它與希臘思想的其他活動(dòng)和產(chǎn)物聯(lián)系起來(lái)時(shí),至少我們開(kāi)始非常有效地,然而也是很少地了解到一些有關(guān)整個(gè)過(guò)程中最初階段的事情。”[2]1—2“這個(gè)最初階段的事情”就是神話(huà)。根據(jù)赫西俄德的《神譜》的說(shuō)法,世界最初是從混沌逐漸演化出來(lái)的,“最早生出的是混沌,接著便是寬胸的大地那所有永生者永遠(yuǎn)牢靠的根基——永生者們住在積雪的奧林匹斯山頂,道路通闊的大地之下幽暗的塔耳塔羅斯;還有愛(ài)若斯,永生神中數(shù)他最美,他使全身酥軟,讓所有神和人思謀和才智盡失在心懷深處。虛冥和漆黑的夜從混沌中生。天光和白天又從黑夜中生,她與虛冥相愛(ài)交合,生下他倆……”[3]100—101可見(jiàn),神話(huà)的世界也是由最初的混沌產(chǎn)生而來(lái),這就為此后哲學(xué)對(duì)本原或根源的探求或追思提供了范例。
但米利都派的哲學(xué)家則是從自然而非神的角度來(lái)思考本原的。這是古希臘最早擺脫神話(huà)、開(kāi)始理性思維的象征,也是人類(lèi)思維的一大跨越。康福德稱(chēng)之為“自然的時(shí)代”,“指的是整個(gè)世界的發(fā)現(xiàn),我們的感覺(jué)給我們關(guān)于這個(gè)世界的任何知識(shí)都是自然的,而不是部分是自然的、部分是超自然的。當(dāng)人們將宇宙看成一個(gè)自然整體、有其自身恒定的方式時(shí),科學(xué)就開(kāi)始了。這種方式也許能被人的理性所認(rèn)清,卻不受人類(lèi)行為的控制。認(rèn)識(shí)到這一點(diǎn)是一個(gè)偉大的成就。如果我們要衡量它的重要性,就必須簡(jiǎn)單回顧一下前科學(xué)時(shí)代的某些特征。這些特征是:(1)自我與外在客體的分離——客體的發(fā)現(xiàn);(2)在對(duì)待客體時(shí),與行為的功利性需求相伴而來(lái)的智力偏見(jiàn);(3)對(duì)無(wú)形的超自然的信仰總是處于需要對(duì)待的客體之后或其中。”[4]5康福德認(rèn)為這實(shí)際上就否定了經(jīng)驗(yàn)和宗教啟示兩種知識(shí)及自然狀態(tài)與超自然狀態(tài)之間的差別,這標(biāo)志著希臘科學(xué)的誕生。愛(ài)奧尼亞學(xué)派的宇宙起源論假定整個(gè)宇宙是自然的,并隱藏在知識(shí)范圍內(nèi)。由此,自然的概念被延伸到超自然所占據(jù)的領(lǐng)地。超自然的東西因此而消失或隱退,所有真實(shí)存在的東西都是自然的。這種觀點(diǎn)無(wú)疑是一場(chǎng)偉大的革命。
當(dāng)?shù)谝晃徽軐W(xué)家泰勒斯提出水是世界的本原時(shí),他無(wú)疑展示了這種理性思維,神開(kāi)始從宇宙或世界中退隱到幕后,自然開(kāi)始成為主宰者,成為本原。選擇水作為本原,既有經(jīng)驗(yàn)觀察的結(jié)果,也有神話(huà)傳統(tǒng)的影響。從前者看,正如亞里斯多德所言,可能是泰勒斯通過(guò)觀察發(fā)現(xiàn),萬(wàn)物都有種子,種子都是在濕潤(rùn)的情況下滋生的,而水則是濕潤(rùn)的本質(zhì)。同時(shí),希臘民族所生活的特有環(huán)境也與海洋、水有著密切的關(guān)聯(lián)性。從后者看,在希臘神話(huà)中,都強(qiáng)調(diào)海洋之神、河流之神的原始性,甚至神話(huà)中的誓言也都是對(duì)著水起誓的。康福德和其他西方古典學(xué)者更證明,在古埃及神話(huà)中,就有水是諸神和萬(wàn)物的本原之說(shuō)。埃及神話(huà)對(duì)古希臘神話(huà)具有極大影響,這是公認(rèn)的。[5]162—163可見(jiàn),水本原思想的提出還有神話(huà)影響的痕跡。
此后,阿那克西曼德提出了無(wú)定形或無(wú)限乃是萬(wàn)物的本原,據(jù)說(shuō),“本原”一詞也是由其提出的。他的無(wú)定形說(shuō)是對(duì)泰勒斯水本原的進(jìn)一步解釋。他認(rèn)為,水是無(wú)定形的,運(yùn)動(dòng)的,所以才能產(chǎn)生萬(wàn)物,然后一切又復(fù)歸為水。本原一定是一個(gè)無(wú)形的東西,唯此,它才有資格成為萬(wàn)物的本原,因?yàn)橛行沃锸菑臒o(wú)形之物中產(chǎn)生出來(lái)的。對(duì)阿那克西曼德來(lái)說(shuō),任何具體的事物都是有限的或者有定形的,但任何有定形的東西就不可能再是別的事物了。因此,它不能成為萬(wàn)物的本原。人們不能用有限之物來(lái)解釋有限之物,只能用無(wú)限之物來(lái)解釋有限之物。由此,阿那克西曼德開(kāi)創(chuàng)了一種新的生滅觀,所謂“生”就是萬(wàn)物從無(wú)定形中分離出來(lái),獲得某種規(guī)定性,成為某物;所謂“滅”,就是去掉規(guī)定性,重新回到無(wú)定形的狀態(tài)中。換句話(huà)說(shuō),生就是從無(wú)限到有限,滅就是從有限重新回歸到無(wú)限。這是一個(gè)根本性的哲學(xué)突破,他的無(wú)定本原說(shuō)使古希臘從自然哲學(xué)理論直接躍升到形而上學(xué)的高度。特別是他第一個(gè)提出了關(guān)于世界的性質(zhì)的系統(tǒng)理論——既涉及到它的組成材料,還關(guān)聯(lián)到它從無(wú)限之物演變?yōu)榫唧w事物的過(guò)程,并賦予這種過(guò)程乃是命運(yùn)法則的體現(xiàn)和道德律則的展示:“根據(jù)命中注定,事物毀滅變成它們由其中誕生的那些東西;因?yàn)楦鶕?jù)時(shí)間的安排,它們向他者進(jìn)行補(bǔ)償,并為它們的不義付出代價(jià)。”[2]8或許,阿那克西曼德最打動(dòng)我們的是他描述事物的誕生和毀滅過(guò)程中所使用的語(yǔ)言,事物消失變成元素被視之為“為不義付出代價(jià)”“進(jìn)行補(bǔ)償”等。它表明,在它們的誕生過(guò)程中實(shí)行了不義的行為,需要懲罰或補(bǔ)償恢復(fù)正義。在他看來(lái),整個(gè)多樣的世界只可能產(chǎn)生于搶奪和盜取這些不義的行為。
人們可以想象動(dòng)物的軀體,它正當(dāng)?shù)奈镔|(zhì)是土,但為了構(gòu)成它的軀體,它盜用了其他元素:水用于血,氣用于呼吸,火用于溫暖,最后的死亡及其分解則償還了這些搶劫。由此我們發(fā)現(xiàn),世界演進(jìn)的基本狀況是:被稱(chēng)為“自然”的原初材料,被分隔為不同的區(qū)域,每一種元素統(tǒng)治一個(gè)區(qū)域。這是一個(gè)連續(xù)的道德秩序,在這種意義上,越過(guò)元素的分界,一個(gè)元素掠奪另一個(gè)元素形成的個(gè)體就是不義的、邪惡的。懲罰即是死亡和分解。沒(méi)有事物能夠違背這個(gè)命定的秩序而獨(dú)自存在。誕生是一種罪惡,成長(zhǎng)是侵略性的掠奪。因此,世界被視為一種從最初的無(wú)序或混亂中形成的復(fù)雜秩序。從元素區(qū)分的簡(jiǎn)單分類(lèi)向獨(dú)特事物的多樣性發(fā)展的每一步,都是一種越界,一種向無(wú)序的發(fā)展,一種向不義、掠奪和戰(zhàn)爭(zhēng)的混亂的衰退。同時(shí),這種錯(cuò)誤的朝圣之旅的每一步都根據(jù)“那被命定的”必然會(huì)被重復(fù),命運(yùn)和正義這兩個(gè)概念在這個(gè)詞里被結(jié)合起來(lái)。它意味著一種規(guī)定了必須是什么和應(yīng)當(dāng)是什么的力量。命運(yùn)和正義的原則已經(jīng)為原初的元素秩序設(shè)定了界限,等待著對(duì)每一次越界進(jìn)行嚴(yán)格的懲罰,主持物質(zhì)世界秩序的力量是道德。這樣,世界從無(wú)定形中產(chǎn)生又復(fù)歸為無(wú)定形,這既被看做是命運(yùn)的規(guī)定,又是道德秩序和正義的體現(xiàn),這種神秘的命運(yùn)觀與希臘神話(huà)和悲劇中的命運(yùn)主題具有某種內(nèi)在的關(guān)聯(lián)性,而且對(duì)后來(lái)的畢達(dá)哥拉斯的“數(shù)”、赫拉克利特的“邏各斯”等形而上學(xué)的實(shí)體產(chǎn)生了重要影響。
此后,阿那克西美尼的氣本原說(shuō)、赫拉克利特的火本原說(shuō)和邏各斯的思想、恩培多克勒的四根說(shuō)、阿那克薩戈拉的種子說(shuō)、留基伯和德謨克利特的原子說(shuō),都以某種或某幾種自然物作為構(gòu)成萬(wàn)物的本原或始基,也就是說(shuō),都是從本原出發(fā)推演出萬(wàn)事萬(wàn)物,最后又回歸到本原。這是自然哲學(xué)家主要的本原說(shuō)理論進(jìn)路,其基本邏輯是從一種或多種自然物——始基演化出整個(gè)世界。在這種演化過(guò)程中,又以命運(yùn)和邏各斯作為代表正義、必然性的道德力量來(lái)解說(shuō)世界的發(fā)展過(guò)程,這就構(gòu)成了自然哲學(xué)本原說(shuō)理論的基本特征。
而畢達(dá)哥拉斯學(xué)派和愛(ài)利亞學(xué)派雖然也是從本原出發(fā)來(lái)推演宇宙生成的過(guò)程,但他們又與自然哲學(xué)有著極大的差別性——這種差別主要表現(xiàn)在后者主要將某種或某幾種自然物作為始基,而前者則將某種抽象物或客觀的精神作為世界的始基,其對(duì)推動(dòng)人類(lèi)理性思維更加邏輯化和促使人類(lèi)思維向更深層次發(fā)展方面都要遠(yuǎn)遠(yuǎn)高于自然哲學(xué)家的理論。
畢達(dá)哥拉斯開(kāi)創(chuàng)了一條注重事物背后的抽象實(shí)體的形而上學(xué)之路,它是與自然哲學(xué)還原論完全不同的路徑。希臘哲學(xué)的主要目標(biāo)是探尋萬(wàn)物的本原,在這一目標(biāo)的主導(dǎo)下,自然哲學(xué)著重于理清一與多的關(guān)系,形而上學(xué)則更加關(guān)注思考現(xiàn)象與本質(zhì)的關(guān)系問(wèn)題。自然哲學(xué)在德謨克利特的原子論中實(shí)現(xiàn)了一與多的統(tǒng)一。希臘的形而上學(xué)在其初始期(如畢達(dá)哥拉斯)就直接把“一”作為世界的本原。但這個(gè)“一”,不同于自然哲學(xué)的某種具體物質(zhì)形態(tài),乃是抽象的數(shù),是不生不滅、始終如一、永恒存在的本質(zhì)。在此意義上講,它也是整個(gè)世界必須遵守的邏各斯或命運(yùn)。由此,從畢達(dá)哥拉斯的數(shù)和比例出發(fā),就順理成章地進(jìn)入到了赫拉克利特的尺寸、尺度或邏各斯的概念。
在赫拉克利特那里,世界既是一團(tuán)永恒的不斷燃燒、不斷熄滅的活火,而火與萬(wàn)物的相互轉(zhuǎn)化又是受邏各斯的制約的。這就體現(xiàn)為復(fù)雜多變的自然之物與永恒不變、單一的邏各斯之間的兩條線(xiàn)索,赫拉克利特視邏各斯為萬(wàn)物背后不出場(chǎng)的主宰者,他深受畢達(dá)哥拉斯的數(shù)本原說(shuō)的影響。火與邏各斯之間的關(guān)系,同具體事物與數(shù)的關(guān)系具有同構(gòu)性。然而,赫拉克利特又?jǐn)[脫不了米利都學(xué)派的影響,故此,赫拉克利特認(rèn)為火本原說(shuō)與邏各斯規(guī)定論就同時(shí)存在。盡管他更強(qiáng)調(diào)邏各斯的重要性,但并不妨礙他承認(rèn)火與萬(wàn)物之間的轉(zhuǎn)化也是真實(shí)存在的。同時(shí),對(duì)赫拉克利特來(lái)說(shuō),正義是一種在各元素領(lǐng)域內(nèi)通行無(wú)阻的生命力量,它按照規(guī)定的程序經(jīng)歷每一階段和形式。他強(qiáng)調(diào),正義或和諧就是邏各斯,是生命的真諦,是恒定的量,并可以穿越所有障礙。它是神圣的靈魂物質(zhì),其生命在于運(yùn)動(dòng)和變化。它也是神圣的法,自然之法(physis),神的意愿。它是遵循“一”的意志的法。這個(gè)法則不僅僅對(duì)人類(lèi)社會(huì)適用,它放之宇宙而皆準(zhǔn),它適用于萬(wàn)物,“那些想要理解宇宙的人必須謹(jǐn)記什么是適用于萬(wàn)物的,如同一個(gè)城市要謹(jǐn)守法規(guī),甚至要比這個(gè)更嚴(yán)謹(jǐn)。人類(lèi)所有的法律法規(guī)都來(lái)自于‘一’的神圣法則,它勝過(guò)一切,滿(mǎn)足所有的盈余。”[2]195這一思想在柏拉圖的《克拉底魯篇》中被完整地保存下來(lái)。在討論正義一詞的起源時(shí),蘇格拉底說(shuō)道,那些認(rèn)為萬(wàn)物都是處于運(yùn)動(dòng)中的思想家們認(rèn)為,某種事物穿越了宇宙,它是萬(wàn)物之因。它是事物中最敏捷和微妙的,沒(méi)有哪個(gè)事物能將它拒之門(mén)外,而它讓其他物體看上去像靜止了一樣。它統(tǒng)攝萬(wàn)物并穿越其中,這就是我們所說(shuō)的“正義”。需要指出的是,赫拉克利特是一位思想極為深邃的哲學(xué)家,他不僅提出了火是世界的本原說(shuō),更明確指出,宇宙的演化遵從邏各斯,而邏各斯不僅是火與萬(wàn)物相互轉(zhuǎn)化的規(guī)律,也是我們思維和言說(shuō)的規(guī)律。同時(shí),他還是古代辯證法的創(chuàng)始人,其思想介于自然哲學(xué)和畢達(dá)哥拉斯及愛(ài)利亞學(xué)派之間,具有承上啟下的作用,對(duì)后世哲學(xué)影響極為深遠(yuǎn)。
與自然哲學(xué)家和其他學(xué)派不同,愛(ài)利亞學(xué)派的哲學(xué)家則開(kāi)創(chuàng)了一條形而上學(xué)的本原之路,其特點(diǎn)是強(qiáng)調(diào)本原乃是一種永恒不變的“一”,并且這種本原只能通過(guò)思想才能達(dá)到。這種傳統(tǒng)最先由克賽諾芬尼開(kāi)啟,后由其弟子巴門(mén)尼德進(jìn)一步發(fā)揚(yáng)光大。克賽諾芬尼凝視著浩瀚天空,宣稱(chēng)這就是一,也就是神。神是不生不滅、獨(dú)一無(wú)二,也就是一,并且只能借助思想才能認(rèn)識(shí)。巴門(mén)尼德繼承并發(fā)展了這一思想,他用六步韻的詩(shī)體寫(xiě)了一部哲學(xué)著作,描述了它怎樣遇見(jiàn)了一位女神將其領(lǐng)入智慧的殿堂,使他認(rèn)識(shí)了真理,并意識(shí)到其他哲學(xué)家對(duì)于本原的認(rèn)識(shí)都不過(guò)是意見(jiàn),他把對(duì)“存在”本身的認(rèn)識(shí)(思想)稱(chēng)為真理,“真理”已不再是“存在”自己有能力顯露出來(lái)的,需要靠人們的思想思考它,要用推理做出判斷,用語(yǔ)言表達(dá)它,它才能顯露出來(lái)。這就是真理之路。另一條路則受感覺(jué)支配,是錯(cuò)誤之路。希臘文的“意見(jiàn)”一詞本是期待、希望的意思,但期待、希望總是偏重于自己所愿望的方面,具有主觀性。于是,“意見(jiàn)”就被引申為某種“想法”“幻想”“猜想”“欲求”之意。再一轉(zhuǎn)就成為“意見(jiàn)”“見(jiàn)解”“看法”了。巴門(mén)尼德吸取了克賽諾芬尼有關(guān)“意見(jiàn)”的思想,認(rèn)為意見(jiàn)是因人而異的,具有不確定、不可靠性。正因?yàn)榇耍庖?jiàn)之路不可取。所以借助于推理,他以其嚴(yán)密冷靜的邏輯論證了統(tǒng)一、完美、神圣的“一”(存在)的特征,拒絕并否定了“多”、非連續(xù)性以及生命的變化運(yùn)動(dòng)。這與赫拉克利特的體系、愛(ài)奧尼亞的學(xué)說(shuō)以及早期的畢達(dá)哥拉斯主義試圖將“一”以某種方式發(fā)展為“多”的思想截然對(duì)立。巴門(mén)尼德的“一”,就是畢達(dá)哥拉斯學(xué)派中的單子,但它不再是“永遠(yuǎn)流動(dòng)的本質(zhì)之泉”。源于“一”的整個(gè)數(shù)列說(shuō)被剪除,因?yàn)橐徊辉倌鼙3肿陨韮?nèi)部繁殖的原則;因?yàn)樗峭耆珖?yán)格的一,對(duì)立之物與“多”不再是其固有的內(nèi)在本性,也不再能從中產(chǎn)生。
總之,愛(ài)利亞學(xué)派開(kāi)創(chuàng)了一條摒棄具體物質(zhì)形態(tài)的本原之路,它探尋的不再是某種具體物質(zhì)形態(tài)的本原,而是某種不變的、不朽的而又具有客觀性的存在,這種存在不能通過(guò)感覺(jué)感知,只能通過(guò)理性思維才能通達(dá)。它強(qiáng)調(diào)存在是一,而非多,從一不能產(chǎn)生多,這種思想不僅深化了古希臘的哲學(xué)理論,更為重要的是它強(qiáng)調(diào)必須通過(guò)理性思維才能達(dá)到真理。也正因?yàn)榇耍瑦?ài)利亞學(xué)派的哲學(xué)理論成為希臘形而上思想發(fā)展的重要推手。
二、通向本原之路
其實(shí),在古希臘哲學(xué)家那里,從本原出發(fā)和通向本原之路是同一條路。赫拉克利特就強(qiáng)調(diào)“上升的道路和下降的道路是同一條路”[6]301。同樣,在泰勒斯、阿那克西曼德、阿那克西美尼、恩培多克勒等自然哲學(xué)家那里都持這種理論。柏拉圖的本原說(shuō)也支持這種理論,“走向本原的道路”和“從本原出發(fā)之路”是同一條路,只不過(guò)方向恰恰相反而已。本文之所以將之分開(kāi)討論旨在說(shuō)明西方哲學(xué)探索的兩條不同方向之路是后世哲學(xué)或隱或顯的線(xiàn)索,也是理解西方哲學(xué)的鑰匙。
明確并詳細(xì)說(shuō)明哲學(xué)的兩條路的是柏拉圖。他不僅對(duì)從本原出發(fā)之路給予了充分的分析和說(shuō)明,而且還對(duì)通向本原之路作了進(jìn)一步的理論解說(shuō)。大家知道,柏拉圖哲學(xué)的基本立場(chǎng)是超驗(yàn)論的,通過(guò)思維和理解來(lái)把握那真實(shí)的、永恒不變的東西。相較于巴門(mén)尼德的思想,柏拉圖的偉大之處在于他提出了理念論,通過(guò)理念把一與多、普遍與個(gè)別、抽象和具體統(tǒng)一起來(lái)。而巴門(mén)尼德還僅僅拘泥于一般意義上的空洞存在。
柏拉圖的理念說(shuō)在其早期對(duì)話(huà)作品里就開(kāi)始觸及這一問(wèn)題,它是一種凌駕于個(gè)別事物之上的東西,代表著本質(zhì)、統(tǒng)一性、整體性的更高存在。盡管柏拉圖最后都沒(méi)有給出最后的回答,常常以疑難困惑的形式結(jié)束談話(huà)。這并不一定就表示其思想尚未成熟,更可能是因?yàn)榘乩瓐D在不同層面上對(duì)不同的讀者群進(jìn)行的設(shè)計(jì)或創(chuàng)作,因此在這些較為簡(jiǎn)單的談話(huà)中有意保留明確的答案,但又給予更多的暗示,以導(dǎo)向一個(gè)更高的統(tǒng)一體。基于此,我們可以對(duì)這一階段的理念予以描述,它應(yīng)具有如下特征:
其一,它是一個(gè)普遍且完整的東西可被許多個(gè)別事物分有。如“德性”本身可以被“勤勞”“公正”“節(jié)制”“勇敢”“智慧”等分有,這些東西因分有了德性都成為了德行。其二,它是一個(gè)“原型”或“相”,個(gè)別事物是對(duì)它的“模仿”。如各種桌子是對(duì)“桌子”理念的模仿。其三,它是個(gè)別事物的本質(zhì)或本質(zhì)存在。它使得分有它的具體事物成為它所是的東西。比如分有“牛”本身就使得具體的公牛、母牛成為了它們所是的個(gè)體。
此后,在《斐多》《理想國(guó)》等以更多知識(shí)和訓(xùn)練為前提的對(duì)話(huà)里,柏拉圖就更清楚地描述了理念及理念與真知的關(guān)系。《斐多》里的一些段落是與著名的“第二次航行”比喻密切關(guān)聯(lián)的。為了回答人們對(duì)“靈魂不朽” 的質(zhì)疑,蘇格拉底需要回到一個(gè)重大的問(wèn)題:“這里涉及到整個(gè)出生和毀滅的原因。”[8]104然后,它描述了蘇格拉底年輕時(shí)期的求學(xué)經(jīng)歷。早期的自然哲學(xué)家有關(guān)本原的思想并不能令其滿(mǎn)意,他決定進(jìn)行一場(chǎng)以“探究本原”為目的的“第二次航行”。在這次航行中,柏拉圖提出了一種簡(jiǎn)單的、樸素的方法,即通過(guò)“理念”來(lái)把握事物的本質(zhì)。任何事物之所以是其所是,不是因?yàn)閯e的,乃是因?yàn)樗钟辛四硞€(gè)理念:“絕對(duì)的美之外的任何美的事物之所以是美的,那是因?yàn)樗鼈兎钟薪^對(duì)的美,而不是因?yàn)閯e的原因。”[8]109蘇格拉底的這段學(xué)習(xí)經(jīng)歷至少說(shuō)明了以下幾點(diǎn)思想:追尋事物生滅背后的永恒原因或本原;“理性”本身雖然是個(gè)好答案,但單一的理性無(wú)法解釋千差萬(wàn)別的事物;需要找到一些理性層面上的存在即理念作為答案。另外,“第二次航行”還有其他含義。在希臘文里,“第二次航行”本是一個(gè)與航海相關(guān)的詞語(yǔ),意思是“第二好的”“次佳的”航海方式。如順風(fēng)揚(yáng)帆是“最佳的方式”,而無(wú)風(fēng)時(shí),只能鼓風(fēng)揚(yáng)帆,這是“次佳的”航行方式。這一詞語(yǔ)被用于許多地方,基本含義是,假若不能達(dá)至最佳的狀態(tài)或獲得最好的事物,則不如退而求其次,爭(zhēng)取次好的事物或狀態(tài)。在此,柏拉圖強(qiáng)調(diào)的是,必須從感覺(jué)退回到思想中去,通過(guò)思想來(lái)把握事物的真實(shí)本質(zhì)。在《理想國(guó)》里,柏拉圖提出了最高本原乃是“善的理念”。雖然他并沒(méi)有說(shuō)明善的本質(zhì)是什么,但卻明確指出它可以通過(guò)不斷的上升的辯證法而獲得。辯證法不是一種直觀,而是一種思維,是一種把此前的思維過(guò)程涵括在其自身內(nèi)的不斷上升的思維過(guò)程。
但理念的發(fā)現(xiàn)并不是柏拉圖的最高或最終的本原,其最終的本原則另有歸屬,柏拉圖借助蘇格拉底之口揭明了這一問(wèn)題,在《斐多》一書(shū)中,蘇格拉底指出:“如果還有必要為那個(gè)前提(理念說(shuō))自身提供解釋的話(huà),那么你將以同樣的方式給出解釋?zhuān)刺岢鲆恍└叩那疤幔缓笤谶@些更高的前提里面提出一個(gè)稱(chēng)得上最好的前提,直到你找到這樣一個(gè)滿(mǎn)足所有方面的前提。”[8]111這段話(huà)向人們揭示了在理念之上還有更高的甚至是最好的前提或本原。那么這個(gè)最高的本原是什么呢?柏拉圖的學(xué)生亞里斯多德曾揭示過(guò)其答案:“在那些認(rèn)為不動(dòng)的實(shí)體存在的人們中,有人說(shuō)一自身就是善自身,不過(guò),他們認(rèn)為善的實(shí)質(zhì)就是單一。”[7]332
根據(jù)圖賓根學(xué)派的研究,柏拉圖的所謂從本原出發(fā)之路,就是指依據(jù)兩個(gè)最終本原,逐級(jí)推導(dǎo)出數(shù)、理念、數(shù)學(xué)對(duì)象、感性事物等[6]第四章。由此可以說(shuō),柏拉圖的哲學(xué)理論究其本質(zhì)來(lái)說(shuō),乃是一個(gè)演繹系統(tǒng)。本原先是派生出數(shù),這里的本原是兩個(gè),即“二”,它們不是數(shù)學(xué)上的“2”,而是一種絕對(duì)的無(wú)規(guī)定性,介于無(wú)窮的大和小之間,能夠任意分割,為“多”“量”的生成提供了最初的可能性。與之相反,巴門(mén)尼德的“一”則是絕對(duì)不可分、永恒不變的單元,純粹的規(guī)定性。根據(jù)阿弗羅迪希亞的亞歷山大、辛普里丘和恩皮里克等人的記述,柏拉圖認(rèn)為,通過(guò)“一”與“二”的結(jié)合,或者“一”對(duì)“二”的規(guī)定,生成的第一個(gè)數(shù)為“2”,依據(jù)同樣的形式,一對(duì)二不斷地進(jìn)行限定并產(chǎn)生新的兩個(gè)數(shù),所有其他數(shù)都從這兩個(gè)本原中生成出來(lái),直至無(wú)窮。由此,我們可以看到,一并不是第一個(gè)數(shù),甚至不是數(shù);同時(shí),每一個(gè)數(shù)都具有唯一性,都是一,體現(xiàn)著一的規(guī)定性。正像亞里斯多德所指出的那樣,柏拉圖的哲學(xué)理論中,一直使用兩個(gè)本原,“一”作為本質(zhì)因(或形式因),“二”作為質(zhì)料因。以同樣的方式,產(chǎn)生諸多理念和數(shù)學(xué)的對(duì)象。
亞里斯多德在評(píng)述柏拉圖的學(xué)說(shuō)時(shí)指出:“(對(duì)于其他事物來(lái)說(shuō),形式是事物是什么的原因,一又是形式的原因。)……一對(duì)形式加以述說(shuō),在這里雙數(shù)就是大和小。他還把兩種元素當(dāng)作善和惡的原因。”[7]45需要說(shuō)明的是,古希臘哲學(xué)家一向把“原因”“元素”“本原”等概念當(dāng)作同義詞來(lái)用。所以亞里斯多德這段話(huà)談的都是本原問(wèn)題。根據(jù)亞里斯多德的記述,柏拉圖盡管把理念視為其他事物的本原,但理念本身也依賴(lài)于某些本原,這些本原即是“大和小”和“一”,它們不僅是理念的本原,而且通過(guò)理念的中介成為所有事物的本原。他們“把一當(dāng)作形式的質(zhì)料,……他們把形式當(dāng)作其他每個(gè)事物的是其所是,把一當(dāng)作那些形式的是其所是”[7]46。同樣,柏拉圖認(rèn)為,根本上的質(zhì)料乃是二,即“大和小”,靠著它,理念在其他事物身上體現(xiàn)出來(lái)。
將這兩段話(huà)結(jié)合起來(lái)看,就能發(fā)現(xiàn),柏拉圖把“一”和“二”(即大和小)置于理念之上,前者規(guī)定了理念和萬(wàn)物的“何所是”或“本質(zhì)”,后者為理念和萬(wàn)物提供了質(zhì)料。換句話(huà)說(shuō),“一”和“二”是比理念更根本的本原。這就顛覆了人們通常的看法,即認(rèn)為理念是柏拉圖哲學(xué)中的最高本原。其實(shí),柏拉圖心目中的最高本原另有所指。需要指出的是,“一”和“二”的并存顯然意味著二元論,但從存在的階次看,那居于最高峰的“一”規(guī)定這一切,本身不接受任何他者的規(guī)定(而“二”必須接受規(guī)定),故此可以從它的至高無(wú)上而又獨(dú)一無(wú)二的地位出發(fā),稱(chēng)這種學(xué)說(shuō)為一元論。鑒于此,我們?cè)诖艘环矫姘寻乩瓐D的本原說(shuō)界定為“二元本原說(shuō)”,把“一”和“二”看作最終本原,但另一方面,唯有“一”才有資格成為“最高本原”。
所以其最高本原就是兩個(gè),即“一”與“大和小”。據(jù)此可將其本原說(shuō)概括為:其一,有兩個(gè)最高的本原:“一”與“大和小”或“不定的二”;其二,整個(gè)存在是從“可感事物”開(kāi)始,歷經(jīng)“數(shù)學(xué)對(duì)象”“理念”“數(shù)”,最后到“本原”的金字塔形結(jié)構(gòu),所有存在都是“一”與“多”的混合,其層次的高低取決于統(tǒng)一性的高低;其三,借助辯證法實(shí)現(xiàn)“向著本原回歸之路和從本原出發(fā)之路”;其四,此種二元本原和“一與多”的辯證法在全部實(shí)踐領(lǐng)域中的實(shí)施。[9]
至此,到柏拉圖這里,通向本原之路得到了最為明確的表達(dá),并在理論上給予了比較完善的解釋?zhuān)灿纱说於宋鞣秸軐W(xué)通向本原的形而上之路,對(duì)后世哲學(xué)產(chǎn)生了極為深遠(yuǎn)的影響。
三、西方哲學(xué)為何要追尋這兩條路
西方哲學(xué)所追尋的兩條路,幾乎在后世的每個(gè)哲學(xué)家的思想中都能發(fā)現(xiàn),似乎是宿命般地糾纏著哲學(xué)家們,好像是他們無(wú)法擺脫的夢(mèng)魘。其實(shí),這是有其深刻原因的。
(一)從本原出發(fā)之路
首先,從本原出發(fā),是為了保持與根源的密切關(guān)聯(lián)性,以獲取永不枯竭的思想之源。由于根源是根,是本,更是源,由根可生枝節(jié);由本可生造化,化育萬(wàn)千事物;由源可生許多支流,形成萬(wàn)千江河湖泊。以此而論,與根源的聯(lián)系,可獲得無(wú)盡的資源,無(wú)論對(duì)思想,還是對(duì)諸多事物,源、根、本,都是萬(wàn)物得以發(fā)生、化育或發(fā)育之基,唯有與它密切相關(guān)聯(lián),才能形成無(wú)窮的造化和生機(jī),才能形成萬(wàn)千的氣象,才能孕育出無(wú)窮的智慧和思想,這或許是西方哲學(xué)總喜歡從本原出發(fā)的一個(gè)重要原因。
其次,從本原出發(fā),是為了獲得合法性。古希臘哲學(xué)強(qiáng)調(diào)本原的唯一性、絕對(duì)性,即至高無(wú)上性,這種規(guī)定最早源于神話(huà)思想,它是世界誕生于混沌的另一種表述方式。而神與根源是共在的,由此,從根源處出發(fā)就有了神圣性的特征。神的存在保證了由此而出的東西也具有了神圣性的色彩,這種神圣性色彩盡管不是神圣本身,但足以保證它的法理上的正統(tǒng)性,也就是由神圣性而提供的合法性保證,從而獲得了毋容置疑的地位。
其三,從本原出發(fā),還可以獲得合理性。由于根源是源頭,由源頭流溢處的東西具有絕對(duì)性和純粹性,它不會(huì)沾染任何經(jīng)驗(yàn)世界的東西。這種不與經(jīng)驗(yàn)雜染的特性,使它借助理性的思辨邏輯,很容易獲得具有普遍性、必然性的形式。這種形式的東西既與源頭相關(guān)聯(lián),又由理性的思辨邏輯而獲得;既有思想源頭的純正性保證,使其出處有根有據(jù),保證了其合法性,又通過(guò)理性的認(rèn)知獲得了這種真理性或善的東西,從而也有了普遍必然性的特征,這就使得其自身獲得了真正的合理性。
(二)向本原*這里,我們需要交代一下本源與本原的替換問(wèn)題。本源論理路是追溯時(shí)間上在先的原始存在。但本源這種存在乃是超驗(yàn)物,它既不在我們的經(jīng)驗(yàn)世界中,又不是我們感覺(jué)的對(duì)象。人們無(wú)法用感覺(jué)經(jīng)驗(yàn)確定其存在,也無(wú)法對(duì)其形成任何知識(shí)。本源是思想對(duì)象,而非經(jīng)驗(yàn)對(duì)象。它的規(guī)定性不能通過(guò)經(jīng)驗(yàn)來(lái)描述,只能在論證中呈現(xiàn)之。巴門(mén)尼德對(duì)本源做了一些論證和規(guī)定,指出它首先是不生不滅的。認(rèn)為它無(wú)論過(guò)去、現(xiàn)在和將來(lái),人們都無(wú)法談?wù)摫驹吹漠a(chǎn)生問(wèn)題。因此,它作為原始的存在,一定不是生出來(lái)的。而且它還必須是不會(huì)滅亡的。否則,它就是一個(gè)無(wú)。“無(wú)”不能成為我們認(rèn)識(shí)的對(duì)象。其次,本源是一。本源作為原始存在必須是單一的,任何兩個(gè)本源的說(shuō)法都會(huì)使人們?nèi)プ肪扛痈竞驮嫉拇嬖凇1驹粗荒苁且粋€(gè)。其三,本源必須是圓滿(mǎn)的,不能有任何的缺乏。此后,人們?cè)谡務(wù)撛即嬖跁r(shí),都堅(jiān)持巴門(mén)尼德關(guān)于“它”必須是不生不滅的論證。而不生不滅的原始存在自然不再是時(shí)間在先的存在,而是不在時(shí)間中的永恒存在。自此,人們就用“本原”來(lái)代替“本源”一詞.之路
首先,通向本原之路是為了尋求存在的根源,只有弄清了根源才能算是找到了根,尋到了源,回到了本,有根有源有本,才能使脈源相通,使脈和源相互交融,脈只有在源、根和本中才能保持自身的存在,獲得力量和無(wú)盡的支持,確認(rèn)自身的合理性、合法性。只有從根源處,才能找到源與流的關(guān)系,才能理清流在何處脫離了源或偏離了源,以便正本清源。事實(shí)上,在古希臘神話(huà)中,在源頭處往往有神靈的存在,神靈的存在則是保證脈源相通的根本。因此,回到源頭就是回到神圣那里,就是獲得存在的合理性、合法性之源、之本的保證。正因此,才有不斷回歸本原的追求,并成為西方哲學(xué)永遠(yuǎn)不竭的力量源泉。
其次,回到本原,乃是為了尋求自身存在的根據(jù)和行為的最高尺度。古希臘哲學(xué)家的本原是指現(xiàn)象世界的根源,這種根源除了指謂萬(wàn)物的源頭之意之外,還有根據(jù)和尺度的意思。這種尺度是存在者的最高尺度或根據(jù),因?yàn)樗莵?lái)自根源處,根源的唯一性也決定了根據(jù)、尺度的唯一性,它是最后的、無(wú)上的尺度,具有唯一性、至高性,而且不再有其他的根據(jù)在其上。同時(shí),這種唯一性也決定了它的純粹性,它不受任何經(jīng)驗(yàn)世界的影響,具有純粹性、先驗(yàn)性、形式性,也就是普遍必然性。它類(lèi)似柏拉圖的“善的理念”,是至高的、無(wú)上的。柏拉圖在界定真正的善時(shí),給出了一些標(biāo)準(zhǔn):其一,真正的善必須是純粹的、唯一的,不能包括任何惡的成分;其二,真正的善是永恒的、不變的;其三,真正的善是普遍的,具有必然性。因此,柏拉圖的這種思想在后世西方哲學(xué)那里就成為了真理的標(biāo)尺,這種影響在康德、黑格爾等哲學(xué)家那里都能發(fā)現(xiàn)。而來(lái)自根源處、與本源同在的根據(jù)、尺度自然就具有這些特征,并且因?yàn)樗c根源的這種同在性,就決定了它是所有存在者的最高或無(wú)上的尺度,唯有這種尺度的存在,才能保證從根源或本源處流溢出的萬(wàn)物以此根據(jù)或尺度,就能獲得善,就能有序和諧,就能保有與根源的相似性和關(guān)聯(lián)性,不至于出現(xiàn)大的變異,不至于背離根本。
再次,回到本原也是回到家園。每個(gè)存在者都有自己的出處,都有自己的家。家不僅僅是棲居處,不僅僅是港灣,也是靈魂和精神寄居之所。沒(méi)有了家,不僅意味著失去了棲居處、停泊棲棲的港灣,也意味著失去了靈魂和精神的寓所,靈魂和精神一旦沒(méi)有了家園,就會(huì)四處漂泊,變成孤魂野鬼,淪為無(wú)根、無(wú)家、無(wú)所的漂泊者。當(dāng)沒(méi)有任何依賴(lài)的時(shí)候,靈魂和精神就必然變異為絕望者或厭世者,最終成為社會(huì)和生活世界的破壞者。因此,必須給存在者找到自己的家園,找到其棲居地,安撫其肉體和靈魂。而本源的存在就為肉體、精神和靈魂提供了最好的庇護(hù)所,它不僅僅收容一切流離失所者,而且還給他們精神和靈魂的慰藉,靈魂和精神從此與肉體得以和諧地結(jié)合在一起。這種結(jié)合的力量就來(lái)自家園——本源,因?yàn)楸驹刺幱猩耢`的存在,神靈會(huì)給靈魂和精神以無(wú)盡的力量,會(huì)時(shí)時(shí)刻刻保佑或庇護(hù)著存在者,守護(hù)著他們的平安和幸福,幸福的原意是為善良的神靈所保佑。亞里斯多德也說(shuō),“如果有某種神賜的禮物,那么就有理由說(shuō)幸福是神賜的,尤其是因?yàn)樗侨怂鶕碛械淖詈玫臇|西。”[1]25
四、存在的問(wèn)題
西方哲學(xué)所遵循的這兩條路,無(wú)疑對(duì)其發(fā)展具有極為重要的意義,它既確定了西方哲學(xué)的范式,又提供了哲學(xué)研究的基本方法,同時(shí),也奠定了西方哲學(xué)的批判精神和批判性思維方式。無(wú)論西方哲學(xué)的發(fā)展遇到怎樣的困難,只要哲學(xué)家回歸到這兩條路,總是能夠找到新的出路或方法,從而使哲學(xué)度過(guò)危機(jī),找到新的發(fā)展路徑。這兩條神奇的路,似乎成了西方哲學(xué)永不枯竭的思想之源,不斷地豐富著其哲學(xué)精神,并不斷地開(kāi)啟著新的哲學(xué)思想。當(dāng)然,這兩條路也先天地存在一些問(wèn)題和不足,主要表現(xiàn)在以下方面:
首先,哲學(xué)理論的超驗(yàn)性。由于這兩條路的最終指向都是超越經(jīng)驗(yàn)世界,尋求普遍性、必然性的東西,乃至最高的存在或存在的最高尺度。這就使得其哲學(xué)帶有超驗(yàn)性的特征。而超驗(yàn)性的東西,因?yàn)楦魯嗔送?jīng)驗(yàn)世界的聯(lián)系,人們無(wú)法用經(jīng)驗(yàn)的東西去把握或理解它,正如康德所言:“形而上學(xué)是一種完全孤立的、思辨的理性知識(shí),它完全超出了經(jīng)驗(yàn)的教導(dǎo),而且憑借的僅僅是概念……因此,毫無(wú)疑問(wèn),形而上學(xué)的做法迄今為止還只是一種來(lái)回摸索,而最糟糕的是僅僅在概念中間來(lái)回摸索。”[10]前言二14—15正是因?yàn)槠涑?yàn)性,雖然使得其理論自身具有無(wú)比的深刻性,但同樣也獲得了無(wú)法確證的惡名。換句話(huà)說(shuō),就是沒(méi)有現(xiàn)實(shí)功用,對(duì)經(jīng)驗(yàn)世界的事物沒(méi)有意義和價(jià)值。這也是備受詬病的原因。
其次,理論的抽象性或形式化。哲學(xué)從其誕生之日起,就試圖擺脫經(jīng)驗(yàn)性思維的糾纏,尋求超越經(jīng)驗(yàn)世界的理性思維,因?yàn)樗鼌拹航?jīng)驗(yàn)思維的不確定性、隨意性,總是試圖尋找經(jīng)驗(yàn)背后的東西,而且這種東西必須具有確定性、普遍性和必然性特征,以便為經(jīng)驗(yàn)思維或經(jīng)驗(yàn)之物尋求根據(jù)。唯此,理論才有價(jià)值、有意義。哲學(xué)理論的這種初衷,使得它輕視經(jīng)驗(yàn)的東西,不屑與經(jīng)驗(yàn)為伍,盡管它偶爾也強(qiáng)調(diào)不能脫離經(jīng)驗(yàn),但在骨子里是拒絕經(jīng)驗(yàn)的。這自然使其與經(jīng)驗(yàn)水火難容。因此,獲得抽象性、形式性之名也就在所難免。相較之下,自然科學(xué)則熱烈地?fù)肀Ы?jīng)驗(yàn),并為經(jīng)驗(yàn)世界提供無(wú)數(shù)科學(xué)理論,這使得哲學(xué)既略感自卑,又自命清高。一方面,他們鄙視自然科學(xué)對(duì)經(jīng)驗(yàn)的奴顏婢膝、阿諛?lè)畛校J(rèn)為自然科學(xué)解決不了形而上的問(wèn)題;另一方面,自然科學(xué)給人們帶來(lái)的真理幫人們解決了許多問(wèn)題,受到了人們的熱烈追捧,這又惹得哲學(xué)家莫名的嫉妒,甚至也想把哲學(xué)改造得像自然科學(xué)那樣具有可驗(yàn)證性,可解決現(xiàn)實(shí)問(wèn)題的樣子,但這又似乎降低了自己的身份或?qū)W科地位。于是問(wèn)題似乎并沒(méi)有解決,抽象性和形式化的惡名也就坐得更實(shí)了。
其三,無(wú)法對(duì)現(xiàn)實(shí)問(wèn)題給出確定性的解釋。哲學(xué)在面對(duì)經(jīng)驗(yàn)世界的問(wèn)題時(shí),總是顯得笨手笨腳,甚至無(wú)法給出明確的解釋。這是由哲學(xué)的特性決定的,哲學(xué)處理的問(wèn)題往往都是理性自身的問(wèn)題,而在對(duì)理性所面對(duì)的對(duì)象——世界和人的問(wèn)題的時(shí)候,則往往顯得力不從心,甚至無(wú)法做出解釋。這是因?yàn)樽匀皇澜绲膯?wèn)題需要經(jīng)驗(yàn)科學(xué)做出解釋?zhuān)軐W(xué)處理的是經(jīng)驗(yàn)之外的事情,是超出經(jīng)驗(yàn)世界之外的,因此,對(duì)經(jīng)驗(yàn)世界的事情,理性是沒(méi)有發(fā)言權(quán)的。而對(duì)人自身的問(wèn)題,這里涉及多個(gè)領(lǐng)域,有人體科學(xué)、人的心理科學(xué)的方面,這些仍屬自然科學(xué)的事務(wù),哲學(xué)無(wú)從置喙。只有關(guān)于人的道德或倫理行為、關(guān)于人的精神世界包括理想、信念、審美、價(jià)值判斷時(shí),哲學(xué)才有機(jī)會(huì)做出一些判斷,但即使如此,它也無(wú)法給出確定性的建議。首先,倫理學(xué)的知識(shí)具有不確定性。按亞里士多德的解釋?zhuān)且驗(yàn)樗膶?duì)象人始終處在變化之中,無(wú)法確定。關(guān)于人的知識(shí)也始終不是必然的和確定的。另外,倫理知識(shí)的前提都是基于約定的基礎(chǔ),而不是基于自然的基礎(chǔ)。何為對(duì)、何為錯(cuò),在不同的傳統(tǒng)、不同的社會(huì)中都有不同的理解[11]23。至于人的精神世界的問(wèn)題就更復(fù)雜,更難于給出確定性的答案了。因?yàn)樯婕暗嚼硐搿⑿拍睢徝篮蛢r(jià)值判斷問(wèn)題的,都關(guān)涉到人的情感、需求、無(wú)意識(shí)等非理性層面的東西,這些東西往往自身就不具有確定性,對(duì)與其相關(guān)問(wèn)題的判斷就更不易了。這也是哲學(xué)面對(duì)經(jīng)驗(yàn)世界的問(wèn)題時(shí)之所以束手無(wú)策的原因。
最后,在實(shí)踐上遭遇的困難。哲學(xué)家雖然提出了很多理論,這些理論也可視為哲學(xué)對(duì)世界的一種理解或解釋。但一旦需要運(yùn)用哲學(xué)理論來(lái)改造世界或付諸實(shí)踐行動(dòng)時(shí),哲學(xué)就開(kāi)始退縮。因?yàn)樗诿鎸?duì)現(xiàn)實(shí)世界時(shí)有一種出自本能的恐懼和不自信。如前所述,哲學(xué)無(wú)法對(duì)經(jīng)驗(yàn)世界給出確定性的答案或正確的解釋。即使對(duì)理性自身的問(wèn)題,哲學(xué)的答案也從未獲得過(guò)人們普遍認(rèn)可。康德就認(rèn)為,理性“為種種問(wèn)題所煩擾,……但它也無(wú)法回答它們,因?yàn)樗鼈兂搅巳祟?lèi)理性的一切能力”[10]第一版序言3。柯拉柯夫斯基更直白地說(shuō):“在維系歐洲哲學(xué)生命兩千五百年的那些問(wèn)題中,沒(méi)有一個(gè)問(wèn)題解決得令我們普遍滿(mǎn)意。由于哲學(xué)家的判斷,所有哲學(xué)問(wèn)題不是懸而未決,就是變得無(wú)效。”[12]2試想,如果連理論本身都無(wú)法保證確定性,又如何來(lái)面對(duì)實(shí)踐問(wèn)題呢?雖然說(shuō)哲學(xué)家對(duì)自己的理論尚有自知之明,還能安于哲學(xué)的玄思。但馬克思的話(huà)卻讓哲學(xué)家感到無(wú)地自容了,“哲學(xué)家們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釋世界,問(wèn)題在于改造世界。”[13]57在哲學(xué)史上,亞里士多德最先提出了實(shí)踐問(wèn)題,但那是道德實(shí)踐,馬克思直接提出理論要解決和改造實(shí)踐問(wèn)題,這是對(duì)哲學(xué)最大的挑戰(zhàn),也使得哲學(xué)的地位更為尷尬。哲學(xué)如何在現(xiàn)實(shí)實(shí)踐中找到自己的位置,這是它不得不面對(duì)的問(wèn)題。
總之,西方哲學(xué)這兩條道路,盡管給其帶來(lái)了無(wú)限豐富的思想,維系著哲學(xué)的綿延和發(fā)展,但它自身蘊(yùn)含的問(wèn)題也令其備感困惑,哲學(xué)如何走出自己造就的牢籠,將是哲學(xué)如何進(jìn)一步繁衍自身的試金石,也是哲學(xué)獲得其期許的地位的最好明證。
[1] (古希臘)亞里士多德.尼各馬可倫理學(xué)[M].廖申白譯.北京:商務(wù)印書(shū)館,2003.
[2] (英)康福德.從宗教到哲學(xué)——西方思想起源研究[M].曾瓊,王濤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
[3] 吳雅凌.神譜箋釋 [M].北京:華夏出版社,2010.
[4] (英)康福德.蘇格拉底前后[M].孫艷萍,石冬梅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
[5] 汪子嵩,等.希臘哲學(xué)史: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
[6] 先剛.柏拉圖的本原學(xué)說(shuō)[M].北京:三聯(lián)書(shū)店,2014.
[7] 苗力田.亞里士多德全集:第7卷 [M].北京:中國(guó)人民大學(xué)出版社,1993.
[8] 柏拉圖全集:第1卷[M].王曉朝譯.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
[9] 先剛.國(guó)外柏拉圖研究中關(guān)于“圖賓根學(xué)派”的爭(zhēng)論[J].世界哲學(xué),2009,(11).
[10] (德)康德.純粹理性批判[M].李秋零譯.北京:中國(guó)人民大學(xué)出版社,2004.
[11] 余紀(jì)元.亞里士多德倫理學(xué)[M].北京:中國(guó)人民大學(xué)出版社,2011.
[12] (英)柯拉柯夫斯基.形而上學(xué)的恐怖[M].唐少杰,左言新,等譯.北京:三聯(lián)書(shū)店,1999.
[13]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