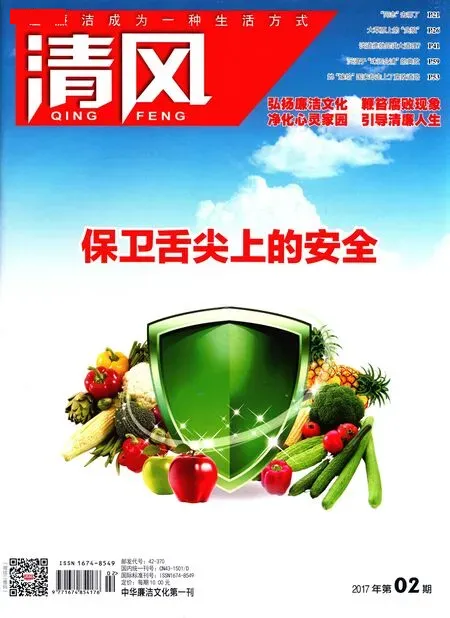武則天的幻想
文_劉吉同(河南新鄉)
武則天的幻想
文_劉吉同(河南新鄉)

武則天
公元699年,武則天已75歲,她知道自己不可能“萬壽無疆”,而又深懼死后李氏與武氏兩大皇族之間同室操戈,血洗對方,于是召集太子、相王(即后來的唐中宗、睿宗)、太平公主和堂侄武攸暨(太平的丈夫)等人,讓他們擬定“團結一心”誓詞,然后“告天地于明堂”,并將誓詞“銘之鐵券,藏于史館”(《資治通鑒》卷206)。在武則天看來,如此這般就可以安心龍御歸天了。
然而,這只是個幻想。專制權力下的官員多人格分裂,“接班人”也不例外,再不可一世的獨裁者,都無法管住死后。秦始皇做夢也想不到,他心目中要傳萬代的錦繡江山,竟“二世而亡”,子孫幾乎被斬盡殺絕。劉邦也想不到他的江山差一點改旗易幟由劉變呂。李世民更不會想到當年身邊的一個小小武媚娘,竟將李唐改朝換代。武則天呢?同樣無法逃脫這一歷史規律,人未死便被趕下龍位。死后呢?家人也很慘,兒子李顯被妻女毒死,朝廷很快又爆發了“唐隆政變”“先天政變”,武氏一族被殺得七零八落,武三思遭開棺戮尸,連武后極為欣賞的太平公主和上官婉兒也都被斬殺。鐵券之類,純為笑談。
那么,武則天何以還執意去鑄什么鐵券呢?可能是太迷信自己的“崇高威望”和無限權力了。武則天秉政近五十年,深知權力的威力和神妙。她叫誰死,誰就必須死,包括像長孫無忌、褚遂良那樣的開國元勛和顧命大臣。她可以隨時制造恐怖,豢養的酷吏僅周興、來俊臣幾個,就能令滿朝文武乃至天下蒼生不寒而栗,包括像狄仁杰、魏元忠那樣名滿天下的重臣名相。她可以一腳踢開三從四德之類的封建禮教,公開包養薛懷義、張昌宗等男寵。她玩弄皇帝于股掌之中,殺、廢、立、辱、貶,全在其一念之間。她殺了武攸暨的妻子,干什么呢?為了讓太平公主“填房”。或許正是這種“無所不能”的“權力觀”,才令她堅信,只要朕讓他們對天盟誓,爾等在她死后就一定會做到“團結一致向前看”。然而,這只能是竹籃打水一場空。
以武則天過人的智慧、見識和閱歷,我想對權力“死后作廢”的道理不可能不清楚,但她為什么還要煞費苦心地去搞這種“笑料”呢?我看只能用無可奈何來解釋了,或者叫“死馬當做活馬醫”。皇權制度因其自身的落后和腐朽,故它有很多胎帶的、無法解決的“千古難題”,選不好“接班人”就是其中之一。
嬴政死后,趙高走了“邪路”,把太子由扶蘇掉包成了胡亥。周勃、陳平鏟除了呂家勢力后,后少帝被殺,遠在代州的劉恒撿了個皇帝。漢昭帝死后,劉徹眾多的皇子皇孫猶如一筐爛杏,霍光無奈之下選了個“海昏侯”。漢宣帝最為欣賞的是“聰達有才”的皇子劉欽,但最終只能選擇昏庸的劉奭做太子,即后來的漢元帝,大漢自他一路下滑直至亡國。晉武帝挑來挑去,最后挑了一個傻子。唐中宗的兒子李重俊在太子位上被迫“起義”,最后掉了腦袋。朱元璋晚年,不會不知道手握重兵、野心勃勃而又桀驁不馴的燕王對未來年輕的建文帝意味著什么,但最終還是把大位傳給了長孫,由此釀成一場持續四年、死傷無數的內戰。明光宗在太子位上如履薄冰苦苦熬了二十年,繼位一個月便蹬腿了,死前期望兒子朱由校能成為像堯舜那樣的明君,但兒子幾近弱智,登基后不問朝政,魏忠賢恣意妄為,政治一片黑暗。諸如此類,不一而足。
武則天晚年同樣深陷這樣的無奈之中。想選侄兒做太子,狄仁杰說:“姑侄之于母子孰親?”想選兒子做太子,武承嗣勸她:“自古天子未有以異姓為嗣者。”她左右搖擺,舉棋不定,最后還是聽了狄仁杰的建議。她估計死后李、武兩家會水火不容,于是把兩撥人召集到一塊,讓他們對天盟誓,保證她死后要“戮力同心”。然而,這不過是掩耳盜鈴、自欺欺人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