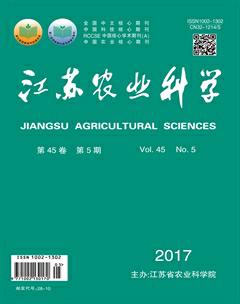江蘇省新型農業經營主體的科技需求影響因素實證分析
傅順+胡浩++盧華



摘要:以江蘇省主要的新型經營主體為研究對象,選取鹽城、淮安、鎮江等地區進行實地調研,運用Probit模型實證研究影響新型農業經營主體科技需求的因素與影響經營主體采用農業新技術的主要因素。結果表明:政府扶持和風險分擔情況在1%的水平下顯著為正,表明政府扶持力度越大,越能顯著提高經營主體采用農業新技術的概率,并且采用新技術后所承擔的風險越小,經營主體采用農業新技術的概率越大;而不同經營主體對科技的需求情況,主要由自身資源稟賦和決策者的風險偏好綜合決定。當前江蘇省農業科技供給主要由政府主導型的農技推廣機構、大專院校和科研院所及農業園區3個方面提供,盡管取得了一系列成就,但同樣面臨著推廣體制不健全、農業科研缺乏市場導向、產學研分離和農業園區后續管理不足、人才流失嚴重等現象。
關鍵詞:農業;新型經營主體;科技需求;影響因素;江蘇省;實證分析
中圖分類號: F323.3文獻標志碼: A
文章編號:1002-1302(2017)05-0332-04
2015年中央農村工作會議指出:加快構建新型農業經營體系,堅持和完善農村基本經營制度,堅持農民家庭承包責任制的主體地位,引導土地經營權規范有序流轉,創新土地流轉和規模經營方式,積極發展多種形式適度規模經營,提高農民組織化程度。而江蘇省農業正經歷著農業生產經營主體重塑和多元化的歷史階段,一大批新型農業經營主體應運而生。張照新等指出,新型農業經營主體是建立于家庭承包經營基礎上的,適應市場經濟和農業生產力發展要求,從事專業化、集約化生產經營,組織化、社會化程度較高的現代農業生產經營組織形式,是傳統農業向現代農業轉變的關鍵[1]。一般而言,新型農業經營主體主要包括家庭農場、專業大戶(種養大戶)、農業合作社和農業企業等4種形式[2]。
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也是農業發展的主要動力,優質的新品種和效率更高的生產工具的創新,都可以對我國農業增產、農民增收作出巨大的貢獻。黃季焜等研究認為,科技服務應基于農戶需求而非政府主導或者專家推廣,從農戶層面出發對科技需求影響因素進行研究有利于科技推廣與農民實際需求相結合[3-4]。徐世艷等通過分析農戶調研數據,得出影響病蟲害防治技術、良種配套技術的主要原因是農業技術信息來源、耕地規模、家庭收入等[5]。然而郭慶海研究表明,當前江蘇省的農業生產經營組織方式正在經歷新型經營主體確立并進一步發展的階段,新型農業經營主體的發育和成長影響著我國農業發展質量和農業現代化進程[6]。目前,規模經營種養大戶、家庭農場、農業合作社和農業企業已經成為發展現代農業的新型農業經營主體,對新型生產經營主體的科技需求進行分析,有利于新型經營主體的培育和發展,對于新型城鎮化建設和“三農”問題的有效解決起到了很好的促進作用。
1研究背景
目前關于農業科技需求的研究主要是基于農戶層面的,一項新的技術是否有用,取決于它能否被農戶接受和利用,但是不同農戶對科技的需求差別可能會很大,農戶的科技需求也會受到很多因素影響。宋金田等基于契約視角研究發現,交易成本對農戶農業技術有顯著影響[7]。也有學者研究外部因素對農戶科技需求的影響,展進濤等研究發現,勞動力轉移、對資源的依賴與市場風險的判斷等因素共同影響農戶科技需求[8]。周波等從江西省種稻大戶科技需求出發,將技術需求分為物化型農業技術需求、操作型農業技術需求2類進行研究,分別得出了影響因素[9]。王建華等在實地走訪中發現,在蘇北一些科技信息接收緩慢的地區,同一區域內種糧大戶之間對科技的采用會出現相互博弈的情況,最終往往會選擇相同或相似的科技,形成某一特定科技集中發展的區域趨勢;但是,專業大戶自身的科技需求意識并不強,需要有關組織對其科技意識進行培養和引導[10]。針對合作社對農業科技需求的研究,董淑華等通過對廣州市35家農民專業合作社農業科技需求的調查顯示:農民專業合作社對農業科技需求的依賴程度是很高的,但是現有科技項目的科技含量一般,他們目前對現代生物技術的需求最多,其次是現代工程技術[11]。農業企業化經營發展是農村市場化、城鎮化的必然過程,要加強教育和科技的推廣。張雨通過研究發現,農業企業實質上是“集成利用資本、技術、人才等因素,將農戶通過各種利益聯結機制相聯系,帶動他們進入市場,使農產品生產、加工、銷售相互促進并有機地結合,在規模經營指標上達到相關標準并經政府有關部門認定的企業”[12]。劉潔等通過研究農業企業如何在農業產業化生產經營過程中完成科技需求演化,并輻射帶動其他農戶,實現區域的增效增收,發現農戶戶主特征、農地流轉市場調整頻率、農戶家庭特征、社區及政府對規模經營的支持等因素影響較顯著,這些綜合因素共同推進了農業企業化生產[13]。
2數據來源與描述性分析
2.1數據來源
筆者所在課題組調查研究的對象是江蘇省新型農業經營主體。樣本選取方法為抽樣調查方法,在江蘇省淮安市、鹽城市、鎮江市選取了17個鎮及經濟開發區進行調查,分別是句容市下轄的白兔鎮、后白鎮等12個鄉(鎮),淮安市萬集鎮、岔河鎮、東雙溝鎮,鹽城市學富鎮、鹽城市鹽都區農村經濟開發區、尚莊鎮,每個地區選取數量不等的家庭農場、專業大戶、農業合作社和農業企業等新型農業經營主體。調查地區的選取根據江蘇省農業生產及新型農業經營主體的分布情況,其中鎮江市、鹽城市、淮安市分別收集有效樣本76、35、59個,共收集170個新型農業經營主體,在一定程度上能夠代表江蘇省新型農業主體的發展情況及農業新技術的采用情況。
調查問卷的內容分為3個部分。第1部分為經營主體的基本信息,包括經營形式、經營時間、主要業務、經營面積、雇工情況、政府扶持政策、收入及家庭資產(包括固定資產和流動資產等)的基本信息。第2部分為農業新技術的使用情況,問卷了解了經營主體近5年內是否采用了新技術,以及新技術的獲得途徑、新技術的風險規避與政府的政策扶持力度,新品種對產量、收益的影響,新技術獲得的成本等。問卷的第3部分為農技推廣的綜合評價,包括經營主體接觸最多的農業技術推廣活動、新技術推廣的滿意程度,新技術在使用過程中獲得技術指導的及時性、準確性,新技術的作用年限、新技術損失的賠償與賠償的滿意程度等。
2.2描述性分析
根據問卷調查數據,重點針對不同新型農業經營主體的農技接受情況予以分析,根據對家庭農場、專業大戶、農業合作社及農業企業的實地調研數據,分析各經營主體在農業投入、生產、加工和流通環節中的農業科技需求。
補貼,占專業大戶總數的32.86%;其次為家庭農場,有6個獲得了補貼,占總數的20.00%;再次為農業合作社,共有3個獲得了補貼,占總數的4.48%;被采訪的農業企業并未因為新技術的采用而獲得政府補貼。本研究認為,新技術的采用一方面是由于不同經營主體自身生產發展的需要;另一方面,政府的政策扶持也對該行為有一定的促進作用。
由表2可見,在采用新技術的經營主體中,采用技術類型最多的為生物技術中的種子技術,共有88個,占采用新技術總數的80.00%,其中使用高產品種的經營主體共有59個,占使用新技術總數的53.64%,采用優質品種的經營主體共有29個,占使用新技術總數的26.36%;采用農藥等病蟲害防治技術的共有1個,占使用新技術總數的0.91%。
機械技術作為替代勞動力的重要手段,共有20個經營主體采用了此類技術,如種植業中的機插秧、養殖業中的切魚機械等,占采用新技術總數的18.18%;此外,田間管理技術也在種植業中得到了運用,共有10個經營主體采用了此類技術,占使用新技術總數的9.09%;共有8個經營主體采用了秸稈還田等環保類技術,占使用新技術總數的7.27%
可見,從是否采用農業新技術來看,67%的經營主體采用了農業新技術,家庭農場采用農業新技術的比例達到72%,為新型農業經營主體中最高的,專業大戶、農業合作社采用農業新技術的比例分別為60%、69%,在一定程度上說明新型農業經營主體存在對農業科技的需求。經營主體經營面積平均為13.87 hm2,其中家庭農場經營的面積最大,平均達到20.80 hm2,其次為農業合作社的19.16 hm2,最小的為586 hm2的專業大戶。3類新型農業經營主體平均擁有的流動資金為39.22萬元,擁有流動資金最多的農業合作社為62.05萬元,家庭農場、專業大戶擁有的流動資金分別為3157萬、21.38萬元。新型農業經營主體享受政府扶持的比例較低,平均僅為32%,享受比例最高的農業合作社僅為37%,家庭農場為34%,專業大戶的比例更是低于30%,僅為25%,可見政府對新型農業經營主體的扶持力度較為薄弱。從農業保險來看,49%的經營主體均不同程度地參與農業保險,家庭農場參與保險的比例最高,達到69%,農業合作社、專業大戶參與農業保險的積極性就明顯低于家庭農場,其比例分別為48%、40%。從農業新技術本身所產生的風險來看,經營主體本身、政府及企業共同承擔的比例較高,獨自承擔新技術帶來風險的比例較低。
應說明的是,在實際調研過程中農業企業由于樣本量不夠,加上主體自身特征的差異,無法將其納入實證分析框架中,因此在進行計量回歸時將其刪除。
3.2實證分析
基于上述調研數據,通過擬合分析,選用Probit模型更合適,運用Stata11.0軟件進行二元選擇回歸分析,在進行具體回歸時,先用F檢驗進行虛擬變量之間的顯著性檢驗。由表5模型的估計系數和邊際效應看出,整體而言,模型的預測準確率達到89.47%,準R2為0.627 1,整體估計效果較好。
政府扶持和風險分擔情況在1%的水平下顯著為正,表明政府扶持越大,越能顯著提高經營主體采用農業新技術的概率,采用新技術后所承擔的風險越小,經營主體采用農業新技術的概率越大。從以上2個變量的邊際效應系數來看,均不同程度地通過顯著性檢驗,影響經營主體是否采用新技術的最重要因素是風險承擔情況,邊際效應系數最大,采用新技術后的風險越小,或政府、企業承擔得更多,越有利于經營主體采用農業新技術。作為“理性經濟人”,追求收入最大化的同時也會追求風險最小,政府或企業承擔得越多,越能緩解經營主體采用新技術后的后顧之憂,會提高采用新技術的概率。政府通過對采用農業新技術的經營主體給予一定的補貼或獎勵,從政策上給予引導和支持,都會激勵經營主體積極采用農業新技術,能夠將科技成果迅速轉化為物質財富和經濟效益,有利于科技進步的同時,也增加了農業生產和農民收入。農業保險的估計系數在1%水平下顯著為正,表明是否參加農業保險是影響經營主體是否采用農業新技術的重要因素。參加農業保險為經營主體采用農業新技術提供了一定的“后勤保障”。在產量增多、收入提高的刺激下,系列的農業扶持政策進一步提高了經營主體采用農業新技術的積極性。可以看出,在當前農業技術推廣過程中,推動經營主體采用農業新技
各經營主體自身基本情況也是影響是否采用農業新技術的重要因素。勞動力人數的估計系數為負,表明經營主體所擁有的勞動力人數越多,采用農業新技術的概率越小,可能的解釋是勞動力越多,分配的靈活度就越大,對農業的悉心照料程度也會提高,在遇到突發情況時,也不會造成巨大產量損失,因此采用農業新技術的概率也會更低。經營面積的估計系數為正,說明經營主體所擁有的經營面積越大,采用農業新技術的概率也就越高。一般來說,相對于傳統小農,新型農業經營主體的單個地塊面積越大,越有利于機械等農業新技術的使用,無論是新品種的推廣還是大型機械等新技術的使用,都要建立在較大面積的土地上,面積越大,越為農業新技術的使用提供了條件,一定的農業補貼等政府扶持更是增強了采用農業新技術的積極性。經營主體所擁有的流動資金雖未通過顯著性檢驗,但其符號為正,說明流動資金越多,經營主體采用農業新技術的概率越大;邊際效應在5%的水平下顯著為正,表明擁有的流動資金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采用新技術所面臨的資金約束,有利于新技術的采用。
相對于專業大戶,家庭農場采用農業新技術的概率更高,家庭農場由于在工商部門進行登記,能從政府得到相關扶持政策,增強了采用新技術的積極性,專業大戶由于不須要進行登記注冊,無法正常獲得政府的相關補貼等政策,采用農業新技術的積極性可能會低些。農業合作社相對于專業大戶采用新技術的概率更低,這同本研究的理論分析結果相反,或許同當前合作社存在的問題有關,現實中正規合作社不多,更多的合作社只是想騙取國家的補貼等政策支持,還有的合作社只是簡單地橫向聯合,并未實現真正的合并,對農業新技術的使用也會存在分歧,不利于農業新技術的采用和推廣。
通過實證分析,本研究得出采用新技術后的風險承擔情況是影響經營主體是否采用農業新技術的最重要因素,其次為政府的各項扶持和農業保險。各類不同經營主體作為“理性經濟人”,會在權衡利益風險的情況下進行決策,作為風險厭惡型的經營主體,當一項技術存在任何風險時,都會減弱經營主體使用該技術的動力。政府提供的補貼等農業扶持政策和參加的農業保險都降低了采用新技術的成本,增強了不同經營主體采用新技術的積極性。經營主體所擁有的流動資金是影響是否采用新技術的關鍵因素,流動資金緩解了采用新技術的資金約束;經營面積越大,則為新技術的使用提供了條件,越有利于農業新技術的采用。
4結論與政策建議
在綜合考慮4種新型農業經營主體的特點、功能定位及存在問題的基礎上,結合實地調研和實證結果,得出以下3點結論:(1)新型農業經營主體采用農業新技術的比例普遍較低,過去5年內采用農業新技術的比例僅為64.71%,農業新技術并未得到新型農業經營主體的廣泛關注。(2)采用農業新技術的類型單一。在機械、生物、管理和環保4類技術中,采用2類以上技術的經營主體占比為12.73%,沒有經營主體同時采用4類技術,采用單一技術的經營主體占比為8727%,技術使用類型的單一難以滿足農業生產、加工、流通
[JP3]等農業各環節的需要。(3)技術類型和經營主體業務存在差距,4類新型農業經營主體普遍采用農業新機型、新品種等生產類技術,對農產品加工、流通領域等方面的技術利用程度較低。[JP]
制度因素是影響經營主體是否采用農業新技術的最關鍵因素,首先以采用新技術的風險承擔情況為考慮重點,采用新技術后的風險越小或政府、企業承擔得更多,越有利于經營主體采用農業新技術;其次為政府的各項扶持和農業保險措施,政府通過對采用農業新技術的經營主體給予一定的補貼或獎勵,從政策上給予引導和支持,都會激勵經營主體積極采用農業新技術。經營主體自身所擁有的流動資金、經營面積是影響經營主體決策的重要因素,擁有的流動資金越多,越能緩解技術采用過程中的資金約束,越有利于采用農業新技術;經營主體擁有的勞動力人數與采用農業新技術呈現相反的關系,可能的解釋是勞動力人數越多,對農業的悉心照料程度就會越高,在一定程度上可能降低了農業新技術的采用率。
[HS2*1][HT8.5H]參考文獻:
[1]張照新,趙海. 新型農業經營主體的困境擺脫及其體制機制創新[J]. 改革,2013(2):78-87.
[2]孫中華. 大力培育新型農業經營主體 夯實建設現代化農業的微觀基礎[J]. 農村經營管理,2012(1):1.
[3]黃季焜,胡瑞法,孫振玉. 讓科學技術進入農村的千家萬戶——建立新的農業技術推廣創新體系[J]. 農業經濟問題,2000,21(4):17-25.
[4]陳志興,樓洪興. 農業科研成果轉化創新模式與激勵機制的研究[J]. 科技通報,2006,22(4):515-518.
[5]徐世艷,李仕寶. 現階段我國農民的農業技術需求影響因素分析[J]. 農業技術經濟,2009(4):42-47.[ZK)][HT][HJ]
[6]郭慶海. 新型農業經營主體功能定位及成長的制度供給[J]. 中國農村經濟,2013(4):4-11.
[7]宋金田,祁春節. 農戶農業技術需求影響因素分析——基于契約視角[J]. 中國農村觀察,2013(6):52-59,94.
[8]展進濤,陳超. 勞動力轉移對農戶農業技術選擇的影響——基于全國農戶微觀數據分析[J]. 中國農村經濟,2009(3):75-84.
[9]周波,陳曦. 江西省種稻大戶不同類型農業技術需求影響因素分析[J]. 江西農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3,12(1):58-65.[ZK)]
[10]王建華,李清盈,Djurovic G. 基于科技需求演化的農業生產經營主體培育與政策建議——以江蘇地區農戶為例[J]. 貴州社會科學,2015(2):162-168.
[11]董淑華,陳華東. 農民專業合作社的農業科技需求現狀及供給機制創新——基于廣州市35家農民專業合作社的調查研究[J]. 南方農村,2011,27(1):86-90.
[12]張雨. 適合農業企業的農業科技成果轉化運行機制[J]. 廣東農業科學,2006(10):97-99.
[13]劉潔,劉永平. 農戶農業企業化經營的影響因素分析——以河北省558個農戶為例[J]. 中國農村經濟,2007(4):18-24,31.
[FQ)]
[HT5”SS〗江蘇農業科學2017年第45卷第5期
[SQ*5]
[HT6F]王宏智,趙揚. 水產品信息可追溯體系構建與對策——基于系統復雜性視角[J]. 江蘇農業科學,2017,45(5):336-3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