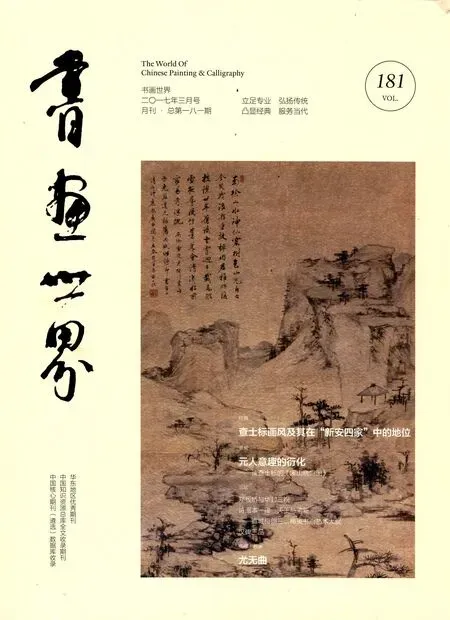鄭板橋與華封三祝
文_朱萬章
中國國家博物館研究館員/中國美術家協會理論委員會委員
鄭板橋與華封三祝
文_朱萬章
中國國家博物館研究館員/中國美術家協會理論委員會委員
“華封三祝”的典故來自《莊子·天地》。華封人祝愿圣人堯“使圣人富”“使圣人壽”“使圣人多男子”,但都被堯婉言謝絕。后來人們便以“華封三祝”祝愿人富貴、長壽和多男子。清代以來,“華封三祝”作為吉祥寓意的題材為畫家所追捧。常見的母題往往繪南天竹(南天竺)和兩種吉祥花卉(如牡丹、月季等)。因“竹”與“祝”諧音,故在此主題中,竹是必不可少的元素。當然,也有純粹繪佛手、桃和石榴三種吉祥物的,因三者分別喻示富貴、長壽和多子,故有“三多”之喻,也常常稱作“華封三祝”。這樣的題材在清代中期商業文明較為發達的揚州地區盛行,因而在“揚州畫派”諸家中,多可見此類畫。到晚清民國時期,同樣以商業文明躍居全國前列的海上地區,也多見此類畫,“海上畫派”的任伯年、王一亭、王個簃等人最為樂此不疲。究其原因,因彼時揚州、海上地區多藝術贊助人,書畫市場異常活躍,書畫家們多因為稻粱謀而畫畫,其作品必以迎合受眾為要務,因而出現普羅大眾所喜聞樂見的繪畫題材也就順理成章了。
在辭官歸里、以鬻畫為生的“揚州畫派”代表作家鄭板橋(1693—1765)筆下,就常見到這種有吉祥寓意的題材。中國國家博物館所藏其紙本墨筆《華封三祝圖》(縱167.7厘米,橫92.7厘米),可稱得上是鄭板橋此類題材的扛鼎力作。有意思的是,他不以花卉與竹相搭配,而是直接以其最為擅長的竹石入畫,畫兩座峭立的石峰和三竿墨竹,構圖簡潔清晰,疏朗明快。如果單以畫面看,似乎與其常見的“竹石圖”并無二致。但鄭板橋在畫中題詩“寫來三祝乃三竹,畫出華封是兩峰。總是人情真愛戴,人家羅拜主人翁”,為構圖畫龍點睛,因“竹”與“祝”,“峰”與“封”諧音,故“華封三祝”之意躍然紙上。作者款識曰“乾隆壬午,板橋鄭燮”,鈐白文方印“鄭燮之印”和朱文隨形印“樗散”,另有朱文長方印“歌詠古揚州”。“乾隆壬午”為乾隆二十七年(1762),時年鄭氏七十歲。在此畫完成之后的第三年,鄭板橋即歸道山。因此,可以說該畫是其晚年的代表作,反映了其人畫俱老、筆力遒勁的藝術面貌。印鑒中,“樗散”一詞源自《莊子》之《內篇·逍遙游》:“吾有大樹,人謂之樗。其大本擁腫而不中繩墨,其小枝卷曲而不中規矩,立之涂,匠者不顧。今子之言,大而無用,眾所同去也。”后人便以此比喻不為世用、投閑置散之意。鄭氏以此作為閑章,或可見其懷才不遇、不容于世的喟嘆與自況。
清人秦祖永(1825—1884)在其《桐陰論畫》中認為鄭板橋“筆情縱逸,隨意揮灑,蒼勁絕倫”,在該畫中便可看出這種特色。但秦祖永同時認為,“此老天資豪邁,橫涂豎抹,未免發越太盡,無含蓄之致”。這在鄭氏傳世的竹石、蘭花諸圖中,都可體現出來。因其題材單一,畫面出現程式化現象也就在所難免,故“無含蓄之致”也就在情理之中了。不過,秦祖永卻另有一番解析,“蓋由其易于落筆,未能以醞釀出之,故畫格雖超,而畫律猶粗也”,認為落筆容易而缺少成竹在胸的“醞釀”,因此畫筆粗率。在筆者看來,不僅如此,更重要的是鄭板橋畫債或應酬較多,作畫無數,也就乏精致之作,終究是與當時的文化語境相關。但就其傳世諸作來看,此《華封三祝圖》應算是得意之作了。
無獨有偶,在其傳世竹石作品中,尚有另一件《華封三祝圖》(天津博物館藏)。該畫亦為紙本墨筆,縱170厘米,橫90厘米,與前述《華封三祝圖》的尺幅大致相當。但其畫面構圖則迥異。該圖所繪為五竿墨竹置于兩座石峰之前,墨竹參差,高低錯落。竹葉墨韻明凈,墨色互異。如果僅從繪畫語言看,是和華封三祝毫無關聯的。但作者在畫上的題識則將其畫境登堂入室:“昔人畫華封三祝,一峰而已。茲益一峰,是增其壽也。三竹而已,茲益以二而為五,是增其福也。上天申錫,有加無已,蓋甚顯上令德之君子,有以致此也。乾隆丙子冬寫,似章翁鄉祭酒年老長翁,有是德即有是福,豈不信然!板橋鄭燮。”鈐白文方印“鄭板橋”。他是在前人約定俗成的一峰三竹的構思中,增加一峰及兩竹。因“石”有“壽”之意,故為增壽;“竹”為“祝”,增加二竹而為五,故為增福。鄭板橋的這種反主流構圖,不僅毫無違和感,反而因其題詞作為注腳而使立意凸顯,與同類題材的畫作相比,自然因其創新意識而略勝一籌。從這個意義上講,其實在畫面上多加任何一座石峰和一竿墨竹,都有增壽增福之意,鄭板橋將本來已經模式化的構圖加以重新解構與解讀,使華封三祝這一主題在創作中增添了無限的可能性。這是鄭板橋的別具匠心處。從款識可知,該圖作于乾隆二十一年(1756),時年作者六十四歲,比前作早了六年,也是其晚年之作。

1.鄭燮 華封三祝圖紙本墨筆 167.7cm×92.7cm中國國家博物館藏

2.鄭燮 華封三祝圖紙本墨筆 170cm×90cm天津博物館藏

3.鄭燮 峭石新篁紙本墨筆 324.6cm×136cm旅順博物館藏

4.鄭燮 竹石圖紙本墨筆 217.4cm×120cm上海博物館藏
值得玩味的是,鄭板橋傳世的多件《竹石圖》,其構圖多與上述《華封三祝圖》相類。如無年款的《峭石新篁》(旅順博物館藏),所繪數竿墨竹置于峭石之前,無論用筆還是構圖,都可稱得上是《華封三祝圖》的翻版。鄭氏題詩曰:“兩竿修竹入云根,下有峰巒石勢尊。甘雨和風三四月,滿庭篁筱是兒孫。”從詩意看,也有祝壽與祝多子之意。作于乾隆十九年(1754)的《竹石圖》(上海博物館藏)也是繪數竿墨竹于石峰之前,連款識也和天津博物館藏《華封三祝圖》的位置一樣。所不同者,是因為題識:“昔東坡居士作枯木竹石,使有枯木石而無竹,則黯然無色矣。余作竹作石,固無取于枯木也,意在畫竹則竹為主,以石輔之,今石反大于竹,多于竹,又出于格外也,不泥古法,不執己見,惟在活而已矣。”不難看出,鄭氏是通過此畫傳遞其對竹石圖創作的理念,但如果將此段文字換成華封三祝的語句,也是并無不妥的。因此可以看出,鄭板橋這種一題多畫或一畫多題的現象極為普遍。這是與其作品的世俗化和商業化傾向分不開的。
因“華封三祝”的寓意明顯,無論身居廟堂之高的如云冠蓋,還是身處江湖之遠的販夫走卒,都會鐘愛此題,寄托人們的美好期許。所以,為了滿足不同層次受眾的審美需求,鄭板橋對這一主題的繪畫保持持久的熱度。據不完全統計,在公庫藏品之外,鄭板橋的《華封三祝圖》尚有近十件之多。雖然這些作品或真贗雜糅,但就其數量看,反映出收藏者對一主題追捧的程度。而鄭板橋創作的多幅《華封三祝圖》也免不了有雷同之嫌。作為具有文學家身份的鄭板橋,往往在題詞和竹石的數量上稍加變通,就使畫面重復的概率大為降低。如將“三竹”增為“六竹”,是為增福;將“一峰”增為“兩峰”,是為“南山雙峙”,亦為增壽。有時甚至直接題詩“南山高迥欲參天,密條叢篁更燦然。欲識周姬年八百,太任太姒乙姜賢”,使福壽的意蘊凸顯無遺。當然,所有這些努力,不外乎在于傳遞一種“福壽雙增,天眷愈加愈厚。惟修德不怠,日增月益者,庶足以當之”的理念,是在勸導民眾“修德不怠”,方能福壽齊增。這也正是中國畫傳統中“成教化,助人倫”思想的折射。
正是因為鄭板橋熱衷于華封三祝題材,收藏者亦熱捧之,故在鄭板橋生活的年代,便已有牟利者仿制贗鼎。筆者所見多件坊間流傳的鄭氏《華封三祝圖》,就不乏乾嘉時期的仿作。至于晚清民國直到二十世紀,仿造其畫作者就不勝枚舉了。而在多種構圖或題材的贗作中,“華封三祝圖”往往是首當其沖的。關于這一點,鑒藏者和畫史研究者,是不可不擦亮法眼的。
約稿、責編:徐琳祺、史春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