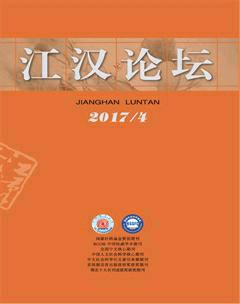從山羊血黎洞丸看《紅樓夢》的成書時間
李曉華++王齊洲
摘要:《紅樓夢》敘襲人被踢傷后,寶玉命人取“山羊血黎洞丸” 藥。據現存文獻可知,最早記載黎洞丸的《外科證治全生集》和《醫宗金鑒》兩書均成書和刊刻于乾隆初年。從醫學角度考察,“山羊血黎洞丸”組方與襲人被踢傷后所需診治的病癥吻合,此方當是作者在生活中接觸或研讀過,且深諳其藥理,故在行文中信筆拈來。據此推斷,《紅樓夢》寫定時間當在乾隆初年或以后,所謂《紅樓夢》成書于康熙朝的說法,難以成立。
關鍵詞:山羊血黎洞丸;《外科證治全生集 》;《醫宗金鑒》;《紅樓夢》成書時間
中圖分類號:I206.5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3-854X(2017)04-0106-04
《紅樓夢》被譽為“中國封建社會的百科全書”,讀者從中可獲得多方面的知識。從醫學角度言,《紅樓夢》中涉及中醫藥知識之豐富,是中國古代其它小說無法比擬的;書中的成方或自擬方皆有依據,且符合中醫之遣藥組方規律。本文僅對《紅樓夢》中的經典方劑——山羊血黎洞丸加以考釋,并據以推斷《紅樓夢》的成書時間。
一、記載黎洞丸的早期文獻
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藏楊繼振舊藏本《乾隆抄本百廿回紅樓夢稿》第三十回末和第三十一回首敘寫襲人被賈寶玉踢了一腳后,“只覺得肋下疼的心里發鬧”,“肋上青了碗大的一塊”,后又引起吐血,寶玉“即刻便叫人燙黃酒,要山羊血黎洞丸來”① 醫治。山羊血黎洞丸即黎洞丸,以地名山黎峒山(即五指山或黎母山)而命名。一說因傳為黎洞真人所創,故名。因黎洞丸配方用山羊血,故全稱“山羊血黎洞丸”。
需要指出的是,黎洞丸是正式方劑名,人民衛生出版社出版的《中醫方劑大辭典》② 和《外科證治全生集》③ 均稱“黎洞丸”。黎洞丸又有異名,或稱“山黎峒丸”,或稱“黎峒丸”等。而黎洞丸與其異名,也反映在《紅樓夢》的不同版本中。
總的來看,大多數《紅樓夢》版本稱“山羊血黎洞丸”。如北京大學圖書館藏《脂硯齋重評石頭記》(庚辰本);國家圖書館藏《脂硯齋重評石頭記》(己卯本);南京圖書館藏《戚蓼生序本石頭記》;國家圖書館藏夢覺主人序《甲辰本紅樓夢》;首都圖書館藏《舒元煒序本紅樓夢》;國家圖書館藏《蒙古王府本紅樓夢》等,均稱“山羊血黎洞丸”。有的版本稱“山羊血山黎峒丸”,如清乾隆五十六年萃文書屋活字本《紅樓夢》(程甲本),清乾隆五十七年萃文書屋活字本《紅樓夢》(程乙本),均稱“山羊血山黎峒丸”。也有版本稱“山羊血黎峒丸”,如啟功等以程本為底本整理的《紅樓夢》注釋本稱“山羊血黎峒丸”。據《中醫方劑大辭典》可知,無論稱“黎洞丸”,還是稱“山黎峒丸”、“黎峒丸”,名雖稍異,實為一方。
中國傳統中醫藥學發達,記載藥方的書籍有很多,據目前所能查到的文獻可知,黎洞丸最早見于清乾隆時期的醫學文獻《外科證治全生集》和《醫宗金鑒》。后世醫書探討黎洞丸方源時或認為出自《外科證治全生集》,如《簡明中醫辭典》④;或認為出自《醫宗金鑒》,如《中醫方劑大辭典》⑤。由于《外科證治全生集》和《醫宗金鑒》這兩部醫書成書時間接近,較易引起人們的誤會,造成判斷上的差異。
《外科證治全生集》為清代名醫王維德(1669—1749年)所著。王維德,字洪緒,別號林屋散人,又號定定子,吳縣人,世代為外科醫家。關于《外科證治全生集》的成書與刊刻時間,《外科證治全生集》自序稱:“特以祖遺之秘,自己臨證,并藥到病愈之方,精制藥石之法,和盤托出,盡登是集,并序而梓之;以質諸世之留心救人者,依方修合,依法法制,依證用藥,庶免枉死;使天下后世,知瘡疽果無死證云爾。乾隆五年歲在庚申仲春朔日,林屋王維德洪緒氏書 。”⑥ 隆乾五年,以干支紀年為庚申,故稱“歲在庚申”,即1740年;仲春朔日,即農歷二月初一。根據古人一般在成書后寫序,或在刻書完成時寫序的通例,我們可以斷定,《外科證治全生集》應該早于乾隆五年編輯成書并于此年農歷二月刊刻完成問世。
《醫宗金鑒》是清代乾隆年間皇帝詔令太醫院御醫吳謙主持編修的一部大型醫藥書。關于成書的背景與時間,《醫宗金鑒》序言的幾篇奏折中有明確交代:“乾隆四年十一月十七日,右院判臣王炳、御醫臣吳謙奉上諭:‘爾等衙門該修醫書,以正醫學。欽此。”⑦ “照管醫書館事務和碩和親王臣弘晝謹奏:請將大內所有醫書,及吳謙刪訂未成之書,一并發與太醫院,選擇吉期,即行開館纂修。其應行事宜,俱照原議辦理。今既有大內之書,并吳謙未成之書,足可纂修。應將行文各省咨取醫書之處,毋庸議等因。于乾隆五年二月十六日具奏。”⑧ “照管醫書館事務和碩和親王臣弘晝等,奉敕纂修醫書,今已告成。謹奉表恭進者……乾隆七年十二月十五日。”⑨ 由以上奏折可知,乾隆四年十一月十七日皇帝下令纂修《醫宗金鑒》;隨后相關人員用時三個月進行查處、商議、斟酌,并于乾隆五年二月十六日具折奏請“選擇吉期,即行開館纂修”;經過近三年的努力,該書于乾隆七年即1742年12月15日前編纂完成。
由上可見,《外科證治全生集》于乾隆五年農歷二月刊刻面世,《醫宗金鑒》尚處于編纂之前的籌備中;顯然,《外科證治全生集》成書在前,《醫宗金鑒》成書在后。當然,《醫宗金鑒》是朝廷組織編纂的醫學經典,有90卷15分冊,由皇帝欽定頒行,無疑更具權威性和影響力。至于《醫宗金鑒》中的黎洞丸方劑是否抄自《外科證治全生集》,我們不敢貿然下斷,因為該書中的方劑都沒有說明來源。
由于《外科證治全生集》、《醫宗金鑒》在醫學界的影響甚大,此后不少醫學文獻都提到過黎洞丸。如成書于乾隆三十年(1765年)的趙學敏《本草綱目拾遺》在“藤黃”條下云:“《綱目》主治條下,只言點蛀牙自落,無他治也。張石頑云:藤黃性毒而能攻毒,故治牙蟲蛀齒,點之即落,毒能損骨傷腎可知。葉氏《得宜本草》云:服藤黃藥忌吃煙。按三黃寶蠟丸、黎峒丸俱用藤黃,以其善解毒也。有中藤黃毒者,食海蜇即解。”⑩ 嘉慶時期成書的《傷科補要》(1808年)、《傷科匯纂》(1818年)、同治時期成書的《厚德堂集驗方萃編》(1865年)、光緒時期成書的《血癥論》(1884年)等,都記載了黎洞丸,只是均未提及方源或所轉引的醫書。因為《外科證治全生集》、《醫宗金鑒》是最早記載黎洞丸方劑的兩部醫書,所以人們自然認為后來這些醫書所載黎洞丸的方源是此二書。到了現當代,關于黎洞丸方源或立方人的研究,便出現兩種意見,一是認為黎洞丸立方人是清王維德或方源是《外科證治全生集》,如《漢藥丸散膏酒標準配本》、《簡明中醫辭典》(修訂本)、《中成藥實用手冊》、《新編中成藥臨床應用》、《中華名方大全》、《北京市中藥成方選集》等;另一是認為方源是《醫宗金鑒》,如《中醫方劑大辭典》、《骨傷方劑學》、《骨傷方歌白話解》等。不過,這些研究結論對本文的討論影響不大,因為二書成書時間接近,都在清乾隆初年。
總之,無論是《外科證治全生集》,還是《醫宗金鑒》,都是清乾隆早期成書并在社會上流傳的,因此,黎洞丸成方并被世人所知當在乾隆初年,這應該是沒有疑問的。
二、黎洞丸的組成、制法、主治和功效
關于黎洞丸的組成和制法,不同醫書的記載略有差異。《外科證治全生集》載:“牛黃、冰片各二錢,阿魏、雄黃各一兩,大黃、乳香、沒藥、兒茶、天竺黃、三七、血竭各二兩,山羊血五錢。前藥各為末,取山羊血拌曬干再磨為末,加藤黃二兩,隔湯煮十余次,去凈浮膩,入末為丸如芡實大,等藥干少加熟蜜可也。丸宜陰干,以黃蠟包裹珍藏。臨用破蠟殼取丸,陳酒化服。專治腫毒跌打危重之證,內服、外敷皆效。”11 《醫宗金鑒》載:“京牛黃、冰片、麝香各二錢五分,阿魏、雄黃各一兩,川大黃、兒茶、天竺黃、三七、瓜兒血竭、乳香(去油)、沒藥(去油)各二兩,藤黃(隔湯煮十數次,去浮沫,用山羊血五錢拌曬。如無山羊血,以子羊血代之)二兩。以上十三味,共為細末,將藤黃化開為丸,如芡實大。若干,稍加白蜜,外用蠟皮封固。內服用無灰酒送下,外敷用茶鹵磨涂。忌一切生冷發物。”12 兩相比較,二方主要藥物相同,后方僅多麝香一味;劑量略有差異;制法基本相同,只是后方更加具體。單就方劑比較,后方更為完善細致,可能是以前方為基礎進行了改進。至于此方的主治和功效,前方載:“專治腫毒跌打危重之證,內服、外敷皆效。”后方則載:“治跌打損傷、瘀血奔心、昏暈不省,及一切無名腫毒、昏困欲死等證。”二方主治完全一致,只是后方比前方在對癥治療上更加具體。
就黎洞丸之組方功效看,方中三七能化瘀止血,消腫定痛。生大黃有活血祛瘀,止血之功效;《本草新編》稱此藥能“導瘀血”,“止疼痛”,“欲其速馳,生用為佳”13。阿魏能解毒。兒茶能活血療傷,止血生肌。天竺黃可清心定驚,用于治療外科創傷時主要取其清熱之功效,如《神農本草經疏》載用該藥“療金創者,總取甘寒涼血清熱之功耳”14。血竭能活血化瘀,止痛止血。乳香和沒藥為活血止痛的常用藥,“乳香功專活血而定痛,沒藥功專散血而消腫”15。雄黃不僅能解毒,而且據《景岳全書·本草正》載其可“化瘀血”16。山羊血能活血散瘀,通絡解毒。麝香能活血,止痛;可“走竅入筋,能通筋竅之不利,開經絡之壅遏”17。牛黃能清熱解毒,化痰開竅。藤黃能止血消腫。冰片有清熱止痛之功效,《景岳全書·本草正》稱此藥“味微甘,大辛。敷用者,其涼如冰,而氣雄力銳,性本非熱,陽中有陰也。善散氣散血,散火散滯”18。而黃酒可活血通絡止痛,燙后增效。
通過對方劑中各成份的功效分析可以見出,黎洞丸確為主治跌打損傷后氣滯血瘀,經絡不通,出現肋下青紫,疼痛難眠,咳痰吐血等一系列癥狀的有效方劑。由此可見,《紅樓夢》寫寶玉“叫人燙黃酒,要山羊血黎洞丸來”醫治襲人的跌打損傷,是有著充分的醫學和藥學根據的。從醫學角度言,此方與診治的病癥可謂絲絲入扣。僅從這點看,也證明黎洞丸絕非《紅樓夢》作者向壁虛構的藥方。此一方劑,當是作者在生活中接觸過或研讀過,且深諳其藥理,故能于行文中信筆拈來;雖是小說家言,卻據之有方,合于醫理。
三、從黎洞丸推斷《紅樓夢》成書時間
關于《紅樓夢》的成書年代,學界存有爭議。有認為《紅樓夢》成書于康熙朝者,有認為成書于乾隆朝者。例如,鄧狂言《紅樓夢釋真》認為原本《紅樓夢》成書于康熙時代:“蓋原本之《紅樓》,明清興亡史也”;“曰‘增刪五次者,見現行《紅樓》之歷史,已非僅原本《紅樓》之歷史也”;“蓋《紅樓夢》之作當在康熙時代(疑吳梅村作,或非一人作)”19。方豪考察《紅樓夢》中提到的西洋物品,依據文獻中有關西洋物品在順治至乾隆時期流傳的情形,從而推斷:“惟乾隆時,無論在朝廷或民間,外國物品已司空見慣,至少若干物品,不應如書中所描寫之為罕見。若在順治時,則宮中之外國物品,亦不能如《紅樓夢》所記之多。故以外國物品論,則《紅樓夢》最適宜之時代,應為康熙朝。”20 歐陽健則依據袁枚、陳其元等人的記載,斷定“曹雪芹是曹寅的兒子,是康熙年間的人”;并據《紅樓夢》中所言“吾家自國朝定鼎以來,功名奕世,富貴流傳,已歷百年”,指出:“從萬歷四十四年(1616)下推至康熙四十四年(1705),已歷九十年,《紅樓夢》大體就是在此時成書的。”21 從而得出《紅樓夢》大約成書于康熙四十四年的結論。然而,據現存文獻可知,黎洞丸最早見于《外科證治全生集》和《醫宗金鑒》,此前未見有文獻記載。《外科證治全生集》刊于乾隆五年(1740年),而《醫宗金鑒》成書于乾隆七年(1742年),則《紅樓夢》第三十一回的成書時間也當在乾隆初年或以后,最早不能早于乾隆五年。據此而論,則上述所謂《紅樓夢》成書于康熙朝的說法,顯然難以成立。
或許有人會說,可能在乾隆五年前就有關于黎洞丸的記載,《紅樓夢》作者在《外科證治全生集》成書和刊刻前接觸到該方;只是因為這些記載我們暫時未看到,或者相關文獻已散佚,今人已無法看到了。我們無法排除這種“可能”,但這種“可能”其實是一種假設。假設是需要事實來論證的,科學研究就是求證。我們可以“大膽的假設”,但必須“小心的求證”,如果不能用事實來證明這一假設,這一假設就暫時不能成立。把未經論證的假設作為前提并在此基礎上開展討論,這樣的研究應該是不科學的。因為假設本身就有兩種可能,假設者并不能排除根本就沒有這種記載的可能。而根據事實得出的結論,即使錯誤也是科學的,因為它是被證實的,也是可以被證偽的,如果誰發現了新的事實,誰就可用此事實來推翻原有的結論,從而推動這一認識的發展22。這是我們所提倡的科學的研究方法和正確的研究態度。
在結束本文之前,有必要說明,“山羊血黎洞丸”在《紅樓夢》的個別版本中稱“山羊血牛黃丸”。如中國藝術研究院紅樓夢研究所據蘇聯科學院東方研究所列寧格勒分所編定的《石頭記》(簡稱列藏本)第三十一回中寫道:“寶玉的意思即刻便叫人燙黃酒,要山羊血牛黃丸等藥去。”23 遍查相關醫藥類文獻,從無“山羊血牛黃丸”方劑記載,臨床也無在牛黃丸里加山羊血的用法。如果斷句為“要山羊血、牛黃丸等藥去”,山羊血雖有藥用功效,但無單獨成方的用法;“牛黃丸”是否為對癥方藥呢?《紅樓夢》描寫襲人被踢后肋上青紫,屬于外科的軟組織損傷后引起局部血瘀所致,氣血瘀阻,經絡不通,不通則痛,故襲人“覺得肋下疼的心里發鬧”,后又出現吐血癥狀。通曉醫理的人都知道,此時最需活血化瘀、止血止痛的藥物,而牛黃丸并無此功效,因而用在襲人身上并不對癥。《中醫方劑大辭典》載有命名為牛黃丸的方劑144種(第15110條—第15254條),方劑雖多,互有異同,但主要用于搜風化痰,寧心開竅,主治小兒各種急、慢性驚風、癇疾和成人中風、熱病發狂、神志不寧等,也可主治小兒疳疾痞癥。此外,牛黃丸還有治風毒、喘嗽、大便不通、傳尸惡疰、小兒腦長、小兒身體溫壯等用法24。牛黃丸用法雖多,卻并無一種是用于治療跌打損傷的。而正如醫學專家和紅學家們論證的那樣,《紅樓夢》的作者精通醫理25,在小說中寫了大量從醫學角度分析都堪稱精辟的醫案26,我們不能設想作者會用毫不對癥的牛黃丸來治襲人之傷。而黎洞丸是治療跌打損傷的常用方劑,用于被踢打至青紫瘀血,肋下疼痛的襲人,正是醫之成理,據之有方。因此,列藏本中“要山羊血牛黃丸等藥”一語,無論斷句為“山羊血牛黃丸”或“山羊血、牛黃丸”,其實都不成立,不是精通醫理的作者的原意。列藏本的這一記載,當是《紅樓夢》傳抄過程中訛誤所致。當然,《外科證治全生集》、《醫宗金鑒》所載黎洞丸方劑中第一味藥即牛黃,山羊血又是其制作藥丸的重要成分,所以寫成“山羊血牛黃丸”也非全無來歷。
綜上所述,《紅樓夢》敘寫襲人被踢傷后,寶玉命人取“山羊血黎洞丸”,從醫學角度而言,此藥與襲人被踢傷后所需診治的病癥完全吻合;而個別版本中的“山羊血牛黃丸”則是傳抄過程中訛誤所致,不足為信。從現存文獻看,最早記載黎洞丸的《外科證治全生集》、《醫宗金鑒》均成書和刊刻于乾隆初年,隨后在社會上傳播開來;隨著這些醫書的傳播,里面的方劑也流行于世,使得醫者、病家和文人等有機會得以接觸、研讀和記載這些方劑。據此推斷,《紅樓夢》第三十一回內容寫定時間當在乾隆初年或以后,最早不早于乾隆五年(1740年),因而所謂《紅樓夢》成書于康熙朝的說法,恐怕難以成立。
注釋:
① 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藏楊繼振舊藏本:《乾隆抄本百廿回紅樓夢稿》,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第367頁。
②⑤24 彭懷仁主編:《中醫方劑大辭典》,人民衛生出版社1997年版,第1331、1331、692—714頁。
③⑥11 王維德:《外科證治全生集》,人民衛生出版社1956年影印版,第23、2、23—24頁。
④ 《中醫大辭典》編輯委員會編:《簡明中醫辭典》(修訂本),人民衛生出版社1979年版,第1011頁。
⑦⑧⑨12 吳謙等編:《醫宗金鑒》,人民衛生出版社1982年版,第3、7—8、9—10、2317頁。
⑩ 趙學敏:《本草綱目拾遺》,人民衛生出版社1963年版,第233—234頁。
13 陳士鐸:《本草新編》,中國中醫藥出版社1996年版,第206頁。
14 繆希雍:《神農本草經疏》,中國中醫藥出版社1997年版,第208頁。
15 嚴潔等:《得配本草》,中國中醫藥出版社1997年版,第197頁。
1618 張介賓:《景岳全書》,上海科學技術出版社1959年版,第958、950頁。
17 張璐:《本經逢原》,中國中醫藥出版社1996年版,第275頁。
19 鄧狂言:《紅樓夢釋真》,轉引自一粟編《紅樓夢資料匯編》,中華書局1964年版,第335—336頁。
20 方豪:《從〈紅樓夢〉所記西洋物品考故事的背景》,《方豪六十自定稿》,臺灣學生書局1969年版,第482頁。
21 歐陽健:《曹雪芹的時代》,《明清小說研究》1999年第1期。
22 王齊洲:《〈三國志演義〉成書時間新探——兼論世代累積型作品成書時間的研究方法》,《中山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4年第1期。
23 中國藝術研究院紅樓夢研究所、蘇聯科學院東方研究所列寧格勒分所編定《石頭記》(簡稱列藏本),中華書局1986年版,第1264頁。
25 參見陳存仁、宋淇:《紅樓夢人物醫事考》,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6年版;高振達:《〈紅樓夢〉中的醫人醫事》,《河南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95年第3期。
26 參見常細樵:《〈紅樓夢〉醫案評述》,《紅樓夢學刊》1982年第3輯。
作者簡介:李曉華,華中師范大學文學院博士研究生,湖北武漢,430079;王齊洲,華中師范大學文學院、湖北文學理論與批評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導師,湖北武漢,430079。
(責任編輯 劉保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