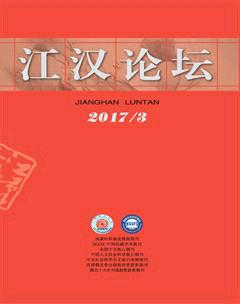互異與共融:民間組織參與藏區貧困治理的能力比較與路徑探究
周曉露++李雪萍
摘要:作為連片特困地區,藏區貧困發生率高、貧困程度深,亟需民間組織參與到貧困治理中來。在社會資本的視角下,本土民間組織與外來民間組織在社會關系網絡、規范與信任這三個要素上都存在差異,這些差異又分別造成了本土與外來民間組織在資源獲取、資源傳遞及社會動員等方面的能力差別。為了使兩種民間組織在藏區貧困治理中的作用最大化,必須將二者融合為一個有機的整體,而“外助內應”是實現這種融合的最好路徑。具體而言,就是借力外來民間組織的開放性、異質性關系網絡,以及公益規范的特點,實現資源獲取與資源傳遞的最大化,同時發揮本土民間組織社會相似性信任度高、組織動員能力強的特點,從而使本土民間組織與外來民間組織相互影響、互為補充,實現民間組織參與藏區貧困治理的良好效應。
關鍵詞:民間組織;貧困治理;社會資本;藏族地區
基金項目:國家社會科學基金后期資助項目“甘孜藏區反脆弱發展研究”(15FSH002);華中師范大學研究生教育創新資助項目“規則與利益:縣域貧困識別的行動邏輯研究——以大別山區H貧困縣為例”(2016CXZZ130)
中圖分類號:C912.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3-854X(2017)03-0125-06
消除貧困、改善民生、實現共同富裕,是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改革開放以來,在經濟高速增長與大規模扶貧開發的強力助推下,我國減貧實踐取得了顯著的成績。與此同時,包括西藏自治區及四省藏區在內的藏族地區,集“民族地區”、“邊疆地區”、“連片特困地區”等特征于一體,貧困發生率高,貧困程度深,是扶貧開發工作中難啃的“硬骨頭”。在藏區的貧困治理工作中,政府的能力有限:一方面,藏區地理環境特殊,高山峽谷、區位邊緣、地震頻發,因地廣人稀而造成的居住形態的分散給政府貧困治理帶來了較高的成本,也制約了政府的公共服務在基層各個領域的抵達。① 另一方面,在藏區環境相似的背景下,各級政府為了規避因貧困治理效益的不確定性而產生的弊端,紛紛采用模仿的策略,導致藏區在扶貧產業的選擇上呈現出極強的同質性。② 鑒于藏區的貧困現狀及政府單向度貧困治理的不足,民間組織參與藏區的貧困治理顯得尤為重要。《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打贏脫貧攻堅戰的決定》強調“鼓勵支持民營企業、社會組織、個人參與扶貧開發,實現社會幫扶資源和精準扶貧有效對接”③。然而,現實境況卻是藏區民間組織數量相對較少,參與扶貧開發工作的深度較為有限,有些區域甚至呈現民間組織在貧困治理中的“不在場”狀態。④ 在考察藏區地域特殊性和民間組織現狀的基礎上,探索民間組織參與藏區貧困治理工作的有效性是本研究的主旨,而從社會資本的視角分析本土民間組織與外來民間組織在藏區扶貧工作中的優勢與不足,并尋求二者優勢互補、形成合力的可行路徑則是本研究的歸宿。
社會資本概念發軔于20世紀初期,在漫長的歷史進程中,它逐漸發展并被運用于理論研究,在社會學、經濟學、政治學等領域產生了廣泛的影響。率先將社會資本概念引入社會學領域的是法國社會學家布迪厄(Pierre Bourdieu),他指出:“社會資本是現實或潛在的資源的集合體,這些資源與擁有或多或少制度化的共同熟識和認可的關系網絡有關,換言之,與一個群體中的成員身份有關。它從集體擁有的角度為每個成員提供支持,在這個詞匯的多種意義上,它是為其成員提供獲得信用的‘信任狀”⑤。布迪厄之后,科爾曼(James Coleman)從功能的角度分析社會資本,他指出:“社會資本的定義由其功能而來,它不是某種單獨的實體,而是具有各種形式的不同實體。其共同特征有兩個:它們由構成社會結構的各個要素所組成;它們為結構內部的個人行動提供便利”⑥。帕特南(Robert Putnam)則認為,“社會資本是指社會組織的特征,諸如信任、規范以及網絡,它們能夠通過促進合作行為來提高社會的效率”⑦。福山(Francis Fukuyama)將社會資本視為“一個群體成員共有的一套非正式的、促進他們彼此合作的非正式規范”⑧,信任則幾乎等同于社會資本。盡管布迪厄、科爾曼、帕特南和福山所處時代有所不同,對社會資本的分析亦各有側重,但他們都強調公民參與、共享規范和社會信任等元素與制度績效、經濟繁榮和社會發展的關聯。概括起來,社會網絡、社會規范和信任可以看作社會資本的三個基本要素。
一、互異的社會資本要素:本土與外來組織的差異探微
民間組織,即社會轉型過程中由各個不同社會階層的公民自發成立的、在一定程度上具有非營利性、非政府性和社會性特征的各種組織形式及其網絡形態。⑨ 它是政府與私人企業之間的正式或非正式的制度空間,不僅包括在民政部門正式注冊的社會團體、民辦非企業、基金會等組織,也涵蓋未按現行法規登記注冊的草根組織及各種網絡型、松散型社會組織等組織形態。本文對藏區民間組織的劃分,既不是根據在民政部門登記與否將其區分為合法民間組織和草根組織,也不是參照民間組織與政府的管理關系將其分為緊密型官辦民間組織、松散型官辦民間組織和草根型民間組織,而是依據民間組織的生成空間將其分為本土民間組織和外來民間組織,其中本土民間組織意指在藏區本土生成的民間組織,而外來民間組織是指在藏區之外生成的民間組織。由于藏區和非藏區的區域差異較大,因而在關系網絡、規范與信任這三個社會資本的主要構成要素方面,本土民間組織與外來民間組織不僅存在差異,而且這種差異幾乎呈現出對立的狀態。
(一)關系網絡的互異:封閉性與開放性
作為社會資本的載體,關系網絡指的是鑲嵌于社會結構之中的人與人、團體與團體等之間的關系構成的復雜網絡。⑩ 社會資本根植于關系網絡,是嵌入于一種社會結構中的可以在有目的的行動中攝取或動員的資源。{11}
民間組織的關系網絡,具體指的是組織所具有的外部聯系。帕特南將關系網絡區分為水平網絡(將平等地位和權力的主體聯系在一起)和垂直網絡(將在等級和依賴不對稱關系中的不平等主體聯系起來)。林南對關系網絡作了進一步探討,指出關系網絡的規模、密度、同質性、異質性、內聚性和封閉性等均可作為社會資本的測量指標。{12} 本土民間組織內生于區位邊緣、交通不便的藏區,因而其關系網絡局限于藏區內部,具有封閉性、同質性的特征。外來民間組織則側重于外部關系的開拓,其關系網絡不僅可以覆蓋全國諸多省市,尤其是經濟活躍的東部地區,而且還能鏈接至國外。它既包括各類同質性的社會組織,更涵蓋異質性較強的藏區外營利組織(主要是企業)及民眾,具有開放性、異質性的特征。
(二)規范的互異:互益性與公益性
正式或非正式的規范是社會資本的重要組成部分,前者是指各種明文規定的制度,后者則是指生活中某些不言自明的習俗規則。它主要包括三種類型,即道德性規范(如輿論、習俗、道德)、契約性規范(如組織規則)和行政性規范(如法律)。{13}
由于地理位置偏遠以及文化性質獨特,在漫長的歷史進程中藏區形成了如雜安部、夏尼、措哇、哈尼等血緣組織,比瓜把、俄拉 {14} 等地緣組織。由血緣組織逐漸向社區互助組織轉化的“沙尼”組織等傳統的民間組織形態沿襲至今,仍葆有極強的生命力,并發揮著重要作用,在社會秩序的維系與調控等方面填補了國家權力的真空地帶。本土民間組織的規范是非正式的,在紅白喜事、蓋房、修牲畜欄、勞動協作、借貸等事務上有一整套資金、勞力等資源共享與互惠的不成文規定。而這種不成文的規定強調組織內的成員相互幫扶,即互益性,其指涉的對象主要是組織內成員及少數組織外成員。
不同于本土民間組織的傳統組織形態,外來民間組織是具有現代組織形態的新型社會組織,具有正式的組織規章制度,紅十字會、慈善組織、民辦非企業單位、基金會等都屬于藏區外來民間組織的范疇。作為外來民間組織,它們進入藏區的目的更多的是為了給藏區民眾帶來福祉,幫助改善藏區的民生。{15} 相較于本土民間組織的互益特征,外來民間組織以公益性為主要特征,其受益者是整個社會,資源基礎也是整個社會。
(三)信任的互異:社會相似性信任與聲譽及法制信任
信任是社會資本的核心內容,信任程度和“信任半徑”是衡量社會資本的重要標尺。學者們對信任有不同的分類,如特殊信任與普遍信任,制度信任與人際信任,一般性信任、技能信任與義務信任等。根據祖克爾(Lynne G. Zncker)的信任源理論,信任的來源包括聲譽信任、社會相似性信任和法制信任。{16}
本土民間組織的信任主要來源于基于強烈的宗教認同形成的社會相似性信任。宗教是藏族文化的靈魂,它形塑著藏區民眾的價值觀、道德準則與行為模式,對藏區民眾的政治、文化、生活等方方面面產生了廣泛而深遠的影響。在財富觀上,宗教也給藏區民眾打上了深深的烙印。藏傳佛教中“重來世、輕現世,重信仰、輕物質”的教義控制著人們的欲望,塑造了藏族文化中“剛夠就好”的淡薄的財富觀念。{17} 受到本土性宗教文化的浸淫及長久以來形成的慣習的影響,農牧民將大量的剩余財物捐給寺廟這類與現行市場經濟趨利性大相徑庭的行為在藏區屢見不鮮,卻有著廣泛的認同。
外來民間組織缺乏社會相似性這一增進信任的途徑,這是由藏區的特殊性造成的。近代以來,國家權力逐步向基層社會滲透,但由于地理位置偏遠,國家進入藏區的深度有限,許多鄉村部落成為事實上的國家權力的“難入之地”。盡管在建國后中央大大加強了在地方基層的行政控制,但是在區位邊緣的藏區,國家權力的滲透較為遲緩,而這也加深了藏區與內地的差異。絕大多數藏民只會說藏語、識藏字,從而阻礙了外來民間組織與藏民的交流,而文化的隔閡更是外來民間組織融入的阻力,因此外來民間組織在藏區建立信任的方式與社會相似性信任無緣,唯有另辟蹊徑,尋求聲譽信任或法制信任。
二、建構的貧困治理能力:社會資本對民間組織扶貧的形塑
在社會資本的視角下,本土民間組織與外來民間組織在社會關系網絡、規范與信任這三個要素上都存在差異,這些差異又分別造成了本土與外來民間組織在資源獲取、資源傳遞及社會動員方面的能力差別。(見圖1)
(一)關系網絡與資源獲取能力的生成
資源的獲取是“貫穿組織生命的一個必需的但又是不斷變化的過程”{18},而社會關系網絡則直接影響到社會組織吸納資金、物質資源以及人力資本的能力。社會組織參與貧困治理急需的物質資源或資金支持主要來源于政府的財政資助以及社會各界的捐助,社會組織的自愿性特征決定了其所需的人力資源以及相應的信息、知識、經驗和技能等依賴于民眾不計酬勞的自愿行動,這極大地考驗著社會組織的招募能力。換言之,囿于自愿性和非營利性,民間組織在獲取資源方面不及政府或企業(后者可以通過財政收入或生產經營等方式獲取資源),因而嚴重依賴于外部的社會資源。{19}
封閉性、同質性的關系網絡,決定了藏區本土民間組織的資源獲取主要來源于藏區內部,而遠高于全國貧困發生率的現狀,意味著本土民間組織能夠獲取的扶貧資源相當有限。{20} 一方面,藏區地方病多發,地質災害與自然災害頻繁,農牧民因病返貧、因災返貧情況突出,就如“站在齊脖深的河水中,只要涌來一陣細浪,就會陷入滅頂之災”{21}。藏區許多非貧困人群尚且自身難保,更是沒有余力參與到貧困治理中來,本土民間組織能夠從藏區內部獲取的人力資源以及依托人力資源的信息、知識、經驗和技能嚴重不足。另一方面,藏區自然地理環境惡劣,占重要地位的農牧業分別陷入“農業靠天收,牧業‘秋肥、冬瘦、春死”的困局{22},而工業發展遲緩,高科技產業所占比重很小,本土民間組織能夠獲取的藏區物力資源與財力資源不足。
外來民間組織的關系網絡具有開放性與異質性特點。通過匯聚不同領域、地域的專家,將這些專家的個人社會關系網絡以及他們在社會網絡中的弱關系等嵌入社會組織的社會關系網絡中,可以為藏區貧困治理帶來更多的人員支持。此外,外來民間組織可以通過與藏區外部各級政府合作、與各類企業聯盟以及接受來自民眾的捐助,從而獲取廣泛的資金來源及物質支持。最后,藏區具有優勢明顯的青稞、藏藥、牦牛等農牧產品及其加工產品,如何實現產品收益的最大化以實現產業扶貧,尤其是如何開發旅游扶貧這種綠色產業,還需要外來民間組織帶來先進的知識、新鮮的信息、創新的制度等。外來民間組織可以將貧困治理所需的資源帶入相對封閉的藏區,彌補本土民間組織資源獲取不足的缺憾。
(二)規范與資源傳遞能力的建構
在市場經濟浪潮中,本土民間組織因其封閉性特點,對市場化社會具有一定的排斥功能,組織內的成員相互幫扶,使得貧困群體的基本需求得到保障。
這種互益的取向,意味著資源分配局限于組織內部成員,而組織外部的成員則因物理距離或心理距離的遙遠而無法惠及。伴隨著經濟的發展,藏區內部分化擴大,藏區本土民間組織的互益取向也使馬太效應凸顯。經濟狀況較好、社會發育程度較高的村莊或部落,組織內成員有能力互幫互助。如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甘孜縣H村作為“美麗幸福新村”,經濟狀況較好,在鄉村精英的帶動下,發展出蔬菜協會、運輸協會等具有民辦互助性質的行業協會,對H村內貧困人口的幫扶有一定的作用。居住于經濟發展較為遲緩的村莊或部落的貧困人口,生計難以維持,幫扶需求更迫切,而本土民間組織的互惠特征及有限的人力、物力和資金,使其難以將資源傳遞到更廣泛的貧困人群。
外來民間組織,因其公益性的規范,在貧困治理中,時間成本、物理距離等客觀困難并不是它們資源傳遞的障礙。將資源向最邊遠、最貧困的村莊或部落傾斜與傳遞,將扶貧的范圍向縱深延伸,擴大扶貧面,既是外來民間組織進入藏區的初衷,同時也是它們的優勢所在。
(三)公眾信任與社會動員能力的培育
“合作的基礎是合作的參與者都能夠切身感受到的極其真實的共同價值觀念,而不是鼓勵人人團結的普遍倫理觀念,或者是有機的社會概念”{23}。根據信任來源的不同,信任程度也有一定程度的分化,它對民間組織的社會動員能力有著重要影響。本土民間組織的信任主要來源于社會相似性,信任程度較高,因而在藏區內的社會動員能力相對強大;反觀外來民間組織,其信任來源于聲譽及法制,信任程度處于劣勢,因而在藏區內的社會動員能力低下。
本土民間組織的信賴來源于社會相似性。{24} 本土社會組織根植于藏區社會,與藏區民眾建立了社會相似性信任,藏區民眾對其具有強烈的情感認同,因而信任程度較高。同時,由于本土民間組織的主要領導者是在藏區具有極高號召力和影響力的民間權威,因而其組織動員能力較強,在調動藏區民眾的能動性方面占據優勢。
外來民間組織,生成于藏區外部,因而在與藏區的情感認同方面存在不足,其信任主要來源于聲譽及法制。聲譽產生信任即根據對他人過去的行為和聲譽的了解而決定是否給予信任。{25} 法制產生信任即基于非個人性的社會規章制度,如專業資格、科層組織、中介機構及各種法規等的保證而給予信任。{26} 聲譽信任與法制信任帶來的信任程度相對較低,造成外來民間組織的社會動員能力不足。當然,如果外來民間組織能夠很好地融入本土民間組織當中,在保證法制信任的基礎之上,不斷提升聲譽信任,也能夠使自己的社會動員能力得以增強。
三、共融的“外助內應”路徑:藏區本土與外來組織優勢組合
由于開放性和異質性的關系網絡,外來民間組織可以網羅更多的社會資本,開拓藏區貧困治理所需的人力資本、物質資源及資金支持,且由于其公益性特征,外來民間組織也可以將獲取的扶貧資源傳遞到藏區的各個角落。外來民間組織就如同一張大網,可以網羅藏區內外的各類資源,覆蓋到所有需要幫助的貧困人口。在外來民間組織社會關系網絡規模較大、廣度有余的同時,這張大網卻不夠緊實。由于信任程度較低,外來民間組織與藏區民眾的關系強度不足,較難將藏區內的資源聯結起來,這限制了外來民間組織在藏區貧困治理中的功能發揮。反觀本土民間組織,盡管關系網絡封閉且同質,但由于與藏區民眾黏合較強,因而能更有效地發揮貧困治理的作用。為了使兩種民間組織在藏區貧困治理中的作用最大化,必須充分發揮各自的優勢,彌補對方的不足。為此,必須克服“各自為戰”的封閉式運作狀態,將二者融合成一個整體,發揮整體大于部分之和的集體效應。怎樣才能實現這種融合呢?筆者認為,“外助內應”是實現這種融合的最好路徑。所謂“外助內應”,通俗地講,就是通過外來民間組織的幫助,以及本土民間組織的響應,形成一個“共融共進”的開放式整體。具體而言,就是借力外來民間組織的開放性、異質性關系網絡,以及公益規范的特點,實現資源獲取與資源傳遞的最大化,同時發揮本土民間組織社會相似性信任度高、組織動員能力強的特點,從而使本土民間組織與外來民間組織相互影響、互為補充,實現民間組織參與藏區貧困治理的良好效應。
(一)資源的外助:異質網絡的借力與公益規范的補充
一方面,借助外來民間組織開放性、異質性的關系網絡,拓寬本土民間組織在藏區獲取扶貧資源上的邊界,從而彌補本土民間組織封閉性和同質性的關系網絡造成的資源獲取不足的缺陷,實現本土民間組織對外來民間組織異質性關系網絡的借力。藏區外來民間組織的關系網絡開放性較強、異質性較高,其網絡資源不僅可以覆蓋全國諸多省市,尤其是經濟發展活躍的東部地區,而且還能囊括國外的豐富資源,既包括各類同質性的社會組織,同時也可以聯結異質性較強的藏區外營利組織(主要是企業)及民眾。與企業的聯盟,可以為藏區基礎設施建設提供充沛的物質保障與資金支持,還能為藏區特色產業開發提供經驗、技術以及銷售渠道方面的支持。與此同時,在藏區貧困治理中,公共服務供給、扶貧政策傳達以及幫扶信息宣傳等需要大量的人員參與,教育扶貧、醫療扶貧、產業扶貧等領域也需要專業的人才給予技術和信息的支持。外來民間組織可借助開放的關系網絡,聯結藏區外大量的志愿者參與到藏區的貧困治理中來,尤其是能夠吸納藏區貧困治理急需的教育、醫療等領域的專業技術人才,甚至還可以使志愿者的個人社會關系網絡嵌入民間組織的社會關系網絡。
另一方面,借助外來民間組織的公益性規范,填補本土民間組織在藏區扶貧資源傳遞中的真空,從而彌補本土民間組織因互益性規范導致的資源傳遞范圍受限的不足,實現外來民間組織對本土民間組織互益性規范的補充。政府在公共產品供給上通常能夠滿足大多數民眾的需求,但是對于少數民眾尤其是需要幫扶的弱勢群體,仍然存在疏漏。本土民間組織能在一定程度上彌合政府資源傳遞的失靈,然而受制于自身的輻射范圍以及互益性特征,本土民間組織無法全面覆蓋困難人群。在扶貧資源的傳遞方面,外來民間組織因其公益性特征而具有無可比擬的優勢,它能夠將其觸角延伸至最需要幫扶的貧困地區和人群,具有廣泛的資源傳遞范圍。
(二)動員的內應:來源于社會相似性的信任傳遞
資源獲取豐富與傳遞范圍廣泛是外來民間組織較之本土民間組織的優勢。然而,單一的資源輸入只能給藏區民眾帶來一時的經濟緩解與條件改善。扶貧不僅僅是錢的問題,藏區的貧困治理也絕非單純的資源輸入。國家頂層設計提倡由“輸血式扶貧”轉為“造血式扶貧”,呼應了學界近年來熱議的“參與式反貧困”理念,即貧困群體應該發揮主觀能動性,積極參與到扶貧項目的決策、實施、監督等各項工作中來,變貧困治理的被動接受者為積極參與者。
“信任的作用就像一種潤滑劑,它使一個群體或組織的運作更有效”{27}。藏區民眾積極參與到貧困治理中,除了要增強他們自身的認識,更要增進他們對外來民間組織的信任,從而使外來民間組織在藏區開展貧困治理工作中得到助力。動員的內應,可以借助社會資本中信任要素的可傳遞性,即“如果A信任B,而B又信任C,則A也會信任C”{28}。如前文所述,本土民間組織因信任來源于社會相似性,因而信任程度高,如若本土民間組織向藏區民眾傳達對外來民間組織的高度信任,則這種信息可以轉化為藏區民眾對外來民間組織信任的增進,從而使外來民間組織在與藏區民眾沒有前期直接接觸的基礎上贏得藏區民眾的信任,并激發藏區民眾在貧困治理中的積極性與行動力,使資源的輸入和傳遞得到藏區民眾的助推。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農村絕對貧困人口已由1978年的2.5億減少到2015年的5575萬,貧困發生率也隨之從30.7%降低到5.7%。{29} 作為貧困治理的“毛細血管”,民間組織在貧困治理中發揮著重要作用。藏區特有的地理環境和文化傳統,使得區內的民間組織也具有很強的獨特性。運用“外助內應”的方式,能夠將藏區內外的民間組織融合為一個有機的整體,充分發揮兩種民間組織在扶貧方面的優勢,不失為藏區扶貧的一條有效路徑。
注釋:
① 吳開松、楊芳:《社會組織在西部民族地區社會治理創新中的價值研究》,《貴州民族研究》2014年第9期。
② 何通艷:《藏區參與式反貧困研究》,西南財經大學博士論文,2013年。
③《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打贏脫貧攻堅戰的決定》,《人民日報》2015年12月8日。
④ 李雪萍、王蒙、龍明阿真:《主體集結整合資源:藏區貧困治理之關鍵——以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甘孜縣為例》,《貴州民族研究》2015年第3期。
⑤ P. Bourdieu, The Forms of Social Capital, in J. Richardson (ed.), Handbook of Theory and Research for the Sociology of Education, Greenwood Press, 1986, p.248.
⑥ [美]詹姆斯·S·科爾曼:《社會理論的基礎》(上),鄧方譯,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99年版,第354頁。
⑦{23} [英]羅伯特·D·帕特南:《使民主運轉起來:現代意大利的公民傳統》,王列、賴海榕譯,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95、197頁。
⑧ [美]弗朗西斯·福山:《大分裂:人類本性與社會秩序的重建》,劉榜離、王勝利譯,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2年版,第18頁。
⑨ 王名:《走向公民社會——我國社會組織發展的歷史與趨勢》,《吉林大學社會科學學報》2009年第3期。
⑩ 姜振華:《論社會資本的核心構成要素》,《首都師范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8年第5期。
{11} Lin Nan, Building a Network Theory of Social
Capital, Connections, 1999, 22(1), p.35.
{12} [美]林南:《社會資本:關于社會結構與行動的理論》,張磊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59—71頁。
{13} 童星、羅軍:《社會規范的三種形式及其相互關系》,《江海學刊》2001年第3期。
{14} 有學者認為“俄拉”不是地緣性組織,而是為了專門的事務性目的而組織并形成的,但是基于它是村莊內生的組織,本文將“俄拉”歸類為地緣性組織。
{15} 當然,不排除有些外來民間組織尤其是境外在藏外來民間組織另有所圖(如進行分裂活動等),但這不在本文的討論范圍內。
{16}{24}{25}{26} L. G. Zucker, Production of Trust: Institutional Sources of Economic Structure, 1840-1920, Research in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1986, 8(2), pp.53-111.
{17} 石碩:《如何認識藏族及其文化》,《西南民族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15年第12期。
{18} [美]W·理查德·斯格特:《組織理論:理性、自然和開放系統》,黃洋等譯,華夏出版社2002年版,第167頁。
{19} 李宜釗:《投資社會資本:中國非營利組織發展的另一種策略》,《海南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10年第2期。
{20} 根據最新數據統計,云南省迪慶藏族自治州貧困發生率最高,為36.38%;其次是西藏自治區與甘肅省甘南藏族自治州,貧困發生率分別為32.95%、22.6%;貧困發生率相對較低的藏區有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四川省阿壩羌族藏族自治州及青海藏區,貧困發生率分別為16.8%、14.5%、14%,均遠高于我國當前總的貧困發生率5.7%。
{21} [美]詹姆斯·C·斯科特:《農民的道義經濟學:東南亞的反叛與生存》,程立顯、劉建等譯,譯林出版社2013年版,第1頁。
{22} 杜明義、趙曦:《中國藏區農牧區反貧困機制設計》,《貴州社會科學》2010年第8期。
{27} [美]弗朗西斯·福山:《信任:社會美德與創造經濟繁榮》,彭志華譯,海南出版社2001年版,第125頁。
{28} 李超玲、鐘洪:《非政府組織社會資本:概念、特征及其相關問題研究》,《江漢論壇》2007年第4期。
{29} 國家統計局:《中華人民共和國2015年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公報》,《人民日報》2016年3月1日。
作者簡介:周曉露,華中師范大學社會學院博士研究生,湖北武漢,430079;李雪萍,華中師范大學社會發展與社會政策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導師,湖北武漢,430079。
(責任編輯 劉龍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