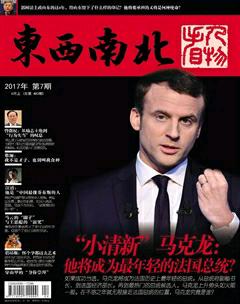支付牌照買賣:扭曲的地下市場
周天
今日頭條和首汽約車都已獲得了護身符,但更多的故事發(fā)生在金融牌照交易市場。“一個什么業(yè)務都沒有的空殼公司,張口就要7個億。”在互聯(lián)網(wǎng)金融持續(xù)降溫的這一年,牌照生意活在一個扭曲的空間。
一下飛機,迎接劉慶的除了北京的霧霾,還有買家派來的豪車。上車直奔談判桌,一推開門,燈光昏暗,一張巨大的長條木桌,熙熙攘攘地圍坐了一圈人,這些人都是為了談牌照買賣的中介。
過去一年多的時間,金融牌照買賣,已成為一門前所未有的好生意。
錢太好賺了。一個隱秘又瘋狂的地下市場誕生了。
“哪怕囤著也好”
交易的牌照越來越少,價格已經(jīng)高得離譜。“不包括中介費的話,2015年牌照價格還是2-3-4,2016年上半年已經(jīng)達到了4-5-6,保守估計,2017年可能會變成7-8-9。”一家并購平臺的負責人金雪松說。
這串數(shù)字的單位是億元人民幣。 “2-3-4”是指:牌照中包含一項內(nèi)容,比如互聯(lián)網(wǎng)支付,價格是2億;包含兩項內(nèi)容,比如互聯(lián)網(wǎng)支付和銀行卡收單,則價格是3億,如果再加上預付卡,三項內(nèi)容,價格就是4億。
包含5項內(nèi)容的全牌照難得一見,按金雪松的說法,“絕對可以賣十幾個億了”。比如,去年9月被美團收購的錢袋寶,其牌照中除了常規(guī)資質(zhì),還包含一項罕見的跨境支付資質(zhì)。一位知情人士透露,最后交易總價超過12億。但美團點評不肯透露收購價格,這個數(shù)字未能得到證實。
2016年,互聯(lián)網(wǎng)金融降溫,打牌照主意的公司卻越來越多。除了美團,為了收購牌照,美的花了約3億人民幣,唯品會據(jù)稱花了約4億人民幣,小米付出了約6億人民幣的代價,就連與支付并無強關(guān)聯(lián)的房地產(chǎn)企業(yè)綠地都將一張牌照收入囊中,正在求購牌照的還有滴滴。
總之,買家一個比一個大。
擁有大規(guī)模用戶的互聯(lián)網(wǎng)公司有足夠動機涉足金融市場。它們通常已經(jīng)具備了某種交易場景,適合嵌入金融業(yè)務。你完全可以將滴滴視作一個金融公司:它天然就有大量高頻現(xiàn)金支付行為在平臺上發(fā)生,并且和出行高度相關(guān),既可以順便搭售車險,也可針對司機提供貸款購車服務。牌照能讓這些順理成章的新業(yè)務合規(guī),無監(jiān)管之虞。
不少尚無此類消費場景畫面的小公司,也計劃在2017年拿點金融牌照,“哪怕囤著也好”。
“監(jiān)管”滋生了一個奇貨可居的市場。牌照就是一種準入證,它與1990年代的批條、大城市的戶口和知名小學學區(qū)房,沒有本質(zhì)差異。它不僅能帶來安全感,也成了一項升值空間有保證的資產(chǎn)。
在這江湖久了,誰都不信任
供求比例是失衡的,大約“1:10”,多位業(yè)內(nèi)人士給出的數(shù)字。
正因如此,買主如果僅憑自己的能力去搶奪籌碼,無異于大海撈針,這讓中介們找到了大發(fā)橫財?shù)臋C會。所有的中介都在拼命賽跑,誰先觸達到牌照實際控制人,誰就能獨攬上千萬元中介費。
單筆交易產(chǎn)生的中介費已經(jīng)水漲船高,“2015年是五六百萬的中介費,去年年初是一兩千萬,去年年底是五六千萬。”金雪松說。
牌照交易的流程是,買家會委托一名中介四處尋找牌照,一名中介往往自身人脈有限,他還會委托若干個中介去找,一層層委托下去,形成一個“樹狀圖結(jié)構(gòu)”——每個人都會發(fā)動數(shù)條分支去尋找,每個分支又會生出更多分支,一旦某個觸點找到賣家,就會把信息一層層往回反饋,最終把兩端的買賣雙方串起來——這條線上的每個人都能分一杯羹。
多的時候,這條線上有七八個中介,彼此維持著脆弱的合作關(guān)系。每個人都怕自己被上下游繞開,于是,這個群體間形成了許多不成文的行規(guī)。比如,因為害怕被“跳單”,談判時每個中介都要來到現(xiàn)場,現(xiàn)場不允許交換名片,也不允許進洗手間,直至合同簽訂,利益分配談妥。
買家中介和賣家中介常常是“四六開”或“三七開”,賣方中介因為地位更加強勢,可以分到更多。若促成一單的總傭金按4000萬計算,如果一共有四個中介參與,兩人屬于賣方委托人,可以拿走2500萬,買方的二人就拿1500萬。
相比動輒上千萬的中介費,中國創(chuàng)業(yè)者做夢都想登陸的A股創(chuàng)業(yè)板,其準入條件也不過是“最近兩年凈利潤累計超過1000萬元”。
據(jù)劉慶的估計,整個支付牌照的買賣市場上,一度活躍著“數(shù)千上萬個”這樣的“居間人”,所有人都在共同維護著一個信息不對稱的地下市場。
在這個極其不透明的市場上,渾水摸魚的大有人在。有一家持牌企業(yè)的小股東以出售為名,冒充實際控制人,從5個買家手里各騙了1000萬定金,最后帶著5000萬跑到國外消失了。
據(jù)劉慶所知,有的牌照2015年就賣掉了,但仍然有人到處擴散,對接到最后才發(fā)現(xiàn)找不到源頭了,這導致很多買方始終沒有買到牌照。劉慶說,有個東北的企業(yè)全國到處跑,連軸轉(zhuǎn),跑了大半年,依然遍尋牌照而不得。
“大家就是賺信息不對稱的錢,很多中介會刻意隱藏關(guān)鍵信息。”劉慶說,“在這個江湖混久了,會對誰都不信任。”
在牌照買賣的零和游戲中,有贏家,也有輸家。據(jù)劉慶所知,一個賣家前幾年就申請到了牌照,但因為一時缺錢,在2015年下半年以8000萬賣掉了。“如果能忍一忍,2016年賣4億沒有任何問題,現(xiàn)在這個賣家后悔不已。”
坐地起價和臨陣變卦
這是一個徹底的“賣方市場”,最接近賣方的中介,處在食物鏈的頂層。
“如果買家不開資金證明,或者不簽財務顧問費,你連見面的資格都沒有。”手握一張支付牌照代理權(quán)的金雪松,這樣描述買賣雙方的地位對比。
對很多企業(yè)來說,要開5億的資金證明尚屬困難,“因為資金往往并不都集中在一個賬戶上,幾個億調(diào)動一下,光利息就是不少錢了。”金雪松說,但這樣的門檻絲毫沒有妨礙買家進場爭搶。因為大家都知道,晚一步,價格可能更貴。
“有一次我撮合的買賣雙方基本快要談妥了,這時突然殺進來一個新的買家,直接把價格從5億人民幣抬高到6億人民幣,賣家受不了這種誘惑,立即和前一家分道揚鑣了。”劉慶感嘆道。
買家瘋狂掃貨,讓賣方的心態(tài)越發(fā)膨脹。金雪松也經(jīng)歷過一次賣方變卦:快要談妥時,賣方突然要加價一個億,談判一下就破裂了。
即使走到了簽完股權(quán)轉(zhuǎn)讓協(xié)議的地步,也并不意味著最終能順利交割。因為交易過程中,還有一個至關(guān)重要的變量——央行。央行明確不允許倒賣和租借支付牌照,獲取牌照的唯一途徑,是獲取持牌公司的控股權(quán),從而間接擁有牌照。
私相授受的民間買賣不被許可,央行對持牌公司控股股東的要求非常繁復,比如要有支付和金融相關(guān)經(jīng)驗,更關(guān)鍵的是,股東如果變化,必須以書面形式去央行進行事前報批,只有批準后才能做工商變更。
由于央行審批過程動輒長達數(shù)月之久,在這種漫長等待中,買方和賣方心理會發(fā)生微妙的變化:如果整個牌照行情上漲,賣方就希望央行別批準了,好擇日再賣;但如果價格下跌,就輪到買方來祈禱央行別批了,以便擇日再買。由于審核增加了復雜性,導致交易過程“更撲朔迷離”。
買方,算賬和市值
2016年這一年,收購牌照的主力軍分為兩股:把金融提到戰(zhàn)略高度的互聯(lián)網(wǎng)公司,和急需新概念到股市圈錢的上市公司。他們就像在巴黎老佛爺搶購LV的中國游客,把每一張剛剛露頭的牌照席卷一空。
一家有牌照的公司,在“賣身”前,把市場上所有潛在買家都分析了一遍:凡是面向消費者、用戶基礎(chǔ)大、交易流水大的,就很容易在支付牌照上疊加錢包、分期、征信等產(chǎn)品,就有誕生金融服務集團的機會。典型案例就是京東白條和錢包,單獨體量估值已經(jīng)很高了。
對于美團、滴滴這種有交易環(huán)節(jié)的產(chǎn)品來說,用戶賬戶體系中會形成余額,有了支付牌照,才能把余額留存在錢包里,這些沉淀資金不僅能產(chǎn)生利息,還能產(chǎn)生黏度,讓用戶反復去使用——通俗地理解,只要一張銀行卡里存了錢,用戶就不會扔掉這張卡。
數(shù)據(jù)安全也是考量因素。對美團這樣的公司來說,如果依賴支付寶的通道,所有交易信息就會被支付寶掌握,企業(yè)經(jīng)營狀況和客戶數(shù)據(jù)一覽無余,自己在競爭對手面前毫無秘密可言,因此美團和滴滴們都急切地想擺脫這種“裸奔”狀態(tài)。
“支付本身不需要賺錢,但戰(zhàn)略意義就像地圖一樣,雖然賠錢,但BAT都必須要有自己的地圖產(chǎn)品。”51信用卡的創(chuàng)始人孫海濤說。
互聯(lián)網(wǎng)金融創(chuàng)業(yè)公司也加入了這場爭奪。華創(chuàng)資本合伙人吳海燕說,2016年下半年,金融領(lǐng)域的創(chuàng)業(yè)公司出現(xiàn)了一些復蘇的跡象,最典型的現(xiàn)象就是金融服務類創(chuàng)業(yè)公司都在忙著申請和收購牌照。
除了戰(zhàn)略意義,牌照的另一個好處是,節(jié)省了采用別家支付通道所產(chǎn)生的巨額費用。
“算了半天賬,我們平臺的盈利還不足以彌補支付手續(xù)費,心好累。支付手續(xù)費在總支出中占比蠻高的”,同程旅游旗下同程金服的一位人士透露。另一家理財平臺的人士也說,這一年付出的通道費共計310多萬元,這對利潤單薄的網(wǎng)貸平臺來說,并不是一個小數(shù)目。
“拿阿里3萬億的交易額來舉例,如果支付通道不掌握在自己手上,假設(shè)被按萬分之二的費率來收取手續(xù)費,那么3萬億流水一年的通道成本就是6億,”金雪松算了一筆帳,“如果是一家上市公司,按30倍市盈率算,這6億現(xiàn)金就對應著180億市值,那他即使花20億去買一張牌照都是值得的。”
2016年春節(jié)過后,金雪松剛發(fā)布消息,就有三十多家上市公司找來洽談,他反向調(diào)查對方,挑了有實力的五家,自己親自和實際控制人見了面,最后發(fā)現(xiàn),“這些傳統(tǒng)行業(yè)公司,意圖通過新概念來維持業(yè)績,號稱雙輪驅(qū)動,其實都是為了去資本市場講故事。”
但凡限制供應,價格一定上漲
一頭是旺盛的需求,一頭是稀缺的供給,這就是牌照過去一兩年瘋狂漲價的原因。
與土地市場一樣,供給方只有一個,那就是政府。
這構(gòu)成了一種壟斷效應。央行發(fā)支付牌照的時間集中在2011年初到2015年初之間。聰明人早已發(fā)現(xiàn),早在央行2011年至2013年的發(fā)牌高峰期之后,發(fā)牌數(shù)量就在逐年跳水。2014年發(fā)放19張,2015年全年僅在3月份發(fā)放一張牌照,這一張也成為絕唱。正是在這一年,牌照交易開始抬頭。
到了2016年8月,央行明確公開宣布,堅持“總量控制”原則,“一段時期內(nèi)原則上不再批設(shè)新機構(gòu)”,并注銷長期未實質(zhì)開展支付業(yè)務的支付機構(gòu)牌照。
這徹底打消了排隊申請牌照的企業(yè)們的希望,也是在這個時間點,牌照交易進入最為白熱化的狀態(tài)。“唯品會、小米、恒大、美的,都在2016年迅速完成牌照的收購。”
“其實聰明的人,在股災期間就應該能預判到牌照會升值,因為監(jiān)管肯定會收緊”,劉慶認為,2015年中期,中國股市遭遇大幅下跌,隨后互聯(lián)網(wǎng)金融開始遭遇強監(jiān)管,作為互金行業(yè)的一環(huán),支付產(chǎn)業(yè)也驟然面臨更嚴苛的監(jiān)管。“過去沒有牌照也能做業(yè)務,監(jiān)管還比較放任,很多企業(yè)就沒當回事,而且申報材料非常繁瑣,一些公司嫌麻煩也就沒有積極去爭取。”
但金融這門生意的獨特性就是有形之手維系的壟斷市場,有壟斷就會產(chǎn)生超額收益。
反之,沒有牌照護身,隨時會面臨滅頂之災。去年2月29日,美團遭到一名律師實名舉報稱,美團在沒有第三方支付牌照的情況下,卻從事第三方支付結(jié)算業(yè)務,違反了《非金融機構(gòu)支付服務管理辦法》,甚至涉嫌構(gòu)成非法經(jīng)營罪。到了6月16日,央行支付司人士向媒體確認稱,已約談過美團,限期其3個月內(nèi)整改。隨后,有人發(fā)現(xiàn),美團App上“我的錢包”中余額已無法充值,而是顯示“原路返回”。
而持有牌照則意味著會享受政府某種兜底性保護。比如,一位保險行業(yè)人士說,監(jiān)管不允許壽險公司破產(chǎn)倒閉,過去爛攤子常常由政府出面來收拾,拿到壽險牌照就意味著取得政府發(fā)放的免死金牌。
央行一共分8批發(fā)放了共計270張支付牌照。據(jù)不完全統(tǒng)計,減去因違規(guī)被吊銷的5張,再加上10家被同行兼并,目前市場上存量牌照應該為255張左右。而隨著針對支付行業(yè)的監(jiān)管趨嚴,中小支付企業(yè)利潤空間遭到擠壓,有業(yè)內(nèi)人士估計會有更多支付企業(yè)遭吊銷資質(zhì),這樣一來,目前全國可供交易的支付牌照所剩無幾。
“現(xiàn)在還剩幾十張可供轉(zhuǎn)讓,我推測有超過180張牌照已經(jīng)沉淀下來,再也不會被擺出來賣了,只要是把互聯(lián)網(wǎng)支付業(yè)務做起來的就不會再賣了,比如支付寶,就算出50億,馬云都是絕對不會賣掉牌照的。”金雪松如此認為。“現(xiàn)在每個月市場上大概只有三四張牌照還在交易,一猶豫,再遇到一張合適的牌照就難了,這樣一個市場,還會維持一年”。
難以承受之重
支付牌照的買賣高潮如今已近尾聲,雖然其一度是各種牌照中最稀缺、昂貴的一種,但它的故事卻是普適的,各行各業(yè)的牌照故事遠遠沒有講完。
半年前,《證券時報》調(diào)查過3家被收購的基金銷售公司的裸牌照金額,發(fā)現(xiàn)已經(jīng)從2015年年底的500萬升到了1500萬。如今,價格似乎還在以這種漲幅飆升。
和支付牌照漲價的原因一樣——也是牌照的發(fā)放審核被收緊,供求關(guān)系開始失衡。
截至2016年6月,獲得證監(jiān)會基金銷售業(yè)務資格的第三方基金銷售公司有100家,而申請牌照的潛在企業(yè)卻近千家。
而審批通過的獨立基金銷售牌照速度卻在放緩。2016年前9個月,核發(fā)牌照的獨立基金銷售機構(gòu)分別為9家、6家、5家、2家、0家、3家、1家、2家和1家,呈逐月下降趨勢。可見監(jiān)管態(tài)度的趨嚴。
有牌照中介表示,有客戶申請長達一年還沒下來,而且還有不通過的風險。如果通過收購的話,三個月之內(nèi)就可以完成變更。因此,等不及的公司就會選擇更快更保險的收購方式。
對于P2P這類理財平臺來說,要想做成理財超市,在互聯(lián)網(wǎng)上售賣基金和保險,基金銷售牌照和保險代理或經(jīng)紀牌照就是必不可少的,否則就有被取締的風險。一位P2P平臺的創(chuàng)始人說,“因為審批幾近停滯,現(xiàn)在就連保險代理牌照,價格也突破千萬元量級了。”
類似的牌照生意在互聯(lián)網(wǎng)金融以外的領(lǐng)域也愈演愈烈,視頻、直播、網(wǎng)約車……監(jiān)管之手已經(jīng)伸入競爭已趨市場化的互聯(lián)網(wǎng)領(lǐng)域。
“全新的政商關(guān)系已經(jīng)開啟。”致力于研究中國企業(yè)史的財經(jīng)作家吳曉波,同時也是一位創(chuàng)業(yè)者,早在兩年前就如此判斷:“稍大一點的‘渡口都可能被牌照化,所有的牌照都會成為尋租的對象及演變?yōu)閹追N資本力量的博弈游戲。”
這一天已經(jīng)不可避免地到來了。
今日頭條短視頻業(yè)務“合法”了。盡管這條消息近日才流出,但它已在去年悄悄行動,收購了注冊地在山西運城的一家有牌照的公司解決問題。
在整個視頻領(lǐng)域,監(jiān)管與創(chuàng)業(yè)公司之間的摩擦一直不斷,最早可追溯至優(yōu)酷時代。一個不完全的統(tǒng)計數(shù)據(jù)是,截至2016年中期,共有588家單位拿到此證。
直播在去年崛起之后,也成了重頭監(jiān)管對象。2016年9月,廣電總局發(fā)文要求,必須持有《信息網(wǎng)絡傳播視聽許可證》才能開展直播業(yè)務。此前,沒有拿到視聽許可證牌照的直播網(wǎng)站,暫時都在用文化部《網(wǎng)絡文化經(jīng)營許可證》,因為申請相對容易。但在9月之后,廣電總局又連發(fā)幾次通知,強調(diào)視聽許可證的必要性。
沒有人對此置若罔聞,資金再捉襟見肘,也要直面生死存亡問題。一家直播平臺的高管稱,一年前,一張直播牌照的價格是幾百萬元,自己平臺購買時的價格已經(jīng)是3000萬了。在其他行業(yè),牌照即便沒有金融業(yè)這么貴,其價格上漲的勢頭卻一點也不輸于此。
在2016年網(wǎng)約車新政之后,“京人京牌”的命令一下壓縮了網(wǎng)約車供給量,以及滴滴的盈利能力,“首汽約車”這樣國資背景的強大對手,現(xiàn)在看來倒可能成為用車領(lǐng)域的利益收割者。
2月8日,“首汽約車”對外亮出了它獲得的網(wǎng)約車平臺經(jīng)營許可證,這是北京市發(fā)布的第一個。“首汽約車”的CEO魏東,當天喜氣洋洋地拿著這張許可證擺拍了照片。
牌照并非萬能,但它已經(jīng)成為創(chuàng)業(yè)公司難以承受之重。
(李麗薦自《華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