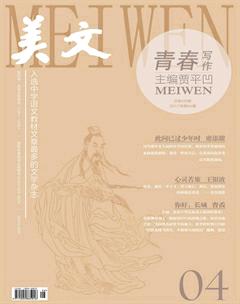雞年話雞
安黎
與人貼得最近的動物,除了貓,大概要數雞了。
雞有家雞與野雞之別:圈養于雞窩的雞叫家雞,散落于山林的雞叫野雞。
家雞與野雞同根同族,但彼此間差異很大。家雞個頭小,野雞個頭大;家雞不能飛得很高很遠,至多能躍上主人家低矮的窗臺或墻頭,野雞卻能縱橫于溝壑,翔越于山嶺,從這根枝頭飛向那根枝頭,從這座山頭飛往那座山頭;家雞長舌婦一般,嘮嘮叨叨個不休,音調相對低沉柔和,而野雞雖不常鳴,卻一鳴驚人,撼天動地。
動物世界自成體系,作為近鄰,人并不能輕易將其讀懂,但以主宰者自詡自居的人,總是習慣于以一己之好惡,給動物貼標簽。標簽雖無形,卻五顏六色。有的形若獎章,有的形若起訴狀,基于此,人便在對待動物的態度上,楚漢有界,褒貶分明:有的動物被頌贊,比如海燕、牛馬、熊貓等;有的動物遭譴責,比如貓頭鷹、烏鴉、豺狼等;有的動物受輕蔑,比如蛇鼠、蝸牛、螞蟻等。受到禮遇的動物,不外乎或效力于人,或儀表堂堂,或瀕臨滅絕。其中最典型的,要數熊貓了。熊貓長相親善,福態憨態兼具,對人既無尺寸之功,亦無點滴危害,只因數量稀少,就演化為人心目中無比金貴的“寶貝心肝”。
雞的名聲相對比較正面,原因在于雞索取極少,奉獻很多。雞雖然和人一樣,有著內斗的嗜好,但對外卻低眉羞眼,絕不張牙舞爪,更不巧取豪奪。雞胃口不大,幾粒米,數條蟲,半缽水,足以滿足得喜氣洋洋,搖頭晃腦。即使主人偶爾在喂食上有所疏忽,雞饑餓難忍,卻也不反抗,不作亂,只是埋頭于草叢中或草垛下啄食,絕不會像老鼠那樣,暗度陳倉地打劫主人的糧倉。
雞對人的貢獻,有目共睹。母雞下蛋,公雞打鳴,分工明確,各司其職。母雞下蛋的勞苦功高,人人耳熟能詳,無需過多贅言。但公雞打鳴的業績,卻常被人忽略。打鳴的歷史與價值,現代人大多懵懵懂懂,無知無感。但事實是,打鳴在華夏族群古老的日常生活中,扮演著不可或缺的角色。在鐘表尚未誕生之日,在電燈電話且無發明之時,在漆漆黑黑的漫漫長夜里,人們對時間的掌握,主要依賴兩種手段:一是觀察月亮的位置,一是聆聽公雞的打鳴。然而,依據月亮的位置估摸時辰,實踐起來有著相當大的難度,唯有上了些許年歲的人,因經驗的日積月累,才具備這等能力。月亮總在游移,今天與昨天同一時辰所處的方位并不等同,一味地照搬老黃歷,只能錯之又錯,謬而又謬;再則,望月頗為費力勞神,眠于枕,躺于炕,無疑難以如愿,唯有爬身起來,或將頭伸向窗外,或披衣下炕走出房門,才能做到與月對視。這等景況,夏天還稍好一些,但若遇冬寒,那就非常地遭罪:不但面臨傷風感冒的威脅,而且睡眠的質量也因之而大打折扣。一趟趟地起床望月,人的睡眠便猶如從高空墜落的瓷器,支離破碎,不復完整。
好在造物主明察秋毫,深諳人之所急,夜之所需,于是便創造出貌似百無一用實則很有大用的公雞,為人幫忙,替人解憂。公雞天生一副擴音器般的大嗓門,白晝它顯得吊兒郎當,東游西逛,一副無所事事的模樣;但在黑夜將盡之時,卻抑制不住地引吭高歌,以迎接晨曦的浮現。城鎮居民想了解時辰,相對容易,只要側耳聆聽更夫的打更即可,但在自給自足的廣袤鄉野,卻并無更夫的身影在晃動,于是人們便把掌握時辰的殷殷期待,寄望于那一只只火紅的公雞。每家每戶,都要圈養一兩只公雞,不為嚼其肉,專為聽其聲。公雞不辱使命,不負眾望,在眾生睡意朦朧之際,一聲接一聲地啼鳴不止。被公雞喚醒的人們,紛紛整衣肅冠,起床出門:腳夫吆喝著毛驢踏足遠行,學童背著書包奔赴學堂,耕者扛著犁鋤去往田疇,老婦拉響風箱籌備早餐,新娘端坐梳妝臺涂脂抹粉……當然,哪怕是做好事,反對者都不會缺席。那些慣于睡懶覺的人,就對公雞相當憎恨。
公雞與母雞,活著時為人效力,死去后被人吃掉,在為人服務方面,堪稱傾其所有,拼盡全力。但遺憾的是,雞卻并未能獲得人的基本尊重。最令雞皺眉的,就是人在指桑罵槐中,常將自己同類中的性亂者,指斥為雞。雞無錯,卻要受侮辱;雞無罪,卻要當被告。潔身自好的雞,無端地被涂黑,卻有口無言,從不辯解——這恰是雞之所以世代為雞的癥結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