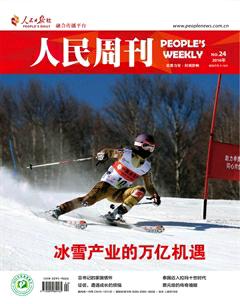盲目撤并學校折射鄉村教育問題
為進一步規范農村義務教育學校布局調整,防止類似事件再次發生,要求切實高度重視、嚴格撤并條件、規范撤并程序、強化督促檢查。
教育部日前發布關于農村義務教育學校布局調整有關問題的通報,要求各地高度重視做好規范布局調整工作,堅決制止盲目撤并和強行撤并,嚴格撤并條件,優先保障學生就近上學的需要,切實辦好必要的鄉村小規模學校。為進一步規范農村義務教育學校布局調整,防止類似事件再次發生,要求切實高度重視、嚴格撤并條件、規范撤并程序、強化督促檢查。
對于堅決制止盲目撤點并校,我國已經三令五申。2012年9月,國務院辦公廳下發《關于規范農村義務教育學校布局調整的意見》,稱“農村義務教育學校大幅減少,導致部分學生上學路途變遠、交通安全隱患增加,學生家庭經濟負擔加重,并帶來農村寄宿制學校不足、一些城鎮學校班額過大等問題”,提出“堅決制止盲目撤并農村義務教育學校”,“在完成農村義務教育學校布局專項規劃備案之前,暫停農村義務教育學校撤并”。今年4月召開的國務院常務會議也提出,要合理布局教學點,按標準配置教學設施和教師。改善寄宿制學校教學、圖書、就餐、取暖等條件,加快消除“大通鋪”現象。到2018年基本解決縣城和鄉鎮學校超大班額問題。
“學生太少”不是盲目撤點并校的理由
不論是學齡人口的數量下降,還是一些有條件、有能力的農村家庭將孩子送到城鎮讀書,抑或部分學生跟隨到外地務工的農民工父母異地上學,在社會流動加速、鄉村空心化的時代背景下,一些鄉村學校“由盛轉衰”成為一種無奈和堅硬的現實。
在功利主義大行其道的當下,資源應該被如何利用,往往取決于哪種利用方式更有效率。八洞村小有3名老師,撤掉八洞村小有助于解決彰加鎮中心小學師資緊張的難題。可是,對于這幾位孩子及其家庭來說,“撤點并校”意味著就近入學落空;孩子們上學要么走更遠的路,要么家長在彰加鎮街道租房陪讀,這無形之中加劇了這些貧困家庭的教育成本。
“撤點并校”盡管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整合教育資源、提升辦學質量,卻也帶來了一系列的負面問題,如孩子們上學路上的安全問題、鄉村文化種子被掏空以及寄宿制損傷親情互動、教育成本上升導致輟學現象加劇等。隨著“撤點并校”后遺癥的漸次凸顯,教育部門對盲目、無序的撤并熱潮潑了冷水、戴上了“緊箍咒”。
“撤點并校”事關老百姓的切身利益,需要在堅持程序正義和“保障就近入學”的基礎上“適當合并”。撤掉八洞村小既不符合“保障就近入學”,也沒有征得家長的同意,更沒有按照相關程序取得行政許可;將“學生太少”作為“撤點并校”的理由,在家長明確表示反對的格局下依然一意孤行,說到底是一些人在利益驅動下自彈自唱。
制止盲目撤點并校須轉變教育決策機制
21世紀教育研究院副院長熊丙奇認為,在我國農村地區,目前辦學普遍存在兩種現象:一是政府部門把農村地區生源不足的學校撤掉,并進城市入學。理由是讓農村孩子上好學,事實上卻增加了農村孩子上學的負擔,也導致了城市大班額問題。二是在國家叫停盲目撤點并校,要求各地保留村小后,一些地方政府以勉強維持的心態對待村小,讓村民覺得鄉村教學點辦學質量差,遲早要撤掉而選擇到城鎮學校上學,由此讓村小在沒有學生生源的情況下“自然”消亡。
“應該說,不轉變地方政府對待鄉村學校的態度以及目前的教育決策和管理機制,很難遏制鄉村學校快速消亡的勢頭。”熊丙奇說。
對此,熊丙奇認為,首先必須在農村學校布局調整決策時廣泛聽取村民意見,不能由政府部門單方面拍板強制推進。針對這些撤點并校后遺癥,國家叫停盲目撤點并校并要求各地在撤點并校時要堅持民主決策。可是一些地方并沒有真正落實,村民在學校布局調整中發揮的作用極其有限。其次,在學校辦學管理中,要引入社區、村民教育委員會進行管理、監督。要讓鄉村學校得到更好地發展,就必須改變這種撥款機制,可以考慮把中央財政轉移支付和省財政統籌經費直接打進學校賬號,同時由社區、村民教育委員會參與教育發展決策,并監督政府投入與學校辦學。
熊丙奇說:“只有這樣,才能辦好村民家邊的學校,讓鄉村有教育基地,讓孩子們在村里就能接受良好的教育。”
撤并流言折射鄉村學校生存困境
鄉村學校,是鄉村的靈魂、鄉村文明的載體。辦好鄉村教育,既是鄉村孩子與他們家庭的希望,也是鄉村的希望。沒有鄉村教育的發展,就沒有鄉村的美好未來。試想一下,在那一片青山環抱之中,能夠有一面五星紅旗迎風招展;在那一片雞犬相聞的地方,能夠清晰地傳來朗朗書聲;在那阡陌交錯的田間地頭,能夠邂逅一隊隊背著書包戴著紅領巾的活蹦亂跳的學童,整個鄉村或許一下就活了,就有生機了,就有希望了。
一定程度上,沒有鄉村教育的發展,就沒有精準扶貧的有效推進,就沒有貧困代際傳遞的有效阻止,就沒有教育的真正公平與均衡。現實中存在的鄉村學校,哪怕只有一個學生,依然可以有它存在的價值,依然可以點亮鄉村的“庠序燈光”。
中國陶行知研究會農村教育實驗專委會理事長、四川省閬中市教育和科學技術局局長湯勇認為,隨著城鎮化進程的加快推進,鄉村教育卻日漸衰落,這既給鄉村帶來了荒涼與凋敝,又給教育帶來了諸多危機與危害。東北師范大學農村教育研究所發布的《中國農村教育發展報告2015》顯示,我國義務教育城鎮化率從2009年的51.04%快速攀升到2014年的72.55%,隨之而來的,是我國鄉村小學在校生減少了2605萬人。這一方面是因為城鎮化自然形成的學齡人口遷移,另一方面卻是因為鄉村學校撤并造成的學生流失。
大批鄉村學校的撤并,大批孩子逃離鄉村,讓我們所培養的鄉村孩子缺乏對鄉村的認同感,這是很可怕的。錢理群先生曾談到,“我憂慮的不是大家離開本土,憂慮的是年輕一代對養育自己的土地和這片土地上的文化,以及土地上的人民產生了認識上的陌生感,情感和心理上的疏離感”。
“固然鄉村學校的生存會面臨很多困境,諸如生源逐年遞減、教師隊伍難以穩定、辦學經費捉襟見肘、學校發展動力不足……這些,只能成為我們改變與發展鄉村教育的責任與壓力,絕不能作為鄉村教育就可以被忽視、被冷落,甚至被遺忘、被撤并的理由。”湯勇說,“鄉村學校的去留,需要綜合考慮各方面的因素,但確保鄉村孩子的就近入學,確保‘讓每一個鄉村孩子都不被落下,確保鄉村文化的薪火相傳,永遠是首要考慮的因素。這方面的態度與作為,不僅考量的是執政者對教育的情懷和對鄉村的情感,還有他們的執政智慧。”
促進教育均衡,顯然不能盲目、無序“撤點并校”。農村學生也有“保障就近入學”的教育權利,鄉村學校不能只算經濟賬。對于一個農村家庭來說,有一個上學的孩子,這個家庭就多一份希望。鄉村學校的文化意義和社會意義,或許會遠遠大于省下的教育經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