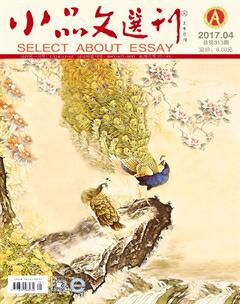說樹皮
武歌
乘車路上,我常常喜歡透過車窗,看路邊飛逝的景物,草的芊影,花的一現。飛過眼簾的,更多的是樹的風姿。現在是初春的季節,古城這個季節,多是沙塵飛舞,春寒料峭。
胡思亂想中,我發覺路邊白楊樹樹皮顏色變得有些清淡,遠遠看去,像是繞著一縷縷輕煙。我隔著車窗急急地注視樹皮。真的!樹皮確實開始泛青,春天來了。
本來樹皮的顏色是變化的。我想大多數人和我一樣,對待樹皮就像對待身邊的母親一樣,樹皮的顏色就像母親的頭發。誰能說得出母親的頭上,什么時候開始生出華發?什么時候全部變成白發?在我們心中樹皮的顏色大約只是淡青色或者褐色。我們的感覺往往是錯的。
曾在自家窗前,我留意過那幾顆槐樹,槐樹皮四季顏色不一樣:春是青,夏成褐,秋微黃,冬灰黑。路邊的白楊我沒有仔細觀察過,我想白楊的樹皮四季顏色定會變化,那是生命的變奏,歲月的輪回。
小時候,冬天去野外揀柴禾,撿到樹皮最是我們興奮和得意的時候。一塊二尺長五寸左右寬的樹皮,可以交換一柳筐冰干的牛糞。土丘大一堆雜柴亂草,也抵不上那塊樹皮的誘惑。在我的記憶中,母親只用牛糞和樹皮燉肉,雜草之類的柴禾只能燒水熱炕。現在想來,烘烘燃燒著樹皮,母親燉在鐵鍋里“咕嘟、咕嘟”的肉,該有多香啊。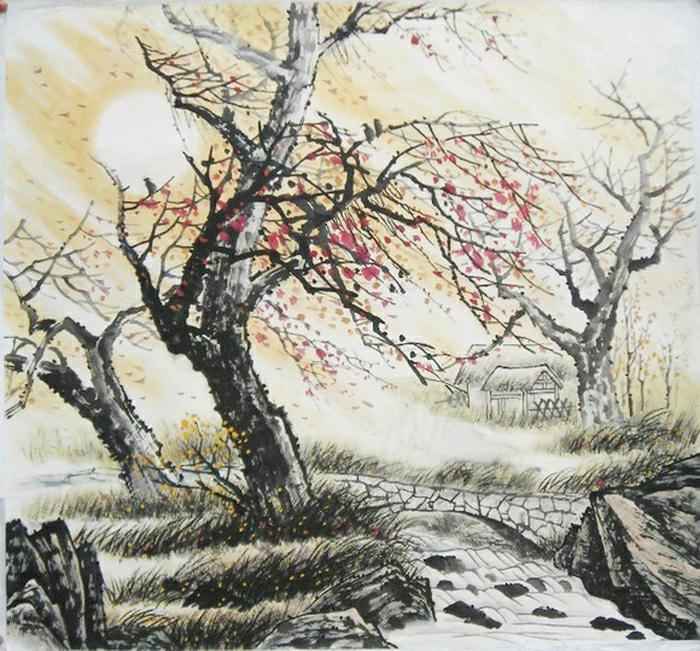
樹皮可食。最近網間流傳,說吃某種樹皮可以治病,于是有人為了健康,亂揭樹皮被治安處罰。看來生活的富裕并不能掩飾內在的愚昧。
樹皮能不能治病,我想樹皮一定有些藥效,但樹皮的藥效是否可以降血糖通血管除腫瘤祛風寒延年益壽,那是科學家們的辯證,我們不必妄下結論。據說“山姆大叔”已經開始研制與樹皮有關的生物技術,那些樹皮派什么用場,大家可以去查尋。
奶奶和母親都曾說,楊樹皮發澀發苦,難以下咽。聽她們的話音,她們一定吃過楊樹皮。回想三年自然災害,很多人連楊樹皮都吃不上,他們便結束了生命,我的祖輩和父輩真是幸運。
楊樹皮我沒有吃過,連嘗試都沒有。小時候吃過奶奶做的一種面食,很好吃。那種面食里奶奶摻和著一種“精蒿”,記憶中那種東西是用干榆樹皮碾壓成的。“精蒿”是不是榆樹皮?奶奶去世多年,無從問起;下次看望母親,定要問個究竟。榆樹皮可以吃,我曾經吃過。榆樹皮嚼起來黏黏糊糊,口感不錯,其中夾雜著一股淡淡的香甜味。
樹皮可以做燃料,可以當干糧,樹皮也可以做建筑材料。小時候,村子里人蓋泥皮土房,有錢人家做房棧板,多用方木塊圓木段劈開,一條一條劈好的木板那是上好的棧板材料。
更多人家勒緊腰帶去蓋房,椽檁早已經將家資耗盡,棧板只能以樹皮充雜。樹皮做棧板,最終是不經久的,過不了幾年,樹皮便干裂的只剩纖維絲,土房漏雨垮塌是躲不過的災難。這不是樹皮的過錯,都是貧窮急就的隱患。
樹皮功績載入史冊不多,但有一個特別閃耀的亮點,得益于大漢蔡倫先生。《后漢書·蔡倫傳》卷七十八載,“倫乃造意,用樹膚、麻頭及敝布漁網以為紙……故天下咸稱蔡侯紙”,“樹膚”一詞比“樹皮”更加親切溫暖。中國古代“四大發明”舉世皆驚,貢獻卓絕。紙的發明雖然不可定位蔡倫,但是麻紙皮紙的革新是蔡倫的功績。后人多記書法絕品“蘭亭序”,忘卻了承載蘭亭序的“蔡侯紙”;當然后人也多記著蔡侯造紙的豐功偉績,又忽略了樹皮的妙用。紙的清白,與樹皮“粉身碎骨”“千錘百煉”有極大關系。
也許有人會說,樹皮貢獻很大,我們也呵護過樹皮。是真的嗎?田間路邊,一些樹干上涂抹著白色的石灰粉,上邊標著一個口紅一樣的警戒圈,高度大約一米左右。科學講那是為了保護樹皮,防凍防霜防止蚊蟲叮咬,以及牲畜蹭啃。
樹干上部呢?一般樹木遠遠高于一米,上部樹干樹枝樹皮任由雀踏鳥啄,雷殛電噬。雪壓樹枝,樹皮早已經凍得發紫休克,人們還詠著,“大雪壓青松,青松挺且直”,這是不是見死不救隔岸觀火呢?!
皮膚粗糙像了樹皮,用來描繪母親的那雙手,是最恰當不過的。我出生在一座貧窮的小山村,母親為了拉扯我們姊妹七人(二妹妹不幸夭折),可謂含辛茹苦。為了掙工分,母親數年秋夏浸泡在水塘里洗麻。在莊稼地里干農活,母親頂著一個壯勞力。打草積肥母親更是一把好手。
糧食短缺,母親為了填飽我們的肚子,只好尋找代食品,母親常去挖苦菜。裝滿苦菜的柳筐母親每次都用頭頂。取下母親頭頂的柳筐,力壯的父親都渾身出汗。后來,父親回憶說,那種特大號柳筐,塞滿一筐苦菜足夠二百斤。
二百斤!壓在一個瘦弱的女人頭頂上,多么可怕。在電視或者電影上,每每看到朝鮮婦女頂水的鏡頭,聽著她們哼著優美的“阿里郎”,我總想起母親。想起母親的艱辛,母親的頑強,不禁熱淚盈眶,心酸楚楚。
母親老了母親的頭發白了母親的背駝了。母親的雙手皴了,母親的雙手裂口子了……,在我的記憶里,母親的雙手一直是老樹皮的樣子,如今母親的臉也變成老樹皮了。唯有這些老樹皮,是溫暖的,里面貯滿了母親的溫度。
是啊,其實所有的樹皮都是溫暖的,那里有母親的溫度!
選自《山西綠色散文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