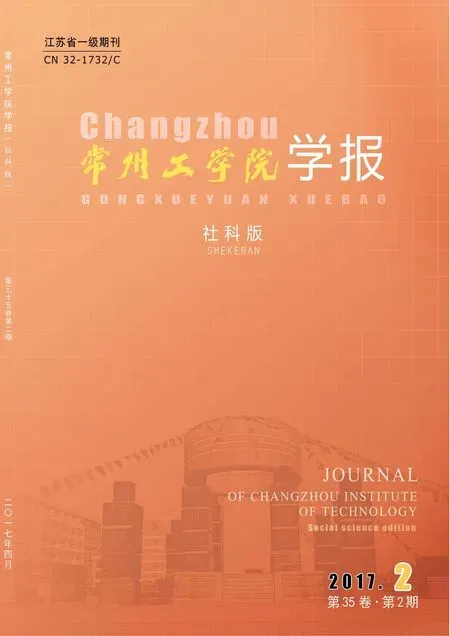城鄉(xiāng)沖突下的退與進(jìn)
——20世紀(jì)80年代小說(shuō)中青年形象的精神軌跡
吳玲
(沈陽(yáng)師范大學(xué)中國(guó)文化與文學(xué)研究所,遼寧沈陽(yáng)110034)
城鄉(xiāng)沖突下的退與進(jìn)
——20世紀(jì)80年代小說(shuō)中青年形象的精神軌跡
吳玲
(沈陽(yáng)師范大學(xué)中國(guó)文化與文學(xué)研究所,遼寧沈陽(yáng)110034)
20世紀(jì)80年代是我國(guó)文學(xué)史上一個(gè)極為重要的時(shí)期,是一個(gè)社會(huì)急遽變動(dòng)的時(shí)期,也是文學(xué)創(chuàng)作日新月異的時(shí)期。尤其是70年代末80年代初期,政治和經(jīng)濟(jì)的撥亂反正給文化的自由與繁榮帶來(lái)了新的生機(jī)。在這個(gè)時(shí)期,一大批迥異于此前作品人物的青年形象開(kāi)始出現(xiàn)在作家的筆下,他們以自己的悲歡歌哭為我們?cè)佻F(xiàn)了那個(gè)大轉(zhuǎn)折時(shí)代的青年的成長(zhǎng)軌跡與心理癥候。以路遙的《人生》為起點(diǎn),作家們通過(guò)這些青年形象對(duì)當(dāng)時(shí)城鄉(xiāng)之間的矛盾傾注了熱切的關(guān)注,同時(shí),也通過(guò)青年人物對(duì)城鄉(xiāng)不同的人生選擇表達(dá)了自己對(duì)于城市和鄉(xiāng)村的不同態(tài)度,相應(yīng)地,也折射出鄉(xiāng)村在城市現(xiàn)代文明擠壓下日漸潰敗的時(shí)代主潮。
城鄉(xiāng)矛盾;知青“返鄉(xiāng)”;農(nóng)村青年進(jìn)城
有研究者稱“城鄉(xiāng)劃分一直是中國(guó)現(xiàn)代文學(xué)史的顯著特點(diǎn)”①,城市與鄉(xiāng)村存在于完全不同的生活空間,生成著迥異的價(jià)值和美學(xué)觀念。從最初的農(nóng)村包圍城市,到以城市為中心,直至“以工促農(nóng),以農(nóng)助工”的發(fā)展政策,從知識(shí)青年上山下鄉(xiāng)到農(nóng)民進(jìn)城務(wù)工,到農(nóng)村開(kāi)展招商引資、開(kāi)辦鄉(xiāng)鎮(zhèn)企業(yè)等,城鄉(xiāng)的交流在20世紀(jì)中國(guó)歷史上從來(lái)沒(méi)有中斷過(guò),二者的沖突與融合也“成為考察20世紀(jì)中國(guó)文學(xué)一個(gè)獨(dú)特而有效的視角”②。這種沖突與融合在當(dāng)時(shí)的社會(huì)背景下呈現(xiàn)出多個(gè)側(cè)面,如路遙所言:“城市和農(nóng)村本身的變化發(fā)展,城市生活對(duì)農(nóng)村生活的沖擊,農(nóng)村生活城市化的追求意識(shí),現(xiàn)代生活方式和古樸生活方式的沖突,文明與落后、資產(chǎn)階級(jí)意識(shí)和傳統(tǒng)美德的沖突,等等,構(gòu)成了現(xiàn)代生活的重要內(nèi)容。”③對(duì)于這些矛盾與沖突、交流與融合,當(dāng)代作家有著十分清醒的認(rèn)識(shí),也都有著廣泛而深入的描述與展示,并且在文本中塑造出了一大批在城與鄉(xiāng)的沖突與融合中掙扎奔突的青年形象。如在1982年發(fā)表的《人生》中,路遙就以高加林這一“個(gè)人奮斗者”的典型想象給了全社會(huì)振聾發(fā)聵的一擊,而高加林為城市夢(mèng)想的奮斗及這一夢(mèng)想最終的破滅,以及他在這一過(guò)程中的精神軌跡恰可成為我們研究20世紀(jì)80年代小說(shuō)中青年形象精神內(nèi)涵的切入口。以此為原點(diǎn),并參照20世紀(jì)80年代具體的創(chuàng)作實(shí)績(jī),本文將當(dāng)時(shí)涉及“城鄉(xiāng)問(wèn)題”的小說(shuō)中的青年形象大致劃分為三類:第一類是從鄉(xiāng)村返回城市后由于無(wú)法在城市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和人生意義,又重新返回鄉(xiāng)村的青年。從作家作品來(lái)看,這一類多是“文革”后的“返鄉(xiāng)知青”。第二類是面對(duì)城市對(duì)于鄉(xiāng)村所具有的誘惑力而固守著傳統(tǒng)觀念的青年,他們或許認(rèn)識(shí)到了現(xiàn)代城市文明對(duì)鄉(xiāng)村傳統(tǒng)觀念所具有的沖擊力,但他們?nèi)赃x擇留在農(nóng)村,延續(xù)著傳統(tǒng)的生活方式。第三類青年清醒地認(rèn)識(shí)到城市文明的優(yōu)越和鄉(xiāng)村傳統(tǒng)的落后,他們渴望擺脫落后而愚昧的鄉(xiāng)村,熱烈地追求著現(xiàn)代、先進(jìn)的城市文明,渴望著能以進(jìn)城作為改變個(gè)人命運(yùn)的起點(diǎn)。
一、“返鄉(xiāng)知青”的烏托邦幻想
“文革”結(jié)束后,知青們最終得以返回“故鄉(xiāng)”——城市。然而,在這“故鄉(xiāng)”,他們卻再次遭遇人生的幻滅與迷惘,城市的污濁,人性的潰散等等,理想再次被延宕。在返回城市之后,返城知青們?cè)陂焺e十年之久的城市遭遇到了種種意想不到的失落,重新歸來(lái)的他們驚愕地發(fā)現(xiàn),城市早已不是身處鄉(xiāng)村的他們想象中的迦南美地,城市里乃至有著至親血緣的家庭里也不再有他們的容身之地。在城市中,他們處處遭遇挫折,時(shí)時(shí)生活在苦悶之中,他們似乎變成了被流放于城市之外的“多余人”,他們無(wú)路可走。凡此種種,都促使他們對(duì)“上山下鄉(xiāng)”時(shí)的鄉(xiāng)村原野乃至山區(qū)生活產(chǎn)生了無(wú)盡的懷想與回味,他們開(kāi)始懷念農(nóng)村社會(huì)里溫馨質(zhì)樸的傳統(tǒng)鄉(xiāng)情、純真和諧的傳統(tǒng)倫理道德,他們不得不逃離城市里讓他們不滿意的一切而重返鄉(xiāng)村。在這種懷想、回味與重返中,包含了這批有著獨(dú)特人生經(jīng)歷的青年們對(duì)自己逝去的青春與理想的懷戀與追尋。如王安憶《本次列車終點(diǎn)》中的陳信、孔捷生《南方的岸》中的易杰與慕珍等。
王安憶在《本次列車終點(diǎn)》中刻畫了一個(gè)男知青陳信,返城之后,陳信面臨的是工作的不順意,是家人冷嘲多過(guò)熱情的窘境,他不能繼續(xù)留在城市,只能懷著“只要到達(dá),就不會(huì)惶惑,不會(huì)苦惱”④的幻想乘著“本次列車”再次流浪。無(wú)獨(dú)有偶,在《南方的岸》中,易杰、慕珍和阿威返城后工作問(wèn)題并未及時(shí)落實(shí),為了生存,他們共同經(jīng)營(yíng)了一間“知青粥粉鋪”,生意尚可,他們本可以此謀生。但在易杰看來(lái),這并不是他想要的生活,他在柴米油鹽醬醋茶和各種利益糾紛中仍堅(jiān)持著浪漫的理想。而這種堅(jiān)持也很快被打破了,麥老師以及“知青工友”的變化,是他始料不及也不能接受的,而慕珍更是在父母姐妹的咒罵聲中成為冷漠家庭的“多余人”。于是他們不得不再次返回“南方的岸”,那里有著他們青春的愛(ài)和記憶,理想和激情。但是,無(wú)論是對(duì)于陳信,還是易杰、慕珍來(lái)說(shuō),此番返鄉(xiāng)注定無(wú)效。那即將踏上的鄉(xiāng)村是只能想象而不能再次經(jīng)驗(yàn)的幻想中的烏托邦。如哲學(xué)家赫拉克利特所說(shuō),人不能兩次踏進(jìn)同一條河流,對(duì)于再次返鄉(xiāng)的知青們來(lái)說(shuō),時(shí)過(guò)境遷,他們的返鄉(xiāng)只能是一次想象中的跋涉,他們?cè)僖膊豢赡茏咴谑昵暗哪菞l路上,也不可能再遇見(jiàn)十年前的那些人和事。當(dāng)年易杰和慕珍們揮灑汗水甚至犧牲生命種植的那片膠林如今已經(jīng)成片成片地枯死了,而王安憶甚至都沒(méi)有給陳信的“本次列車”設(shè)置可行的終點(diǎn)站。
對(duì)此,作家韓少功有著清醒的認(rèn)識(shí),他創(chuàng)作于1985年的小說(shuō)《歸去來(lái)》⑤,主人公黃治先在一次訪友的途中鬼使神差地進(jìn)入一個(gè)破落的村莊,雖未曾相遇卻似曾相識(shí),而且他也被村里人誤認(rèn)為是知青“馬眼鏡”,被詢問(wèn)各種相關(guān)的人與事,他疲于應(yīng)付。此時(shí),歷史在他眼前呈現(xiàn)出多重面目,而這歷史所帶來(lái)的熟識(shí)感又讓他唯恐失去自我、陷入迷障。面對(duì)這不能合理闡釋的遭遇,他選擇了不告而別,逃回城市。黃治先的倉(cāng)皇出逃似乎打出了一手反牌,當(dāng)作家們紛紛將回城之后百般受挫的知識(shí)青年以各種方式“遣返”鄉(xiāng)村時(shí),韓少功卻道出了鄉(xiāng)村對(duì)他們的拒斥。也就是說(shuō),黃治先逃離鄉(xiāng)村并不是主動(dòng)的選擇,而是在鄉(xiāng)村社會(huì)獨(dú)有的社會(huì)倫理和生存哲學(xué)面前他無(wú)力融入,最終被無(wú)情驅(qū)逐。
二、“鄉(xiāng)村留守者”的現(xiàn)代失落
李杭育在《最后一個(gè)漁佬兒》里塑造了一個(gè)固執(zhí)地堅(jiān)守著傳統(tǒng)文化倫理和生活方式的“葛川江上的最后一個(gè)漁佬兒”柴福奎,“他每夜都數(shù)那一溜街燈,卻從沒(méi)數(shù)準(zhǔn)過(guò)究竟是多少。他對(duì)這些街燈很感興趣。……如今西岸這富麗堂皇的氣派,委實(shí)叫人著迷”⑥。雖然他心里熱愛(ài)著現(xiàn)代化城市里的一切,但他仍然守在住了一輩子的葛川江,守在那污染越來(lái)越嚴(yán)重,甚至連一個(gè)釣鉤都買不到的地方——對(duì)于柴福奎這個(gè)漁佬兒來(lái)說(shuō),“死在江里,就跟睡在那蕩婦的懷里一般,他沒(méi)啥可抱屈的了”⑦。然而,并不僅是這個(gè)老人固執(zhí)地不愿走進(jìn)城市而寧愿死在落后而守舊的漁船上,在一些小說(shuō)中,如陳忠實(shí)的《棗林曲》、魏雅華的《丟失的夢(mèng)》和賈平凹的《他和她的木耳》等,青年主人公不但在進(jìn)城的路上一步一回頭,最終甚至反身重新回歸了農(nóng)村。不同于陳信和易杰等人,在另一些作家如陳忠實(shí)和魏雅華等的筆下,塑造出了一批經(jīng)過(guò)重重掙扎之后最終留在鄉(xiāng)村生活的青年形象。在這些小說(shuō)中,青年主人公對(duì)城市現(xiàn)代文明有著了解與接觸,享受過(guò)城市文明所代表的高于鄉(xiāng)村傳統(tǒng)文明的物質(zhì)與精神食糧。但是,他們依然愿意留在鄉(xiāng)村而拒絕城市,或者是在城市夢(mèng)想受到挫折時(shí)無(wú)可奈何地退回到鄉(xiāng)村生活中去,最終在現(xiàn)實(shí)的剝蝕中泯滅了曾經(jīng)對(duì)于現(xiàn)代城市的夢(mèng)想。
1980年《延河》雜志發(fā)表了陳忠實(shí)的短篇小說(shuō)《棗林曲》,小說(shuō)中的女知識(shí)青年玉蟬放棄了在城市落戶與工作的機(jī)會(huì)而返回農(nóng)村投入改天換地的工作并收獲了愛(ài)情。雖然姐姐和姐夫?qū)τ裣s的前途有著明確的規(guī)劃并幫助斡旋,給她爭(zhēng)得了調(diào)回城市和進(jìn)入工廠工作的機(jī)會(huì),但是玉蟬卻跟隨著內(nèi)心的愿望放棄了這一切而再次回到棗林溝。她和棗林溝的好青年社娃的戀情,她對(duì)棗林溝一望無(wú)際的青山的熱愛(ài)等等,無(wú)一不是棗林溝對(duì)玉蟬的牽引,而她對(duì)以姐姐和姐夫的家庭所代表的城市的厭惡則進(jìn)一步加深加重了這種牽引的力道。就這樣,玉蟬撕碎了姐夫辛苦為她求來(lái)的進(jìn)城機(jī)會(huì)——合同工登記表,毅然地回到了靠山吃山的鄉(xiāng)村生活中去了。
但是,小說(shuō)總是以其無(wú)意識(shí)的力量向我們展示著文本所具有的潛在內(nèi)蘊(yùn),而比較有意思的是,從《棗林曲》我們不難讀出“十七年”文學(xué)的固有味道——“姐姐的家——是一個(gè)世界,一層世事;她和玉山叔以及社娃所在的青山坡的棗林溝,是另一個(gè)世界,另一層世事;兩層世事,兩個(gè)世界,玉蟬只能憑直覺(jué)看出這個(gè)存在和差異……反正想到棗林溝那個(gè)世界,她心里好生快活!想到姐姐的家事,姐夫出來(lái)進(jìn)去神秘的樣子,她好生煩膩!”⑧當(dāng)社娃為了集體的事業(yè)生病住院時(shí),玉蟬覺(jué)得自己在姐夫的斡旋下出來(lái)在工廠做合同工自己掙錢是一件十分不光彩的事情。于是她大義凜然地對(duì)姐姐吶喊道:“人活著圖啥呢?只有錢嗎?人得為集體辦好事,大家才尊重你……”⑨這些無(wú)不讓我們有一種似曾相識(shí)感,而事實(shí)上我們的感覺(jué)從來(lái)不會(huì)說(shuō)謊,在柳青的《創(chuàng)業(yè)史》中,當(dāng)徐改霞報(bào)名參加工業(yè)化建設(shè)時(shí)其內(nèi)心感受與玉蟬可謂有異曲同工之妙。或許筆者在此可以做出大膽的結(jié)論——如果玉蟬的選擇是符合時(shí)代潮流的話,那么在“撥亂反正”已進(jìn)行過(guò)數(shù)年的時(shí)代里,這未必不是一種逆歷史潮流而動(dòng)的行為。也就是說(shuō),玉蟬所選擇的這種歷史道路注定要被時(shí)代所拋棄。


三、“個(gè)人奮斗者”的艱難追求



因此,如果對(duì)這三種青年形象在20世紀(jì)80年代同時(shí)并存的現(xiàn)象做出歸納的話,我們就會(huì)看出變動(dòng)的年代對(duì)青年人物的多方面要求與影響。主流文化需要青年人具有凌云壯志,但是城市空間確實(shí)有限,這就產(chǎn)生了有才華的青年人數(shù)日漸增多而可供他們展現(xiàn)才華的工作崗位尤其是城市工作崗位緊缺之間的矛盾。玉蟬留在農(nóng)村大干一場(chǎng)的選擇或許給我們青年提供了一條可行的人生道路,但是其意指內(nèi)涵的陳舊卻使得這種選擇變得面目可疑,而凌云進(jìn)城的失敗與皈依更是給我們提供了一條重新思考中國(guó)社會(huì)制度與城鄉(xiāng)差別的不同的路徑,高加林和沈萍的人生追求卻由于現(xiàn)實(shí)的逼仄而處處受阻……這一切都不得不引人深入思考這樣一個(gè)問(wèn)題:青年們?nèi)绾卧谛碌臅r(shí)代語(yǔ)境中實(shí)現(xiàn)自我的個(gè)人價(jià)值,而這種價(jià)值的實(shí)現(xiàn)又如何完成對(duì)主流意識(shí)形態(tài)的契合?這將是一個(gè)值得長(zhǎng)久探討的文學(xué)與社會(huì)選題。
注釋:
①②高秀芹:《文學(xué)的中國(guó)城鄉(xiāng)》,陜西人民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34頁(yè),第34頁(yè)。
③⑩路遙:《面對(duì)新的生活》,《中篇小說(shuō)選刊》,1982年第5期,第17頁(yè),第16頁(yè)。
④王安憶:《本次列車終點(diǎn)》,《王安憶小說(shuō)編年(卷一)》,人民文學(xué)出版社,2009年,第230頁(yè)。
⑤韓少功:《歸去來(lái)》,《上海文學(xué)》,1985年第6期,第32-39頁(yè)。
⑥⑦李杭育:《最后一個(gè)魚(yú)佬兒》,《當(dāng)代》,1983年第2期,第179頁(yè),第184頁(yè)。
⑧⑨陳忠實(shí):《棗林曲》,《延河》,1980年第7期。




責(zé)任編輯:莊亞華
10.3969/j.issn.1673-0887.2017.02.008
2016-10-21
吳玲(1990— ),女,碩士研究生。
I207.42
A
1673-0887(2017)02-0031-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