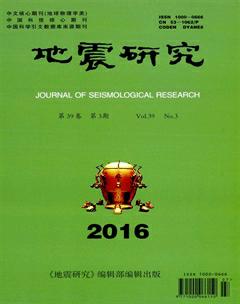利用sPn震相測定柴達木盆地地震的震源深度
李啟雷 崔煜 安黎霞 李玉麗
摘要:
利用青海省遙測地震臺網的觀測記錄,對比分析震相特征,提取出了兩次地震記錄的sPn震相,并分別推導出單、雙層地殼模型下的震源深度公式,計算了兩次地震事件的震源深度。為驗證計算結果的可靠性,利用滑動窗互相關技術進行對比,兩者計算出的震源深度相差10 km。但分析相關系數圖后,認為由于地震震級較小,滑動窗法在識別sPn震相時存在誤差,誤差修正后得出的結果與人工識別計算的結果一致。
關鍵詞:sPn震相;震源深度;地殼模型;波形互相關;滑動時窗相關法
中圖分類號:P3156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0-0666(2016)03-0473-06
0引言
地震定位意指根據地震觀測震相反演地震的發震時刻、震源位置等基本地震學參數。它是地震學中最經典、最基本的問題,在地震發生機制及地震構造研究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隨著科技的進步和臺站的不斷加密,地震的發震時刻和震中位置(震源在地面的垂直投影)已經相對精確。但震源深度依然是一個難以準確測定的地震參數。
1956年前蘇聯地震科學家AA維琴斯卡婭發現了sPn波,她發現各地震臺站sPn和Pn震相的到時差不隨震中距變化而變化,可以很好約束震源位置。在20世紀70年代初,張誠曾對甘肅地區sPn震相做過一些研究,但限于我國當時的觀測環境,sPn震相資料稀少,該方法難以得到大力推廣。20世紀70年代起,世界各國陸續建立了數字地震臺網,中國的數字地震臺網建設起步于20世紀80年代。1983年5月國家地震局與美國地質調查局開始規劃設計中美合作的中國數字地震臺網(CDSN),各省區域地震臺網也陸續成立。而后,隨著臺網的不斷加密,震相記錄更為豐富,震相識別更為精確,sPn越來越多地出現在地震觀測記錄上。眾多學者開始利用sPn震相測定震源深度。任克新等(2004)用sPn震相測定了2003年8月16日發生在我國內蒙古地區地震的震源深度。蔡杏輝和邵平榮(2011)總結了發生在我國臺灣地區地震的sPn震相特征。洪星等(2006)分析了發生在臺灣海峽南部地震的sPn震相特征并在不同地殼模型下用sPn-Pn走時差計算了震源深度。房明山等(1995)給出了華北、山西、華東、西北及四川地區的sPn-Pn走時差對應震源深度表。本文將利用sPn震相計算發生在青海柴達木盆地內兩次地震的震源深度。
2015年5月青海格爾木相繼發生M40、M36地震,青海數字地震臺網清晰完整地記錄了這兩次地震的發生過程。這兩次地震震中位置相同,地震發生在柴達木盆地內。但由于青海地震臺網密度小,臺站難以較好地包圍震中,臺網給出的的震源深度是否準確有待檢驗。
在這兩次地震記錄上觀測到多個臺站出現了sPn震相,本文利用這些觀測資料重新計算了震源深度。
1sPn波的射線路徑和走時方程
當地震發生在地殼內時,從震源出發的S波入射到地表,反射轉換為P波后入射到莫霍界面,當入射角達到臨界角時,沿著莫霍界面傳播形成Pn波。由于它是S波轉換而來,所以記為sPn波。本文分別以單層和雙層地殼模型為例進行討論。
11單層地殼模型
假設v1和vS分別表示地殼內P波和S波的傳播速度,v2表示Pn波的傳播速度,射線路徑如圖1所示,其中O點表示震源,h表示震源深度,則sPn與Pn的走時差方程為
由此可以得出sPn震相的一個重要性質,即無論地震發生在單層地殼還是雙層地殼內,其與首波Pn的到時差與震中距無關,僅與介質傳播速度和震源深度有關。根據已有的研究成果和地質調查結論(趙文津等,2014;趙俊猛等,2003;張誠等,1998;藤吉文,1997;安昌強等,1993),柴達木盆地速度模型為:上地殼厚度H1=18km,下地殼厚度H2=34 km,vS1=355 km/s,v1=614 km/s,vS2=385 km/s,v2=666 km/s,v3=81 km/s。則有:
(1)雙層地殼模型,震源在上地殼內(或單層地殼模型),震源深度為
h=ΔtK1=278Δt.(6)
(2)雙層地殼模型,震源在下地殼內,震源深度為
h=Δt-CK2+H1=318Δt-26.(7)
如果震源在下地殼內,則滿足Δt≥647 s。
所以,當到時差Δt<647 s時,震源位于上地殼內,震源深度使用式(6)計算;據張國民研究(2000),中國青藏高原地區地震震源深度可達45 km,所以當647 s≤Δt≤1497 s時,震源位于下地殼內,適用式(7)。當震源深度超過52 km時,雙層地殼模型不再適用。
2sPn震相識別與震源深度計算
因為sPn是由S波轉換而來,所以它保持著橫波的動力學特征,并最終以縱波的形式出現在地震記錄上(房明山等,1995;張少泉,1998;高立新等,2007),在波形記錄上表征為:垂直分量顯示清晰,兩個水平分量也有明顯變化,振幅和周期均大于縱波。根據震相走時表,sPn震相出現在Pn之后、Pg之前,并且根據上述結論,其與首波的到時差不隨震中距改變而改變,所以如果將各臺站的首波Pn相互對齊,可以比較容易地辨認sPn震相。
在青海格爾木M40及M36地震中,青海數字地震臺網有多個寬頻帶臺站記錄到了sPn震相,臺站震中距在300~1000km間。從中選取震相清晰且信噪比較高的臺站記錄資料進行震源深度計算。根據震相走時表(國家地震局地球物理研究所,1980),震相Pg與 Pn的到時差在10 s以上,而本文觀測到的sPn震相與Pn震相的平均到時差為45 s,故sPn震相的識別不會被Pg干擾。
在計算sPn與Pn到時差時,因為sPn震相在垂直向和水平向都很發育,所以我們取其震相到時兩向平均值,從而盡量減少震相讀取引起的誤差。在計算震相周期和振幅比時,考慮到這次地震臺站震中距均在300 km以上,而且首波一般震相非常微弱,本文采用量取震相后兩個周期然后取平均值的方法。由表1、2可以看出,sPn震相的周期略大于Pn震相,平均振幅是Pn震相的3倍多,在波形記錄上也可以觀測到Pn震相后有一組比較強的波列,持續數個周期。由于利用單臺數據求取震源深度時偶然誤差較大,所以本文在計算完所有臺站的sPn-Pn到時差后,求取平均值。因為sPn-Pn到時差的平均值為450 s,小于647 s,所以根據上面結論,震源深度計算適用式(6),可得震源深度為125 km。這個結果與張誠等(1989)的甘、青震相走時表比較一致。在表1,2中,各臺站sPn-Pn的到時差與平均值的差值在02 s以內,對應的震源深度誤差約為05 km;另據Ma(2010)的研究,地殼模型會引起震源深度10%~15%的誤差,對應本文約有15 km的誤差,所以震源深度總的誤差大概為2 km。考慮誤差后,這兩次地震的震源深度為(125±20)km。
3與波形互相關結果對比
由于Pn和sPn同屬首波性質,初動振幅較弱,人工識別震相可能存在讀取誤差。為了驗證計算結果,本文進一步利用滑動時窗波形互相關疊加技術提取sPn震相(王俊等,2013;孫茁等,2014)。其基本原理是,對于同一個地震事件的N條波形記錄,兩兩組對計算相關系數,然后進行疊加、歸一化后得到總的互相關系數。其中正峰值大小反映了波形相同極性的相似度,負峰值反映波形之間相反極性的相似度,峰值之間的時移即為各震相到時差。
從表1與表2列出的臺站信噪比可以看出,前一地震由于震級大于后一地震,各臺的信噪比明顯大一些,又因為這兩次地震的震中位置相同,所以記錄到sPn震相的臺站基本相同,因此本文僅對第一個地震事件進行波形互相關計算。從波形記錄資料可以看出,各臺不同分量sPn的位置差異很小,故本研究中只計算了垂直分量。圖4即為各臺經過05~10 s的帶通濾波后按Pn到時對齊后的波形記錄圖。
由于地震發生于柴達木盆地內部,其莫霍面深度約52 km(趙文津等,2014),故震源深度可假定在5~40 km,依據IASPEI91模型,sPn與Pn的最大理論到時差約為13 s。滑動窗長一般取信號最大周期的1/2(Bensen et al,2007),由于Pn波的周期約為05~3 s,所以每次取15 s時長進行互相關計算,將12個臺站組成的66條互相關系數疊加、歸一化后得到Pn與sPn的相關系數圖(圖5)。
從圖5中看到在-06、39、42 s處有3個明顯的峰值,其相關系數分別為091、067、069,其中標注星號的為自動識別出的兩個震相。根據IASPEI91模型,可知前一星號處為Pn震相,后面星號處為sPn震相,兩者到時差為48 s,根據式(6)可計算出震源深度為135 km。但第2、3處的峰值時差僅為03 s,結合波形圖和IASPEI91模型可以判定為同一震相,可計算出第二個峰值與Pn的到時差為45 s, 與人工識別結果的平均值一致。
圖5中Pn震相的相關系數達到091,表示經過波形相關法拾取的Pn震相走時數據更為可靠。由于sPn震相存在兩個相關系數非常接近的峰值,該震相的識別不具有唯一性和排他性,且第二個峰值處起伏尖銳、波形光滑,周期和振幅都有顯著變化,具有明顯的震相特征,因此本文認為滑動窗方法在此次提取sPn震相時存在誤差。這可能與本文研究的地震震級較小、振幅較弱有關,而滑動窗法更適合中強地震的震相走時拾取。但借助滑動窗法可以更為直觀地找到目標震相的可能位置,然后通過與波形記錄對比確定震相標注的最佳位置。
4結論與討論
本文基于sPn震相與Pn震相的到時差不隨震中距變化的特性,利用多臺數據資料識別出sPn震相,并根據當地地殼模型推出了柴達木盆地地震震源深度公式。這有助于在出現sPn震相時快速精確地測定震源深度,為地震準確定位及后續研究提供更為可靠的地震參數。本文確定了2015年5月青海格爾木M40及M36兩次地震的震源深度為(125±20)km。
這種計算震源深度的方法簡單實用,但其準確性受限于Pn震相和sPn震相識別的精度。因為這兩個震相同屬于首波,震相不夠尖銳、清晰,識別有一定困難,存在讀取誤差。誤差的另一主要來源是地殼模型的誤差,包括速度模型的誤差、地殼厚度的誤差以及介質非泊松體引起的波速比誤差。
利用滑動窗互相關技術得到sPn與Pn的到時差為48 s,由此計算出震源深度為135 km。但仔細分析相關系數圖,筆者認為由于本次地震震級較小,滑動窗法在識別sPn震相時存在誤差,誤差校正后得出的結果與人工識別計算的結果一致。這表示人工識別法計算出的平均震源深度是可靠的。
參考文獻:
安昌強,宋仲和,陳國英等.1993.中國西北地區剪切波三維速度結構[J].地球物理學報,36(3):317-325.
蔡杏輝,邵平榮.2011.中國臺灣地區地震sPn震相分析及其震源深度計算[J].山西地震, (1):25-28.
房明山,杜安陸,董孝平等. 1995.用sPn震相測定近震震源深度[J].地震地磁觀測與研究,16(5):13-18.
高立新,劉芳,趙蒙生等.2007.用sPn震相計算震源深度的初步分析與應用[J].西北地震學報,29(3):213-218.
國家地震局地球物理研究所.1980.震相走時表便查表[M].北京:地震出版社
洪星,葉雯燕,邵平榮等.2006.臺灣海峽南部一次5.0級地震的sPn震相分析[J].地震地磁觀測與研究,27(3):26-31.
任克新,鄒立曄,劉瑞豐等.2004.sPn震相計算震源深度的初步分析與應用[J].地震地磁觀測與研究,25(3):24-31.
孫茁,吳建平,房立華等.2014.利用sPn震相測定蘆山Ms7.0級地震余震的震源深度[J].地球物理學報,57(2):430-440.
藤吉文.1997.中國地球深部地震探測研究的序幕-柴達木盆地的地殼與上地幔結構和構造[C]//地球物理與中國建設——慶祝中國地球物理學會成立50周年文集.
王俊,繆發軍,詹小艷等.2013.利用sPn震相精確測定江蘇高郵、寶應交界M4.9地震震源深度[J].防災減災工程學報,33(3):354-360.
張誠,高世壘,邵世勤.1989. 甘青區域地震波走時表[J]. 西北地震學報,(1):11-15.
張誠,邵世勤,高世壘.1998.甘青區域地震波走時表的地殼模型的選取[J].地震地磁觀測與研究,(2):27-34.
張國民,汪素云,李麗等.2000.中國大陸地震震源深度及其構造含義[J].科學通報,47(9):663-668.
張少泉.1998.地震波分析與應用[M]. 北京:地震出版社.
趙俊猛,張先康,鄧宏釗等.2003.拜城-大柴旦剖面的上地殼Q值結構[J].地球物理學報,46(4):503-509.
趙文津,吳珍漢,史大年等.2014.昆侖山深部結構與造山機制[J].中國地質,41(1):1-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