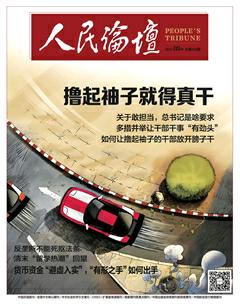廉政文化建設應擺脫傳統“父母官”思維
楊卓
【摘要】廉政文化的基礎理路中,秉承著幾千年封建社會的認識。現代社會,在充分繼承傳統文化中優秀成分的同時,也應看到為政理念的發展。當今廉政文化建設,應充分、合理吸收“法治精神”“契約精神”的內核,突破以血緣關系為出發點的“父母官”理路。
【關鍵詞】廉政文化 血緣關系 法治精神 契約精神 【中圖分類號】G459 【文獻標識碼】A
古代廉政文化的基本理路是“愛民如子”
漫長的封建社會,對于廉政文化的建設,其理路基本上是由上到下的,把老百姓當作“子女”“子民”,廉政主體者是“父母官”。所謂廉政,就是要把自己治下的百姓當作自己的孩子,也即是要“愛民如子”。另一種廉政文化建設,其理路,對于封建社會來講,轉換是根本性、顛覆性的。老百姓真正被當作了“衣食父母”,這個進步是空前的。在這種理路的前提下,為官者不再是高高在上的“父母”“老爺”,而是老百姓的子女。觀此二種理解,是對“父母官”一詞的理解做了發揮。
第一種情形中,把做官的視作百姓的“父母”,因而,就稱其為“父母官”,這似乎也是絕大多數語境中的通常理解。第二種情形中,視老百姓為“衣食父母”,做官的則順理成章地自稱為老百姓的子女,是為自己的衣食父母、為老百姓這些“父母”在為官,是以被稱作“父母的官”。應該客觀地講,第二種理解具有一定的進步性,因為做官者在把百姓視為“衣食父母”的情況下,也就不會作威作福、貪污腐敗,而是一定要為“父母”主持公道、伸張正義,要孝順父母,為父母帶來功德等。兩種情形中,人們都有一種想象:民與官的關系,理所當然地應該是“父母”和“子女”的關系。將“父母官”解釋成“老百姓之父母的官”也好,解釋成“老百姓的父母官”也罷,將“做官的人”和“老百姓”看成父母與子女的關系,其本意就是為了拉近官與民的關系,創建出一種“一家人”的“大同社會”表象。因而,不論把為官者視為百姓之“父母”,還是將百姓視為做官者之“父母”,其目的無非是拉近官與民之關系,顯得親密無間,親似一家人。
“父母官”這個詞語,到底出自哪個朝代,已經不好考證,這已經是民間的一種約定俗成的稱謂。而許多民間戲曲、評書中,將“父母官”看作“老百姓父母的官”者有之,視為“百姓的父母官”者更是不在少數。如將“父母官”解釋成“老百姓的父母官”,為官者就成了老百姓的長輩,長輩自然也就是“老爺”,就成了新中國成立之初黨中央所批評的“當官做老爺”。在這種理解前提下,如果將為官者稱為“父母官”,廣大人民群眾很自然就把為官者視為“老爺”了。在當官者那你喊冤下跪,磕頭哀求者,皆為是。如將“父母官”解釋為“老百姓父母的官”,為官者則是老百姓的子女,老百姓是為官者的衣食父母。在這種情形下,做官者就是全心全意為百姓服務,被叫為“父母官”似乎也沒有什么不可以的。
從歷史上看,即使在漫長的封建社會,但凡被百姓稱道的好官,都是真正把百姓看作自己的衣食父母。現代社會,我們的許多革命領袖、先進典型,也都是將自己看作老百姓的兒女。既然是老百姓之兒女,就得對父母有孝心,要孝敬老百姓,那些革命領袖、人民的好干部、各行業的模范人物,都行如其言,說到做到了。
從而,我們不難看出,此二者之理路,皆以血緣關系為其紐帶。究其根源,是幾千年儒家思想中以血緣關系為出發點,將“孝道”推廣到社會管理領域,將統治者與百姓的關系視為“父子關系”,所謂“君臣如父子 ”。但不管是民本思想,還是官本位,其實都把“民與官”對立起來了。
“民本”思想立足于統治者而非百姓
對于政治及國家治理,我國思想的發軔期,也就是春秋戰國年代,就有了老莊孔孟韓非墨翟等一批思想家為代表的“百家爭鳴”盛況。那時,在各家思想中,已經有了較為成熟的“廉政”的觀念,盡管各家表述不同。比如,在《周禮》中,就已經有了一些官員考核的標準,這些標準就是我們熟悉的“六廉”,也就是“廉善”、“廉能”、“廉敬”、“廉正”、“廉法”、“廉辨”。值得注意的是,這六個方面雖然在今天看來不完全是“廉”的內容,但在當時,都以“廉”作為其冠首語。也就是說,當時的人是將能夠使一個官員勝任的一切要求,都當作“廉”的內容。我們這里只探討狹義的“廉”之義,并且只著重談廉政的思想基礎,以及廉政的現實基礎。
《周禮》的“六廉”中,雖然不直接涉及廉政的思想基礎,但《周禮》,以及“三禮”中的《儀禮》與《禮記》,顯然都有很成熟的思想基礎,就是我們后來非常看重的儒家所謂的“民本思想”。我們這里要著重論證的“廉政”方面的內容,在“周禮”中,基本就是儒家與法家兼融,德治為主,但也輔之以刑罰。
這種儒家與法家的融通,也造成了對廉政思想基礎的“民本”思想理解的混亂與誤讀。人們錯誤地認為,儒家的思想就是鐵板一塊的“民本”主義,在極度推崇傳統思想的民族主義者眼中,儒學的現代化成了當今社會最好的出路。其實,就在儒家內部,孔子與孟子在對待“民”的態度就是不同的。孔子是儒家學說的初創者,其思想本來來源于禮儀執行者,而禮儀執行者的初衷就是為統治者張目。因此,“以民為本”,在提倡“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孔子那里,事實上就成了一種策略。本質上,孔子是在為統治者開藥方,是從統治者如何治理百姓入手,而非是從百姓如何獲得平等自由著力。
如果我們看到了儒家初創階段,包括孔子在內,都是在為統治者張目,作為內在核心的“仁”也好,外在表現的“禮”也罷,都與作為駕馭臣民手段的“帝王之術”的“法家”是互相融通的。記錄孔子及其弟子言行的《論語》,并非是“孔子生活的那個時代是一個物質極其匱乏的時代,在那個時代,真正快樂的力量,也就來自于心靈的富足,來自于一種教養,來自于對理想的憧憬,也來自于與良朋益友的切磋與交流。”其實,不論《論語》中的孔子,還是《孔子世家》中的孔子,抑或是《孔子家語》中的孔子,都不是“快樂”的孔子,因為他自己努力周游列國要給統治者開藥方,但統治者并不領情,他只能“知其不可為而為之”。
到了孟子時期,《孟子·盡心下》中明確提出:“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是故得乎丘民而為天子,得乎天子為諸侯,得乎諸侯為大夫。”也即是說,國家、天下、君王、諸侯、大夫,最終都是為了老百姓而存在的。應該說,在戰亂頻仍、生產力落后的先秦時代,孟子是一個真正意義上的初步的“民本”主義者。在等級制度森嚴的時代,孟子的傾向性明顯地倒向作為大多數人的勞動者一方。但我們也不得不指出,孟子實現“民本”的道路,仍然是說服統治者去實施“愛民”的所謂“仁政”,這不過是一種站在道德制高點上的“人道主義”而已。這樣的立場,既看不到社會不平等的根源,更找不到解決的出路。
當代廉政文化的培育應以官民平等為基點
官,在現代社會就是管理者,是一種職業,是納稅人雇傭的“公務員”,但同時他們自身也是納稅人之一分子。所以,現代意義上的官,就是民的一部分。所以,處處以一種政府與納稅人對立的姿態談論廉政文化,本身也是不可取的。
我們應該明確,以血緣關系為根基的儒家思想,如果不經過脫胎換骨的現代化改造,肯定是不能勝任現代政治理念的。“父母官”的說法,固然能夠拉近官與民之關系,但根本上看,這種關系還不是官民關系的實質。不論是為官者視百姓為“衣食父母”,還是老百姓將做官者看作“父母官”,都不是本質意義、現代意義的官民關系。現代意義上,官與民是平等的,是職業分工不同,同為納稅人,同樣用自己的勞動換取報酬。只有看到了這一點,才可能把廉政文化的理路與根基擺在一個較為合適的基點上,從而創造出新型、現代意義上的法治文化理路。
(作者單位:內蒙古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
【參考文獻】
①俞志慧:《〈論語·泰伯〉“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章新解》,《孔孟月刊》(第三十五卷第五期),1997年1月號。
②王昌銘:《“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新解》,《語言文字報》,2004年8月24日。
③錢穆:《論語新解》,成都:巴蜀書社,1985年。
責編/張蕾 美編/楊玲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