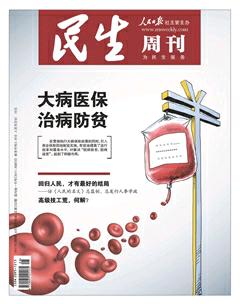《人民的名義》爆紅折射民生焦慮
胡印斌
《人民的名義》顯然讓人們找到了一個公共場域,而那些被反腐遮蔽了的民生焦慮也再度被關注。
盡管不乏爭議,甚至還有“不解渴”的吐槽,反腐題材電視劇《人民的名義》還是火得一塌糊涂。不管線上線下,人們張口閉口就是“侯亮平”“高育良”“李達康”“祁同偉”,不少人熱衷于“對號入座”,為劇中人尋找“原型”……各種社會階層人士的代入感表現得如此強烈,至少從近年來的影視劇作品看,并不多見。
一部已經成形的藝術作品,存在這樣那樣的缺陷,或者說仍有一些思慮不甚周詳之處,也是很正常的。拍了,也播了,剩下來的,就是接受公眾的檢閱。如何評價,原本就沒有標準答案,如果從接受美學的理論看,公眾的參與、批評也是完成劇本的一個環節,觀眾的品頭論足,本身就是文本的一種再創造,是藝術作品實現其價值的必要過程。
從這個意義上講,公眾的互動越是強烈、爭論越是激烈,則說明這部電視劇就越是具有某種普遍價值,引發、激發出某種共同的社會情緒。在一個價值觀分歧越來越大的時代背景下,發生這樣的現象,當然是一件好事。
這部劇最吸引人的話題自然是反腐。無論是家里到處都塞滿錢、就像一個銀行金庫般的趙德漢,還是表面上不動聲色、暗地里男盜女娼的高育良,還有那位賣了房子住到養老院的老檢察官陳巖石,這些人都有著無限的話題延展性,可以讓人多方評說。甚至還會結合現實中法院公布的判決書,媒體挖掘出來的貪腐官員細節,加以證實或證偽。
但拂去“反腐”這一主題,人們其實也發現,這部劇其實反映的是當下中國一個波瀾壯闊的切面,就像編劇周梅森說的那樣,《人民的名義》就是“想做一個大中國的故事,從官場的高層到底層的弱勢群體都有涉及,同時借人物、劇本把自己對中國十幾年來巨大的社會思索量容納進去”。
也因此,于反腐“宮斗戲”之外,更有豐富的社會人生,乃至深廣的民生焦慮。如何協調城市發展中的拆遷與補償問題,普通民眾遭遇冤屈后如何伸張正義,還有下崗工人生計問題等等,這些問題可能在高官眼里只是宴會上的推杯換盞,而在每一個具體生活在當下的民眾身上,卻是千鈞重負,一點都不輕松。
大概已經有十多年了,因為類似反腐題材影視劇基本絕跡,盡管中央打虎拍蠅的行動浩浩蕩蕩,但公眾往往鮮有一個可以討論的“共同話題”。而《人民的名義》顯然讓人們找到了一個公共場域,而那些被反腐遮蔽了的民生焦慮也再度被關注。人們發現,與反腐相比,如何保障民眾的權益不被侵害,或者即便遭遇侵害如何找回公正,具有同樣重要的意義與價值。
而破解諸多癥結的關鍵,無疑應該是制度建設。應該通過完備的制度建設約束權力,重塑正常的政經生態。一方面可以擴大反腐的戰果、固化反腐的成績,構建“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防范機制,形成對腐敗行為的壓倒性態勢;另一方面,也可以切實保障民眾的合法權益,緩解民眾的不適感、不安感,不被權力肆意侵凌,不被資本悍然碾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