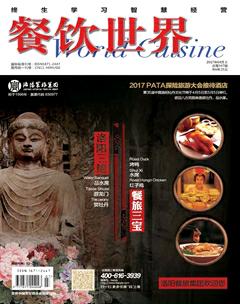蕭紅 命運,比青杏還酸
Cincly
1932年蕭紅次見到蕭軍,她已經寫下了自己的第一篇作品,“這邊樹葉綠了/那邊清溪唱著……/姑娘啊/春天到了……/去年在北平/正是吃著青杏的時候/今年我的命運/比青杏還酸/……”。一個“青杏”比擬,讓人對蕭紅這個隔在時空彼岸的女子,心生愛憐。
與民國時的才女蘇青不同,蕭紅并沒有刻意的去描寫食物,但是她筆下的食物卻讓人刻骨銘心。食物中體現了蕭紅與祖父與父親及戀人蕭軍,三個男人之間的關系。呼蘭河畔祖父的花園是她生命中是的最美之地,連祖父給她留的一個烤苞米,都是最香的;蕭紅常常對父親充滿了情緒,但是她在《餓》中輕描淡寫地說道:“讀書的時候,哪里懂得‘餓·”雖然只一句話,我們可以想到父親的苦心。在兵荒馬亂的年代,依舊讓她過著衣食無憂,安心讀書的生活。骨子里,父親依舊深愛著這個小女兒;和蕭軍在一起之后,或者說蕭紅獨自面對世界,一場場的愛情在生命中穿梭而過。她為愛情寧可過著顛沛流離的生活,但是多年之后,戀人之一的蕭軍只淡淡地評價,蕭紅沒有妻性。蕭紅與愛情相關的文章中,常常看到“餓”字。她更說:“今年我的命運,比青杏還酸。”
祖父的園子
常常為饑餓所苦的蕭紅,童年時,對美食卻有著鮮明的美好記憶。
蕭紅寫道:“太陽在園子里是特大的。花開了,就像花睡醒了似的。鳥飛了,就像鳥上天了似的。蟲子叫了,就像蟲子在說話似的。一切都活了,要做什么,就做什么。要怎么樣,就怎么樣。都是自由的。倭瓜愿意爬上架就爬上架,愿意爬上房就爬上房。黃瓜愿意開一個黃花,就開一個黃花,愿意結一個黃瓜,就結一個黃瓜。玉米愿意長多高就長多高,它若愿意長上天去,也沒有人管。蝴蝶隨意的飛,一會從墻頭上飛來一對黃蝴蝶,一會又從墻頭上飛走了一個白蝴蝶。它們是從誰家來的,又飛到誰家去?太陽也不知道這個。只是天空藍悠悠的,又高又遠。”
這個園子里充滿了愛和美食。有一回,一只小豬溺死于井內,祖父把撈起的死豬抱回家,用黃泥裹起來,放在灶坑里燒。蕭紅說:“祖父把那小豬一撕開立刻就冒了油,真香,我從來沒有吃過那么香的東西,從來沒有吃過那么好吃的東西。”
第二次,又有一只鴨子掉進井里,祖父也用黃泥包起來,燒給她吃。祖父讓她選嫩的部分來吃,她吃得滿手是油,隨吃隨在大襟上擦著,祖父看了也不生氣,只是說:“快蘸點鹽吧,快蘸點韭菜花吧,空口吃不好,等會兒要反胃的……”寥寥數筆,祖父溺愛她的形象便躍然紙上了。
濃烈的愛,留在記憶的最深處。蕭紅在《呼蘭河傳》尾聲里寫道:“呼蘭河這小城里邊,以前住著我的祖父,現在埋著我的祖父。”
“饑餓”的青春
蕭紅寫的“餓”尤其為打動人心。也許因為饑餓,所以她筆下的美食,雖然有時候只是面包蘸鹽,也讓人似乎能隔著“光陰”聞到麥香。
蕭紅的散文集《商市街》中有一篇《餓》,寫了自己最饑餓的狀態:“輕輕扭動鑰匙,門一點響動也沒有。探頭看了看,‘列巴圈對門就掛著,東隔壁也掛著,西隔壁也掛著。天快亮了!牛奶瓶的乳白色看得真真切切,‘列巴圈比每天也大了些,結果什么也沒有去拿,我心里發燒,耳朵也熱了一陣,立刻想到這是‘偷。兒時的記憶再現出來,偷梨吃的孩子最羞恥。過了好久,我就貼在已關好的門扇上,大概我像一個沒有靈魂的、紙剪成的人貼在門扇。大概這樣吧。街車喚醒了我,馬蹄嗒嗒、車輪吱吱地響過去。我抱緊胸膛,把頭也掛到胸口,向我自己心說:我餓呀!不是‘偷呀!”
在《商市街》的另一篇《提籃者》中,蕭紅寫道:“第二天,擠滿面包的大籃子已等在過道。我始終沒推開門。門外有別人在買,即使不開門,我也好象嗅到麥香。對面包,我害怕起來,不是我想吃面包,怕是面包要吞了我。”
在《黑“列巴”和白鹽》中,蕭紅寫道:“他連忙又取一片黑面包,涂上一點白鹽,學著電影上那樣度蜜月,把涂鹽的‘列巴先送上我的嘴,我咬了一下,而后他才去吃。一定鹽太多了,舌尖感到不愉快,他連忙去喝水:‘不行不行,再這樣度蜜月,把人咸死了。黑‘列巴和白鹽,許多日子成了我們唯一的生命線。”
“列巴”是俄文譯音,是俄羅斯的主食面包。小的1斤重,大的可達3斤重,酸甜可口,松軟香酥,貯存簡單。在哈爾濱,很多食品的名稱都沿用了俄文譯名,小的俄式面包叫“沙克”,面包干叫“蘇克立”等等。黑列巴也就是黑面包,由面粉、蕎麥、燕麥等原料烤制而成,顏色很深,有酸味。吃的時候要切片就著黃油、蘇波湯才有味道。黑列巴蘸鹽,是一種無奈之舉。誠如蕭紅說:“許多日子成了我們唯一的生命線”。但是蕭紅,縱然自己朝不保夕,但凡自己有錢買食物的時候,也會給路邊的叫化子一個銅板。饑餓奪不去的是心里的善良。
哈爾濱的小飯館
就像今天的大食堂一樣,1930年代哈爾濱的小飯館也常常人滿為患。蕭軍找到家庭教師的工作之后,有了20元的收入,便帶蕭紅去中央大街旁的小飯館吃飯。蕭紅說:“我跟著進去,里面擺著三張大桌子。我有點看不慣,好幾部分食客都擠在一張桌上。屋子幾乎要轉不過身。我想,讓我坐在哪里呢?三張桌都滿滿的人。我在袖口外面捏了一下郎華的手說:‘一張空桌也沒有怎么吃?他說,在這里吃飯隨隨便便的,有空就坐。他比我自然得多,接著,他把帽子掛到墻壁上。堂倌走來,用他拿在手中已經擦滿油膩的布巾抹了一下桌角,同時向旁邊正吃的那個人說‘借光,借光。”第一次去,點了豬頭肉來吃,還有丸子湯和五六碟小菜,蕭軍就著豬頭肉喝了一壺小酒,蕭紅也幫著喝。
第二次去那個飯館的時候,蕭紅已經習慣,還不等蕭軍坐下,就先搶了個地方坐下,而且也把菜名記熟了:“什么辣椒白菜啦,雪里蕻豆腐啦……什么醬魚啦!怎么叫醬魚呢?哪里有魚!用魚骨頭炒一點醬,借一點腥味就是啦!我很有把握,我簡直都不用算一算就知道這些菜不超過一角錢。因為我用很大的聲音招呼,我不怕,我一點也不怕花錢。”辣白菜、豬頭肉、肉丸子湯、雪里蕻豆腐今天依舊是東北人愛吃的美食。
蕭紅和蕭軍住的商市街,是今日哈爾濱最有名的“中央大街”。他們的朋友后來回憶道:在白俄人很多的中央大街上,看到過蕭軍和蕭紅。蕭軍的脖子上系了個黑蝴蝶結,手里拿著把三角琴,邊走邊彈;蕭紅穿著花短褂,下著一條女中學生通常穿的黑裙子,腳上卻蹬了雙蕭軍的尖頭皮鞋,看上去特別引人注目。他們邊走邊唱,就像流浪藝人一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