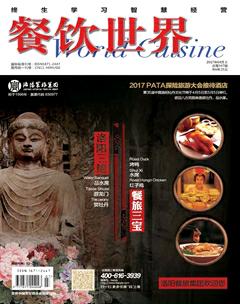汪曾祺、李登年、劉樸兵 美食家筆下的宋朝美食
宗蓮籽
宋朝是一個創造美食的年代,豆芽菜、火鍋、火腿、東坡肉等美食的最早記載都在宋朝。安陽師范學院飲食文化研究所所長劉樸兵先生,在其《唐宋飲食文化比較研究》中說,宋代的飲食文化顯得細膩精致。經過宋代的發展,無論是主食面點還是副食菜肴,都全面完成了品類的細化,花色品種眾多。宋代時,素菜開始成為一個獨立的菜系,受到了人們廣泛的歡迎。只有烹飪技術相當精致的基礎上,才有可能把蔬菜、菌類、竹筍、豆腐等素料加工成各種色、香、味俱佳的美饌來。宋人的酒文化也減少了大呼小叫的豪邁成分,多了幾分輕言細語的文雅。酒宴之上,賓主不再像唐人那樣盡情地表演歌舞,而儒雅地坐在座位上欣賞舞女的專業表演。助飲的酒令也漸漸演變成為各種文字游戲了,很少能激起唐代酒宴上那種豪爽的熱烈的氣氛來。宋代的飲食店肆普遍重視內外裝潢,店內多懸名人字畫,文化味十足,這些都盡顯了宋代飲食文化的細膩。
宋朝人的吃喝
當代著名作家汪曾祺先生在散文《宋朝人的吃喝》中細致描述了宋朝的吃喝小事。他在文章中說:“唐宋人似乎不怎么講究大吃大喝。杜甫的《麗人行》里列敘了一些珍饈,但多系夸張想象之辭。五代顧閎中所繪《韓熙載夜宴圖》主人客人面前案上所列的食物不過八品,四個高足的淺碗、四個小碟子。有一碗是白色的圓球形的東西,有點像外面滾了米粒的蓑衣丸子。有一碗顏色是鮮紅的,很惹眼,用放大鏡細看,不過是幾個帶蒂的柿子!其余的看不清是什么。蘇東坡是個有名的饞人,但他愛吃的好像只是豬肉。他稱贊‘黃州好豬肉,但還是‘富者不解吃,貧者不解煮。他愛吃豬頭,也不過是煮得稀爛,最后澆一勺杏酪——杏酪想必是酸里咕嘰的,可以解膩。有人‘忽出新意以山羊肉為玉糝羹,他覺得好吃得不得了。這是一種什么東西?大概只是山羊肉加碎米煮成的糊糊罷了。當然,想象起來也不難吃。”
汪曾祺還在文中講了一些宋朝美食的八卦,他說:“宋朝的面食品類甚多。我們現在叫做主食,宋人卻叫‘從食。面食主要是餅。《水滸》動輒說‘回些面來打餅。餅有門油、菊花、寬焦、側厚、油鍋、新樣滿麻……《東京夢華錄》載武成王廟海州張家、皇建院前鄭家最盛,每家有五十余爐。五十幾個爐子一起烙餅,真是好家伙!”
另外,汪曾祺先生還說:“遍檢《東京夢華錄》、《都城紀勝》、《西湖老人繁勝錄》、《夢粱錄》、《武林舊事》,都沒有發現宋朝人吃海參、魚翅、燕窩的記載。吃這種滋補性的高蛋白的海味,大概從明朝才開始。這大概和明朝人的縱欲有關系,記得魯迅好像曾經說過。”
宋代的筵席
食文化專家李登年的《中國宴席史略》中,詳細解讀了宋代的筵席。宋時的文人,喜歡聚會宴樂,自古亦然。他們擇清節佳日,游名山圣水,詩酒唱和,吟詩作賦。現代人常說,生活要有儀式感。事實上,宋代的飯局充滿了“情調”。
飛英會
李登年的文章中提及飛英會。他寫道:“北宋范外鎮居許下,于長嘯堂前作荼蘼架,春日花時,招友設筵其下,花落誰杯中,誰飲酒一杯。微風輕揚,落英滿座,稱為‘飛英會。”
北宋翰林學士范鎮,居住在許昌(今屬河南),在宅院里建造了一座大堂,起名叫“長嘯堂”。堂前有荼蘼架,每到春末夏初荼蘼花盛開的時候,就在花架下宴請客人,約定說:飛花飄落到誰的酒杯,誰就干杯。有時微風過后,飛花紛紛飄灑,滿座無一不干杯。行這種酒令的宴會,當時號稱“飛英會”(“英”即“花”)。宋時,有一種制作荼蘼酒的方法,是先把一種叫做“木香”的香料研磨成細末,投入酒瓶中,然后將酒瓶加以密封。到了飲酒的時候,開瓶取酒,酒液已經芳香四溢,這時再臨時在酒面上灑滿荼蘼花瓣,酒香聞來正如荼蘼花香,幾乎難以分辨二者的區別。這一做法,是受了“飛英會”的影響。于是,浮著片片荼蘼花瓣的酒杯,便成就了宋人在暮春里的一場場歡宴。
錢龍筵
《中國宴席史略》中還描述了錢龍筵。文章中寫道:“《云仙雜記》載,洛陽富貴人家有歌伎,于三月三日結錢為龍,將錢龍一條條掛起為簾子,在簾內設筵,稱‘錢龍筵。”李登年先生說:“因物而名,因花成宴,可謂酒不醉人花醉人,‘尋常不醉此時醉。”
歐陽修的醉翁亭宴
文人出游,更是別有一番情趣。《中國宴席史略》中摘錄了歐陽修的《醉翁亭記》:“臨溪而漁,溪深而魚肥;釀泉為酒,泉香而酒冽;山肴野蔌,雜然而前陳者,太守宴也。”李登年先生說:“這是北宋文學家歐陽修任滁州(今安徽滁州市)太守時舉辦的郊游宴。”
歐陽修的太守宴,用現代流行語來形容,就是“天然綠色的農家菜”。看得見的好食材,吃得歐陽太守心滿意足,寫下千古名篇《醉翁亭記》。
北宋南味海珍佳肴
海鮮也是北宋王公貴族的心頭大愛。《中國宴席史略》中摘引了歐陽修的《京師初食車蜇》:“累累盤中蛤,來自海之涯。坐客初未識,食之先嘆嗟……自從圣人出,天下為一家。南產錯交廣,西珍富邛巴……豈為貴公候,閭巷飽魚蝦。此蛤今姓生,其來何晚邪。螯蛾聞二名,久見南人夸。璀璨殼如玉,斑爛點生花。食醬不肯吐,得火邃已呀。共食惟恐及,爭先屢成嘩。但善美無厭,豈思來甚遐。多慚海上翁,辛苦斫泥沙。”李登年先生說:“這是歐陽修《京師初食車蜇》詩,形象地描寫北宋時南方海珍大舉進入京城的盛況。宋代經濟繁榮,交通便利,南方的海錯珍品,大批運到京城,進入宮廷盛宴,成為‘貴公候稀世珍味,海鮮佳肴。”
御宴
李登年對御宴有比較詳盡的考證。汪曾祺對御宴的描述比較簡潔。汪曾祺說:“宋朝人的吃喝好像比較簡單而清淡,連有皇帝參加的御宴也并不豐盛。御宴有定制,每一盞酒都要有歌舞雜技,似乎這是主要的,吃喝在其次。幽蘭居士《東京夢華錄》載《宰執親王宗室百官入內上壽》,使臣諸卿只是‘每分列環餅、油餅、棗塔為看盤,次列果子。唯大遼加之豬羊雞鵝兔連骨熟肉為看盤,皆以小繩束之。又生蔥韭蒜醋各一碟。三五人共列漿水一桶,立杓數枚。‘看盤只是擺樣子的,不能吃的。‘凡御宴至第三盞,方有下酒肉、咸豉、爆肉、雙下鴕峰角子。第四盞下酒是子骨頭、索粉、白肉胡餅;第五盞是群仙、開花餅、太平畢羅、干飯、縷肉羹、蓮花肉餅;第六盞假圓魚、密浮酥捺花;第七盞排炊羊、胡餅、炙金腸;第八盞假沙魚、獨下饅頭、肚羹;第九盞水飯、簇饤下飯。如此而已。”
寒食與清明
劉樸兵博士在《唐宋飲食文化比較研究》一書中,對寒食與清明做了細致的解讀,并講出清明兼并寒食的文化依據。他說:“寒食在冬至后的第105日,故此節又稱‘百五節,寒食禁火,只吃冷食,所以又稱‘冷食節。清明為二十節節氣之一,在寒食之后的一二日。唐代以前寒食與清明是兩個主題不同的節日,一為懷舊悼亡,一為求新護生。寒食禁火冷食祭墓。清明取新火踏青出游。一陰一陽,一息一生,二者有著密切的配合關系。禁火為了出火,祭亡意在佑生,這就是后來清明兼并寒食的內在文化依據。”
清明吃什么?劉樸兵的文章中說:“宋代時,寒食期間出現了不少新的節日食品,如蒻葉飯、姜豉凍肉、臘肉等。呂原明《歲時雜記》載:‘寒食以糯米合采蒻葉裹以蒸之,或加魚鵝肉、鴨卵等 ,又有置艾一葉于其下者;‘寒食煮豚肉,并汁露頓,候其凍取之,謂之姜豉。以薦餅而食之,或剜以匕,或裁以刀,調以姜豉故名焉;‘去歲臘月糟豚肉掛灶上,至寒食取之以啖之,或蒸或煮,其味其珍。”
劉樸兵表示,不少寒食食物在兩宋時期也做了改良。他表示,兩宋時期,不少傳統的寒食食物的名稱也發生了變化,莊綽《雞肋編》卷上《馓子》云:“食物中有‘馓子,又名‘環餅,或曰即古之‘寒具也。”王仁興先生據此認為:“北京宋時,寒具始名‘馓子。”宋代馓子的制作技術高超,馓子色澤嫩黃,蘇軾《寒具》詩云:“纖手搓來玉數尋,碧油輕蘸嫩黃深。夜來春睡濃于酒,壓褊佳人纏臂金。”子推蒸餅在宋代改稱為“子推”、“子推燕”等。宋代高承《事物紀原》卷8《子推》載:“故俗,每寒食前一日謂之炊熟,則以面為蒸餅樣,團棗附之,名為子推。穿以柳條,插記戶牖間。”傳統的寒食麥弱在宋代也易名為“醴酪”了。
在宋代清明已經完全取代了寒食的地位,除禁火冷食仍為寒食特有的外,清明已承擔了許多原屬于寒食的節俗功能,如唐開始形成的寒食上墓祭掃的風俗,到宋代時上墓祭掃完全成了清明的節俗了。宋代清明掃墓,除酒肴外,已經普遍使用麥糕、乳酪、乳餅等做祭品了。其中,乳酪、乳餅為宋代新增加的節令食品。劉樸兵說:“人們往往借清明上墳之際踏青宴飲。”他還在文章中引用了《東京夢華錄箋注》,說:“四野如市,往往就的芳樹之下,或園圃之間,羅列杯盤,互相勸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