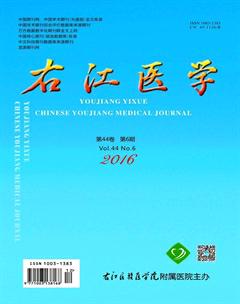生長分化因子—15與心腦血管疾病相關性研究的最新進展
張婷 黃華佗 王榮 覃海媚 韋葉生
心腦血管疾病是世界范圍內嚴重危害中老年人健康的一類臨床常見疾病,因治療效果不理想且缺乏有效的早期診斷和預警方法,已成為致死率和致殘率最高的一類疾病。目前,其發病機制雖然尚未得到充分闡釋,但炎癥因素被認為在其發病過程中起著關鍵的作用,大量與其發病相關的炎癥因子被陸續報道。生長分化因子-15(growth differentiation factor-15,GDF-15)為轉化生長因子-B超家族的成員之一,于1997年被Bootcov等從單個核細胞系U937 cDNA文庫中分離出來,并被命名為巨噬細胞抑制因子。后來,Bottner等將其重新命名為GDF-15。GDF-15具有豐富的生物學功能,在調控胚胎發育、細胞遷移、分化、增殖以及黏附等方面均發揮著重要作用。GDF-15被認為是在心腦血管疾病診斷、預后、危險分層以及心腦血管疾病藥物研發領域極具希望的因子。近幾年來,GDF-15在心腦血管的相關研究更新得比較快,已取得了較大進展。筆者就近年來GDF-15在心腦血管領域的研究做一系統綜述,為GDF-15的進一步研究和臨床藥物開發提供便捷參考。
1.GDF-15的生物學特性
GDF-15,又稱為巨噬細胞抑制因子-1(macrophage inhibitory cytokine,MIC-1)或胎盤轉化生長因子-B(placental transforming growth factor beta,PTGF-B)或非甾體抗炎藥活化基因-1(non-steroidal anti-in-flammatory drug-activated gene.NAG-),為轉化生長因子-B(transforming growth factor-p,TGF-p)超家族的成員之一。與其他家族成員相似,GDF-15蛋白鏈的C端是由7個半胱氨酸組成的結構域,然而,其序列與其他家族成員比較只具有15%-29%的同源性。編碼GDF-15蛋白的基因位于19號染色體短臂上(19p13.2-p13.1),包含1個內含子和2個外顯子。第一外顯子長度為309個堿基,并包含一個長為71個堿基的5非翻譯區:而第二外顯子長度為647個堿基,包含一個長為244個堿基的3非翻譯區。成熟的GDF-15蛋白由含有308個氨基酸殘基的多肽前體經過蛋白酶的剪切、聚合和折疊,形成分子量約為62000的二聚體,最后經過Fruin樣蛋白水解酶的作用,生成包含224個氨基酸,大小為25-kDa的同源二聚體蛋白質,以自分泌和旁分泌的形式作用于自身以及周圍的組織和細胞,發揮廣泛的生物學功能。
在生理條件下,GDF-15的表達呈現出明顯的組織特異性,Northern雜交分析顯示,除胎盤組織外,GDF-15僅少量表達于腎臟、胰腺、結腸和前列腺等組織及器官而幾乎不表達于除外的其他組織和器官。然而,在手術、組織損傷、缺氧以及各種炎癥因子作用等病理條件下,受刺激部位的巨噬細胞、血管平滑肌細胞、心肌細胞、脂肪細胞以及內皮細胞GDF-15的表達可被顯著上調。例如,在冠狀動脈搭橋手術后GDF-15水平顯著升高,與術后心肌損傷有關;在被結扎股動脈造成缺氧的條件下,鼠成骨細胞的GDF-15表達水平顯著增加,升高的GDF-15可促進破骨細胞的分化,與缺氧條件下骨吸收密切相關。此外,急性心肌梗死時,GDF-15水平顯著增加,與急性心肌梗死患者復發和致殘相關。
研究發現,白細胞介素-1B、腫瘤壞死因子-a、血管緊張素Ⅱ、巨噬細胞集落刺激因子和轉化生長因子-B等多種細胞因子可顯著刺激GDF-15的表達。非甾體抗炎藥、吲哚美辛、吲哚-3-甲醇、5F-203和共軛亞油酸等多種藥物也能夠刺激GDF-15的表達。GDF-15的表達受到多種因素的調控,應激反應、炎癥因子和多種藥物的刺激可以促進GDF-15的表達,表明GDF-15很可能是在應激條件下可被誘導表達的基因,通過上調GDF-15的表達執行廣泛的生物學功能。
2.GDF-15與動脈粥樣硬化
動脈粥樣硬化(atherosclerosis,AS)是一種嚴重危害中老年人健康的臨床常見疾病.同時也是血栓性疾病、冠心病以及缺血性腦血管病等多種心腦血管系統疾病的重要病理基礎。AS為血管壁對各種損傷和炎癥刺激的一種異常反應的結果,其中細胞因子在AS發病中的作用引起科學家們的廣泛關注,TGF-B超家族是其中的焦點之一。GDF-15為TGF-B超家族的成員,為近年來發現的與心腦血管發病密切相關的細胞因子。
早期研究發現,GDF-15可抑制巨噬細胞的活化,可能在調節As炎癥中起著重要作用。后來Johnen等學者發現,經高脂喂養6個月的載脂蛋白E基因敲除的AS模型老鼠,在過表達GDF-15條件下,AS斑塊面積較之前明顯縮小,然而粥樣斑塊的促炎癥因子和抗炎癥因子生成水平及血脂的水平與之前比較并未有統計學差異,表明GDF-15可能在AS發展進程中起保護作用。國內學者顏毅等人通過比較冠狀動脈擴張組、冠狀動脈粥樣硬化組和冠狀動脈造影正常組血漿GDF-15水平時發現,冠狀動脈擴張與冠狀動脈粥樣硬化的不同病理階段,GDF-15的生成水平不一致,表明GDF-15可能是冠狀動脈粥樣硬化的保護因子,GDF-15可能在AS的發生發展中起著保護作用。上述研究從基礎和臨床等兩個方面證明GDF-15可能在動脈粥樣硬化中起到保護作用,然而其具體機制卻未能得到充分闡釋。
目前,雖然GDF-15與AS相關疾病的研究很多,但其作用的具體機制研究進展仍相對緩慢。Schlittenhardt等學者發現,用氧化低密度脂蛋白(oxLDL)及其介質作用于體外培養的巨噬細胞可引起巨噬細胞活化并顯著刺激巨噬細胞GDF-15的分泌,進一步的免疫組化實驗發現,人類頸動脈粥樣硬化病灶中,GDF-15誘導的免疫反應定位于活化的巨噬細胞中并且與oxLDL、錳超氧化物歧化酶(MnSOD)、凋亡誘導因子(AIF)、細胞凋亡蛋白酶-3(CPP32)、PARP、c-Jun/AP-1和p53誘導的免疫反應同時共存,表明GDF-15可能參與動脈粥樣硬化病灶中巨噬細胞的凋亡及其炎癥反應的調節,從而發揮其在AS的保護作用。Eggers等采用直線相關分析方法分析GDF-15與多個心血管疾病標志物關系時發現,GDF-15與內皮細胞活化因子(E-選擇素、P選擇素、細胞問黏附分子-1、血管細胞黏附分子-1)、細胞外基質降解因子(基質金屬蛋白酶-9、基質金屬蛋白酶抑制劑-1)、凝血活性因子(血管性血友病因子、D二聚體)以及纖維蛋白溶解因子(纖溶酶原激活劑抑制劑-1和tPA抗原)具有相關性,表明GDF-15可能與內皮細胞激活以及血管壁的炎癥密切相關,GDF-15可能通過多種途徑參與AS的發生、發展過程。Preusch等在通過對低密度脂蛋白受體敲除的AS小鼠模型實驗研究中發現,GDF-15表達缺陷的老鼠表現為AS斑塊巨噬細胞聚集增強和AS斑塊不穩定性增加等特性,并且GDF-15缺陷的老鼠細胞黏附因子-1的表達量增加,表明GDF-15可能通過減少細胞黏附因子-1的分泌,減輕巨噬細胞聚集及其炎癥介質的釋放,從而達到緩解動脈粥樣硬化炎癥,抑制AS進一步發展、惡化的作用。
3.GDF-15與冠狀動脈粥樣硬化性心臟病
2002年,Brown等的研究發現,GDF-15是獨立于其他傳統心血管疾病危險因素的新風險因子,基礎GDF-15水平高的婦女發生心血管事件的概率比基礎GDF-15水平正常的婦女高(618 vs 538 pg/ml,P=0.0002),而且當GDF-15水平大于基礎水平90個百分點時,發生心血管疾病的概率增加2.7倍(95%CI 1.6-4.9,P=0.001)。Brown等的發現掀起了醫學研究人員對GDF-15在心血管領域研究的熱情,引起人們的廣泛關注。隨后,GDF-15與心腦血管系統疾病的相關性研究被大量研究報道,在冠心病的研究方面也取得了較大的進展。
GDF-15是預測心血管事件的良好指標。Wollert等學者在一個病例對照研究中發現,大約有2/3的非ST段抬高性急性冠脈綜合征(non-ST-seg-ment elevation acute coronary syndrome,NSTE-ACS)患者GDF-15水平高于正常水平上限(1200 ng/L),其中約1/3的病人GDF-15水平大于1800 ng/L,GDF-15水平在<1200 ng/L、1200-1800 ng/L和>1800 ng/L的患者一年內死亡的百分比分別為1.5%、5.0%和14.1%(P<0.001),GDF-15被認為是預測NSTE-ACS患者死亡風險的有效預后指標。Dominguez-Rodriguez等分別檢測入院時和36個月后NSTE-ACS患者血液中GDF-15和超敏C反應蛋白(hsCRP)的濃度,評估二者在預測主要不良心血管事件(major cardiovascular adverse events.MACE)的作用,結果發現GDF-15而不是hsCRP起到預測MACE發生的作用。此外,Dominguez-Ro-driguez等還研究了NSTE-ACS患者GDF-15與syntax評分的關系,經過兩年的隨訪發現,在這兩年中有20.5%的NSTE-ACS患者發生了MACE,而發生MACE的患者血液中GDF-15的濃度和syntax評分均高于未發生MACE的患者,表明在NSTE-ACS患者中,GDF-15水平與syntax評分相關且高水平GDF-15的NSTE-ACS患者兩年內MACE發生的概率增加。
GDF-15可應用于冠心病患者的危險分層中。Wollert等學者在對2079例NSTE-ACS患者兩年的隨訪研究中發現,770位NSTE-ACS患者GDF-15水平中度升高(1200-1800 ng/L),493位患者GDF-15水平明顯增高(>1800 ng/L),與采用介入治療組比較,保守治療組的病人升高的GDF-15水平是預測疾病復發和患者死亡復合終點風險的良好指標(P=0.016)。當GDF-15水平>1200 ng/L時,介入治療組的死亡復合終點減小,此時患者接受介入治療獲益,介入治療死亡風險較低。然而,當GDF-15水平<1200 ng/L或肌鈣蛋白T水平>0.01 ng/L時,患者接受介人治療時死亡風險增加。
4.GDF-15與缺血性腦卒中
缺血性腦卒中(Ischemic stroke,IS)是嚴重危害中老年人健康的常見腦血管疾病,占所有腦卒中比例的80%以上,是目前世界范圍導致人類死亡和殘疾的最常見病因。因此,深人開展IS的病因學研究,以推動IS防治仍然是目前醫學研究領域的重點問題。
目前,國內關于GDF-15與IS的相關性研究還比較少。盧昌均等報道,急性缺血性腦卒中組血清GDF-15水平顯著高于健康對照組,升高的GDF-15水平與美國國立衛生院(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NIH)的卒中量表評分呈正相關。經過3個月的隨訪盧昌均發現,急性缺血性腦卒中后殘疾患者血清GDF-15水平顯著高于急性非殘疾患者,表明急性缺血性腦卒中患者GDF-15的表達量明顯增加,可用于急性缺血性腦卒中的預后評估。
相對于國內學者,國外的相關性研究比較深入,取得了較大進展。Worthmann等在分析IS后血漿GDF-15水平與患者預后的關系時發現,在腦卒中發生后6小時,68%的IS患者血漿GDF-15水平升高(>1200 ng/L),GDF-15水平與血液循環中的IL-6、神經膠質S100蛋白、鈣結合蛋白B以及頸動脈內中膜厚度相關:與7-90天內量表評分0-1的IS患者比較,量表評分>1的IS患者具有更高的GDF-15水平,表明IS患者GDF-15水平升高,與IS患者的預后相關。Groschel等分別收集急性IS患者入院后6 h和24 h血液標本,研究急性IS患者血液GDF-15水平在判斷患者出現癥狀后90天功能預后的應用價值.以腦卒中后90天的量表評分(modified ranking scale,MRS)作為主要結局參照指標,經多元回歸分析發現,美國國立衛生研究院腦卒中量表評分(NIH-SS)[OR=1.269,95%CI:1.141-1.412,P<0.001]和GDF-15水平(OR=1.029,95CI:1.007-1.053,P=0.011)與MRS均呈MRS≥2的相關性,并且,GDF一15水平隨著NIH-SS分值的增高而升高,與NIH-SS呈現良好的相關性;此外,ROC曲線分析表明,在判斷不良腦卒中預后方面GDF-15水平與NIH-SS聯合應用[0.774(95%CI,0.717-0.832)]比GDF-15[0.629(95%CI,0.558-0.699)]比NIH-SS[0.753(95%C10.693-812)]單獨應用要精確得多。而Andersson等對3374位未患腦卒中的Framingham后裔進行隨訪研究,研究參與者血液GDF-15水平與隨訪期間腦卒中發生以及腦卒中后血管性腦損傷的關系,經過腦卒中傳統危險因素、B型利鈉肽、hsCRP和尿蛋白水平等指標調整后,GDF-15仍與參與者低腦容量和差的行為測試表現相關,表明GDF-15與參與者亞臨床腦損傷以及認知障礙相關。
5.總結與展望
綜上所述,GDF-15是一種具有豐富生物學特性的細胞因子,多種因素可以刺激GDF-15的分泌。GDF-15可能通過抑制黏附因子的分泌、抑制巨噬細胞聚集、減輕動脈粥樣硬化病灶的炎癥反應以及調理內皮細胞炎癥等多種途徑參與動脈粥樣硬化相關疾病的發生和發展過程,在心腦血管疾病的發病中起著保護作用。GDF-15可作為多種心腦血管疾病標志物,在不同類型冠心病的診斷、危險分層和疾病預后判斷以及缺血性腦卒中的診斷、風險評估等均具有極高的應用價值和發展前景,有望將其應用于心腦血管疾病的藥物開發研究。但是,目前要將GDF-15應用于臨床仍存在諸多問題,GDF-15作用的具體機制和通路的相關性研究還較少,不能有針對性地作用于問題的根源,而且相關成果還處在論證階段,目前沒有統一的國際規范,仍需要大家共同努力。隨著科學技術的不斷發展和研究的不斷深人,我們必將對GDF-15的生物學特性、發揮作用的信號通路以及致病機制有更全面而深入的了解,最終將GDF-15應用于心腦血管疾病的診療和藥物開發中,給心腦血管疾病患者帶來福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