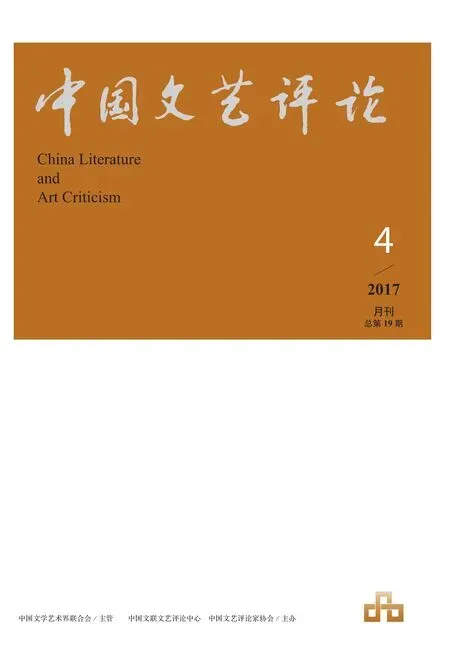由中國古典美學探尋文藝評論的根脈與未來
——訪美學家劉綱紀
采訪人:劉耕 王海龍
由中國古典美學探尋文藝評論的根脈與未來——訪美學家劉綱紀
采訪人:劉耕 王海龍

劉綱紀簡介 哲學家、美學家和美術史論家。現為武漢大學人文社會科學資深教授、博士研究生導師,并入選中共湖北省委命名表彰的首批“荊楚社科名家”,任中華美學學會顧問、國際易學研究會顧問、湖北省美學學會名譽會長。1960年出版了個人第一部專著《“六法”初步研究》,引起了很大反響。著有《美學與哲學》《藝術哲學》《美學對話》《傳統文化、哲學與美學》《中國書畫、美術與美學》等多本哲學美學專著。所著《中國美學史》(一、二卷),填補了中國很長時期以來沒有一部系統的中國美學史的空白。著有《書法美學簡論》《龔賢》《黃慎》《劉勰》《文征明》等多本書畫理論專著,2008年被中國美術家協會授予“卓有成就的美術史論家”稱號。主編多種著作、叢刊,如《王朝聞文藝論集》(共三卷)《美學述林》《中西美學藝術比較》《現代西方美學》《鄧以蜇美術文集》《馬克思主義美學研究》(年刊)等。參編《〈實踐論〉〈人的正確思想是從那里來的?〉解說》《〈矛盾論〉解說》《美學概論》(王朝聞主編)《中國大百科全書·哲學卷》《中國大百科全書·美術卷》《中國儒學百科全書》等。所著《書法美學簡論》榮獲中南五省優秀教育讀物一等獎,《中國美學史》第一卷,榮獲湖北省社會科學優秀成果獎一等獎;《〈周易〉美學》榮獲教育部全國高校人文社科優秀成果二等獎。
一、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和美學是文藝評論的根本原則
劉耕、王海龍(以下簡稱:劉、王):
先生您好!受《中國文藝評論》雜志委托,我們為您作一次專訪。您是我國著名的美學家,能否先請您談一談文藝評論與美學的關系?劉綱紀(以下簡稱劉):
這個問題很重要,十分值得研究。我感到,習近平總書記在文藝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中,已對文藝評論的重要作用,它和文藝理論、美學的關系作了全面深入的說明。因此,我想依據我學習這個講話的體會,回答一下您提出的問題。要回答這個問題,我們首先應該明確文藝評論的功能與任務。我認為文藝評論肩負著兩個相互聯系的任務。首先要推動我們的文藝家創作出能夠傳播當代中國價值觀、體現中國文化精神,反映中國人審美追求,思想性、藝術性、觀賞性有機統一的優秀作品,并及時發現和向群眾推薦這樣的作品;其次,還要通過評論,有充分說服力地講出這些作品的優點、美點在哪里,不斷提高廣大群眾對文藝的欣賞能力,其中也包含對古代、外國優秀文藝作品的欣賞能力。此外,對于一切有害于人民的作品,要敢于鮮明表態,作出有充分說服力的批評。
馬克思主義的文藝理論與美學是文藝評論的根本指導原則。在文藝評論中,每個評論家都是依據他所認同的某種文藝觀、美學觀去評論他所要評論的作品的,不論他自己是否明確地意識到或者是否承認這一點。所以,我很贊同俄國19世紀的革命民主主義者別林斯基的觀點,他把文藝評論叫做“運動中的美學”。但是,從古至今的文藝觀、美學觀是各式各樣的。其中,只有產生于19世紀40年代的馬克思主義,才第一次把對文藝和美學的認識變成了一門科學。因此,只有堅持以馬克思主義的文藝觀、美學觀為指導,我們才能以同實踐相符合的,歷史的、人民的、藝術的、美學的觀點去評判鑒賞各種各樣的作品,得出符合時代發展要求的,正確深刻的論斷。當然,在特定的條件下,歷史上的某些非馬克思主義的文藝觀、美學觀也有它的進步性,但又有歷史局限性,如18世紀法國啟蒙主義的文藝觀、美學觀就是這樣。當時的啟蒙主義者們不僅進行文藝創作,還寫過與文藝評論相關的著作,如狄德羅寫的《論繪畫》(1765)、《論戲劇詩》(1758)。他把文藝看作是反對封建貴族的有力武器,主張文藝家要關心社會問題,擔負起教育人民的任務。為此,他還主張文藝家要到鄉村的茅屋里去仔細觀察人民的生活。馬克思、恩格斯都曾給予狄德羅高度的評價。但即使像狄德羅這樣激進的啟蒙主義者,也還認識不到馬克思主義所說人民群眾是歷史的創造者這一偉大真理,反而把社會進步的希望寄托在領導反封建革命的新興資產階級身上。馬克思、恩格斯的劃時代的貢獻就在于他們既繼承了啟蒙主義,又超越了啟蒙主義,提出只有通過全世界聯合起來的無產階級的斗爭,最終實現科學社會主義、共產主義,廣大人民群眾才能得到真正徹底的解放。因此,馬克思主義的文藝觀、美學觀從它產生的第一天開始,就是和科學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的實現不可分離地聯系在一起的。離開了它,就不會有馬克思主義的文藝觀、美學觀。當今,文藝的發展是和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弘揚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實現“兩個一百年”的奮斗目標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分不開的。它將帶來中國文藝空前的繁榮,并使中國文藝在當代世界文藝的發展中占有不可取代的重要地位。
劉、王:
將馬克思主義的文藝理論與美學作為文藝評論的根本原則,具體應當怎樣理解并體現在文藝研究和評論中呢?劉:
我認為,當前最重要的是在馬克思主義指導下,繼承創新中國古代文藝評論,這就要求我們對中國古代文藝評論進行細致、系統的梳理,首先要認識到中華美學的獨特性。我認為世界古代美學有三大系統:中國美學、希臘美學、印度美學。其他文明古國,例如埃及,雖然在文藝上有不可否認的貢獻,但除了中國、希臘、印度之外,沒有任何一個國家有關于文藝與美學的著作流傳到后世,并在世界范圍內產生顯著影響。就三大美學系統而言,中國美學不僅在產生的時間上早于希臘和印度,而且在思想的合理性與深刻性上也有超越希臘、印度的地方。但直到現在,由于西方至上主義的存在,也就是習近平總書記作了生動概括的“以洋為尊”“以洋為美”“唯洋是從”的思想的存在,使一些人看不到中國古代美學所作出的重要貢獻,而把發端于古希臘的西方美學放在最高位置。2015年10月14日,《參考消息》曾登了一篇譯自英國《衛報》網站的文章。文章對秦始皇時期的大型陶塑兵馬俑持肯定態度,但又說它是在希臘雕塑家的幫助和指導下完成的。這是極其荒誕的無稽之談。首先,從藝術上說,古希臘的雕塑是石雕,在表現男性時都是裸體的,目的是為了表現男性身體的強壯,身體再高也不及真人一樣高;而兵馬俑是陶塑,每個人都穿上了戰士所穿的盔甲,與真人一樣高,目的是要表現秦國自商鞅變法之后培養出來的許多質樸、勤勞、英勇的“耕戰之士”。這說明古希臘再好的雕塑家都不可能指導兵馬俑的創作。其次,在中國史籍中,從未有秦始皇時期希臘人曾到過中國的記載。即使有DNA鑒定說明那時曾有歐洲人到過中國,也不能證明到來的人必定是希臘人,而且還正好是一位雕塑家。秦始皇時代面臨國內種種緊急的問題需要處理,他沒有必要也不可能去和他一無所知的希臘人交往。實際上,中國和歐洲的交往,始于漢代絲綢之路開通后,與羅馬帝國(當時中國人稱之為“大秦國”或“海西國”)在商業上的交往。如果說古希臘雕塑在東方也曾發生了影響,那決不是對中國兵馬俑制作的影響,而是對印度雕塑的影響。只要把印度雕塑和希臘雕塑一加比較,就可以發現兩者的相似之處是很明顯的。原因很簡單,公元前327年,馬其頓時代的希臘人入侵和占領了印度河流域的上游地區,把古希臘文化帶到了印度。直至公元前317年,馬其頓的希臘駐軍全部撤離印度。除希臘人外,曾入侵和占領印度某些地區的還有屬于印歐語系的印度·雅利安人(后成為古印度的主要居民)、波斯人、安息人、塞種人、大月氏人。因此,曾有人認為上古時代的印度好像是一個“人種博物館”。當然,從文化上看,古印度也有自己的文化,這就是以婆羅門教的教義及其后釋迦牟尼在反婆羅門教過程中創始的以佛教教義為中心的文化。但這種文化又深受希臘文化的影響,就像前面所指出的,印度的宗教雕塑就深受希臘雕塑的影響。再如婆羅門教所講的諸神類似于希臘人信仰的眾神,因此馬克思說,從印度“婆羅門身上我們可以看到希臘人的原型”。印度古代著名的史詩《摩訶婆羅多》與希臘荷馬史詩《伊利亞特》也很相似,被馬克思稱為“印度的《伊利亞特》”。

《藝術哲學》
反觀中國,比印度歷史更早的中國古代文化的發展與印度古文化的發展有根本性的不同。它是在沒有遭受任何外族入侵占領的情況下獨立地發展起來的,這就形成了中華民族所特有的“中國文化基因”和與之密切相聯的“中華審美風范”,并取得了為古希臘、古印度所不及的更高成就。深入研究“中國文化基因”和“中華審美風范”,對我們今天繼承創新中國古代的文藝評論,具有十分重大的意義。但這種研究,涉及到和中國古代社會發展相關的種種復雜問題,這里暫時略而不談。
劉、王:
那么,中國的文藝評論的傳統是如何在歷史中形成的呢?劉:
文藝評論的發展與文藝的發展分不開,而中國文藝的發展又與上古時代“樂”的發展分不開。這里所說的“樂”,不僅包含聲樂和聲樂的唱詞詩歌,還包含古代的各種樂器,其中最重要的又是中國古代特有的打擊樂器的伴奏。在伴奏下演唱的同時,還有舞蹈表演,舞又分為文舞與武舞兩大類。這種“樂”,可以說是中國古代的一種綜合性的藝術,演出的場面十分壯觀。它是在國家舉行祭祀天地、先祖和慶功的隆重典禮上演出的,目的是為了激發君主統領下的百官、臣民對國家的熱愛和自豪感。據《書經》記載,至遲在虞舜的時代(我推斷為公元前2030年至2069年)就曾舉行了一次十分成功的演出,并由舜所委任的樂官夔專門管理此事。舜之后,到了夏、商、周三代,在舉行重大的祭祀典禮時,都各有代表自己國家的“樂”的演出。正因為中國古代文藝的發展離不開“樂”的創作與演出,所以中國古代文藝評論最初的發展,是與后世對“樂”的評論分不開的。如《左傳》記載了季札“觀于周樂”,不斷用“美哉”來形容他對“周樂”(包含歌與舞)的感受。但這還只表達了季札對《周樂》的感受,缺乏更深入的評論。季札之后,同樣是生活于春秋時代的孔子,把對古“樂”的評論大大向前推進了一步。孔子注意吸取了《老子》一書提出的“味”的概念。老子談到“道”時說:“道之出口,淡乎其無味”,但他又認為只有這種“味”才真正值得品嘗,因此又提出了“味無味”的說法。老子的這種說法并不是針對文藝而提出的,但我們可以看到,不僅孔子在講到古樂的美時使用了“味”這一概念,而且在后世的中國文藝評論中還成了一個占據中心地位的概念。這不僅因為中國古代很早就講到了“五味”“五色”“五聲”的美,而且還因為文藝評論是同評論者對作品的美的品味欣賞分不開的。《老子》一書雖然一開始就對“五味”“五色”“五聲”的美統統予以否定,但在使人深入體驗領會他所說的“道”這個意義上,又仍然保留了“味”這個概念。孔子在講到他對古樂之美的看法時使用了這個概念,也與孔子認為對古樂之美的欣賞與品味有關。此外,孔子對季札連聲不斷地贊美的《周樂》是有保留意見的。《論語》中記載說:“子在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圖為樂之至于斯也。”“三月不知肉味”,是說三個月中吃起肉來也感到沒有什么味道了。“不圖為樂之至于斯也”,是說想不到對《韶》樂的欣賞引起的快樂會這么大,也就是一種超越了滿足口腹之欲的“肉味”引起的生理感官上的愉快,即一種審美上的精神的快樂。由此還可以見出,孔子借用了老子所說的“味”的概念,既與他認為對古樂之美的欣賞和品味有關,也與孔子主張的治國之道有關。因為在孔子的思想中,“藝”是不能脫離“道”的。反觀老子所說的“味無味”,也不只是指對食物的“味”的品嘗,而是指體驗把握老子的治國之道。但孔子的治國之道不同于老子的“無為而治”,孔子高度推崇的是古代的堯、舜之治。《韶》樂之所以引起了孔子極大的快樂,就因為它是舜時期的樂。由于孔子認為古樂的美和古代帝王的治國之道相關,因此孔子又曾將舜代的《韶》樂和周代的《武》樂加以比較,認為“《韶》,盡美矣,又盡善也”;“《武》,盡美矣,未盡善也”。這是因為在孔子看來,舜是由于堯授位而得天下的,周卻是通過武力征伐而得天下的,所以前者要高于后者,從而舜的《韶》樂也要高于周的《武》樂。但從文藝評論的觀點來看,重要的不在孔子對《韶》樂與《武》樂的比較,而在他區分了“美”與“善”,提出了樂既要“盡美”,又要“盡善”的思想。與此同時,由于古代的樂是一種綜合性的藝術,因此也可以說孔子認為各門藝術的創造都既要“盡美”又要“盡善”。這是一個極為重要的思想,它對后世文藝的創作、欣賞與評論產生了十分深遠的影響。另外,還要看到,孔子說周的《武》樂“盡美矣,未盡善也”,這不是說周代的樂只有“美”,沒有“善”,而是說在“善”的方面尚未達到應有的高度。因此,孔子對周代的文化仍然持充分肯定的態度,并說:“郁郁乎文哉,吾從周。”孔子編《詩經》,選入的詩絕大部分是周代的詩,只有少數幾首屬于商代,這也證明了孔子對周代文化是充分肯定的。實際上,生活在春秋時代的孔子完全知道要返回他向往的堯舜時代去已不可能,他只能立足于西周去實現他的理想。所以,后世把孔子的思想概括為“祖述堯、舜,憲章文、武”(指周文王與周武王),這種說法符合孔子思想。
孔子不僅區分了“美”與“善”,并指出兩者必須統一起來,而且還講到了真的問題。在孔子的思想中,最高的善就是“仁”,“仁”的完滿實現就是美,而“仁”的實現又離不開“知”,即人對外部世界(包含自然與社會)的認識。孔子曾兩次講到“未知,焉得仁”。在“知”的問題上,孔子曾教導他的學生子路說:“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是知也。”在孔子講到他自己時,他又曾說過:“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又說:“蓋有不知而作之者,我無是也。”由此可見,對于孔子來說,對外部世界的真知是實現他所說的最高的善——“仁”的根本,從而也是實現由“仁”而來的美的根本。因此,真、善、美在孔子的思想中是相互統一而不可分離的。習近平總書記說:“追求真善美是文藝的永恒價值。”從全世界古代思想和美學的發展來看,文藝的永恒價值與真善美不能分離,這是從中國古代的思想家孔子開始的。
孔子的思想為后世的文藝評論奠定了基礎。孔子之后,我國古代文藝評論又經歷了漫長的發展過程。為了繼承發揚我國古代文藝評論的優秀傳統,我認為需要在馬克思主義哲學、美學的指導下寫出一部中國古代文藝評論發展史,并且堅持從中國的歷史實際出發,去除一切將馬克思主義簡單化、教條化、公式化的做法。在這里,我只能就和文藝評論發展相關的幾個重要問題,概略地說一下我國古代文藝評論在解決這些問題上,直至今天仍然值得我們借鑒學習的地方。這些問題,總的來看又可以概括為文藝評論與文藝的社會功能的關系、文藝評論與文藝創作的關系、文藝評論與文藝欣賞的關系等三個問題。在這三個問題上,我國古代文藝評論為我們留下了至今仍值得仔細深入研究的寶貴遺產,而且就是放到世界古代文藝評論發展史上去看,也有不可否認的重要價值。
二、文藝評論應為“經國大業”
劉、王:
在先生看來,我國古代文藝評論是如何處理文藝評論與文藝的社會功能之間的關系的?劉:
不論古今中外,文藝評論家對文藝作品的評論都和他對文藝的社會功能的看法分不開,這種看法又和他對美與藝術的看法分不開。凡是他認為成功地實現了文藝的社會功能的作品,就予以充分的肯定;反之,則加以批判和否定。孔子通過對上古時期綜合性的文藝——“樂”的分析得出了文藝既要“盡美”,又要“盡善”的結論,同樣是因為只有這樣作品才符合孔子所說“興于詩,立于禮,成于樂”的治國理念,從而對國家的治理具有最佳的社會功能。但在孔子的時代,文藝評論還不可能得到充分獨立的發展。到了西漢初年,由于“賦”這種文體獲得了空前迅速的發展,而戰國時代楚國屈原所寫的“賦”又被絕大多數人公認為是最成功的,于是就在《史記》的作者司馬遷和《漢書》的作者班固之間,引起了一場如何評價屈原的“賦”和看待“賦”的寫作的激烈爭論。從中國古代文藝評論的發展史來看,這也是第一次圍繞著如何評價歷史上一個極負盛名的作家而展開的爭論。爭論中的分歧集中到一點,就是“賦”的寫作要怎樣才能有利于君主對國家的治理。生活在春秋時代的孔子還不知道“賦”,只知道“詩”與“樂”,但他已提出了“詩”與“樂”都要符合“禮”才能有助于君主對國家的治理,這就是孔子對文藝的社會功能的根本看法。漢代關于“賦”的爭論,本質上就是漢賦大為興盛之后,對“賦”這種新興的文體的社會功能的爭論,它是不能脫離孔子對文藝的社會功能的根本看法的。
《中國書畫、美術與美學》
司馬遷在《史記·屈原賈生列傳》中,極為熱烈地贊美了屈原的偉大精神,指出他是一個“正道直行,竭忠盡智以事其君”的人。雖然他因楚懷王的臣下向楚懷王進讒言而被疏遠,最后又被流放,但他仍然不改為國效力的初衷。司馬遷說:“推此志也,雖與日月爭光可也。”為了充分說明這一點,司馬遷還全文轉載了屈原所寫的《懷沙》賦,說明屈原被懷王流放后,顏色憔悴,行吟江畔,哀怨萬端,最后抱著石頭投汨羅江而死。接著又說屈原死后,楚國的宋玉、唐勒、景差等人雖然也善于辭賦,但無人“敢直諫”,結果是“楚日以削,數十年竟為秦所滅”。
和司馬遷對屈原的看法根本相反,班固在他所寫的《離騷序》中認為司馬遷對屈原的種種贊美都是夸大之詞。在他看來,屈原實際上是一個不知“明哲保身”,只求“露才揚己”的人,“非明智之器”,雖然他也不能不承認屈原有作賦的“妙才”。班固對屈原的這種看法是十足的誤判,根本不能成立。但是,不論班固無端給屈原加上了多少罪名,他否定屈原的重要原因,仍然與他對“賦”這種文體寫作的社會功能的看法分不開。班固在《兩都賦序》中對漢賦的發展大為稱贊,指出“奏御者千有余篇,而后大漢文章炳焉與三代同風”。但在他看來,“賦”的作用在于“或以抒下情而通諷諭,或以宣上德而盡忠孝。雍容揄揚,著于后嗣”。而屈原的“賦”卻根本不符合于班固提出的標準。如司馬遷所言,他“敢直諫”,在賦中毫無顧忌地批評楚懷王及其臣下的不智與無能,這就成了班固所不能容忍的冒犯圣上,“露才揚己”的表現了。司馬遷與班固之間展開的關于“賦”的爭論,還一直延續到東漢初年。在歷史上第一個寫了《楚辭章句》的王逸在《楚辭章句序》中直接批評了班固認為屈原“露才揚己”是根本不對的。他說:“且人臣之義,以忠正為高,以伏節為賢。故有危言以存國,殺身以成仁。”相反,“若夫懷道而迷國,詳愚而不言,顛則不能扶,危則不能安,婉娩以順上,逡巡以避患,雖保黃耇,終壽百年,蓋志士之所恥,愚夫之所賤也。”這些話很好地說出了屈原的《離騷》等賦的可貴之處。此外,他還引了見于《詩·大雅·抑》中的“嗚呼小子,未知臧否”“匪面命之,言提其耳”等語,以證明“屈原之詞,優游婉順,寧以其君不智之故,欲提攜其耳乎?”因此,班固認為屈原“露才揚己,怨刺其上”的說法是完全錯誤的,不能成立的。總起來看,王逸的《楚辭章句序》有力地肯定了屈原的偉大貢獻,批駁了班固的謬說,對西漢以來關于楚辭的討論作了一個不錯的總結。
但是,我們要從兩個相互聯系的方面來估價這次討論所取得的成果。一方面,這次討論大為加深了我們對屈原的“賦”的價值的認識,并且充分證明了人們對某個文學家的評價與其對文學社會功能的認識分不開。以王逸來說,如果他不充分肯定屈原具有忠貞報國的精神,他能對屈原的“賦”的價值作出有力的論證,并徹底駁倒班固強加在屈原身上的謬說嗎?當然不能。另一方面,我們又要看到這次討論雖然取得了不可否認的成績,但終究又只局限于對“賦”這種文體的認識。沖破這一局限,從中國自古以來的“文章”出發,全面認識文藝的社會功能,展開對文藝評論的看法,這是東漢末年出現的建安文學理論開始的。
從曹丕立為太子開始直至建安二十五年曹操去世,迎來了中國文學史上一個前所未見的新時期,即“建安文學”發展時期,而曹丕就是推動建安文學發展的領導人。為了推動建安文學的發展,曹丕寫下了我國古代文藝評論史上第一篇篇幅最長而又很有系統性的文章:《典論·論文》,從下述幾個方面有力地推動了我國古代文藝評論的發展。
第一,從文藝的社會功能來看,曹丕第一次指出了:“蓋文章,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盡管在曹丕之前,孔子在《論語》中熱烈贊頌堯治國的業績時也曾說過:“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煥乎,其有文章”這樣的話,但極為明確和直截了當地把“文章”看作是“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卻是始于曹丕的。其所以如此,又是因為建安文學的奠基人曹操寫詩,始終是和抒發他的“起義兵,為天下除暴亂”的壯志豪情聯系在一起。在曹操的影響和教育下,不但寫詩而且還寫賦的曹丕和曹植,特別是從小就跟隨曹操南征北戰的曹丕,也同樣是把詩賦的寫作和他們的父親曹操平定北方的斗爭聯系在一起的。因此,在曹丕看來,包含詩賦的寫作在內的各種“文章”,都是和“經國之大業”,即治國之大業不能分離的,不可能設想有什么“文章”可以脫離“經國之大業”而存在。為此,曹丕一再勉勵建安時代的文人們要懂得“年壽有時而盡,榮樂止乎其身,未若文章之無窮”的道理。愛惜光陰,抓緊時間,努力寫出有助于“經國之大業”完成的好文章,這樣就能使自己的文章流傳于后世而獲得不朽的名聲。相反,如果只關注如何解決與自己的“饑寒”與“富貴”有關的“目前之務”,拋棄了有“千載之功”的文章的寫作,其結果只能是“日月逝于上,體貌衰于下,忽然與萬物遷化,斯志士之大痛也”。這也就是曹丕何以把文章既看作是“經國之大業”,又看作是“不朽之盛事”的根本原因。這兩個方面是互相聯系在一起的,但前者是從“文章”和“經國之大業”的關系來看的,后者則是從深知“文章”對完成“經國之大業”的重要性,在自己短暫有限的一生中,寫出有助于“經國之大業”完成的好文章,使自己生存的意義與價值獲得最高肯定的文人而言的。在曹丕看來,他們也是一些愛國的志士仁人。今天看來,曹丕上述看法最值得我們肯定的地方,就是他第一次明確地把“文章”的寫作和國家的強盛聯系起來,體現了在中國古代建安文學發展過程中產生的一種真摯熱烈的愛國主義精神。中國自古以來全部文學史已充分證明了凡是能在歷史上流傳的不朽的作品,都是在藝術上成功地表現了中華民族百折不撓的愛國主義精神的作品。這其中也包含了建安文學最重要的代表人物曹操、曹丕、曹植的作品。
曹丕的《典論·論文》的第二個貢獻在于他第一次對中國自古以來所說的“文章”作出了具體的分析。最早見于中國古籍中的“文章”一詞,從詞源學上考證起來是和線條、花紋、色彩的美分不開的,而且這種美的感受最初又是和人們對動物的皮毛、花紋、色彩的美的感受分不開的。直到孔子的時代,孔子所說的與君子應有的“質”相對應的“文”也有美的含義,主張“文”與“質”要恰到好處地統一起來,避免“文”勝于“質”或“質”勝于“文”。這就是孔子所說的“文質彬彬,然后君子”。但在許多情況下,古代所說的“文章”一詞又指用文字寫成的各種典籍著作,曹丕就是在這個意義上使用“文章”一詞的。為了把能給人以審美感受的文學作品從古代典籍中區分出來,曹丕提出了“文本同而末異”的觀點。“本同”指一切“文章”都是“經國之大業”,“末異”指不同的文體有不同的特征、功能和作用。曹丕把自古以來的文體分為“四科”,并指出“奏議宜雅,書論宜理,銘誄尚實,詩賦欲麗”。前三種文體都是政治性、應用性、說理性的文體,這里略而不談。最重要的是曹丕講到第四種文體——詩賦時,斬釘截鐵地說“詩賦欲麗”,肯定了詩賦的根本特征在于它能引起人們的審美感受。這是一個十分重要的觀點。曹丕之所以能提出這樣的觀點,首先是因為他認為他所說的廣義的“文章”是“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即要能推動人們為建設一個強盛的國家而奮斗。而包含在他所說的“文章”中的“詩賦”這一體裁,由于具有美麗的文采,因此也正好具有從情感上推動人們為建設一個強盛的國家而奮斗的力量。其次,和這一看法相關聯,曹操寫詩和曹丕、曹植寫詩與賦又已受到漢代的樂府詩和東漢末年產生的《古詩十九首》的強烈影響。它是和東漢末年與國家興衰密切相關的個人的種種遭遇直接聯系在一起的,具有強烈的抒情性,而沒有生硬地說教。在詩體上又產生了與《詩經》的四言詩不同的五言詩,在情感的抒發上就更為自由。正是在上述種種情況下,曹丕直截了當地提出了“詩賦欲麗”這一要求,從我們今天看來,不論曹操所寫的詩或是曹丕、曹植所寫的詩和賦,都符合這一要求。以曹操所寫的《短歌行》一詩為例,它學的是《詩經》的四言詩的寫法。詩中曹操深感人生苦短,并為他在統一北方的斗爭中碰到的種種困難而感慨萬分。“月明星稀,烏鵲南飛。繞樹三匝(“三匝”即“三圈”),何枝可依”?但最后仍不失去信心,堅信“山不厭高,水不厭深,周公吐哺,天下歸心”。這正是一首極富抒情性,寫得悲而能壯氣勢磅礴的好詩。它不僅符合曹丕所說的“詩賦欲麗”的要求,而且還“麗”而能“壯”,這也正是曹操詩作的一大特點。
從歷史上看,雖然在班固所著的《漢書·藝文志》中已把詩賦與古代其他典籍分開,列為一類,但從班固對《藝文志》的說明來看,他還遠未達到曹丕所說的“詩賦欲麗”的觀點。班固首先講到詩,最終把詩的作用歸結為“別賢不肖而觀盛衰”,不提詩也有它的美。接著又講到賦,說從荀子以至“楚臣屈原離讒憂國,皆作賦以諷,咸惻隱古詩之義”,但從屈原之后楚國的宋玉、唐勒開始,直至漢代的枚乘、司馬相如以及揚雄,又“競為侈麗閎衍致辭,沒其諷喻之義。是以揚子悔之曰:詩人之賦麗以則,辭人之賦麗以淫,如孔氏之門用賦也,則賈誼升堂,相如入室矣,如其不用何”。這樣一來,又把孔子之后產生的賦這種新興文體的美否定了。最后,班固又講到漢武帝時采集的“樂府”詩,認為它“皆感于哀樂,緣事而發,可以觀風俗,知厚薄”。這是對的,但班固完全不提“樂府”詩特有的美以及它對后世中國文學發展產生的重要影響。總體來看,在班固的思想中,詩賦的倫理道德教育作用和詩賦的美是相互對立而無法統一的。曹丕則不同,他提出“詩賦欲麗”恰好同他肯定“文章”是“經國之大業”分不開的,兩者完全能夠而且必須統一在一起。最后還要說一下,班固在《藝文志》中對屈原的賦基本上是持肯定態度的,但到了他后來所寫的《離騷序》中,卻對屈原的賦作了根本否定的猛烈的批判。

《傳統文化、哲學與美學》
三、提高社會大眾的欣賞水平是文藝評論的重要任務
劉、王:
先生從漢代初年圍繞對屈原的“賦”的爭論一直講到曹丕的《典論·論文》,生動地說明中國古代評論的優秀傳統之一就是把文藝評論和文藝的社會功能緊密地結合在一起,那么,中國古代文藝評論又是如何處理與文藝創作、文藝欣賞之間的關系呢?劉:
到了曹丕,把“文章”看作是“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這可以說是對文藝的社會功能的最高概括,具有劃時代的重大意義。而且曹丕在闡明他的這一看法怎樣才能得到實現時,又已經深入到了和文藝的創造、欣賞相關的種種問題之中,取得了不少重要成果。但他之所以能取得這些成果,仍然又是和他把文藝的社會功能提到了“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的高度分不開的。下面我想再從文藝評論與文藝創作及文藝欣賞這兩個角度,概略地說一下中國古代文藝評論所作出的貢獻,因為曹丕盡管已涉及了這兩個方面的問題,但還未對這兩個問題分別作出專門的探討。沒有文藝創作就不會有文藝評論,而且文藝評論的一個重要任務就是要推動文藝創作的發展。正因為如此,如果文藝評論家對文藝創作的基本規律一無所知,他就不可能完成這一重要任務。在我國歷史上,分門別類地研究各門類文藝的創作規律的著作非常之多,堪稱洋洋大觀。無論從事哪一個部門的文藝評論的人都需要了解各門文藝創造的最普遍的規律。從這個角度來看,我認為劉勰的《文心雕龍》是最值得注意的一本著作。盡管它所討論的只是文學問題,而且還是把各種政治性、說理性、應用性的文體都包含在內的廣義的文學,但由于它經常能從寬廣的中國哲學的高度去觀察思考問題,這就使得這部本來是討論廣義的文學的書提出了不僅限于文學,而且還可以通于其他各門文藝創造的普遍原理。其中最為重要的又是兩大問題,一個是“文”與“道”的關系問題,另一個是文藝的發展變化問題。從“文”與“道”的關系來看,劉勰依據《周易》“一陰一陽之謂道”的理論,得出了“道”是推動整個世界萬物產生發展的最根本普遍的原理,同時“道”又產生了在自然和人類社會生活中都有美的意義與價值的“天文”與“人文”。這樣,“道”與“文”在最高的“形而上”的層面和直接訴諸人們感官的“形而下”的層面都是不能分離而統一在一起的。由此劉勰又提出了“觀天文以極變,察人文以成化”,然后能“彪炳辭義”的說法,并指出“道沿圣以垂文,圣因文而明道”,“辭之所以能鼓天下者,乃道之文也”。正因這樣,文學家們才能“雕琢情性,組織辭令”,創作出能“寫天地之輝光,曉生民之耳目”的偉大作品。今天來看,劉勰所說“道”與“文”的不可分離的統一,相當于文藝的思想性與藝術性的統一。這是一切優秀的文藝作品的根本特征。用思想性來否定藝術性,或用藝術性來否定思想性都是錯誤的。宋代的理學家重“道”輕“文”,用“道”來否定“文”,把“文”看作是用來說理的工具,甚至宣稱“作文害道”,這是根本錯誤的。但它終究不可能取消“文”,阻擋文藝的發展,所以這種理論在宋代嚴羽所著的《滄浪詩話》中遭到了有力的批判。在文藝的發展變化的問題上,劉勰也提出了有價值的理論。他把《周易》的“系辭”所說的“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的理論運用到了文藝創作上,認為文藝的發展變化是永無止境的。如果有的文藝家認為文藝已到了再也不能變化創新的地步,那并不是因為事情真的如此,而是因為他們“通變之術疏”,即缺乏創新的能力。因此,劉勰鼓勵文學家要明白“文律運周,日新其業”的道理,“趨時必果,乘機無怯。望今制奇,參古定法”。這在當時是一種難能可貴的正確看法。
文藝作品要在社會生活中發生作用,只有當它能為人們所欣賞時才有可能。因此,如何不斷提高廣大群眾的文藝欣賞水平,是文藝評論的一個不能忽視的重要任務。文藝批評家盧那察爾斯基曾說過:“批評家是美的博物館的導游者”,這話是對的。從這方面來看,在我國古代齊梁時期出現的一系列和文藝的欣賞品評相關的著作非常值得我們仔細深入地加以研究。齊梁時期,由于門閥士族的地位趨于下降,寒門庶族的地位上升,再加上社會相對穩定,因此許多出身庶族的文人紛紛參與各門文藝的創作,由此又引出了如何欣賞各門文藝作品和判別不同文藝家作品的優劣高下的問題。在這種情況下,各門文藝都出現以“品”為名的著作。按先后次序而言,如南齊謝赫的《畫品》,梁代庾肩吾的《書品》,鐘嶸的《詩品》。這里的“品”包含兩重相互聯系的意思,一是要對不同文藝家進行品味欣賞,二是要通過這種品味欣賞劃分出不同文藝家的作品的優劣高下的等級品第。這種劃分又采取了兩種不同的方法,一是按政治上的“九品論人”的方法來劃分,即把人劃分為上、中、下三品,每品又再細分為上、中、下三品,合起來就是九品。庾肩吾的《書品》,鐘嶸的《詩品》都是采取這種劃分方法的。謝赫的《畫品》則有所不同,由于他提“六法”作為評定畫家優劣的標準,所以只分為六品。所有這些品評又都深受劉宋時期劉義慶所著記述魏晉“人物品藻”的《世說新語》一書的影響,能用簡明生動的語言,說出不同文藝家作品的個性風格。在這一時期,老子提出的“味”的概念成了文藝欣賞評論的中心概念。如鐘嶸在《詩品序》中說,好的詩要能使“味之者無極,聞之者動心”,不取“理過其辭,淡乎寡味”的作品。這里所說“味之者”指的就是詩的欣賞者,如果他能恰切地把握住不同的詩人的作品特有的“味”,那他就是一個對詩有很高欣賞水平的人了。這個“味”不僅適用于詩的欣賞,也適用于對書法、繪畫的欣賞。上述這種對作品的優劣高下品第的劃分還有一個很值得注意的地方,那就是對列入下品的文藝家也要講出他有什么優點,不是簡單地加以否定。這是一種有包容性的公正的做法,直至現在也值得我們參考借鑒,避免那種認為好就是絕對的好,壞就是絕對的壞的簡單化的看法。中國自古以來就有對人不應“求全責備”的說法,這也很充分地表現在齊梁時期的文藝評論中。此外,由于評論者必然要受到個人的知識、文化素養、審美愛好、時代條件的限制,因此不可能要求齊梁時期的文藝評論對不同文藝家的作品的優劣高下等級的判定都是完全正確的。如鐘嶸在《詩品》中評論到建安文學時,把曹植列為上品,曹丕列為中品,曹操列為下品,這顯然是不對的。但他對列為下品的曹操寫下了一句評語:“曹公古直,甚有悲涼之句。”這說明了鐘嶸對詩的欣賞感受能力還是很敏銳的,只不過他還看不到他所說的“古直悲涼”正好是同曹操的詩具有真切、誠摯、悲壯的特色密切相關的,特別是在悲壯這一點上,是曹植、曹丕的詩所不能及的。
四、汲取古人智慧,培養文藝評論領軍人才
劉、王:
您從文藝評論與文藝的功能、文藝創作、文藝欣賞三者的關系角度,梳理了中國古代文藝評論的發展脈絡及其重要貢獻讓我們深受啟發。您在教育事業耕耘多年,桃李滿天下,能否談談對文藝評論人才培養的看法?劉:
我還是從古代文藝評論談起,古人在這方面已經貢獻了許多智慧,前面我提到了曹丕的《典論·論文》。曹丕把他所說的“文章”劃分為“奏議”“書論”“銘誄”“詩賦”等“四科”,同時又指出:“此四科不同,故能之者偏也,唯通才能備其體”。為了解決何以會有“能之者偏”的問題,曹丕又提出了“文以氣為主”的觀點。這里所說的“氣”,實際就是指不同作者天賦的氣質、個性、才能。他曾以“音樂”的演唱為比譬,指出“曲度雖均,節奏同檢,至于引氣不齊,巧拙有素,雖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清楚地說明了這一點。在世界文藝評論史上,這是第一次明確地指出了天才在文藝創作中的重要作用,并且去除了古希臘認為詩人是在有“神靈”憑附的狀態下進行創作的神秘主義說法。此外,盡管曹丕很強調天才在創作中的作用,但并不因此忽視作家后天學習的作用。曹丕認為作家具有天賦的不同的氣質、個性、才能,因此,不同作家的作品自然也就會具有不同的風格和成就。為了促進建安文學的發展,曹丕從建安時代的文學家中挑選出各有不同風格和成就的七個文學家,并一一加以評論。這七個文學家是孔融、陳琳、王粲、徐幹、阮瑀、應玚、劉楨,也就是后世所說的“建安七子”。在一一評論這七個文學家之前,曹丕又講了他已說過的由于文學家天賦的個性氣質不同,因此“文非一體,鮮能備善”,而許多人不懂得這個道理,“各以所長,相輕所短”,而“七子”卻沒有這種文人相輕的惡習。曹丕說:“斯七子者,于學無所遺,于辭無所假,咸以自騁驥騄于千里,仰齊足而并馳,以此相服,亦良難矣”,是說“七子”就像是一群能奔馳千里的駿馬,齊足并馳而又相互心服,是很難得的。
七子之中除孔融外,其他的人原來都是曹操的部下,而孔融又是曹丕在即太子位之前九年被曹操殺了的。但曹丕把他列為七子之首。據《后漢書·孔融傳》及其他有關材料看來,曹操與孔融之間的關系是復雜的。孔融的《六言詩三首》中譴責了董卓乘漢家中衰作亂,還肯定了曹操起兵討董卓的功績。由于孔融早年在政治思想上與曹操有一致之處,因此曹操在決定殺孔融之前,曾讓他的軍事參謀路粹代他給孔融寫了一封信,內容是勸他與御史大夫郗慮(字鴻豫)和好,實際是要孔融歸順曹操。因為這個郗慮正是漢獻帝派去封曹操為魏王的特使,而且獻帝還曾經接見過他和孔融。在接見時,獻帝問孔融認為郗慮有什么優點,孔回答說:“可以適道,未可與權”。這是來自《論語》中的話,意為雖知“道”,但辦事不知看實際情況作出不同的、恰當的處理。郗慮立即加以反駁,說孔融在治理北海時,搞得“政散民流”,他有什么“權”可言?曹操要路粹代他寫信給孔融,其實就是要促使孔融反省自己,不要與曹操對抗。但從《漢書·孔融傳》中我們可以看到,在董卓大亂過去之后,孔融對曹操始終是持反對態度的。道理很簡單,孔融看到了隨著曹操勢力的不斷發展,他完全可能取漢朝而代之。盡管如此,由于孔融與曹操的關系的復雜性,再加上前面講到的孔融的《六言詩三首》確實寫得不錯,明白曉暢而又很有抒情性和氣勢,和曹操的詩有類似之處,因此曹丕就把他列為建安七子的第一人(這也可能與孔融年長于其他六人有關),并作出了這樣的評語:“孔融體氣高妙,有過人者;然不能持論,理不勝辭,至于雜以嘲戲。及其所善,揚、班儔也。”這個評語大致是恰當的,特別是“體氣高妙”一語,就前述孔融的《六言詩三首》來說,是當之無愧的。
對其他六人,曹丕也一一作了評論。這些評論雖然涉及了曹丕所說詩賦之外的其他政治性、應用性文體,如“章表”、“書記”的寫作,但主要還是講詩賦的寫作。曹丕說:“王粲長于辭賦,徐干時有齊氣,然粲之匹也。”“齊氣”指文章風格舒緩,實際也含有氣勢不足的意思。曹丕又說:“應玚和而不壯,劉楨壯而不密。”總起來看,曹丕不僅要求詩賦的寫作要有一種雄壯的氣勢,而且要“和”而“壯”,“壯”而“密”。“密”指詩賦的寫作要有一種細密緊湊的條理結構(包含對仗與押韻),而不是松散,雜亂無章,前言不對后語。曹丕的上述看法,已明顯包含了后來梁代劉勰在《文心雕龍》中作了集中闡述的“風骨”問題,而且劉勰的闡述也明確地引用了曹丕《典論·論文》中對建安七子的評論作為他立論的依據。劉勰所說的“風”,就是曹丕所說詩賦的寫作要有和情感的表現相聯的雄壯氣勢,所以劉勰說:“深于風者,述情必顯”;相反,“索莫乏氣”正是“無風之驗”。曹丕說詩賦要“壯”而能“密”,這就是劉勰所說的“骨”,即“結言端直”,“析辭必精”,沒有“繁雜失統”的毛病。但劉勰沒有像曹丕那樣明確提出“和”與“壯”的統一問題,但他要求文章要“意新而不亂”大致可以包含“和”的問題。不過,這仍然與曹丕不同。曹丕提出“和”的問題,是與他在東漢末年天下大亂,曹操統一北方,使社會初步安定下來之后所下的《禁復仇詔》密切相關的。他在詔書中指出,“喪亂以來,兵葛縱橫,天下之人多相殘害”,現在天下初定,禁止任何人為報過去的仇怨而相殺,人人都必須“相親愛,養老長幼”。這是很有見地的看法。就曹丕講到的詩賦的寫作而論,如果只“壯”而不“和”,這種“壯”就有可能走到暴虐的道路上去。曹操、曹丕、曹植在文學創作上,都是“和”而能“壯”,“壯”而能“密”的。到了唐代初年,陳子昂提倡“漢魏風骨”,就是從建安文學而來的。當然,曹丕尚未使用“風骨”一詞,陳子昂使用這個詞當是受到劉勰的影響,但他一語不提劉勰。
我認為,曹丕的這些看法,實際上是提出了作為一個文藝評論家應堅持的品行以及應掌握的技能。用今天的話說,也就是德與藝兩個方面。汲取古人的智慧,結合我本人的思考,我想就文藝評論人才培養提出以下幾條看法以供參考:
第一,分門別類地培養各門文藝的批評人才。這不僅包含文學、書法、繪畫、戲劇、音樂、舞蹈等文藝部門,還應包含電影、電視、動漫等創作。如中央電視臺綜藝頻道播出的,歌頌各行各業的凡人善舉,很有幽默感而又伴隨著善意的規勸,很受觀眾歡迎的小品劇作,就很值得我們的文藝評論家加以研究,充分肯定取得的成就,促進它的不斷發展、提高。還有我看到的表現長征的繪畫,有的比較好,但也有的構圖雜亂,人物主次不分,對于背景、色彩、明暗的處理也存在不少問題,需要進一步研究提高。第二,除了分門別類地培養各門文藝的評論人才外,我以為還要培養密切追蹤當代文藝評論的發展,能對當代中國文藝評論發展的趨勢、前景提出有深度見解的人才,以引領、推動當代文藝評論的發展。第三,為了培養文藝評論的人才,我們還要研究自五四新文藝以來我國文藝評論的發展所取得的成果。僅就新中國成立后的文藝評論而言,我認為王朝聞同志是一位杰出的文藝評論家,至今仍值得我們研究學習。他的第一部著作《新藝術創作論》出版后曾得到毛澤東主席的肯定決不是偶然的。第四,我們的文藝評論要走出國門,不僅要評論我國的文藝,還要對世界公認的歷史上的文藝大家寫出高質量、有深度、有創見的文藝評論,以促進我國和世界各國的文化交流。
訪后跋語:
劉師綱紀先生雖已八十有三,卻依然精神矍鑠,很是健談,尤其是對經典非常熟悉。訪談中,我們提出一個問題,先生馬上就能追根溯源,將它的來龍去脈娓娓道來,且有自己的思考和判斷,每有發人深省之語。這種旁征博引、信手拈來的自信和大氣,非有幾十年如一日的學術熱忱和勤思篤學是不可能達到的。在先生看來,美學研究應以馬克思主義哲學作為理論基礎,從實踐本體論出發,美和藝術不能脫離它背后的社會基礎和生產實踐活動。中國美學和古希臘美學、印度美學共同構成美學的三大系統,它有自己獨特的價值。對于中國美學,我們應有民族自信心。先生同我們交談了許久。在先生的諄諄教導下,我們對一些問題的理解終于漸漸明晰起來。臨別之時,先生還對我們殷殷寄語,盼望我們能堅持學術探索的精神,將美學研究繼續推進,為文藝的繁榮貢獻青年的力量。
劉耕:武漢大學哲學院講師
王海龍:武漢大學哲學院博士研究生
(責任編輯:韓宵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