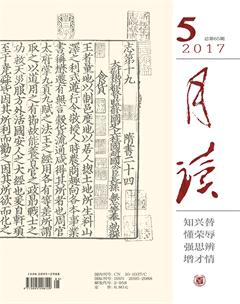粉絲與知音
“粉絲”來自英文的fans,許多英漢雙解詞典,迄今仍都譯成“迷”,實際搭配使用的例子則有“戲迷”“球迷”“張迷”“金迷”等等。“粉絲”跟“迷”還是不同:“粉絲”只能對人,不能對物,你不能說“他是橋牌的粉絲”或“他是狗的粉絲”。當初把它譯成“粉絲”的人,福至心靈,神來之筆竟把復數一并帶了過來,好用多了。單用“粉”字,不但突兀,而且表現不出那種從者如云紛至沓來的聲勢。“粉絲”當然是多數,只有三五人甚至三五十人,怎能叫作fans?對偶像當然是說“我是你的粉絲”,怎么能說“我是你的粉”呢?粉,極言其細而輕,積少成多,飄忽無定。絲,言其雖細卻長,糾纏而善攀附,所以治絲益棼,卻理還亂。粉絲之為人群,有縫必鉆,無孔不入,四方漂浮,一時嘯聚,聞風而至,風過而沉。這現象古已有之,于今尤烈。宋玉《對楚王問》曰:“客有歌于郢中者,其始曰下里巴人,國中屬而和者數千人。……其為陽春白雪,國中屬而和者不過數十人。”究竟要吸引多少人,才能稱粉絲呢?學者與作家,能號召幾百甚至上千聽眾,就算擁有粉絲了;若是藝人,至少得吸引成千上萬人才行。現代的媒體傳播,既快又廣,現場的科技設備也不愁地大人多,演藝高手從帕瓦羅蒂到周華健,輕易就能將一座體育場填滿人潮。
與粉絲相對的,是知音。粉絲是為成名錦上添花;知音,是為寂寞雪中送炭。杜甫盡管說過“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但真有知音出現,來肯定自己的價值,這寂寞的寸心還是欣慰的。所謂知音,其實就是“未來的回聲”,預支晚年的甚至身后的掌聲。梵高去世前一個多月寫信告訴妹妹維爾敏娜,說他為嘉舍大夫畫的像“悲哀而溫柔,卻又明確而敏捷——許多人像原該如此畫的。也許百年之后會有人為之哀傷”。畫家寸心自知,他畫了一張好畫,但好到什么程度呢,因為沒有知音來肯定、印證,只好寄希望于百年之后了。
知音與粉絲都可愛,但不易兼得。一位藝術家要能深入淺出,雅俗共賞,才能兼有這兩種人。如果他的藝術太雅,他可能贏得少數知音,卻難吸引蕓蕓粉絲。如果他的藝術偏俗,則吸引粉絲之余,恐怕贏得不了什么知音吧?知音多高士,具自尊,粉絲擁擠甚至尖叫的地方,知音是不會去的。知音總是獨來獨往,欣然會心,掩卷默想,甚至隔代低首,對碑沉吟。知音的信念來自深刻的體會,充分的了解。知音與天才的關系有如信徒與神,并不需要“現場”,因為寸心就是神殿。粉絲則不然。這種高速流動的人群必須有一個現場,更因人多而激動,擁擠而歇斯底里,群情不斷加溫,只待偶像忽然出現而達于沸騰。粉絲對偶像的崇拜常因親近無門而演為“戀物癖”,表現于簽名,握手,合影,甚至索取、奪取“及身”的紀念品。披頭的粉絲曾分撕披頭的床單留念;湯姆·瓊斯的現場聽眾更送上手絹給他拭汗,并立即將汗濕的手絹收回珍藏。
“知音”一詞始于春秋:楚國的俞伯牙善于彈琴,唯有知己鐘子期知道他意在高山抑或流水。子期死后,伯牙恨世無知音,乃碎琴絕弦,終身不再操鼓。孔子對音樂非常講究,曾告誡顏回說,鄭聲淫,不可聽,應該聽舜制的舞曲《韶》。可是《論語》又說:“子在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圖為樂之至于斯也!”這么看來,孔子真可謂知音了,但是竟然三月不知肉味,豈不成了香港人所說的“發燒友”了?孔子或許是最早的粉絲吧。今日的樂迷粉絲,不妨引圣人為知音,去翻翻《論語》第七章《述而》吧。
不惜歌者苦,但傷知音稀。
粉絲已經夠多了,且待更多的知音。
(選自余光中《粉絲與知音》,九歌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