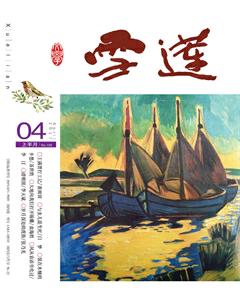大地向我們打開錦囊
袁海勝

土地之味
吃水果時,譬如蘋果,它的甜進入人的味蕾的定位系統(tǒng)后被鎖定,蘋果——甜。如果吃桔子,維生素C與檸檬酸挾持著長江流域的甜,是一種新的滋味,味蕾檔案又記上一筆。吃香蕉時,“香”里有熱帶雨林綿軟的甜,又是一種味道,也在味蕾記憶里存檔。還有眾多的蔬菜糧食,人類的味蕾庫存豐富。
無論什么時候,我們見到任何一種水果,它們的味道就從味蕾的記憶庫里釋放出來,與食欲融合。人還沒開始吃呢就已經(jīng)知其味,口水,老家人叫“哈拉子”、古人稱之“金津玉液”生矣。
春天采食野菜,拿苦麻子(遼西的一種野菜)來說,它把春天的“苦”轉化成一種清爽口感,找不到“苦”的本義了,難道是在捉迷藏嗎?到了夏天,“苦”突然回過神來,根莖葉鉚足了勁,苦啊!苦麻子的“苦”確實讓人舌頭尖發(fā)麻,名副其實。
如此說,季節(jié)也是調節(jié)味道的一道手續(xù)。
《心經(jīng)》說“色聲香味觸法”,“味”名列其中。味是人一生在飲食中須臾不離的追求和探索。佛家說,味只存于人的三寸舌頭上,三寸舌頭風云變幻間,演繹著人生每一個細節(jié)。享用水果,和享用苦麻子均在其例。有知識的人都知道,獲得味覺過程是相當復雜的化學反應。但主觀上,我們以為味道取決于自身器官,如口鼻舌獲悉。譬如糧食,說起哪一種就有哪一種味道在記憶里蘇醒。人的味覺系統(tǒng)是一個龐大的存儲庫,有無以數(shù)記的庫房,每一個庫房住著一種味道,A庫是高粱味道,B庫是玉米味道,爾后大米白面以此類推。當說起、想起或看見哪一種糧食時,歸屬的庫房門“叭”地打開,釋放出所儲的味道,比軍管還要嚴謹。之后,醋的酸、水果的甜、草藥的苦、還有辣椒的辣,凡此種種、不一而足,都在各自庫房里預備著,等待召見。
土地不僅是一切生命的母親,也是天下味道的主人。而土地并無特定的味道(除去被人類污染過的土地)。我不僅一次地捏起一縷土放在舌尖,即味蕾最敏銳的地方品嘗,除了沙土的綿澀,沒有其他明顯的滋味。像甜或苦。土地無味,卻奉獻百味,當然,這些味道藏身于植物或礦物上,是大自然所有玄妙里的一種。土地用了什么奇妙手段讓糧食果蔬的味道變得豐富與繁復?奇跡就是佛家所說的“不可思議”,當然無法解釋。
從百變(何止百變)的味道,看出土地為眾生味覺系統(tǒng)操得那份心,何其艱辛。而土地卻毫不費力,她在偷窺眾生由味道引起的喜怒哀樂,即李叔同(弘一法師)手書“悲欣交集”時,更像個調皮的孩子。慈善是土地的本性,是唯一的。土地做每一件事都有善良的影子。她讓植被,包括神秘的莊稼從其博大的胸懷里長出來的同時,還變魔術似地讓草本植物或礦物質具有藥性,拯救眾生脫離病痛苦海。中醫(yī)藥不用說了,西醫(yī)藥品無論是合成還是從礦物質中提煉,仍沒脫離土地組織。這些有機物或無機物重新組合,形成一種神奇的戰(zhàn)斗力,為人類消弭病痛。
害人的藥是人類自己出了問題,與人性有關,與土地無關。
土地捧出果實和水,看著眾生享用,這種情懷不可言表。
土地調味的主要功能在土壤里,土壤是門學問,門系龐大,在大學里深造同樣需要四年甚至更長時間,最終誰也沒解釋出植物果實令眾生癡迷的味道從何而來。你可以說A分子和B分子結合,但味如天生,你說不出來。這不是科學的無力,而是土地的博深。我們無限敬仰土地,就像敬仰我們的母親。感謝土地精心地操持,讓生活如此豐富多彩,讓我們在味道的迷宮里不斷收獲意外驚喜。再有能耐的人,像神農(nóng)或美食家(這么說對前者確有不恭,只是打個比喻),也不可能嘗遍天下所有味道。只有虛懷若谷的土地,知道味道所有的秘密。就像土地深諳時間的秘密一樣。
民間把對萬物的感恩,上升到某種敬畏的程度就會神化,這里隱含信仰。民間的信仰產(chǎn)生于對大自然物種的愛惜和崇拜。在他們樸素的觀念里,動物如狐如蛇,植物如樹如葫蘆均可成仙,值得人們焚香叩拜祈禱。民間大眾希望世間存在一種超能力,懲惡揚善,讓心中的愿望有所依靠。這不是單一的迷信問題,而是更為廣泛的、精神依托問題。
對于味道,反而心安理得,認為味道與生俱來,何需爭執(zhí)?
土地真的無味?此問貌似天真。我也常盯著土地看,土地除了泥土沙子,看不出什么名堂。我不是超人,甚至比正常人略笨些。在我俗不可耐意識里,不相信色香味出自土地之手,但事實的確如此。我更相信大自然具有神性,這就對了。我想起朋友說過的話,“人學那么多知識干嘛?透支資源,眾生不得安寧。”他的話雖偏激,但也不無道理。珍愛大自然,珍愛土地,珍愛環(huán)境,是人類所有選擇中最明智的一種。
味道不過是生命中某一個背影。土地的平凡之處是冥冥中的一切安排均合情合理。
譬如眾多味道,讓我們癡迷并為之肅然起敬。
土地的無味,實乃人間大味。
土地之色
遼西朝陽冬天的色彩并不單調,像畫家鋪開畫布后的凝思。曠野中潛伏人類不易覺察的線條。冬天里,土地的棱角極為清晰,讓人們看清大自然的紋理。萬物沉寂后,主要是色彩的流逝,讓土地恢復本色。我們看清土層、石頭、植物的骨骼。地域間的特點只有在冬天才明朗,山之高,地之平,溝壑河流交錯,層次的起伏比語言描述真切。色彩的界限毫無敷衍,直接明了。這樣的過渡讓人心里明白。冬天是四季中最冷靜的參與者,讓萬物在跌宕起伏的色彩爭議中,保持住了最為原始的底稿。
春天像女孩子精心挑選的花布,草和花簡單,由水一樣清凈的背景襯托。此時的綠以點為據(jù)點,慢慢擴散。像草尖剛鉆出枯草覆蓋的地表。綠剛一露臉就被兄弟們挽住了手,它們手拉手地搶占地盤,隊伍逐漸擴大。飄動的綠煙像春天欲張未張的眼眸,在枯白乃至斑駁的地表上飄逸。綠的出現(xiàn),仿佛沉睡的土地一下子醒了,睡眼惺忪。春天的秘密馬上要揭曉,這是一場色彩的革命。春天的色彩先在綠色鋪成的地毯上行走,每一步都極為小心、羞澀。色彩的綻放是植物由心而至的喜悅——生命進行到一種忘我的程度后,“嘭”的一下,把愛情升華為完美。譬如梨花,在曠野中舉著怒放的乳白色火焰,丘陵像白銀堆砌,梨花驟張像開懷大笑。蜜蜂背斂雙翅鉆進花蕊,余夢未消的蝴蝶站在最高的花瓣上。天地間頓時異彩紛呈。用一種顏色來顯現(xiàn)大自然色彩的繁復與層次,這種效果,只有春天里才能做得出。
夏季色彩雜亂無章。熱戀季已經(jīng)過去了,冬的沉積和春的孕育此時只有噴發(fā)。植物的青春期特點是腰身漸豐。譬如莊稼,像集蓄了夏天所有的激情,以塊為單位,彰顯茁壯與蓬勃。對人類來說,在眾多的色彩中,莊稼的色彩極為醒目。夏季里,色彩的突圍需要大兵團作戰(zhàn)。枝葉呼應,熨帖合適,形成四面八方的陣勢,大地完全被這種萬馬奔騰的場面覆蓋。山泉、鳥鳴、風聲、昆蟲的吶喊聲,這些背景音樂為夏季魯莽造勢。夏季是四季中最為得意的季節(jié),不但在色彩上,還在狂放不羈的性情上。激情,是夏天的主色調。
秋天是色彩沉淀的關鍵,色彩的激流轉入平穩(wěn)的河面,突然想起過去的時光。秋天確實是色彩沉淀的好場所。新鮮的色彩不易出現(xiàn)了,樹上最嫩的芽,也不像春天那樣稚氣,夏天那樣莽撞。葉子轉瞬間出現(xiàn)的黃與紅,看得出時間的倉促和猶豫,秋天的色彩是季節(jié)底層積攢的夢境。秋天出現(xiàn)的花朵是最清晰的回憶,每一朵都有不同的信息,每一朵都有不同的心情,這是一種跨越季節(jié)的投遞。秋天的美悄悄聚攏于果實,哪怕是草籽,也能看出時光的飽滿。糧食(此時不能稱其莊稼)旋即散發(fā)令人迷醉的氣息。人,此時是感知幸福最為真切的時刻。人類負重的大車碾過,把撲過來的草壓到泥水里,水塘的積水浮著一層厚厚的綠銹,有時露出青蛙鼓脹的眼睛。秋天更為安靜。色彩演變被秋天安排在民生以外的地段,秋天的豐厚顯示在果實的種類和分量上。秋天的大道上,各種植物莊稼的枝葉陳橫,略顯斑駁。拉糧食的大馬車涂上余輝,鞭桿子上的簪纓鮮艷。場院里堆著金黃的玉米。玉米用金子一樣的顏色告訴眾生糧食的珍貴。高粱滿臉漲紅,醉漢一樣臥在麻袋里。谷穗成捆,像是要逃跑被人綁縛。黃豆溜圓,因而身手敏捷,現(xiàn)在只能安靜地歇在糧倉里。各種糧食保持住最終的色彩,讓日子安穩(wěn)平靜。
四季輪回,色彩是大地的衣衫,須臾不離。
大地上的事情
人把種子播進大地里之后,就把三分之一的命交到土地手里。種子在大地里飽吸水分后開始膨脹,各種酶像地下工作者一樣發(fā)展組織,催化生化反應。種子地下組織的核心即胚開始分裂,莊稼的芽錐鉆出地面。莊稼的生長是一個莊嚴的時刻。這里面有無窮盡的化學反應,產(chǎn)生一些新物質,譬如糖分和碳水化合物,過程繁復。
時令一到,外觀看地面(耕地)先拱包,然后,莊稼(草也算)伸出一芽葉片。最初看不出是葉來,卷在一起了,像根針。此針柔軟,對任何物體都無殺傷力,卻穿透厚土。像植物聚精會神生長的一種表態(tài)。草本植物發(fā)芽時樣子差不多。只要仔細觀察,地面上的事情都能看得見。莊稼伸出第二片葉子時,譬如玉米,又長了。這是目測。過幾天再看,葉子已經(jīng)出到五六片,看清莊稼拔出的第一個節(jié),放大了像竹子。莊稼開始生長了。除了科研人員或特殊設備,百分之八十的生長過程是無法看到的。我們沒耐心也沒時間。
播種和收獲,是大地上最溫馨的故事。
植物生長的勁都使在地底下,根是植物特殊的血管,輸送水分和溶解無機鹽并分發(fā)養(yǎng)分。我們拔出一棵草,看到亂麻似的根須,也像人類的胡子。但人的胡子極無用處,除消耗人體能量、包括剃須刀電池的物理消耗外,沒給人帶來一丁點好處。植物的根在生命傳承里肩負重任。根是植物的另一張“嘴”,是營養(yǎng)供應商。根在植物的生長中苦心孤詣,維護生長每一個細節(jié)。根一身土腥味,說明根無法離開土。即使離開,根也要帶著土里的一些氣息,包括水分和氣味。等這些信息耗盡,植物也就干枯了。干枯的植物不再是植物,會變成另外一些東西,像秸棵、柴火、木頭、房梁或窗框等等。植物是享用了土地給養(yǎng)后,轉爾賜予眾生給養(yǎng)最多的物種,形成大地的肝膽。
季節(jié)界限,主要是由大自然的變化決定。有的地方,像熱帶,只有雨季和旱季兩個季節(jié)。季節(jié)的劃分復雜,全球都不一樣。季節(jié)是大地的衣衫,款式、面料、顏色隨冷暖定奪。而植物——說季節(jié)必然提及植物——在季節(jié)里扮演不同角色,以顯季節(jié)的渭涇分明。還有風,冬的寒、春的暖、夏的熱、秋的涼,風比誰的嘴都快。風的潛能已被人類重視,風輪發(fā)電機隨處可見。這個好!這是人類為自己干的事情中極具意義的一件。大自然的行囊里還藏著雨和雪兩件重要的禮物,它們不但代表季節(jié),也代表萬物生存指數(shù)。其次有露水和霜,是夏轉秋、秋轉冬之際的個性簽名,類于提醒:“下一個季節(jié)即將到來。”其次有雷電和冰雹,它們的益處甚少,但作為大自然的情節(jié)又不能缺少。
大地的故事里,四季及大自然變化極盡豐富,個個精彩。
地球上,人類活動的領域越來越大,說明人的貪心也越來越大。人類的發(fā)展,是地球最頭痛的事。人類是地球上衍生故事最多,卻又最出乎意料的物種。人類存在的虛偽空間要比其他物種大出N倍。
人類搞得一些事情,無疑是對大地的威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