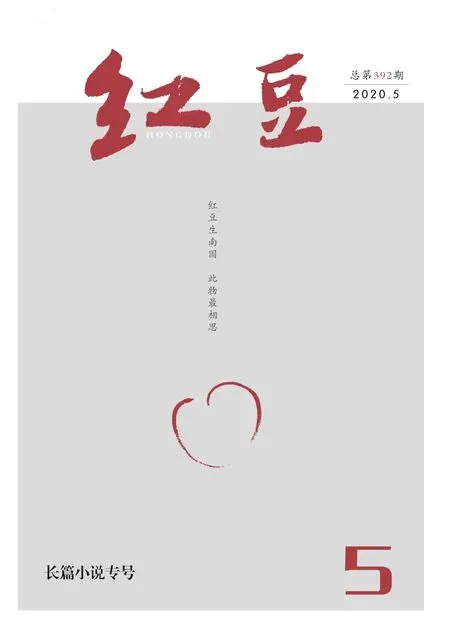東江冰舌
南宮羽走在東江邊上,腰肢依然輕柔,盡量繞開水葫蘆,還是一踩一個響,鞭炮般噼里啪啦,聲音歡快嘹亮,與她的心情一樣。
汽笛聲起,悠悠揚揚,一艘渡輪從下游向上游駛去,船艙裝滿細軟的沙子,像起伏的山丘,在水中游弋。
最初,她分不清哪端是上游哪端是下游,有時候看見江面的水草從右邊流向左邊,有時候又從左邊流向右邊,渡輪駛過,尤其是渡輪在江面相向駛過之后,水草似乎也暈了芳心,在江水中打著漩兒,改變了最初的流向。
很長一段時間,南宮羽對這件事捉摸不透,不知道是自己出了問題,還是江水出了問題。她在清晨和黃昏一次次來到江邊,在冬夏春秋不同季節來到這里。當然,東江流域是沒有冬夏春秋之分的,冬夏春秋只在她心里,在與秦巴山地有關的記憶里。這里似乎只有夏季,一年四季都可以穿裙子,穿薄如蟬翼的漂亮衣服,她越來越喜歡這里,喜歡東江的日出與日落。
現在,她已經能分得清上游下游了,一方面是從岸上的樓房橋梁定位,一方面是從江水的潮漲潮落分辨。漲潮時,水葫蘆隨江水隨海浪魚蝦逆流而上,江面就漂著碧綠的水葫蘆和嫩紫色的花朵。直到一簇水葫蘆漂移到眼前,俯下身子拿捏到岸上,才發現紫色的花朵是水葫蘆開放的,與水葫蘆相伴相依。花朵潔凈明媚,紫色里透著白皙,一點也不像隨波逐流來的,倒像是一秒鐘以前才怒放的。舍不得用手掌觸摸花瓣,只用食指與中指指尖輕輕撫過,有一種雪的沁涼。水葫蘆圓潤光潔,綠茵如翠,剝開了,竟是細密規則的網,蜂巢一般,凈白安謐。退潮的時候東江像大地上的所有江河,從高處流向低處,從陸地流向海洋。流淌的過程中,江面偶爾漂浮著枯枝敗葉,有一次,竟然蕩漾著一朵艷麗如火的芭蕉花。
其實呢,東江并沒有一下子流進海洋,而是流到了珠江口。
這是她在珠江三角洲尋找李青林的時候得出的結論,知曉這一事實的時候,她驚得發了好一陣呆。東江離大海那么遠,遠得足可以走上一天,海水怎么就倒流到東江了呢?海邊濕地伴生的連天碧葉水葫蘆,就那么悠閑自得,無根無基,漂呀漂,漂入河道,一直漂到抵達不了的地方,又隨江水流到大海之濱。
浮萍。南宮羽無數次望著浩浩蕩蕩的江水,倏忽間逆流而上,倏忽間順流而下,望著脆生生泛著亮光的綠葉和嬌美的紫色花朵,感嘆噓唏。
也許因為對東江的迷戀,無數次去往江水最終抵達的地方。那次短暫的海洋艷遇,成為她永久的記憶,以至于后來每次置身于碧水藍天,哪怕在泳池游泳,只要身心放飛,四肢漂浮,就會微閉眼簾,享受那份記憶的酣暢,身體的起舞。
忽然,“啪”的一聲,抖擻間,看見三三兩兩垂釣的人或立或坐,有人把釣竿用力扔進江水,水面泛起圈圈漣漪。小小浪花消失以后,另一支釣竿高高揚起,在空中畫出一彎柔韌的弧線,款款落在岸上,岸上芳草萋萋。一尾銀色小魚活蹦亂跳,在青草間拼命掙扎。垂釣者彎腰去抓,南宮羽的一只腳就快踩著銀魚了。噼里啪啦,水葫蘆在短暫的寂靜中發出脆響,驚得小魚騰空躍起。南宮羽的身子向后一仰,同時看見垂釣者將身子彎得更低,差不多就要觸到地面了。這個時候,銀魚像一只白鴿,在青草與江水之間變幻成一條潔白的綢帶,瞬間就消失得無影無蹤。
海水中的男人,多么英俊哦,古銅色的皮膚,性感的唇齒,異國的新奇,全都隨著銀魚消失。
南宮羽來不及看那飛走的銀魚,快速掃視了一下地面,地面陽光燦爛。她穩穩地站住,終于站在一小片裸露的地上,然后才看那垂釣者,那雙眼睛正注視她,水滑的眼神背后是深深的驚愕。
她眨了一下眼睛,翕動嘴唇,想說一聲對不起,把你的銀魚嚇飛了。聲音還沒有發出,對方的驚愕就變成了羞澀。哦呀,中年男人還有這般表情,真是奇妙哦。看來不但嚇著了他的銀魚,還嚇著了他本人。
李青林當年的羞澀遠比這個男人深遠廣博。
她微微一笑,低了低頭,什么也沒說。
他也微微笑了一下,羞澀的感覺輕淡了一些,伸手捏起一小團釣餌,往釣鉤上安放。
鳥兒從渡輪的旗桿上飛來,掠過垂釣者和南宮羽的頭頂,停歇在木棉樹上。那是一只羽毛華麗的小鳥,雙翅暗紅,尾羽鵝黃,是暗綠繡眼鳥,還是金繡眼鳥,或者八哥,她分辨不清。木棉花開得正艷,紅彤彤的花朵熾烈似霞,點綴在藍天白云間。鳥兒從木棉枝頭飛到紫荊花枝上,搖曳的紫荊花絢麗清新,洋溢著香艷的色澤。
徜徉在四季開花的東江邊上,南宮羽總會思考一個問題。也許是這些花香和鳥鳴,也許是這潮起潮落的江水,驅走了對李青林的怨恨,讓自己的心逐漸平復,腳步不再凌亂。
這樣說來,應該感謝李青林的。的確,應該感謝他,如果沒有他,她就不可能從四季分明的秦巴山地來到空氣潔凈、樹木蔥蘢、連樹梢都開花的地方。
這個時候,她聽見了歌聲。“在那桃花盛開的地方,有我可愛的故鄉,桃樹倒映在明凈的水面,桃林環抱著秀麗的村莊……”
回眸間,再次與那雙眼睛對視,慌張里夾雜著絲絲難為情。音樂戛然而止,他舉起手機,“喂”了一聲,低一低頭,把手機在掌心掉了個方向,繼續接聽,同時轉過身去,靦腆中將筆挺的脊梁對著她。
她有點愕然,這分明就是李青林往昔的神態,似乎又不全是。那是誰呢?如此遙遠又熟悉。
喔,可不是嘛,真的是多年以前的事了。
依然走在東江岸邊,一陣馨香撲面而來。循著香味望去,是一樹長在堤岸上的四季桂,芝麻粒般大小的桂花在光照下金黃溫婉。南宮羽一時興起,拽住榕樹的氣根向桂花樹攀去,氣根紅潤柔軟,握在手中仿佛握著一條小蛇。她自小最怕的就是蛇,柳巴松曾經把一條死蛇放進她的書包里,嚇得她好長時間不理他,這個長相怪異的家伙好像對她有好感,后來也不了了之了。
是的,就是柳巴松,多少年不曾想起他了,想起可怕的蛇,他就突兀地蹦出來。
用力拉拽,氣根發出細微的響聲,她連想也沒想,立即松手,氣根仿佛秋千,在濃密的枝葉里蕩了一個來回,嘩啦啦,落在地上,恰好掉在幾片榕樹葉上,葉子顯然是熟透了的,泛著紅艷艷的光華。氣根確乎有些蛇的模樣,慵懶地打著卷兒,不規則地盤在落葉上。急促地看了一眼,害怕再看,伸手一攬,拽住一條柳枝。柳枝微風般飄搖,南宮羽的身體失去了重心,順著斜坡向下滑,滑到半道上,被一株棕櫚樹攔住了去路。棕櫚樹有一個巨大而渾圓的羅漢肚,樹干剛正挺拔,伸向天空,在白鷺扇動翅膀的地方,舒展著條形闊葉,盛開的花朵一樣,阻攔陽光,帶來陰涼。
依著棕櫚樹凸起的肚子,仿佛貼著大安略有贅肉的肚皮,伸手去摸樹干上的紋路,圈狀的紋路或粗糙或細膩。輕輕地喘一口氣,把臉貼在棕櫚樹上。她有點想念大安了,想念大安的身體了。
雨滴就在這個時候落在臉上。
她摸了一下臉頰,沒有摸到雨的痕跡,陽光從棕櫚樹葉間傾瀉而下,婆娑斑斕。再次仰望天空,幾粒桂花正往下落,金燦燦,亮晶晶,原來不是雨滴,而是桂花粒兒。一個箭步沖到桂花樹下,雙手抱住樹干用力搖晃,如同欲望高漲時與大安的床笫之歡。桂花粒兒撲撲簌簌,連綿不斷,雨滴一樣下個不停。瞬間,渾身上下落滿了桂花粒兒,仿佛沐浴在桂花雨中,樹冠下鋪了一層金色,間或還蹦跳一些桂花粒兒,明麗香醇,溫軟誘人,如同盛典時貴妃的拖地長裙,迤邐,妖嬈。
索性順著樹干溜到地上,像小小少年一樣無拘無束,隨意躺在桂花間,望一眼滿地落英,望一眼高峻的棕櫚樹,收住了自己的想象,畢竟直逼四十歲了,離無所顧忌的年歲有點久遠。
顧盼的時候,樹木邊緣,一個廣告牌吸引了她,“在那桃花盛開的地方攝影展”,并附有展覽時間地點和主辦方。廣告語印在整張照片上,畫面有些模糊,但看得出是一張從高處俯瞰拍攝的照片,畫面上有油菜花和桃花,蜿蜒的河水中央長著一些綠樹。
她以為看錯了,水面上怎么會有那么多樹木呢?從長勢來看,樹齡還不小,這是她第一次看見樹在水中央。眼前的東江自然不長樹,再高大的樹木在浩蕩的江水中也生不牢根。秦巴山間的河流也不長樹,只在河灘泉水邊長一些淺草和小灌木,這幅廣告,顛覆了她對樹的認識。
真稀奇哦。她嘀咕道。
仔細注視主辦方的名字,更加驚訝,“西藏林芝”赫然在目。
天呀,西藏就已經夠遠了,林芝又在哪里呢?
只在電視里見過西藏,更多的是在歌曲里聽過,還知道有人坐著火車去拉薩,并大張旗鼓把這件事兒譜上曲子唱出來,廣場上跳舞的大媽大姐最喜歡隨著這首曲子載歌載舞了。
她像風中的蒲公英,輕盈歡暢,離開東江江堤,在樹木和鮮花掩映的綠道上走了不大一會兒,來到可園門口,幾乎沒有停留,乘上一輛出租車就到了目的地。
攝影展室不大也不小,觀者稀稀拉拉,兩位穿藏袍的男女與電視上的藏族男女一樣,唇厚鼻闊,眼睛水靈,臉龐紅中透黑。
她在與廣告牌同一模板的照片前停下腳步,畫面構圖清晰,色澤亮麗。顯然,這是一張用廣角鏡頭拍攝的照片。田疇里的油菜花黃得醉人,油菜花四周是開得正艷的桃花,一樹一樹,樹樹嬌艷,粉紅,嫣紅,殷紅,桃紅。紅中有白,白里透紅,田疇連著田疇,桃花連接桃花,田疇和桃花一直延伸到河面,河邊有兩頭貌似牛一樣的黑色動物,大概在低頭吃草。河水像葳蕤的藤蔓,繁衍出粗細不等、長短不一的細小枝蔓,婉轉迂回,白亮亮清幽幽,泛著縷縷晨光。水蔓之間,河水中央,屹立著株株綠樹。
上前幾步,辨析那樹,是法國梧桐還是香樟樹,或者榕樹,隨即否定了自己。法國梧桐太高大,枝葉繁盛招搖,屬于闊葉樹;榕樹長有茂盛搖曳的氣根,有獨木成林的本領;而水中的樹木看起來有些纖弱、孤零。
又走到另一張照片面前,這張照片的角度是從低處向高處仰拍而成。由低及高,依次有金燦燦的油菜花,淡白淺紅的桃花,油菜花與桃花中間,橫亙著五顏六色的彩條布。彩條布上方是茂密的樹木,也可能是森林,每株樹都像利劍一樣,直指天宇。樹木之上,是白雪皚皚的山巒,山巒氣勢恢宏,散發著橘色光芒,雪峰之巔,飄著旗幟般的白云,離山巔越遠,白云越淡,越不規則,直到更遠處,與天空一個顏色。而那天宇,碧如浮萍,比珠江口的海面不知幽藍幾許,完全能與那次艷遇的海水媲美。
她猛吸一口氣,后退兩步,怕呼出的氣息浸染了如詩的畫面。夢一般地,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在她不長不短的生命歷程中,見識過不少美景,從北方到南方,從天空到海洋,還在海水中演繹過曠世激情,坐在大安的越野車上,穿云度柳,欣賞過半輪月亮,一湖秋水,滿眼龜背竹。無數次被自然景觀震撼,但沒有哪一處比得上這張照片多姿多彩,豐饒重重。
終于,忍不住伸出右手,用食指的指肚輕輕撫了一下照片上的雪峰和旗幟一樣的白云。
這是旗云。一個聲音在她身后響起。
回頭去看,正是那位穿藏裝的年輕男子。
四目相視,覺得那眼神并不陌生,她回了一聲:謝謝。
還是掩飾不住好奇,問道:什么是旗云?
男子說:旗云嘛,就是風把正在蒸發的積雪吹成旗子一樣的云彩。
南宮羽指著彩色布條問:這是什么?
經幡啊,祈福的經幡,在風的吹拂下,相當于轉動的經筒。
南宮羽說:電視上見過的,經幡。那是牛嗎?
是牛,牦牛,西藏人把牦牛叫牛,與你們內地的牛不一樣,不過套上犁鏵也能耕地。
男子邊說邊指著樹木與雪山之間影影綽綽的白色說:你們那里見不到這個。
南宮羽湊近照片,努力仰望男子指點的地方,透過黑色的樹木縫隙,隱約看見一些白色,應該是雪吧,但那白色只集中在一個地方,并沒有遍布整片樹林。
冰舌,見過冰舌嗎?
男子似乎有些興奮,還沒等她詢問,就自問自答起來。
聽見“冰舌”,南宮羽倏地后退,不小心碰著了一個人。她沒有向對方道歉,就低聲念叨,冰舌,冰舌,好奇怪的名字噢,冰還長舌頭呀?
忽然,她指著第一張照片問:河中間是什么樹呢?一直長在河水里嗎?
男子說:這是柳樹,這是柏樹。
南宮羽說:柏樹還長在水里呀,柳樹怎么沒有長長的枝條呢?柳樹不都是垂柳依依嗎?
男子歪著腦袋,睜大眼睛,不解地問:什么是垂柳依依?
她被問得目瞪口呆,男子笑瞇瞇地望著她,很認真的樣子。南宮羽搖擺一下腰肢,想用“婀娜”兩個字回答,想一想覺得不妥帖,就用淺笑回答他。
然后,她指著田疇中間的綠色問:這是小麥嗎?我們老家桃花盛開的時候,小麥長得正旺呢。
不,不是小麥,是青稞。男子聲音異常洪亮,似乎還帶著一點點氣惱。
南宮羽不再問了,這個時候,她注意到照片右下角的幾個字:巴松攝影。
巴松,柳巴松不就是這個名字嗎?會不會就是這張照片的拍攝者呢?
想到這里,心跳加速:這么大氣磅礴、內容豐富的照片如果出自柳巴松之手,可真是戲劇又傳奇呀。
莫名其妙地,想立即知道此巴松是不是柳巴松,側目看那男子,男子已經走到大門口。她徑直向穿藏袍的女孩子走去。見她走近,女孩子立即從座位上站起來,盈盈地迎著她。
南宮羽也微笑著,一邊點頭一邊問她:請問巴松是柳巴松嗎?
女孩被問住了,笑容停滯,迷茫地望著她。
南宮羽補充道:我是問攝影師巴松是哪位?
女孩立即扯開嗓子大叫:巴松,巴松。
剛才那位藏族男子繞過幾位參觀者,向這邊走來,邊走邊問:掐烈卡日云啊?
南宮羽奇怪,這人說的什么話呀,根本聽不懂,喔,或許是藏語吧,才問:他就是巴松,攝影師?
女孩子笑呵呵地說:他是我們西藏有名的攝影師,巴松啦。
南宮羽愈加迷惑:巴松啦?不是巴松嗎?
女孩哈哈大笑,剛剛笑出聲,又用手背遮掩,男子已經走到跟前。
女孩對男子說:她問你為什么叫巴松啦?
男子也笑起來,露出潔白整齊的牙齒。她暗自感嘆,牙齒可真白呀,比銀魚都白,能夠與大海中的那位異國男子媲美呢。
女孩說:巴松啦,是愛稱昵稱,藏族人喜歡在名字后面加一個啦,就是這個意思。
南宮羽笑一笑,表示已經聽懂了。
女孩盯著她的眼睛,小聲問道:你不快樂嗎?
南宮羽吃驚不小,重新審視女孩,女孩神情泰然,眼神潔凈,目光澄澈。仿佛一雙沒有被污染的眼睛,當屬十三四歲女孩的眼睛,可從面容來看,只比自己小幾歲。
南宮羽裝作沒有聽清的樣子,追問道:你是說我嗎?我很高興呀。
女孩撥弄著胸前的菩提珠子,不連貫地說:你不想,讓人知道,你不高興。
南宮羽望望四周,還好,沒有人注意她,沒有熟悉的人,巴松也不見了蹤影。
南宮羽輕聲問她:你會相面?
女孩說:什么是相面?
南宮羽簡直要爆炸了,這到底是些什么人?是不是跟冰舌一樣,思維被凍住了?怎么連話都聽不懂?唉唉,秀才遇見兵,自認倒霉吧。
女孩把一張彩頁遞給她,說一聲:歡迎你到林芝觀光旅游。
她順手把彩頁塞進手拎包里,走到展廳門口,有些不舍,更多的是為了打發時間,便返回展室,繼續欣賞。
她從別樣的風景走進霓虹燈閃爍的街區,感到了巨大的沖擊。
夢幻一般,不真實,不確定。進了臥室,一頭撲到床上,腦海中還上演著花海、雪山、冰舌、森林、牦牛。
一連幾天,這些畫面幻燈片一樣,無處不在,時時縈繞,占據著南宮羽的大腦和光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