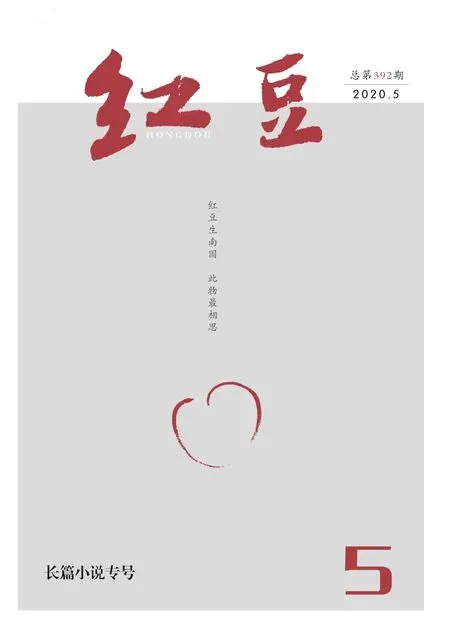北方別
學校馬上就要開學了,還不見李青林的影子,這讓南宮羽生出不祥之感。這種感覺就像荷葉上的露珠,在心頭滾來滾去,晃晃悠悠,卻難捧于手心。又如陣陣秋風,吹拂在臉上,冷在心里,則無可奈何。
剛開始,南宮羽還收到過李青林的一封信,字跡潦草,用力輕重不一,短短幾句話,意思是深圳熱已經過去,海南熱也已過去,現在正熱的是上海浦東,許多人在浦東發了大財,目前對廣東用人市場還不了解,有著落以后再告知。
南宮羽捧著信,一頭霧水,以前也知道深圳特區、海南特區、浦東開發區等等,都是些名詞概念,跟自己八竿子打不著,而現在,幾乎是一夜之間,同自己發生了關系。
在此以后的每一個清晨、每一個黃昏,期盼李青林的來信成為她的頭等大事,有時候等不及郵遞員的身影,假裝路過郵電所,不斷看那扇忽開忽閉的斑駁紅漆木門,待郵遞員將綠色帆布口袋架上自行車后座,快速立在他身邊,直勾勾盯著郵件袋。驚嚇幾次以后,郵遞員每次從郵電所出來都條件反射,顧盼四周,看有沒有近乎麋鹿般的眼睛。后來她有點不好意思,街巷里畢竟人來人往,熟悉和不熟悉的眼睛與她相視的時候,閃爍著不確定的星光。她干脆直接到郵電所分發室,分發報刊郵件的小伙子一邊忙碌,一邊與她搭訕,聊一些可有可無、無鹽無油的閑話,有時候她被問得實在不耐煩,翻開報紙,低頭去看,眼角卻不停地瞟那兩個木格框子,一個是水電站,一個是鎮小學。
一天,她正抻長脖子往油膩膩的帆布袋探望,一陣涼風掠過,后頸窩處被什么東西擊中,隨即罵罵咧咧的女高音響徹整個空間,唾沫星子夾雜著濃重的油墨味。
飛來的是一個年輕女人,女人皮膚白皙,一條辮子垂在胸前,另一條蜷曲在肩上,左眼下方有一顆黃豆大小的肉色痦子,薄薄的嘴唇蝴蝶般翻飛。
女人一手叉腰,一手直指她臉,大著嗓門罵道:仗著自己是個大學生,四處勾引男人,你不要臉,我們還要過日子呢。
待她反應過來,才感到后頸窩生疼,伸手去撓,抓了一手稀泥,隨即向一旁甩去,一甩就甩到女人腳背上。女人穿了一雙暗紅色豬皮涼鞋,看見扔出去的稀泥最終回歸自己,嘴角用力抽動,一個猛子撲上來,揪住南宮羽的頭發,就往沒有刷過漆的報欄木柜上撞。
南宮羽眼前一黑,接著就聽見“砰”的一聲,然后是劇烈疼痛,一股熱流由上而下,從額頭流淌到臉頰,再滴到脖頸和胸脯。
小伙子呵斥一聲,女人像扔爛白菜一樣,扔掉南宮羽的腦袋就跑,跑也沒跑幾步,剛跑到門口,怪聲怪氣地叫了一聲,媽呀,順著墻根就滑下去了。
南宮羽睜開眼睛,感覺自己變成了血人,倚在木柜上,有些恍惚。小伙子顯然已經被嚇住,站在原地一動不動,但只遲疑了瞬間,就向那女人沖去。南宮羽充了電一般,三步跨欄,越過男人和女人,向有陽光和青草的地方跑去。奔跑的時候,把順手抓走的報紙緊緊罩在頭上,像圍圍巾一樣從頭頂圍到胸前,報紙在頭頂和臉頰邊飄蕩,呼呼作響。跑到電站旁邊的水渠邊,以為沒有人注意,正要蹲下身子清洗,夏克從幾株綠茵茵的枇杷樹下走來,一臉驚喜,然后是愕然,接著就歡天喜地地說,你怎么跟魔術師一樣,分秒間就變成了戲中人?
南宮羽恨不得吐他一臉,想起幾分鐘前自己被侮辱,就后悔有這種想法。抓起報紙遮住臉便跑,一個趔趄,沒有站穩,整個人掉進水渠里,幸好水只沒過膝蓋,順勢將頭扎進水里,水面浮出幾縷紅艷。夏克走到跟前,她已渾身濕透,變成了落湯雞。夏克把手伸過去,她沒有理會,雙手在渠坎上一撐,雙腿一蕩,就坐在了水渠沿上。
夏克站在她身邊,連連感嘆,額頭怎么在冒血呀?快讓我看看。
南宮羽鷂子翻身,一躍就站了起來,灑出些許水珠,頭也不回地走了。
李青林剛走沒多久,父母照常來學校給菜地澆水間苗,把門窗打開,讓空氣對流。偶爾與相識的老師客氣幾句,有人就問什么時候喝李老師的喜酒。老兩口笑呵呵地回答,快了,快了。歇息的時候,就在兒子房間里燒水做飯,把桌椅板凳擦拭一番,地掃一遍,還給地上撩些水。太陽偏西的時候,才相跟著離開學校,專程繞到水電站,若是南宮羽值班,就進去打聲招呼,順便問問青林多會兒回來。頭幾次,南宮羽還信心十足,一一回答老人的問話。后來,連她也困惑納悶,怎么還不來信呢?但對老人依然笑臉相迎,盡量輕松地說,可能就這幾天吧。
連陰雨過后,母親把兒子的所有被褥棉衣單衣曬到晾衣繩上,發現兒子只有一件過冬的羽絨服,還是上師范學校第二年買的。那一年天氣助人,漆樹特別出漆,老頭子割了一季漆,自家留了一桶,為兩口白皮棺材上了兩層漆,賣給供銷社兩木桶,買了一床大花被面和兩條床單。分配這些東西的時候,意見高度統一,被面裝進新棉花,里襯依舊是自家織的白色老粗布,連同一條床單硬讓青林拿到學校,剩余的錢也塞到他手里,兒子就是拿這筆錢買的羽絨服,純黑色的,綿軟柔和。留在家里的那條藍色仙鶴床單,只在兒子回家的時候鋪到他床上,兒子前腳離開,后腳就收起來折疊好,裝進松木箱里。
有一次鄰居家大兒子結婚,要借這條床單鋪婚床,父親一口拒絕,不借,堅決不借。迎親隊伍都出村子了,母親才把床單抱在懷里,急急慌慌到了鄰居家,女主人連連抹淚,抹得臉上的紅色印油斑斑駁駁。收起床上滑了絲的老布床單,請兒女雙全、命又好的李青林母親和其他幾位婦女鋪床,在床頭床尾枕頭底下撒些紅棗花生蓮子。
末了,女主人把幾顆帶殼花生塞進她手心才說,以前是我們對不起你家,建茅廁的時候多占了你家巴掌寬一溜地皮,不過嘛,你們家老頭子硬在茅廁邊上種了花椒樹、桑樹。后來聽說房前屋后不能栽種這些不吉利的花草樹木,花椒就是焦子,晚輩焦苦,桑樹就是喪事。茅廁挖好第二年,沒發洪水,沒下冰雹,光天化日的,河水才過小腿肚子,竟能淹死人。挖石斛的又不是大牛他爹一人,偏偏淹死了大牛他爹。死鬼一死,大牛一氣之下,才砍了你家的花椒樹和桑樹。你家老頭子見到我就像見了母老虎,那個恨呀,唉唉,如今,大牛二牛粘起來連青林指甲蓋里的垢圿都不如,結個婚就這么難場,親家說好要陪床單被褥的,臨到昨天擦黑捎信來,說要留給兒子娶媳婦用,你說這親家多坑人,全家人就是去偷,也偷不來全新的床單被褥呀。
想起這些,母親淺淺地笑了。羽絨服在晾衣繩上抖動,忍不住輕輕去摸,綿綿的,軟軟的,一根絲掛到手指的老繭上,抬手時,扯得老長,趕緊低頭,上下牙一咬,咬斷了絲線,鼻子和臉全都埋進羽絨服里。熟悉的氣味好聞極了,微微閉眼多聞了一會兒,剛睜開眼睛,就看見老頭子故意撇過臉。老頭子手背上的黑色印痕非常明顯,每年割漆,都會被割傷或被漆感染,手心手背的傷疤一年半載都是黑的,有的疤痕終生不褪,直到帶進棺材。
母親木木地望一陣,緩緩轉身進屋,取出兩雙棉鞋,一雙是半新不舊的化纖布黑膠底鞋,一雙是鞋幫已經松軟的人造革氈鞋。拍拍鞋子上的灰塵,松開鞋帶,放在房檐下的地上,想一想,怕狗叼走,便整齊地擺在窗臺上。最后取出的是一條紅色絨褲,襠部已經磨得透亮。坐在小凳上,手撫絨褲發了好一陣呆,才從一條破床單上剪下一塊紋路稍微密實的布,墊到里襯,給針鼻穿線的時候費了好一陣工夫,即便把線頭含在嘴里打濕,嘴唇捋一遍,手指捋幾遍,拿捏揉搓幾次,還是穿不進去。
老頭子看見了,沒有絲毫表情,心想老伴真是老了,當年半夜三更坐在床頭納鞋底,閉著眼睛穿針線,現在照著太陽也枉然。
不知道穿了多少回,重復了大半生不知道重復過多少次的動作,終于穿進去了。穿一次不容易,線就穿得特別長,比胳臂都長出許多,捋抹了好幾次,防止線與線打結,還算聽話,一個小結都沒有打。針腳細密地縫好,還把床單疊成幾層,破洞疊在里面,晾在繩子上,這樣別人就不會笑話兒子都當老師了還用這么破舊的床單。當然,這床單早就不能用了,好好留著,將來給孫子當尿布。
老兩口摘了幾個紫亮的茄子,一抱粗細不一的黃瓜,幾條鮮嫩的絲瓜。黃瓜頂花帶刺,黃艷艷的花朵柔和溫潤,花粉時不時滴落出來,絲瓜花已經枯萎,懨懨地頂在頭上。茄子黃瓜絲瓜都有老得吃不了的,就沒有摘,任其掛在枝椏藤蔓上,霜降以前摘下來,留到明年當種子,絲瓜瓤還能刷鍋洗碗當抹布。倆人還在茄子地壟一側栽下一溜韭菜,韭菜根是從家里背來的,連土帶須,一小撮一小撮分種在地里,培土澆水以后,才拍拍手離開。
老人要把采摘的蔬菜留一些給南宮羽,明知道她不稀罕,還是去了。
老人一出現在水渠邊,南宮羽的心跳迅速加快,竭盡全力使自己平靜,說出的每一句話盡量溫和禮貌,但還是掩飾不住慌亂,手都有些顫抖。父親背著背簍一腳朝前一腳朝后,站在一簇米蘭前吃旱煙,嘴里嘖嘖有聲,眼神卻沒有離開她們。
母親早看出了端倪,原本就心慌掉氣,看見南宮羽無主的神情,終于沒有忍住,猛地拉住南宮羽的手,聲音有些變調,明顯帶著懇求。
她說:閨女,這幾天夢好亂,前天天快亮的時候,夢見他爹穿了一件皇帝穿的長褂子,唱的咋是漢調二黃,臺下人吵吵嚷嚷,把我鬧醒了,從床上爬起來。有東西撲棱棱從豬圈飛走了,我以為是九斤紅冠子公雞,聽叫聲才知道是烏鴉,清早睜眼就看見烏鴉,心里不安噢。昨兒夜里夢見堂屋垮塌,壓著了大牛家的肥豬,趕忙拿鐵锨刨豬。豬一頭躥起,驚得我一身冷汗,清醒以后,聽見在下雨。你說怪呀不怪,咱這兒半夜三更不常下雨,唉,阿彌陀佛,保佑青林平平安安。
老人的手在她手背上揉搓,有一種將她吸進肚子的感覺,浸透著濃烈的依賴和無助。
忽然間,她想哭,想依偎在老人懷里放聲大哭,就像小時候柳巴松把死蛇放進她書包,嚇得她跑回家一頭撲進媽媽懷里哇哇大哭一樣。而此時此刻,她不敢哭,也不能哭。老人把她當成救星,當作主心骨,她得像未來的女主人,讓老人放心。
她把手從老人的手心抽出來,抽出的時候,老人指肚上掌心上的老繭和粗糲的指甲劃得她手心手背銳痛。她伸出雙臂,把老人攬了一下,拍拍老人的肩膀,安慰道:別著急,說不定青林在外面干大事哩,等發財以后你二老跟著享清福吧。
幾十年來,老人還是第一次被人擁抱,而且是被未來的兒媳婦攬在懷里,盡管只是短短一小會兒,這種事在村里想也不敢想,更不可能見到做到,老人家立即轉憂為喜,不自然地笑了笑。
老人走后,南宮羽對著一渠豐韻清水,愣怔了很久很久。
暑假結束學校開學以后,父母再也不到學校來了,沒人澆水施肥,辣椒茄子韭菜絲瓜全都枯黃起來。老人從其他老師和熟人眼里看到了與以前不一樣的內容,這讓他們更加焦慮。
李青林沒有履行任何請假手續,擅自離崗,應該除名,但學校沒有這個權力,只能將情況上報給縣教育局,等待教育局批復。學校找到李青林的父母,讓他們把宿舍的東西搬走,騰出房間給接替他代課的老師住。
青林的二叔和堂弟來到學校,兩背簍就背走了他的所有東西。堂弟建議把被褥臉盆水壺放在南宮羽的宿舍,省得結婚的時候還得往鎮子上背。
二叔的臉明顯被馬蜂叮過,額頭鼻梁上有幾個黃豆大小的坑,臉色蠟黃,表情古板,揮舞著骨節粗大的右手,哼出幾聲,才大聲罵道:自打第一眼看見這個女人,就知道不是個安生果子,眉心那么大一顆痣,簡直要把男人管死。喔,管定,管牢。
堂弟說:五嬸還說我青林哥的媳婦銀盤大臉,下巴像金元寶,標準的旺夫相,讓我以后照著這個樣子尋媳婦呢。
二叔說:尋你娘的腿,頭發長見識短,才相處多長時間,你青林哥活不見人死不見尸,好不容易掙到的鐵飯碗說沒就沒了,你嬸急得躺在床上起不來,眼睛都快哭瞎了。明明是克夫,還旺夫?旺她娘個巴子。
堂弟說:不是說他到南方發財去了嗎?要是那樣就好了,打虎親兄弟,上陣父子兵,他當老板,我給他當保鏢,兼管保險箱。
二叔把搭杵撐在背簍底下,抓住背簍帶子,直起身子,繼續大罵:放你娘的狗屁,一個李青林折騰得全家雞犬不寧,你還想上房揭瓦不成?老老實實給老子待在家里。
這些情景,李青林是不知道的,后來堂弟當然念叨過,也是片段的,不連貫的。
多年以后,綠蘿藤蔓,落地玻璃,李青林獨自喝著功夫茶,腦子里時而空空蕩蕩,時而飽滿異常。
時間過去了那么久,想起來后頸窩依舊冒汗,后怕之情還在瘋長,那是一段多么艱辛的時光啊。
火車原本直接到廣州站的,卻在漢口停了下來,停下來就沒有走的意思,有人換乘其他列車,有人搭乘長途汽車,還有人去了長江碼頭,乘坐渡輪。他不知道怎么辦,就在火車站廣場游蕩。說是游蕩,其實也沒有多大空地,地上幾乎都是移動的腳步和汗濕的屁股,太陽赤裸裸照在大地上,烘烤得人焦躁不安,干渴得嗓子冒煙。最難的,還是找廁所,離廁所幾十米,惡臭味就撲面而來。相比之下,李青林更喜歡傍晚,涼風微拂,影影綽綽,隨便在樹影墻角方便。
開始,他還期望能躺在候車室的長椅子上過夜,被驅趕幾次以后,就像眾人一樣,把提包往地上一放,或枕或抱在懷里,就地蜷縮在地上,隨時能看見星星,不敢睡得太死,怕有車出發不知道,耽誤了趕車,迷糊一會兒,竭力睜開眼睛,看幾眼星星,順便看看有沒有人奔跑,一旦有人奔跑,爬起來就跟上。
幾年教師經歷,使他更相信自己的眼睛,愈加覺得眼見為實耳聽為虛的道理,火車站廣場上的腳步,單憑耳朵就能辨析。有一回,他差點誤上了火車。幸虧聽到一個女人細聲細氣呼叫同路人,這聲音只在鎮政府的電視里聽過,是綿軟悠揚的四川腔調。迅速向車窗下面的運行區間標識字樣看去,才發現是一輛長沙開往成都的普通快車。
在廣場上睡到第三個夜晚,月色朦朧,只有幾顆若有若無的星星。迷糊間再次睜開眼睛,發現一個穿黑色汗衫的男人正彎腰蹲在一個女人身邊,一手輕輕抬起女人的臂腕,一手緩而穩地從臂腕撫下小包的帶子。女人哼唧幾聲,一翻身,側向一邊。男人將小包塞進汗衫下面,弓著腰,踩梅花樁一樣,在滿地的頭腳肩膀屁股之間繞來拐去,稍后便消失在夜色中。李青林忽地坐直身子,下意識地把手伸向自己的提包,還好,一切正常。望一眼男人逃走的方向,看一眼近在咫尺睡得正酣的女人,陷入深深的糾結中,是叫醒她,還是拔腿去追那男人?最簡單的方式是大喊一聲抓賊。正在他試圖扯開嗓子喊叫的時候,一眼就看見好幾雙眼睛正盯著他看,那眼睛有男人的,也有女人的,有壯漢的,也有老人的。盡管夜色濃重,晚風逸動,還是能分清燈光與目光。
遲疑間,將提包環抱在臂彎里,復又躺下,但睡不著,眼前總是晃著一把尖刀,對著他的臉龐。他不想睜開眼睛,也害怕睜開眼睛,怕眨眼的工夫,尖刀真的刺向自己。如果他死了,父母怎么辦?他還沒有好好孝敬父母呢,還有南宮羽,這個精靈般的女人,腦袋瓜里裝滿了遠大理想、宏偉目標,令他越來越著迷,越來越順從。相戀的日子,每天都快樂無比,能與她白頭偕老,生多多的孩子該多好。喔,不能生太多,國家不允許的,生一個也好,負擔不重。有幾間自己的房子,種一片菜地,養幾只雞,祖孫三代,衣食無憂,快快樂樂,呵呵,真好呀。
稀稀疏疏的聲音若有若無,想睜開眼睛,看看是不是有去深圳或廣州的火車,但他忍著,忍著,仿佛能聽見自己睫毛跳動的聲音。雨滴就在這個時候落下來,一滴兩滴,然后是細碎的噼啪聲。忽然,毫無提防的,撕心裂肺般的哭聲劃破夜色,穿過雨幕,響徹整個空間。猛然間站起來,聽見女人洶涌的哭號,肌肉抽搐了一下,明明知道女人就在自己的左前方,努力不看那里,深深地吸了一口氣,打了個冷戰,酷暑季節的漢口夜晚怎么還這樣冷呢?
他向車站進口處跑去,恰好一輛南下的綠皮火車進站,人們像脫韁的野馬,沖向檢票口,棍棒根本攔不住有勇氣的人,檢票口的欄桿如同虛設。李青林和眾多沒有車票又身強力壯的男人一樣,繞開車廂門口驗票的乘警,連滾帶爬從車窗爬上車。車廂的擁擠超出了他的想象,到處都是人體的各個部位,雙腳不能同時踩踏實,他的一只腳在半空懸了足有幾分鐘,轟隆隆的聲音由悠長緩慢逐漸急促高亢,車身前后晃動了幾下,就奔馳起來。如同竹筐里的青草,在搖晃顛簸中體積變小空間變大,李青林終于收住了金雞獨立的姿勢,雙腳穩穩落地。只要中途不出差錯,再過十多個小時就能安全到達廣州。從報紙上得知,那里的土地不長莊稼,長的全是廠房,廠房里全是機器,機器一轉,鈔票嘩嘩響。想到這里,焦灼感減弱,心情好了許多,眼前的艱辛算不了什么,不久的將來就可以見到廣州的天藍地闊了。
他在肩膀與肩膀之間,大腿與大腿之間,搖搖晃晃,偏偏倒倒,實在站不住的時候,眼睛一閉,腦袋一歪,呼呼睡去。
待他醒來,發現倚在一個中年男人的肩膀上,他向男人道歉,男人只是笑一笑。車廂一片光亮,依然擁擠不堪,卻還安靜。他想喝水,想去車廂與車廂銜接處找水,抻長脖子,越過齊刷刷的人頭望去,覺得這個想法實在奢侈,過道根本無法通行。喉結上下滑動,咽了一下口水。就聽到肚子咕咕在叫,用了很大力氣才彎腰從提包掏出燒餅。有人往外挪了兩步,中年男人一屁股坐在地上,差點坐在李青林的左腳背上。
男人仰起脖子望了他一眼,凸起的喉結顫抖了一下。李青林一低頭正好看見,順手將半塊燒餅遞給他,遞出去的同時,自己的臉先熱了。看那衣服裝扮,雖然不富裕,一包方便面還是買得起的。
男人笑了一下,向一側靠了靠,讓出一小塊空地,李青林會意地笑笑,趕快將包放在那里,直著身子坐在包上。他把燒餅握在手中,不知道再次遞給他,還是繼續細嚼慢咽。
男人指指廁所方向,又指指自己的肚子。他立即明白了,原來是上廁所不方便,干脆就不吃東西。看來他是有經驗的乘客,既然是同路人,應該對廣州比較了解,試圖跟他說話,男人只笑不答,大概是個啞巴,或者根本就不愿意和他交流。
窗外,稻黃樹綠,沃野千里,兩湖熟天下足,課本上是這么說的,今日果真見識了。車窗旁的小茶幾兩側坐著幾位男女,正嘻嘻哈哈說話嗑瓜子。一位與自己年齡相仿的小伙子,臉上長滿疙疙瘩瘩的青春痘,鼻子尖上的那一顆紅得透亮,如一粒飽滿的小櫻桃,大有一觸即破的樣子。他替他捏了一把汗,那粒青春痘可不能破,一破血水就射到對面女孩的臉上了。女孩笑得多開心呀,笑著笑著,將一塊圓圓的餅干喂到男孩嘴里。
就在這一瞬間,他對男孩充滿了嫉妒。酸楚過后,似乎明白了一個道理,人長得好賴不重要,重要的是要有一個屬于自己的位子。
太陽升起來了,車廂更加悶熱,醬肉啤酒甜瓜蘋果的味道在車廂彌漫,汗臭越來越濃烈,還有一種氣味李青林一時半會兒辨別不清楚。這味道以前似乎很美好,小時候在母親懷里聞到過,后來在南宮羽的身上也聞到過,那味道有種童話般的甘美,令人癡迷留戀。
又嗅了嗅,是的,的確是的,又不全是。與母親和南宮羽的味道相似,但感覺南轅北轍。
這是一種什么味道呢?
喔啊,想起來了,體味。
體味,人體的味道。人體的味道原來不全是好聞的味道,竟然這般難聞,簡直可以用惡臭來形容嘛。
悄悄的,抬起臂膀,把鼻子埋進臂彎里,只輕吸了一下,就不好意思起來。自己也不干凈,也有那種味道,體臭,哦,真的是體臭。身體不但能生發各種各樣的語言和表情,還會制造這種味道,奇奇怪怪的人呀。
正感嘆著,眼前就出現了一雙細膩白嫩的大腿,短短的月白色裙子連膝蓋都沒遮嚴實,一雙米黃色塑料涼鞋半新半舊,光裸的腳丫子上有一塊污漬,明顯是被人踩踏過的,腳趾甲有一些長了。
李青林不好意思盯著看,又不得不看,太近了,近得都快觸到額前的發梢了。抬頭仰望,只能看見女孩的下巴,下巴上有幾顆褐色雀斑。
正在他觀察琢磨的當兒,給他讓位子的男人身體扭動了一下,越過李青林的肩膀,望了女孩一眼,這一眼望得有點久。過一會兒,又望她一眼,望著望著,頭就低下了。
李青林有點詫異,將頭顱向后仰,再次仰望,女孩沒有什么稀奇的,與剛才見到的神情一模一樣。斜著眼睛看男人,男人的臉紅彤彤的,布了一層羞色,像正要向戀人表白的神情一樣。
他又仰望那女孩,從頭頂打量到腳跟,這一望不打緊,差點驚得跳起來,臉頰瞬間灼熱,羞恥感倏地升騰,恨不得立即跳出車窗,徹底消失。
自從進入青春期,就知道女孩子與男孩子最大的區別是每個月來一次月經,小時候從母親躲躲閃閃晾曬一小團一小團棉花絮開始,就意識到母親隔一段時間就神秘,隔一段時間又光明正大,初中以后,男生常拿女生開玩笑,其中就開這方面的玩笑。師范期間,學過生理衛生課,課堂上一目十行,聽的時候大而化之,老師干脆說,這節課自習。其實又特別愿意看那些文字,看到敏感的字詞句,臉熱心跳,想入非非。直到與南宮羽牽手,對女人的身體大致有了一點了解,也只是表象,還沒有實質性的進展。南宮羽生理期時也很神秘,女人一旦神秘就有吸引力,就愈加美好,愈受男人呵護。
眼前這位近得不能再近的女孩子,大腿內側蜿蜒下來一條血線,一直流淌到腳踝。他不敢看,不想看,不能看,多看一眼就是對母親的不尊重,對南宮羽的不尊重,對自己眼睛的褻瀆。
他扭捏起來,坐臥不寧,巨大的無奈狂風般襲來。如果有一塊布,一定給她遮羞。如果有一卷軟紙,一定送給她擦拭。唉唉,自己不是還有一方領地嗎?盡管只能坐下一個屁股,也能稍稍安撫一下自己的心緒,讓自己的內心平靜稍許。
他立即起身,輕輕拍了一下女孩的肩膀,指點了一下地面,頭也不回,用力鉆進人群。他不想看清女孩的臉龐,不想知道她漂亮還是丑陋。多看她一眼,就是拿刀子殺她,他在尷尬之中,她更是尷尬中人,尷尬者相遇,羞辱就平方立方地爆增。
沒有同時能容納一雙腳的地方。
不知道越過了多少人的肩膀,聞過多少人的汗味體臭,終于順著車廂靠穩。更濃烈的臭味縈繞不去,不用探究,就知道離廁所太近。似乎是條件反射,想去廁所的愿望愈加強烈,只好硬著頭皮進去,頭剛伸進去,就往后縮,沒有后退的余地,緊緊咬住雙唇,屏住呼吸,快速小便以后,“咣”地關上廁所小鐵門,張開嘴巴,仰起脖子,呼出一口長氣。
就在這一瞬間,眼角有點潮濕,特別想喊一嗓子,想哭一聲,在他二十多歲的生命歷程中,從來沒有經歷過如此不堪的旅行。
這是一種怎樣的狀態啊?怎么會有這么多人行進在如此擁擠的道路上呢?
后來,就是現在了,不到萬不得已,堅決不乘火車,即便是有了動車高鐵,依然不愿踏上列車一步。
這一切,南宮羽當然也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