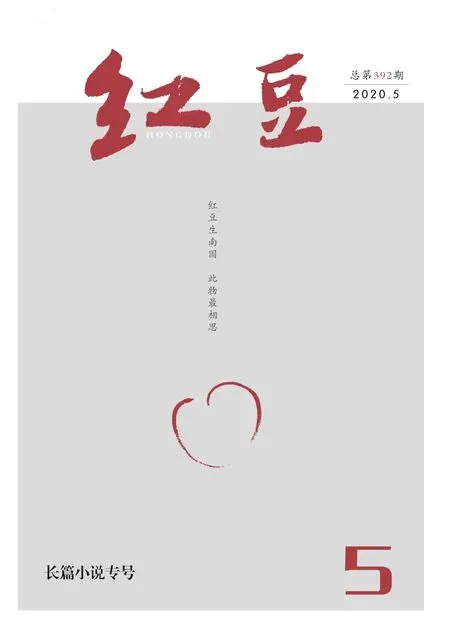原機返回
本次到西藏支教一共有六人,三位音樂教師,三位美術教師,南宮羽算作美術教師。由于她在幼兒園教過幾年繪畫,還有小學教師資格證,報名審批比較順利。不知道什么原因,六個人分兩批出發,她與一男一女兩位教師同行。
換登機牌的時候,三個人第一次見面。陽光灑滿停機坪的時候,登上了廣州白云機場至成都雙流機場的飛機,三人座位自然在一排,飛機盤旋幾圈以后,平穩飛行。
南宮羽的座位靠舷窗,女教師坐中間,男教師坐在靠過道位置。三人互通姓名就算認識了,女教師叫歐美尼,神態自信,豐韻貌美,衣著時尚。男教師身材魁梧,留一圈絡腮胡子,眼神犀利敏銳,一看就不是南方人,說不定是剛剛南下的落魄藝人呢。一開口,中氣十足的河南話就冒出來。他自我介紹,本人高宏偉,男性公民,叫我大高也中,從此咱們就是一個戰壕的戰友啦。
南宮羽推測,兩位同行者和自己一樣,來自廣東以外,屬于粵漂族。第一眼,就發現男子的頭發粗糲,烏黑,營養過剩,過剩的部分可能叫欲望。
見到高宏偉,立即想起《碧海藍天》,和戴墨鏡的外國男子同樣偉岸,甚至比他年輕俊朗。
高宏偉說:知道我那幅《東江畫廊》售價多少嗎?說出來嚇壞你們。
南宮羽一臉茫然,沒有搖頭,她怕搖頭對他不尊重,但真不知道這位同路人是畫家,畫作既然售價很高,應該很成功,大畫家干嗎支教呢?
歐美尼似乎很配合,瞪大眼睛,普通話比較標準,音色也很甜美:哇塞,太好啦,大款呀,到西藏請我們吃水果,聽說那里蔬菜水果奇缺無比。
男子說起了夾生粵語:小菜一碟,毛毛雨啦。
南宮羽輕聲問:你準備給學生教國畫還是油畫?
高宏偉說:哎喲我的姐姐噢,還真難為你了,小屁孩子,能學什么呀?隨便教點鉛筆畫、蠟筆畫,涂上五顏六色的顏料就行啦,藝術家不是教出來的,是自己冒出來的,況且還不知道藏族孩子愿不愿意當畫家呢。
歐美尼接過話茬:聽你這樣說,好像糊弄學生嘛,那你何必去西藏?聽說那里連氧氣都吃不飽,冬季漫長寒冷,夏季低溫短暫。
高宏偉說:當今社會還有這么馬列的人,你跟知青好像不搭噶嘛。知道嗎?人一輩子可以不出國,不能不去西藏,尤其是藝術家,青藏高原是一個每時每刻都生長靈感的地方,西藏是攝影家的天堂、畫家的福地。如果不出意外,支教一年,畫遍西藏的藍天白云,草原戈壁,春天的雨,夏天的花,秋天的紅葉,冬天的飛雪,到那個時候,我的畫就不是現在這個價碼了,肯定會翻幾倍。我要把莫奈和凡·高的技巧融會貫通,洋為中用,創造出屬于本人的繪畫風格,自成一派。
見兩位女士聽得專注,他繼續說:電影界有個標準,不管電影有沒有票房,只要獲得奧斯卡獎、柏林國際電影獎、戛納國際電影獎,就站在了全球電影的頂端,獲獎的男女演員終生享譽影帝影后的榮耀。音樂界也有規則,誰要在人民大會堂舉辦個人演唱會,就能登上國內一線歌唱家的寶座。能在維也納金色大廳開個人演唱會,就是世界級歌唱家、藝術大師。國內畫壇也有約定俗成的規則,畫遍江南水鄉、黃山勁松、海上日出,人物肖像,都難顯山露水,一旦涉獵西藏元素,雪山牦牛,信徒牧人,經筒唐卡,菩薩喇嘛,立即引起轟動,不但能參加各種畫展,還能獲獎,價碼像火箭一樣,飆升得連自己都不敢相信。
歐美尼側臉看一眼南宮羽,又看高宏偉,不慌不忙地說:人在大自然面前脆弱得不如一棵草一朵花,支教期間能保證身體健康,安全返回內地就是萬幸,到一次西藏就想名揚天下,純粹是癡人說夢。你以為西藏是廣東呀,有雨有花,告訴你吧,那里只有冰雹飛雪,狂風肆虐,沒有草長鶯飛,四季也不分明,除了冬天,還是冬天。沒聽說過嘛,七月草綠,八月草黃,九月下雪。六月雪,七月冰,一年四季都過冬。天氣奇冷,氧氣稀薄,有人喝完酒,走在路上,走著走著,一跤摔倒,酒醒時就起不來了。也有人只是患個感冒,稀里糊涂就死了。現在情況好多了,還有飛機可乘,以前進藏得搭汽車,聽說20世紀50年代,為了修建進藏公路,死了很多人,路基下面到處都有尸骨。
南宮羽頓時緊張起來,還是第一次聽這樣的話呢。她向歐美尼靠近一點,碰了碰對方胳臂,輕聲問:真的嗎?那么容易死人呀?
歐美尼湊近她耳朵,悄聲說:別怕,咱們去的是林芝,比藏區其他地方氣候好得多,我是嚇唬他,看把他狂妄的。
南宮羽笑了笑,透過舷窗俯瞰,霧氣還沒有散開的意思,飛機穿梭在云霧間,一團一團晨霧裹挾著機身,機翼上水珠點點。緊貼窗玻璃,想看到不同于濃霧的景象,一眼就看見一架飛機在機身下航行。她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微微閉了一下,再看,的確是一架飛機,小型飛機,但飛機周圍有一圈橘紅色的光暈。驚愕之中,重重地碰一下歐美尼,指給她看。
歐美尼傾斜著身子,差點壓著她,張望了一會,沒有發現什么。
南宮羽將臉再一次貼到舷窗上,再俯瞰,還是一圈光暈圍著一架飛機,一直向前,沒有停歇的意思。
歐美尼干脆把腰上的安全帶取掉,學著南宮羽的樣子,斜著身子向下望,同時大聲驚呼:佛光,天呀,真的是佛光。
歐美尼的驚嘆有些突兀,南宮羽一迭聲地說:聽說寺廟才有佛光,飛機上怎么會有佛光呢?
歐美尼戀戀地再看一眼,輕快了許多:聽說能見到佛光的人身體健康,生意興隆,看來咱們到西藏一路上會非常順利。
高宏偉的聲音有些變化,變化在哪里,一時半會辨不清楚,他說:佛光是自然現象,陽光照在云霧表面所起的衍射和漫反射形成,你倆看到的是一架同咱們乘坐的飛機一模一樣的飛機吧。
倆人齊聲說:是的,跟咱們乘坐的飛機一模一樣,只是微縮版。
高宏偉說:飛機在云霧夾層中飛行,陽光照在飛機上,把飛機映射到下面的云霧上,就形成了佛光,你們帶紅景天了沒有?頭痛。
南宮羽問:什么是紅景天?
歐美尼說:還沒有到成都就頭痛啦,不會吧?真把你嚇著啦,對不起,對不起。
高宏偉說:一周前我就在喝紅景天口服液,還吃了一盒紅景天膠囊,怎么天暈地轉的?
南宮羽和高宏偉的飲料杯子已經被空姐收走,歐美尼只好把沒喝完的飲料遞給他,并安慰說,大概快到成都了,紅景天口服液放在托運行李中,到成都以后,取出行李,喝上兩支就好了。
高宏偉有氣無力地說:到成都換成小飛機,但不能取行李,要到終點才能取呢。
歐美尼說:成都轉機的時候應該有賣的,你好好休息,到了我們叫醒你。
高宏偉沒有答話,沒過多久,就聽見凌亂的呼嚕聲。
忽然間,南宮羽對這對男女產生了好奇,他們怎么那么了解西藏?對進藏這件事如此重視,提前一周喝口服液,自己卻稀里糊涂,一無所知,西藏與其說是一個地方,不如說是一張白紙。
她還是提出了那個問題:什么是紅景天?
歐美尼說:到西藏這么大的事,你沒做攻略嗎?
南宮羽不好意思問什么是攻略,便微微笑了一下。
歐美尼用近乎演唱的腔調說:紅景天是生長在高寒地帶的一種藥材,有抗缺氧、抗疲勞、增強耐力的功效,我都喝好幾天了。西藏與內地不同,環境非常惡劣,至于惡劣到什么程度,我也不清楚。
南宮羽說:廣東又不缺氧,飛機上也不缺氧,提前喝不是浪費嗎?
歐美尼說:不能這么說,早一點喝,能增加體內血紅蛋白數量,提高血氧含量。這些都是從網上查到的,其實我也是一知半解,只知道飛行員潛水員運動員喜歡服用。
然后問她為什么去西藏。南宮羽本來想說去支教,想一想還是告訴她,只是喜歡,喜歡桃花盛開的地方。
倆人便有一搭沒一搭地閑聊。歐美尼說自己開一家咖啡店,每天聽各種各樣的音樂,聽著聽著,就喜歡上了唱歌,經常參加歌詠比賽,還總拿獎。拿獎也不過癮,就去世界各地拜訪諸位音樂大師,幾年下來,沒有見到幾位活著的大師,倒是拜謁了多位大師的墳墓,貝多芬,莫扎特,肖邦,李斯特等,許多大師的墓地都留下了她的足跡。最喜歡的還是捷克斯洛伐克花腔女高音格魯貝羅娃,樂壇評價她的歌聲像夜鶯一樣婉轉,夜鶯一樣圓潤光澤,顫音像綢緞一樣美艷,清泉一樣沁人心脾,有時候細若游絲,有時候直沖云霄,對她演唱的《茶花女》和《弄臣》喜愛到如癡如醉的地步。
她對這位女教師陡生好感,連連感嘆:太好啦,太好啦,咱們三個人多熱鬧哦,有畫家,有歌唱家,我水平最低,只是個學生,你教孩子唱歌劇還是民歌呢?
歐美尼說:什么都教,咱們支教的重點是傳播理想與愛,讓孩子開闊眼界,知道外界更多文明。不僅教唱歌跳舞,還講古今中外名人典故,讓他們從小樹立遠大志向,放眼全球,胸懷世界。
南宮羽說:能與你們共事,真是幸運,太感謝你倆啦,讓我大開眼界。
歐美尼說:咱們同行,但并不共事,到了林芝會被分到各個學校,大概只有到周末或節假日才能見面。
飛機顛簸得越來越厲害,仿佛擦著冰塊飛行,磕磕絆絆,間或發出隆隆聲。南宮羽身體隨機身前后晃動,收起小桌板,雙手交叉在胸前。不緊張是不可能的,心想是大飛機,廣州與成都都是省會城市,兩城之間的航班應該比較安全。瞇起眼睛,睡不著。望向窗外,艷陽高照,晴空萬里,側目低頭去看,佛光消失。一架飛機閃著銀光由遠及近,身后是移動的太陽,飛機走,太陽也走。過了一陣,太陽不見了,飛機拖著長長的白色云霧,由近及遠,徐徐而去。碧空之上,白云一幕一幕,瀑布一樣傾過來,由高到低,斜著飄拂,純凈逶迤,光滑自然。白的云絮與蔚藍的天空,將天宇映襯得靈動多姿。浮云繚繞,變幻成溝壑與山巒,河流與田野,耕牛與樹木,更多的是辨不清形狀的云彩。
顛簸沒有影響她的興致,一眼一眼觀望天空,就聽“咕咚”一聲,一個倒栽蔥,高宏偉倒在過道上。
最先沖過來的是坐在經濟艙第一排的一位小伙子。小伙子英武清爽,棱角分明,肌肉健碩,南宮羽眼前一亮。小伙子緩慢而沉穩地松開高宏偉腰上的安全帶,將他仰面朝上平放在過道上。高宏偉口吐白沫,抽搐不止。兩位空姐分別從過道兩頭走來,款款地蹲下身子。幾位乘客抻長脖子望向這邊,歐美尼和南宮羽慌忙起身。
一位身材挺拔、玉樹臨風、穿制服的空乘人員拎著一只保健箱健步而來,從箱子最先取出聽診器,聽了一小會兒心臟,伸手從座位某個位置拉出一根細細的軟管。待他從容熟練地將軟管伸向高宏偉的鼻孔,南宮羽方才明白是氧氣管。那人偏著頭向小伙子嘀咕了一句,小伙子迅速向駕駛室方向走去。
南宮羽一眼不離地看他,注視他的背部,兩肩與后腰形成一個大大的V字,雙臂擺動得很有節奏,步履有致。
“青春”二字油然迸出,接著是力度。的確,小伙子走路的樣子充滿力量,應該經過正規訓練的吧。
力度是什么呢?健康,有爆發力,活力四射,精力充沛。經濟艙與頭等艙之間掛著一道藍色布簾,簾子一動,小伙子就不見了,阻隔了南宮羽的追光。她把目光收回來,看地上的高宏偉,他臉色鐵青,雙目緊閉,嘴角的白沫已經被擦拭干凈,輸氧管直通鼻孔。再看身旁的歐美尼,已經坐好,雙拳緊握,有點發抖。她探過身子,想到高宏偉跟前,幫著做點什么。空姐制止了她,要她坐好,別緊張。
又一架飛機披著銀光迎面而來,銀色閃閃,炫目耀眼,頓時生出慌亂:高宏偉不會死吧?兩架飛機不會相撞吧?這個念頭一旦冒出,繚繞悱惻,驅趕不散。
高宏偉依然躺在過道上,沒有好轉的跡象,空姐詢問她倆是不是病人家屬。
南宮羽搖晃著腦袋,一個勁兒地說,同路人,同路人。歐美尼沒有回應,面如白紙,哽咽了一會兒,淚珠就下來了。
她說:沒想到真把他嚇倒了,對不起,不會出事吧,嗚嗚。
南宮羽愈加緊張,一共三個人,一個倒下了,一個流淚了,她該怎么辦呢?
正在她為難無奈之時,機艙響起了廣播聲,男士音調溫厚平和:由于一名乘客突然患病,本次航班需要原機返回廣州白云機場,請各位乘客諒解。飛機大約在半小時后著陸,地面溫度攝氏××度,華氏××度。
周圍頓時嘩然,紛紛交頭接耳,有人再次站起來,將目光投向高宏偉。只騷動了短短一小會兒,一切如常。
歐美尼抽抽噎噎,彎腰想要攙扶高宏偉,被空姐伸手攔住。南宮羽就勢握住歐美尼的手,歐美尼腦袋一歪,靠在她肩膀上。
歐美尼哭出了聲,哭聲無遮無掩,徹徹底底。空姐沒有阻攔她,南宮羽也沒有阻攔她,旅客像什么都沒有發生一樣,有的閉目養神,有的翻閱航空雜志。
盤旋幾周,飛機停穩,乘客全都站起身,目送擔架把高宏偉抬走。南宮羽和歐美尼被空姐叫到機艙門口,詢問高宏偉發病前有無其他病癥,倆人都說沒見異常,以前根本不認識。
空姐說:你們回座位吧,家屬已經在機場等候了。
南宮羽追問一句:不要緊吧?
原本的意思想問會不會死,“死”字快要出口,覺得不妥,生吞回去,才冒出這么一句。
空姐說:大概他沒休息好,精神緊張,情緒亢奮,血壓升高,血壓降下來應該就正常了。
歐美尼“哎喲”一聲,音調輕松了許多。
南宮羽問:血壓降下來以后,他就到西藏嗎?
空姐被問得莫名其妙,眼睛像兩彎新月。
歐美尼輕輕拽一下她的衣袖,相牽著,走回座位,剛坐好,飛機就起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