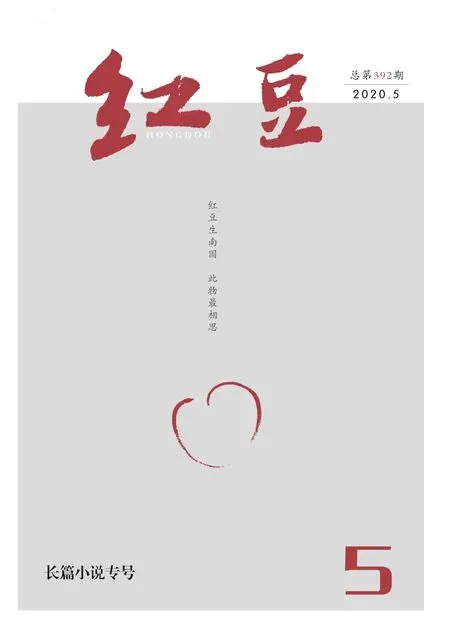她已飛
到成都雙流機場的時候,下起了小雨。
雨珠點點,變成絲線,悠悠漫漫,一條一條由上而下,天女散花一般,繽紛爛漫,連綿不斷,在天地間形成巨大的水簾。落在機翼上,濺起水花,一朵一朵,此消彼長,喇叭花一樣開放,白的花蕊,白的花瓣,白的葉蔓,白的氣息,相互勾連,相互比肩,一朵比一朵開得更璀璨,一朵比一朵消失得更瞬間。看不見天空,看不見遠方,只看見白茫茫水淋淋,裊裊曖昧的地面。
飛機降落得沉穩而緩慢,起落架著地以前,隨著機身旋轉,水簾被氣流吹成弧線,拋撒出細碎的水珠水線。著地的時候,發出巨大的聲響,既像水與水撞擊的聲音,又像機器與機器摩擦的聲音。起落架在地面劃出兩道水轍,水花像夾道歡迎的人群,激情熱烈。
終于,戛然而止,起落架停止滑行,穩穩地泊在雨花中。地面快速騰起一陣煙霧,旋即消散。
歐美尼感嘆一聲,嗨。
南宮羽收回目光,有人打開行李架取行李,有人站在過道上,等待出艙門。路過經濟艙第一排的時候,偏著頭多看了那位小伙子幾眼,歐美尼輕輕推了一下她,并說:空中警察,有什么好看的?
南宮羽側身湊近她,驚訝地說:公路上有交警,社區有片警,火車上有乘警,原來飛機上還有空警呀?
歐美尼說:自然的啦,各行各業都有帥哥。
在候機廳等了許久,一直等到肚子咕咕叫,才被告知今天沒有飛西藏米林機場的航班,要到明天才有消息。
倆人取出行李,就近住下,雨水連連,心中惶惶。第二天早晨來到機場,依然沒有飛往米林的航班,有人改簽飛拉薩貢嘎機場,她們商量了一陣,還是等待。
等待的時間里,一起吃飯,一起聊天,同時也知道了這位衣食無憂的咖啡店女老板名字的由來。歐美尼說,原來的名字土得掉渣渣,年齡越大越不好意思讓人知道,生活條件改善以后,生出改名字的主意,完全是崇洋媚外西為中用,才為自己取了這個名字。南宮羽也向她解釋自己姓氏的由來,歐美尼說如果時光倒流兩千年,她這小家碧玉連南宮羽的婢女都見不著。
介紹年齡的時候,表面上都說自己大,對方年輕,說到具體年月時,則含糊其辭,遮遮掩掩。盡管如此,南宮羽大致稱歐美尼為姐姐。
倆人一起逛了武侯祠,喝了寬窄巷子的云霧茶,吃了錦里的龍抄手鹵兔頭酸辣米粉。吃米粉的時候,歐美尼多放了一小勺紅艷艷的辣椒油,并自言自語,四川人不怕辣,湖南人辣不怕,貴州人怕不辣。
南宮羽隨口說:你的普通話很好聽,一點都聽不出方言。
歐美尼笑一笑,沒說自己是哪里人,南宮羽也沒有追問。
第三天,終于登上飛往西藏米林的航班,登機的時候,南宮羽奇怪地發現,無論是漢族人,還是藏族人,幾乎每個人都大包小包,恨不得長出千只手,再多的行李都能帶上。
當她能辨認出藏族人的時候,恍惚了好一陣,覺得這是個巨大發現。藏族人身材普遍高大魁梧,臉部輪廓比漢族人更立體,臉色暗紅,或者稱為古銅色,臉龐有曬出的紅暈。眉骨挺立,眼睛總是汪著水,有的眼神犀利,有一股穿透力,有的眼神波瀾不驚,靜若處子。相比之下,攝影展上見過的兩位藏族男女衣著更講究,氣質更大方。
一個小小少年不知從什么地方躥了出來,笑嘻嘻地望著她倆,匆匆走過,回眸間,少年還滿面笑容,覺得在哪里見過。
喔呀,在哪里見過呢?南宮羽疑惑起來。
是一架小型飛機,每排四個座位,中間一條過道,一邊兩個座位。乘客并不多,坐得稀稀拉拉。
倆人自然坐在一起,空姐在示范安全事項以前,要求乘客最好集中坐在機艙中間,保持飛機前后左右載重量平衡,防止遇到強氣流機身顛簸。
南宮羽的心思卻在少年身上,左顧右盼一番,沒有看見。
明眸皓齒清晰潔凈,眼里放射著夏日清晨太陽的光芒,她被映照得回味悠長。柳巴松的影子忽地蹦出來,那少年,不就是柳巴松嗎?飛機上那么多藏族男人女人水汪汪的大眼睛,不就是柳巴松的眼睛嗎?
柳巴松是藏族人?柳巴松原來是藏族人啊。多年以來,一直沒有柳巴松的消息,當然,她也很少與同學聯系。
怪不得他長得與其他同學不一樣,性格張揚,喜歡惹是生非,被招惹過的人大罵他丑八怪、豬八戒、怪模怪樣的小混蛋。
難怪在攝影展上見到攝影師巴松,覺得那雙眼睛似曾相識,原來柳巴松一直藏在記憶里。
她被這個驚天發現弄得臉頰滾燙,激動不已。
伸手摸一下臉頰,燙得落不住一根蘭花指。索性向衛生間走去。大部分飛機衛生間在中部和機尾,這架飛機衛生間則在靠近機頭的位置。飛機沒有頭等艙經濟艙之分,也就沒有布簾子隔斷。
衛生間外的電子屏上顯示里面有人,便站在過道上等待。
一位身著便裝的小伙子仰起脖子,對她說:你好,請坐下。
她沒有反應,依舊站著,腦子里全是柳巴松的模樣。
因為柳巴松長相與眾不同,似乎也沒人疼愛,衣服破破爛爛,吸氣鼻涕變短,出氣鼻涕變長,整日里兩條黏稠的鼻涕在鼻孔與下嘴唇之間跳躍游蕩。現在想來,他應該是孤單,才四面出擊,招蜂惹蝶,討人厭惡。趁她不注意,喜歡拽她馬尾松似的頭發,在一個同學的作業本寫上另一個同學的名字,把黑板擦藏到班長的抽斗里,給籃球畫上亂七八糟的顏色,把老師自行車輪胎扎漏氣,將螞蚱蜻蜓放到男同學的脖子里女同學的頭發上。這一切,或許是想引起關注,爭取平等與友愛吧。
小伙子又說:你好。
南宮羽低頭看他,對方的帥氣和英俊超出了她的想象,同廣州飛往成都航班上的那位空中警察一樣年輕颯爽,但比那位漢族小伙子更特別,感覺用什么樣的溢美之詞都無法準確表達,挺拔,健康,干凈,雙目含情。她向他微微點頭,算是打招呼。他也向她點頭,并伸出一只手,向身邊的空座位示意。
南宮羽想,這藏族小伙子可真喜氣呀,大概也是空中警察吧。柳巴松如果穿上這套服裝,如此彬彬有禮,全班同學恐怕都無地自容,羞愧難當。初中快畢業的時候柳巴松已經顯示出別樣的俊美,只是太單薄,青澀。
恰巧,衛生間的門開了,進去以后,擰開水龍頭澆了一臉涼水,然后望向鏡子,鏡子里映出年少的自己。課間休息時,一位女生從后面推了她一掌,額頭碰到墻上,疼得她差點哭出聲。放學鈴聲剛響,柳巴松一個箭步沖到那位女生身后,一把揪走她的紅領巾,龍卷風一樣跑到操場邊上,向上一躍,雙臂吊到櫻桃樹上,在樹枝上蕩了一陣秋千,折下一根樹枝。再一跳,雙腳著地,將紅領巾纏到樹枝上,舉起樹枝就跑。同學們嘻嘻哈哈跟在后邊,南宮羽也夾雜其中,那位女生哭聲忽高忽低,忽長忽短。南宮羽樂得呵呵直笑,時不時回頭看那女生。女生大叫一聲,追了上來。正要推她,柳巴松掉轉頭跑到跟前,把樹枝在空中一橫,大刀一樣砍下來,將兩位女生隔開。女生就勢拽下紅領巾,一溜煙跑去,飄散一路哭聲。
拍打聲中斷了她的思緒,慌忙出了衛生間,發現門外有人等候。再望那小伙子,覺得格外親切,感覺他就是當年的柳巴松,一位有意無意照顧她的少年。
送飲料和零食的空姐擋住了去路,她站在原地沒動。身旁一位中年男人面前的小茶幾上放了三只飲料紙杯,還把手伸向空姐。
空姐說:只有三種飲品,都給你了。
男子說:那就每樣再來一杯。
空姐稍稍遲疑一下,每樣飲品又倒了大半杯遞給他。男子的小茶幾上一下子擺了六只紙杯。南宮羽驚訝不已,一眼一眼地看他,發現他很精瘦。
男子大概感到有人關注,仰起脖子看她,笑呵呵地說:內地人真小氣,小碗吃飯,小盅喝茶,價錢還死貴,好不容易碰上免費飲料,不喝白不喝。
南宮羽笑一笑,沒有回應,空姐推著小車向前走去。
男子指一下身邊空位,對南宮羽說:隨便坐,隨便坐,這種小飛機不必嚴格對號入座,想坐哪里就坐哪里,跟你們內地的公交車一樣。
望一眼幾步之遙的歐美尼,正歪著腦袋睡覺,莫名其妙的,真就彎腰坐了下來。
見她坐下,男子順手遞給她半杯茶水。她擺擺手,說聲謝謝。他則一仰脖子喝了,又端起一杯,仰起脖子喝了。
喝完以后,“吧唧”一陣,連聲說:過癮,過癮,還是西藏好,想咋個吃就咋個吃,想咋樣喝就咋樣喝,自由王國,神仙寶地。
南宮羽依舊沒有搭話,微笑著,任他自言自語,自說自話。那人彎了彎腰,變戲法一樣,將一把南瓜子遞給她。
稍稍遲疑一下,接住了。握著南瓜子,不知道是吃,還是不吃,干脆握著不動。腳下被什么東西絆住了,低頭去看,是一堆包裹,將雙腳收回,規規矩矩端直坐好。
猛然想起,登機的時候,許多人大包小包,有的包袱比頭頂都高,覺得奇怪,就說:好富裕哦,這么多東西。
男子像引燃的導火索,絮叨個不停:西藏不比內地,從一個地方到另一個地方好遠喲,糧食蔬菜運輸很不方便,西藏人一年能去一次內地就是了不起的大事,大部分西藏人沒有出過藏區,好不容易到內地,回來的時候給老人買一件保暖內衣,給孩子買幾樣玩具零食,給同事朋友買點西藏沒有的香煙圍巾口紅。現在還好,很少帶瓜果蔬菜,以前西藏沒有蔬菜溫棚,長途貨車也少,人們從內地回來,個個都帶大包蔬菜水果,走親戚看老鄉,水果蔬菜是最珍貴的禮物,一個熟人總愛說他小時候過年,鄰居送給他家五個青椒,青椒炒羊肉,嘖嘖,成為他童年最難忘的記憶。
南宮羽想一想問:西藏沒有南瓜子嗎?
男子說:有,都是千里迢迢從內地運去的,價錢高得咬人。說起來通往西藏有幾條公路,川藏公路,青藏公路,新藏公路,滇藏公路,可這幾條公路你也是知道的哈,翻山越嶺,泥石流塌方雪崩啥啥都有,稀爛得一塌糊涂,不能保證天天通車。你算有福之人,有飛機可坐,成都到米林通航時間并不長。青藏鐵路也通車幾年了,火車一跑,整車皮的南瓜子、葵花籽、西瓜子、花生豆、葡萄干、怪味胡豆、炒青豆,好多好多好吃的東西都運進去,但火車只開到拉薩,從拉薩到林芝還有好幾百公里路程,技術好的司機也得開上一兩天,豆腐都盤成肉價錢了。
南宮羽說:你喜歡吃零食呀?
男子說:不是我喜歡吃,是我賣這些東西,水果蔬菜販子,我的店在八一鎮緊靠尼洋河邊上,歡迎光臨,說是水果蔬菜店,大部分賣干果。
南宮羽說:飛機進貨,夠奢侈的嘛。
男子說:不是進貨,是回老家蓋房子順便帶點干貨。飛機多方便,一個多小時就到,以前搭乘長途汽車,從成都到林芝一千多公里,路上走六七天或上十天,上車的時候互不認識,遇上河水暴漲道路中斷,患難見真情,下車的時候成為難兄難弟,有的成為終身朋友,有的結為夫妻。你第一次進藏,不知道這邊情況,有藏族人的地方,就有四川人重慶人,架線修路的,開飯館教書的,當官開出租的,當兵坐臺的,什么行當都有。
南宮羽不覺笑了起來,這人很幽默嘛,繼續說:你怎么知道我第一次進藏?
男子說:嗨呀呀,內地人西藏人,一眼就能分清楚,林芝城區幾萬人,機關單位也就幾十家,不用扳指頭都能數得清,做生意開店鋪的都是熟人,一年三百多天,通航時間就算一百天,乘坐飛機的人非貴即富,溝子大個地方,抬頭不見低頭見,誰不認識誰呀?你看,那一位,臉色多黯呀,知道嘛,她是一位軍嫂,丈夫在一個通信連當連長,每年丈夫回內地探親一次,她來林芝探親一次,結婚十多年了,還沒生孩子,焦心呀,唉唉。
南宮羽還沒看清軍嫂長什么樣子,男子又指著前兩排一位禿頂男人說:瞅瞅他,愁得頭發都沒幾根了,老婆孩子在內地,他在林芝工作,辛辛苦苦掙一年工資,全都花在路上,一年回家一次,七大姑八大姨,家家都得行禮。一輩子掙錢,一輩子受窮,你說難場不難場?
然后,男人回頭望了望后排,偏著腦袋悄聲說:后面那位藏族老頭,不知道得了什么病,林芝拉薩幾家大醫院都看了,查不出名堂,這次到成都住了一個多月醫院,你猜怎么著?好啦,高興得捻了一路佛珠,誦了一路菩薩。
正說著,飛機顛簸起來,男子伸出兩條胳膊,環成弧形,把六只杯子圍在中間。其中一只杯子里的雪碧潑了出來。一手繼續圍住杯子,一手快速端杯,喝干一杯,再喝一杯,一邊喝,一邊“吧唧”嘴巴,然后把六只空杯子重合在一起,咬住杯沿,吹起了喇叭,吹一陣,又放下。
南宮羽起身想走,被男子拽了一下衣袖,并說:這個時候可不敢動,飛機正遇上強氣流,不穩當,坐著安逸。
飛機似乎很配合,果真上下顛簸得厲害,她只好坐著不動。
男子說:西藏的飛機跟內地的飛機也不同,你知道咱這飛機上有幾位機長嗎?
南宮羽還真被問住了,從來沒有想過一架飛機有幾位機長,她眨巴著眼睛,用眼神詢問他。
男子伸出剪刀手,果斷地說:兩個,不知道吧?西藏的機場都是高高原機場,氣流多變不穩,氣溫又低,飛機一般在上午飛來飛去,不太在高高原機場過夜,怕把油路水管凍壞。清早從內地飛西藏的時候坐的人多,返回內地的時候乘客少,這與機場溫度有關,機場氣溫高載重量就會減少,就要少賣幾張機票,氣溫低載重量增加。飛機還得保證足夠的自身載油量,得保證在備用機場上空盤旋足夠時間。一個機場一般有多個備降機場,多個備降機場一般不在一個氣壓帶。所以,咱們這架飛機看起來小,乘客不滿,返回內地的時候乘客更少,就是這個原因。
南宮羽頓生興趣,問道:這與兩個機長有什么關系呢?
男子說:哎喲,差點忘了,能飛高高原機場的飛機性能高于普通飛機,一般是進口高檔飛機,對駕駛技術要求更高,普通飛機一般一個機長,飛高高原機場的飛機一般配雙機長,有的機長很厲害,還給其他機長當師傅,屬于同領域頂尖人物,吃飯都不能隨便在街邊小攤上吃,怕不安全,吃出胃潰瘍就麻煩了。
南宮羽說:感覺你像機長。
男子說:你在西藏待久就明白了,西藏不像內地,把人分成三六九等,農民沒有鄉長朋友,縣長不敢同省長開玩笑。西藏卻不同,牧民丟一只羊,直接跑到縣長辦公室,讓縣長幫忙找羊,小商小販經常同縣長一個桌子吃飯,在內地想都不敢想。
南宮羽說:你咋知道?
男子說:縣長是我老鄉,小販就是我,我們經常一起搓麻將,吃石鍋雞。
南宮羽忍不住笑出了聲,說:機長也是你老鄉吧?
男子說:機長不是我老鄉,機長的一個老鄉經常到我店里買核桃。朗縣薄皮核桃非常有名,我送給他幾斤,請他給機長說一聲,幫我機票打個折,人家不同意。
南宮羽說:下次去你店里買核桃,喔,石鍋雞是什么雞?
男子說:石鍋雞嘛,主要是鍋有特點。墨脫人用喜馬拉雅山石頭鑿的鍋,煮飯燉菜味道一絕。到林芝不吃石鍋雞就算白來,下次我請你,你到八一鎮打聽馬干果,沒有不知道的。
南宮羽笑著說:原來你是林芝名人,墨脫,墨脫不遠吧?
男子“哼哼”兩聲,才說:像你這種來一次西藏就算征服地球的人,說了也是白搭。
南宮羽說:你怎么知道我只來一次西藏?我又不是游客。
男子說:你看看飛機上的人,有幾個像你倆這樣?薄衣短衫,濃妝艷抹,告訴你吧,花架子再多的人,在西藏待久了就跟我一樣,回到出生時候的模樣。
張望出去,穿藏袍的男女臉紅齒白,有的安詳平靜,有的興奮喜悅。穿西服運動裝的漢族人,有的昏昏沉沉,有的一臉木然,她和歐美尼的著裝真的有些時尚。
望了一眼歐美尼,還在沉睡,表情似乎略有變化。
與馬干果說了再見,向自己座位走去,正要坐下,隨意地望了一眼舷窗外,這一看,立即屏住呼吸。
白雪皚皚的山巒,一峰連一峰,連綿不斷,遼遠得沒有盡頭,扶著前面座位靠背,一動不動。空姐走到跟前,伸手示意,說著什么。
她沒有聽見,依然盯著雪山。這是她從來不曾見過的,不曾想象過的景象。攝影展上,看到的雪山是立體的,局部的,此時的景象是平鋪直敘的,大氣磅礴的,坦坦蕩蕩的,無遮無掩的,俯瞰的,真實的。
她望了一眼馬干果,希望得到共鳴和呼應,他則抻長脖子與前排人說話。她無法獨自一人承受這份震驚,這份突如其來的撞擊。
空姐輕輕拍了一下她的肩膀,她還是沒有反應。這個時候,她看見了一片藍色水域,雪山與水域之間有一條貌似瀑布的白色小河,水域近旁,有幾個凹下去的漏斗樣白色坑洞。
她傾斜著身體,將臉幾乎貼到舷窗上。空姐拽了一下她的衣襟,再次示意她坐下。她坐了下來,手指卻指著窗外。
空姐微笑著說:剛到西藏不能過于激動。
南宮羽終于合上大張的嘴巴,一個勁兒地問:怎么會有那么藍的水?比珠江口的海水還藍,怎么會有瀑布一樣的白色小河?還有漏斗,雪山上怎么會有漏斗呢?
空姐依然笑著,請她系好安全帶的同時告訴她:青藏高原上的湖泊含鹽量高,即便結冰,顏色也很藍,你看到的是冰瀑布和冰漏斗。
冰瀑布,冰漏斗。哦啊,冰瀑布是不是冰舌?南宮羽激動得聲音都變了。
空姐笑一笑,緩步走開。望著空姐婀娜的背影,棗紅色印花藏袍,南宮羽方才意識到,空姐是一位藏族姑娘,標準的普通話,彬彬有禮的舉止,氣質好。
舷窗像一個磁場,全心全意地吸引著她,一眼一眼望出去,每一眼都有驚喜。后來,不需要俯視,隨意地望出去,就能看見雪山。再后來,就看見了森林山谷和一條藍幽幽的河流。
飛機在山與山的谷地中間滑翔,幾乎貼著地面,又沒有著陸。她覺得奇怪,其他機場,飛機下降的時候會盤旋,由高到低,盤旋數圈,才緩緩落地,在跑道上跑一陣就停住了。而這架飛機一直低飛,一個方向低飛,順著山谷和河流飛行,幾乎沒有盤旋,一直向前。
一片綠,又一片綠,綠到地老天荒,綠到天涯之角,飛機才停住,停得戛然而止,毫無提防。她舍不得停,舍不得這份綠,舍不得飛翔時經見的前所未有的景致。
她靠在座位上,任由大包小包從她身邊擠過,任由漢語和聽不懂的藏語在她耳畔低低緩緩流過。她沒有動,沒有站起來的一點想法,沒有離開飛機的絲毫欲念,想成為其中一份子,與環境融為一體,想把那些驚艷擁入懷中,據為己有。想一直在這架飛機上,在飛往西藏的飛機上,雪山,冰瀑布,冰漏斗,結著冰雪還藍徹心底的湖泊,還有那天空,蔚藍潔凈的天空,碧空萬里的明澈,潔白似銀的云朵。這種壯麗,這份澎湃,秦巴山間不曾有,東江也不曾有。
那些安詳的、寧靜的、表情豐富的、一成不變的臉龐,全都變得輕松、快樂、踏實,有的低頭看她一眼,有的端直走出機艙。
一個聲音傳向她:妹兒,下飛機啦,記著來找我哈,請你吃石鍋雞。
她聽見了他的聲音,記住了他的名字,馬干果。但她沒有回應,她不想下飛機,想一直沉浸在飄飄欲仙的狀態中,想讓這種氣場一直存在,籠罩她,護佑她,不滅,不朽,不離,不棄。
四周安靜下來,過道里沒有行人,空姐走近她,確切地說,是她們,她和歐美尼。那位英俊得無與倫比的藏族小伙子也走近她,她們。
空姐的笑容依舊職業,小伙子的笑容相對矜持。空姐雙手半握拳,上下疊放在胸前,微微含胸,微笑。小伙子雙手緊貼褲縫,望著她,她們,微笑。
她望向窗外,依然的綠,綠里有些色彩,一定是花朵。她這樣想著,就有走出機艙去到綠地的想法。忽地,就站了起來,安全帶在腰間擋住了她的腳步,低頭看,歐美尼還在沉睡。
搖晃著她,沒有醒,繼續搖晃,還是沒有醒。表情是有的,除了痛苦,還是痛苦,偶爾,輕輕呻吟一聲。
空姐望一眼小伙子,小伙子伸手示意她離開座位,南宮羽起身離座。小伙子彎下腰,用手背試了試歐美尼的鼻息,向空姐點了點頭。
南宮羽再次搖晃了一下她的肩膀,不輕不重地說:歐姐,到西藏了,下飛機啦。
歐美尼猛然驚醒,炸雷般地叫道:到西藏啦?真的到西藏啦?剛才夢見演唱《多么親切的名字》,學生不喜歡,把我攆了出去,那可是格魯貝羅娃的經典唱段呀。
南宮羽說:他們可能聽不懂外語,你得用藏語演唱。
歐美尼說:藏語難學嗎?我都資深成這樣了,恐怕學不會藏語吧。
倆人拎起包就往機艙門口走,走了兩步,想起應該有人接機,打開手機一看,提示有過來電。反撥過去,一位男士說在出口等候,牌子上寫有你們三位老師的名字。
南宮羽說:只有兩個人,兩位女士。
對方“啊呀”一聲,掛斷了手機。
接機口外陽光格外明艷,前面走著一位身材魁梧背著加長旅行包的男人,一手扔掉遮陽帽,一手扔掉登山杖,伸開雙臂在空中揮舞,邊舞邊大聲吶喊——西藏,我來啦!
“啪”,只一聲,男人就像布袋一樣,轟然倒下,不偏不倚倒在陽光里,背上的旅行包滾了過來。
歐美尼避讓不及,腳背被男人的旅行包壓了個嚴嚴實實。南宮羽幫忙去搬,覺得那包格外沉重,用了很大力氣都沒有移動。
馬干果雨后春筍般,不知從什么地方冒了出來,飛起一腳踢開那包,并且大叫:哎喲嗨,剛到西藏不能干重活,更不能大哭大笑,用力過猛,用情太烈,都會高原反應,現世現報,看看吧,多少人就這樣,就這樣……
有人向這邊沖過來,立即給男子吸氧施救,南宮羽和歐美尼站在原地,目瞪口呆。
馬干果催促她倆快走,并說有什么好看的,這種事在西藏天天發生,記住了,西藏可不是內地,海拔高,氧氣少,能坐著別站著,能躺著別坐著,能少出力就少出力。
南宮羽感激地望一眼馬干果,覺得他像馬戲團跑出來的丑角,渾身上下掛滿包裹,背上背的,肩上挎的,雙手拎的,腰上拴的,大大小小,花花綠綠,看得她眼花繚亂。
南宮羽騰出一只手想幫他提一個包裹,他一扭身,周身發出窸窣聲,螃蟹一樣橫在接機口。
南宮羽追問道:那人不會出事吧?
馬干果說:說不清,這種事在西藏跟喝涼水一樣,機場醫務人員已經救他了。
南宮羽問:那他什么時候能恢復正常呀?
馬干果說:這種事嘛,好比小伙子逛窯子,三眼槍打兔子,沒個準數。
說話間就看見一塊高舉的牌子,上面寫著三個人的名字:高宏偉,歐美尼,南宮羽。
看見高宏偉的名字,南宮羽方才想起那位美術教師,慶幸他原機返回廣州,若是來到這里,說不定跟剛才那個男人一樣——倒在陌生的西藏還不如倒在家門口。
她朝那牌子走去,邊走邊回頭輕喚:歐姐。
沒有回聲。
又叫一聲:歐姐。
還是沒人應她。
她把包放在地上,轉身張望,發現歐美尼一瘸一拐正往這邊來。奔過去,攙著她就走。走著,走著,心慌氣短,腿腳有點不聽使喚。心里升起一縷悲涼,出發的時候精神抖擻、豪言壯語的三個人,才幾天時間,還沒有走到西藏的田間地頭、教室校園,沒有教學生畫一幅畫,唱一首歌曲,就成了殘兵敗將。
恰在這時,歐美尼咳嗽起來,咳得上氣不接下氣。
馬干果在一旁大聲驚呼:趕快送醫院,越快越好,剛來西藏就感冒咳嗽可不是好兆頭。
南宮羽正想罵他烏鴉嘴,就被接機人喚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