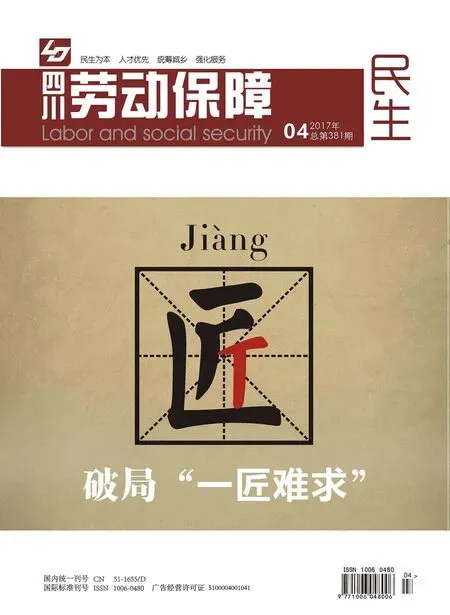高級技工去哪兒了
文/雷露
高級技工去哪兒了
文/雷露
【深度】
有報告顯示,日本產業工人隊伍中高級技工占比40%,德國占比50%,而我國這一比例僅為5%左右。今年4月,中國社科院社科文獻出版社發布的2017年人才藍皮書《中國人才發展報告(NO.4)》更是明確指出,我國高級技工缺口高達近1000萬人。
那么,到底是何原因導致高級技能人才如此匱乏?
缺乏社會認同
近年來,我國技工院校畢業生就業率一直保持在97%以上。而尷尬的是,自2009年開始,全國高職院校生源卻持續6年下降,多地招生計劃連續幾年無法完成,呈現出“就業容易招生難”的怪現狀。導致這一現象的因素有很多,社會對職校學生的歧視與偏見就是其重要一環。
家住成都市武侯區的市民楊愛國告訴記者,他的兒子在一所普通中學念高三,6月將參加高考,但孩子成績僅為中等偏下,對考大學沒把握。“不少朋友建議我將兒子送去職業技術學校學一門實用技術,但我沒同意。”在楊愛國看來,技校學習氛圍不好,而且學生大多成績差,有不良習慣,怕孩子學壞。另外,他覺得孩子讀幾年技校出來很可能淪為廉價勞動力,“哪怕就是復讀,也要上大學”。
楊愛國的想法反映了當下眾多學生和家長的心態。我國自古就有“勞心勞力”一說,在國內許多地方,孩子考上普通大學要招待親友,考上職業學校卻連門都不敢出,覺得自己低人一等。2016年初,浙江省一學校發給學生家長“不要與社會不良青少年或職高學生混一起,以防上當受騙或被欺負”的通知短信,更是在網上引起熱議,折射出社會對職業教育的偏見。
教育學家熊丙奇指出,職業教育在國外與普通教育平等、平級發展且互相流通,但在我國,職業教育卻被作為低層次教育來看待,低于普通教育。中考考分進不了普高的學生才進中職學校,而高考中,高職高專的招生也在靠后批次。“如果不提升職業教育的地位,即使大力發展現代職業教育體系,也可能會導致學生不愿意選擇職業教育,無法實現整個高等學校辦學的轉型。”
四川鍋爐高級技工學校校長郭大治對此深表認同:“許多家長認為孩子讀技校,將來做技術工人,沒有出路,面子上也抹不開。”在他看來,重仕途輕工匠,重書本輕實踐的現象長期存在,導致學歷教育“千軍萬馬過獨木橋”,不少技校盡管學生就業率高,卻因生源不足而陷入困境,“高技能人才的價值未得到社會應有的認同,這是技工教育發展舉步維艱的主要因素之一”。
未形成激勵機制
今年23歲的攀枝花小伙王晨宇是中國十九冶集團(防城港)設備結構有限公司的一名焊工高級技師,曾在第42屆世界技能大賽焊接項目中獲得第5名的好成績,被授予“全國技術能手”“2016全國焊工之星”“中國十九冶首席技師”等稱號。他在接受媒體采訪時曾透露,自己除了作為技能大師擁有每個月400元補貼外,工資收入與其他普通工人并無太大差異。“公司收入不保底,車間實行承包制,多勞多得,平均下來每月有3000元—4000元的樣子。”王晨宇在學校是佼佼者,在企業也是頂尖人才,但“收入忽高忽低”的現狀讓他有些迷茫。
“一般中職生畢業后只能從普通工人做起,月薪在2000元—3000元左右。”成都市技師學院一名老師告訴記者,很多人不愿意從事技能工作,就是因為工資收入沒有吸引力。受職業發展前景以及社會地位較低等因素影響,很多年輕人失去耐心而打起退堂鼓,“曾經在一個有30名電焊專業學生的班級中,只有3人干老本行”。
而在發達國家,許多技術工種都是高收入。在美國,水管工很受女性青睞,流行著“嫁人要嫁水管工”的說法,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就是水管工“很有錢”——其工資是一般美國人的兩倍以上。而這在美國“藍領”中還算不上拔尖的。收入最高的電梯安裝修理工,平均年收入能達到7.8萬美元,超過美國一些大學的終身教授。

川鍋公司職工在焊接大型設備(四川川鍋鍋爐有限責任公司供圖)
“技術工人整體收入不高是導致技能人才短缺的重要原因。”陜西法士特集團公司首席技能培訓師曹晶指出,一個剛畢業的技校生成長為一名高水平技工,通常需要10年甚至更長時間在臟累差環境下的專業訓練。此時他們的年齡已經40歲左右,作為家中的頂梁柱,需要在多個方面向家庭提供經濟支持,但現實工作卻難以提供與其付出相匹配的待遇,使得大批人才從現有技工隊伍中流失,從而導致高技能人才總量不足、斷層等問題出現。
人才培養問題凸顯
在川鍋技校的高級工班教學樓里,整齊劃一的標準實訓間寬敞明亮,學生們井然有序地接受著老師指導。“在過去,由于實訓場地不足,學生上實操課都是分批進行,一堂課下來基本上學不到什么。”郭大治校長表示,隨著數控、機電、鉚焊、汽車修理等實操性強的專業成為熱門,技校設施設備短缺的問題日益凸顯。川鍋技校正是基于這種形勢,不斷加大硬件設施設備投入力度,滿足教學需求。
相比川鍋技校,目前大部分技術類院校都面臨著設施設備不完善的困境,導致職業教育和企業需求難以對接。許多企業由此不敢讓職校學生來實習,怕他們不僅幫不上忙,還反把設備弄壞。“我兒子上學的職校,教學還在用我上班時用的老舊設備,不少都已經過時報廢,讓學生看一看、摸一摸,能學到啥?”退休工人黃師傅向記者抱怨。
“職業教育作為一種技能教育,需要實習實訓基地、設施設備和大量的耗材,教學設施設備需要適應市場變化不斷更新。”泰豪科技董事長黃代放認為,目前國家對教育的總體投入為GDP的4%,對職業教育的投入僅占教育投入的8%左右,有限的投入遠遠滿足不了發展的需求。
存在人才培養問題的不僅僅是職業學校。記者采訪發現,許多企業,尤其是中小企業忽視技能培訓,對工人重使用輕培養。“培養技術人才,投資時間長,見效慢不說,萬一培養出來他就跳槽跑了,豈不是虧大了?我還不如用這錢更新設備。”一家企業負責人坦言。
“想培養又收效慢,養成后留不住”已成為企業對人才培養的普遍擔憂。許多企業只能一邊招聘新人一邊流失熟手,使得人才隊伍青黃不接,并出現工人與技術發展難以匹配的現象,陷入惡性循環。樂山市夾江縣某機械制造公司負責人表示:“隨著企業發展,機器設備在更新換代。但工人缺乏深厚的理論知識,很難操作高級設備。另外,在產品標準提升后,工人也很難盡快適應新標準。”
“制造業是國家經濟的基石,工人的實際能力、經驗水平具有決定性的價值和意義,教育投入不足,將嚴重影響其正常發展。”黃代放說。
結構性矛盾突出
“文員有什么要求?”“需要出差嗎?”“試用期多長?”4月15日,在中國(成都)人才市場舉行的招聘會上,一家文化公司的展位被求職者圍得水泄不通。盡管該公司行政文員崗位月薪只有2000元,但求職者依然趨之若鶩。與之形成鮮明對比的是旁邊的一家模具生產公司,其公司招聘簡章上寫著“誠聘熟練技工,工資3000—6000元”。雖然薪酬豐厚,但卻鮮有人問津。該公司負責招聘的工作人員向記者大倒苦水:“整個上午就收到2份簡歷,其中1個的條件還完全達不到要求。”
這樣的場景絕非個例。今年年初,四川省統計局對全省261家企業用工情況進行了跟蹤調查,結果顯示:部分企業“缺工”與“招工難”并存,中、高級專業技術人才緊缺難聘,用工結構性矛盾突出。其中,熟練普工和中高級技工缺口較大,占比分別為35.5%和30.1%。另外,省人社廳統計數據顯示,全省技能人才總量680萬,其中高技能人才100余萬,現代制造業等領域高端領軍技能人才稀缺。
一方面是應屆畢業生“一崗難求”,一方面是工廠企業“一匠難尋”,以致有人戲謔:“博士碩士滿街跑,高級技工難尋找。”對此,原國家人社部副部長王曉初指出,2017年,我國進入市場的新增勞動力大約有1500萬人,其中高校畢業生達到795萬人,加上化解產能過剩、農村勞動力轉移等因素,就業壓力依然很大。在這一過程中,人力資源結構與就業市場需求的不匹配、就業人員的能力與崗位要求不適應等結構性矛盾也更加突出,“技工荒”正是表現之一。“解決這種結構性矛盾不僅需要加強職業培訓,提高勞動者的就業能力,也迫切需要從培養人力資源的源頭,從教育上著手,來解決結構性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