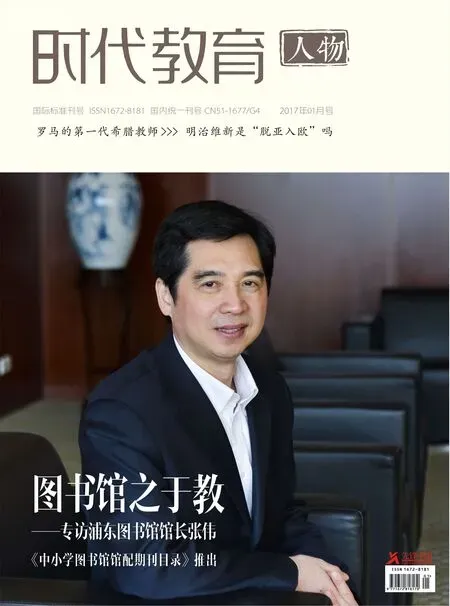關于霸凌的《告白》
文_楊軍
關于霸凌的《告白》
文_楊軍
最近最熱門的教育討論莫過于校園霸凌。事情起源于“中關村二小事件”,隨后波及媒體、網絡,一時眾說紛紜。
之所以引起多數人共鳴,大概也是此種事由來已久。只因網絡普及,一個單一事件才被大范圍關注。甚至這種關注本身也可視作一種教育社會學、心理學事件。但人們同時發現,在“眾目睽睽”之下,意見顯然被分裂了。
一方面,專家學者和有關部門更多訴諸具體的制度解決。如在學術上明確“霸凌”的認定、在學校建立“霸凌”相關干預項目以及加強法律介入等等(參見《南方周末》等相關報道)。另一方面,網友卻大張旗鼓地宣揚“打回去”(參見豆瓣社區討論“對校園霸凌說不”)。這種簡單粗暴的“辦法”隨后遭到理性學者批評。
造成分裂的原因不一而足。就社會層面,站在管理者的位置,人們自然更關注制度約束,要求加強家長、老師和學校的作用。而對大部分親歷過霸凌的網友,則更在意代入“當事者”角色的“自我反思”(不論事件當時他們是如何行為的,也試圖在事后找到應然的臨場反應),從個體層面考慮。
誠然,正如一些學者指出,“‘打回去’的校園反霸凌話語……倒更像是一種傷害”“校園霸凌指望靠小孩自己的能力來處理和解決,必然是無解的”。必須家庭、學校和社會合力介入。但考慮制度解決時,人們常常忽略了事件當事“孩子”作為真實個體的感受。如研究指出,霸凌長期發生,因為“無論男女,都不愛跟家長和老師報告”。制度解決要求作“霸凌”認定,這是困難之一。有學者無奈地說,“目前校園一旦出現問題,要么做思想工作解決,要么用道德灌輸去解決,沒有從人文角度真正走進孩子的內心世界。”可謂中肯。
事實上,粗暴地說“打回去”自然無益于解決問題,但卻正好戳中了問題的實質:即當我們自身面臨“霸凌”時,應該如何行動?(擴大言之,也可說校園霸凌就像成人社會霸凌問題的縮影,關系每個人。)
無論事件如何發生,當人們訴諸道德教育或制度解決時,并沒注意到,“告老師”“告家長”這樣的“告密”行為同樣不受社會道德或制度歡迎。沒有或不敢打回去被認為是“懦弱”,“告密”同樣被認為是“懦弱”。當事人在道德上實際處于“孤立”境地。其次,尤其在國內,當事件解決時,也通常是在家長之間達成意見,而很難深入孩子內心。
常常發生的情況是,小孩“告密”后,他可能在同學中更不受待見,因為“愛打小報告”的行為更容易受到“霸凌”。這也是在西方校園建立“霸凌干預機制”后霸凌同樣嚴重的原因之一(如美國校園霸凌幾乎和槍擊案一樣嚴重。但正如槍擊案,也無法簡單通過槍支管制法案解決)。
由此,與其泛泛談論“愛的教育”“包容的教育”,一團和氣,在完善制度的同時,尤其在如今社會矛盾復雜的背景下,更應去關注兒童內在的成長,讓孩子自己強大,引導孩子直面“霸凌”。“打回去”固然不好,但“打回去”的背后正是要求個體的獨立和勇敢精神。由于社會制度變遷,在現代學校教育中,雖仍有“勇”的教育,但由于缺乏實質操作手段,常常只是一種“書面語”。這正如社會上經常表彰“見義勇為”,而在事件當時,人們卻慣于“冷眼旁觀”。人們習慣制度解決時,就忽略了有關“勇”的責任、技巧和智慧的(這也是面對“中關村二小事件”時,知識分子和網友表現截然不同的原因)。
在傳統教育中,無論中外,“勇”被作為一種道德品質的同時,也賦予了相應的技巧和智慧教育(希臘四德行:智慧、勇敢、節制和正義)。在古希臘城邦,公民教育不僅要求“三藝”(即文法、修辭、邏輯等),還要求嚴格的體育訓練,學習戰斗方法。其體育項目田徑、球賽、打獵、擲鐵餅、擲槍矛、拳擊和角力等都帶有軍事實戰性。其中極端者如斯巴達尤其強調武藝練習、全民皆兵。而在雅典,這種訓練不僅在應付戰爭,更注重和平,作為靈魂的修養。柏拉圖在《拉克斯》中談論“勇敢”時,就由兩位大將軍的爭論入手,而后蘇格拉底以“助產術”辯明勇敢和智慧對靈魂的提升。
同樣,在中國封建時代,“勇”也作為“三達德”(智、仁、勇)之一,通過“六藝”教育完成。射御不僅是一種武術訓練,同時也是禮。如《論語》言:“君子無所爭,必也射乎!揖讓而升,下而飲,其爭也君子。”孟子更說:“仁者如射,射者正己而后發。發而不中,不怨勝己者,反求諸己而已矣。”在徐浩峰電影《箭士柳白猿》中,柳白猿以箭術仲裁武林糾紛,其師父訓練他說“你的箭射出去了,還沒收回來”。所謂“收回來”,正是“反求諸己”的意思。“勇”的技巧和智慧的訓練同時包含著“打出去”的氣勢和“收回來”的德行,即文武之道。
換言之,道德教育不應是空話,本身就包涵了相應的技巧和智慧(“勇者不懼”,而“仁者必有勇”)。對比古今,這可謂正是今日德育中所缺乏的:體育和武術教育過于注重形式,德育過于注重訓誡,相互脫節。針對校園霸凌問題,道德教育和制度干預自然不可或缺,但“固本”更是關鍵。正如《論語》中子貢和孔子討論:我不欲人之加諸我也,吾亦欲無加諸人。孔子說:非爾所及也。成人一味訴諸制度干預和道德教條,而孩子在“加諸我、加諸人”的真實處境中不也正是“非家長和老師所及”嗎?

告白 (2010)
導演:中島哲也/日本/劇情/日語/106分鐘
在這部電影中,教師森口悠子的女兒死于班上兩個學生之手。警察雖認定為意外,但森口決定以自己的方式“復仇”。在辭職前最后一堂課上,她靜靜地向學生做告白,不動聲色地指責犯人A和B,并宣布“復仇”。這部電影可算是日本長期以來“校園霸凌”現象的縮影。在視聽效果上,電影畫面以冷色調的高速攝影鏡頭和舒緩音樂為主,突出了當事人的心理活動,最終將校園問題帶出校園,不以批判學生和教師或是教育體系的矛盾為題,而是直面復雜的個人處境。

欺凌Bully (2011)
導演: Lee Hirsch/美國/紀錄/英語/128分鐘
這是一部講述美國青少年在學校、街頭包括家中遭受欺負甚至被虐待、射殺等嚴重問題的紀錄片。電影上映后,被美國電影協會定為R級(主要因語言粗俗)。但密歇根州一位高中學生Katy Butler自發征集簽名,請求協會將影片分級修改為PG-13,以便更多人可以看到。據美國教育部統計,校園霸凌事件逐年遞增,2016年就有23.1%的中學生自承遭受霸凌。Katy Butler還曾于2010年在網絡發起簽名,征集超過5萬人簽名,廢除了一項她認為可能導致宗教與精神方面欺凌的法案。

箭士柳白猿 (2012)
導演:徐浩峰/中國/武俠/普通話/90分鐘
徐浩峰的作品還原了真實的武林世界。在民國武行中,沒有太多過往武俠電影宣傳中的行俠仗義,而更多是社會矛盾和世情的展現。在《師父》中,師徒的道德關系更被降到最低點。然而,在動作的還原和道德解構中,自有人情在。

忠臣蔵 花の巻?雪の巻 (1962)
導演:稻垣浩/日本/歷史/日語/207分鐘
改編自日本家喻戶曉的赤穗藩武士47人為主君報仇的事件。《忠臣藏》在日本戲劇和電影史上一直長盛不衰,有似中國之《三國演義》。影片除了以表現傳統道德為特色,同時也和武俠片一樣注重武打賣點,稱為“劍戟片”。日本武士階層消失后,其劍道、弓道等修身方法還一直保留為學校教育項目。日本社會至今仍帶有極強的“封建”色彩。另推薦電視劇《半沢直樹》。
志藝
COLUM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