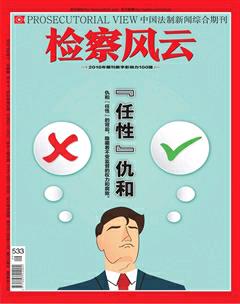布雷迪案:辯護交易何以合法
林海
“自愿”認罪:有時并不心甘情愿
所謂辯訴交易(plea bargaining),是指被告人以放棄庭審權利為代價,與控方就指控和量刑達成協議,并經法官審查和認可后,在不經歷完整的庭審的情況下,就能結案的一種案件處理方式。這一實踐在19世紀就已經在美國出現,進入20世紀后得到突飛猛進的發展。目前,在美國,適用辯訴交易方式處理的刑事案件比例在95%~96%之間,在英國這一比例也高達87%左右。雖然辯訴交易實踐在美國已經有至少兩個世紀的歷史,但是直到1970年的布雷迪訴美國案(Brady v. U.S.),這一制度的合法性才被聯邦最高法院以判例的形式確認。提起訴訟的人叫約·布雷迪。1967年,他以原審判決錯誤為由,向聯邦最高法院提出申訴,要求法院釋放自己——此時,他已經在獄中度過了八年時間。案件要從1958年6月說起。時年25歲的無業青年布雷迪愛上了有夫之婦南希·博布里特,還讓她懷上了自己的孩子。一貧如洗的布雷迪決定弄點錢來養家糊口。于是,他和南希的兄弟唐納德·博布里特合謀,打算搶劫銀行。為了實施搶劫,他們還需要一輛速度快、性能好的汽車。布雷迪提議,竊取其朋友布魯克斯新買的一輛福特汽車。于是,6月27日,他們在布魯克斯家附近的馬路上橫了一根圓木,守候在那里等他回來。當布魯克斯停車下來移動圓木時,兩人從隱蔽處跳了出來,用獵槍擊打布魯克斯的頭部,隨后將其拖到汽車后座上。布雷迪開車將昏迷的布魯克斯帶到事先預謀“動手”的一處空地。兩人用襯衫勒死了布魯克斯,并將尸體搬到樹林深處拋棄。但是,自始至終無法弄清的細節是,到底是誰下手勒死布魯克斯,兩人對此都不承認,且分別指稱對方“才是動手勒死布魯克斯的人”。這一細節查不清楚,就無法對兩人定罪量刑。
布雷迪對警方表示,想偷車、出主意、用槍管擊打布魯克斯,都出自自己之手。但是,他否認自己有謀殺的故意和行動。當兩人將布魯克斯搬到車后座上后,博布里特想用槍打死布魯克斯時,他還出言阻止;博布里特堅持要勒死布魯克斯時,他就沒有再說話。然而,博布里特那一面的證詞卻不能支持這一說法。他先是稱自己才是勸阻同伙的一方,而后又提出,布雷迪和他共同作出了滅口的決定。勒死布魯克斯,是布雷迪的主意,自己不過是個執行者罷了。
1959年7月,對于布雷迪的審判開始了。他因觸犯聯邦綁架法而受到綁架指控。依照綁架法(a)條款,如果受害人在解救時已受到了傷害,在陪審團的建議下,可以對被告判處死刑(以下簡稱死刑條款)。由于在該案中,指控書認定,受綁架的受害人被解救時已死,因此如果經審判團審判,布雷迪可能將面臨死刑。
但是,由于案件的細節錯綜復雜,布雷迪和博布里特互不認賬,控方摸不清細節。如果交由陪審團判斷,說不定也會因“證據鏈條不成立”或“無法排除合理懷疑”而導致罪名不成立。為此,控方和辯方最終達成了協議,布雷迪承認搶劫罪成立。在審判法官兩次詢問,他接受“有罪答辯”是否出于自愿之后,法官認可和接受了他的有罪供述。布雷迪被判處50年監禁,后來被減刑為30年。最后,服刑至18年時他得以假釋出獄。
有趣的是,當服刑至第八年時,布雷迪和他的律師決定“放手一搏”,提出申訴。他認為,他的有罪答辯是在“非自愿”的情況下做出的,理由有三點:第一,他當時受到“死刑條款”的恐嚇,擔心再進行審判,會被判處死刑,從而失去了理性的判斷力。第二,他當時的辯護律師向他施加了不應當的壓力——這就是前面說到的,法律專業人士的冷漠合謀,只想著盡快結案收錢,而未為當事人進行利益最大化的考慮;第三,他當時受到了減刑和寬大處理陳述的引誘。事實上,他被認定有罪之后,仍然被關押在死刑囚牢內“服刑五十年”,所謂的寬大處理顯得并不那么有說服力。
布雷迪主張,審判法官并未完全遵守聯邦刑事訴訟規則第11條有關審查有罪答辯自愿性的條款,要審查他是不是真的“心甘情愿”接受辯訴交易。然而,在舉行聽證后,新墨西哥地區法院駁回了他的申訴。法院先是認定,辯護律師并未向他施加“不被允許的迫使他做有罪答辯”的壓力,所謂的“減刑和寬大處理的承諾”也并不成立。法院認定,布雷迪做出有罪答辯,是因為他意識到他的共同被告將做有罪答辯,而不是因為“死刑條款”或法官的任何行為。新墨西哥地區法院得出結論:“答辯是在自愿和明知的情況下做出的。”
辯訴交易合法性的基礎
布雷迪不服,上訴至聯邦第十巡回上訴法院。在上訴法院維持新墨西哥地區法院的裁決后,他進一步訴至聯邦最高法院。此時他援引了1968年的一項判例,來支持自己的主張,這就是美國訴杰克遜案(States v. Jackson)。杰克遜同樣被指控犯下綁架罪,但法院認定“死刑條款”違憲,因為該條款僅根據陪審團的建議就可以判處死刑,從而迫使被告必須以放棄陪審團審判為代價來規避死刑。聯邦最高法院同意了地區法院的意見,認定綁架法中的“死刑條款”向被告施加了不合理的負擔。
然而法院提出,這并不意味所有受威懾于死刑條款做出的有罪答辯,都是無效的。聯邦最高法院在判決書中寫道:“死刑條款有可能會使那些堅持無罪和要求陪審團審判的人感到氣餒,但這并不意味著每個按照有罪答辯的人都是在不自愿的情況下做有罪答辯。”只要答辯是自愿和理智的,就是有效的,和是否存在死刑條款的威懾無關。而且,辯護交易的核心并不是最終被告會被定什么罪,而是被告是否自愿接受認罪,成為不利于自己的證人,并放棄第五修正案不得強迫自證其罪的特權。
懷特大法官在判決書中寫道:“答辯不僅僅是對過去行為的承認,它也表明被告已經同意,可以在沒有陪審團和法官審判的情況下作出有罪判決。放棄憲法權利不僅必須是自愿的,而且必須是知情的和理智的行為,必須是在對相關情況和可能的后果有足夠的了解的情形下做出的……不管基于以上哪一點,布雷迪的答辯都不是無效的。”
如果認為存在死刑條款,就認定有罪答辯皆為被迫,那么,是否也意味著,只要存在判重罪的可能,被告產生了畏懼心理而接受辯訴交易的,只要有朝一日被告提出自己“并非自愿”,那么這些辯護交易都應當推翻呢?聯邦最高法院在判決中寫道:“盡管政府行為對于刺激辯護交易的達成,負有一定的原因和責任,但是這并不意味著所有這些答辯都是無效的。決定是否自愿,關鍵在于當事人當時的理性與決斷。”當然,控方不可以通過威脅或強迫的方式,達成辯訴協議。但是在本案中,這些情形并不存在。相反,有證據表明,布雷迪在律師的幫助下,理性地衡量了庭審和認罪之間的輕重利弊。可以說,是理智而自愿的。
因此,聯邦最高法院認定,布雷迪的有罪答辯是理智的,他知曉指控的性質,沒有證據表明他是在失去理智和能力的情況下做出有罪答辯的。他是在共同被告認罪并可能出庭指證他時,為了確保不會面臨比終身監禁更嚴厲的懲罰而做出有罪答辯的。布雷迪在認罪時能夠準確認識到自己的所作所為。因此,懷特大法官在判決書中這樣寫道:“盡管布雷迪的有罪答辯,可能部分是受到避免可能的死刑這一動機的影響而做出的,但是我們確信他的答辯是自愿和理智的。我們沒有理由懷疑他所做的嚴肅的認罪行為的真實性。”
最終,被駁回申訴請求的布雷迪就這樣在監獄中度過了十一年的時光。他一直保持著沉默。盡管他有權就量刑問題重新提起申訴,但他最后也沒有行使這一權利。控方其實也有權重新審判布雷迪,但是他們也保持了辯訴交易的穩定性。雙方都均未采取任何行動。布雷迪被轉移出了死囚牢,在很多監獄關押過。他甚至在獄中和一位來自巴爾的摩的護士結了婚。假釋出獄后,他移居南部,成為了一名卡車司機。余生再未惹上嚴重的法律麻煩。在這個意義上,辯訴交易對于他的人生還是有積極意義的。如果不能定罪,也不能脫罪,那么他的一生,或許還將在無窮盡的偵查、重審與羈押中度過。檢察官們恐怕也無法在“疑案從無”的正當程序,與“打擊犯罪”的職業使命之間完成平衡。
自此一案后,辯訴交易的正當性基礎更為明晰了。被告在接受有罪認定時,應當是自愿和理智的——這是司法對其自我意志的尊重,也是對于社會秩序迅速恢復的一種期待。在這個意義上,被告或許并沒有放棄憲法上的“不得被迫自證其罪”的權利——因為,他是自愿而非被迫。然而反過來,如果確實能夠證明,檢察官與律師,在某種職業的自私與自負的引領下,讓被告不那么理智或自主地做出決定,或許這樣的辯訴交易就將失去正當的基礎,并成為對于被告權利和憲法秩序的再一次傷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