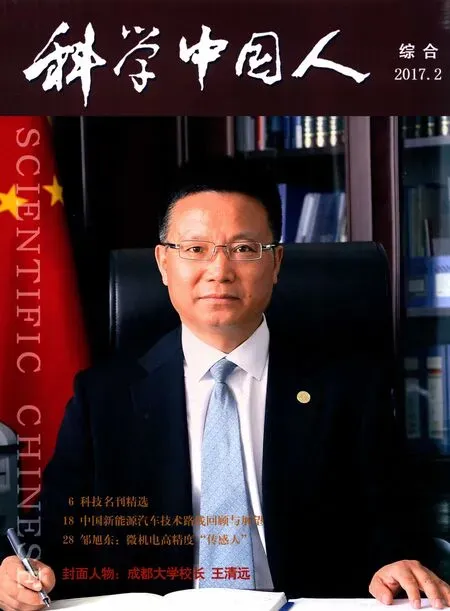“幸運”的奮斗者
倪萍

生活往往會在某個時刻為我們打開一扇窗,讓我們看到一個嶄新的方向,王金輝的人生就印證了這一點。以他的話說:“我能走進腦科學這個領域,其實蠻幸運的。”
新的方向
讓我們把時間拉回到2006年,這一年年初,西安電子科技大學四年級學生王金輝正在等待研究生復試通知。時值北京師范大學認知與學習國家重點實驗室成立不久,認知神經科學在國內尚屬新鮮事物并未走入大眾視野。機緣巧合之下,出身電子信息工程專業的王金輝幸運地得到了北京師范大學認知神經科學與學習國家重點實驗室伸來的橄欖枝,并成功地通過了面試,自此開啟了人生的新篇章,“雖然對我來說,這是個新的領域,但是我還是決定一試,”王金輝說。
然而真的到了新領域,王金輝才發現,他不得不面對晦澀難懂的英文專業詞匯、紛亂復雜的大腦解剖結構、宛如天書的數學公式等,這令他一度迷茫甚至想要放棄,“直到研究生二年級,我都沒有入門,更別提找到合適的研究方向”。正在這時,他聽到了賀永教授(著名腦網絡研究專家)的一場學術報告,“通過賀永教授深入淺出的講解,我對腦網絡研究領域產生了濃厚的興趣,并在碩士導師的大力支持下開始跟隨賀永教授開展腦網絡方面的研究。”
多模態磁共振成像技術是研究活體人腦網絡的最主要手段,如何從磁共振圖像中提取穩定可靠的人腦網絡是本領域面臨的核心問題,該問題的解決是其得以臨床應用的前提。在眾多可能影響腦網絡穩定性的因素中,以合理劃分腦區進而定義腦網絡節點最為關鍵。針對于此,王金輝率先采用不同的腦圖譜構建了人腦功能網絡,證實了人腦功能網絡受到腦區劃分方法的顯著影響。該成果順利發表在國際著名期刊Human BrainMapping上,并入選了ESI Top 1%高被引論文。“這對我來說是非常大的鼓舞,堅定了我繼續開展腦網絡研究的信心。”王金輝說。
碩士畢業后,他直接轉到賀永教授門下,全身心地從事基于磁共振技術的活體人腦網絡研究,談起過往,王金輝總會說自己很幸運,但這個轉變的過程并不輕松。腦科學屬于典型的多學科交叉,作為一個門外漢,需要惡補大量的知識。不懂,就從頭學。那時候,他沒少跟資料或者公式較勁,對他來講,既然當初選擇了,總得摸索出點門道來。
“我想一個人不論從事什么行業,不論起點有多低,只要有一種不服輸的精神,并將其至始至終貫穿下去,那么成功遲早會到來。”王金輝說。封面“達人”
2012年,王金輝接過了博士畢業證,來到了杭州師范大學認知與腦疾病研究中心任研究員。今天,在認知神經科學領域,他已經嶄露頭角,經過數年的積累,發表了多項原創性成果。
復雜腦網絡在腦疾病中的應用是王金輝的一個關注點。輕度認知障礙是正常老化和阿爾茨海默病之間的過渡狀態。他首次證實該階段患者的大腦默認網絡內部以及不同網絡之間的功能連接異常降低。“這些異常不但與患者的認知缺陷顯著相關,更能以高正確率區分患者和正常對照,表明腦網絡失連接特點在阿爾茨海默病早期輔助診斷和預警方面的重大應用潛力。”王金輝介紹說,該研究成果發表在國際權威期刊Biological Psychiatry上,不但被選為封面論文,更是入選其2013年度最杰出的論文(12篇文章入圍,排名第一),并入選ESI Top 1%高被引論文。王金輝也因此榮獲2014年生物精神病學協會頒發的Ziskind-Somerfeld研究獎。在此基礎上,他進一步闡釋了載脂蛋白E-4等位基因這一公認的阿爾茨海默病的遺傳風險因素,是如何調控患者的腦功能網絡的,相關研究成果再次以封面論文形式發表Y~Human Brain Mapping。
“抑郁癥是一種多神經環路紊亂的精神疾病。我們首次研究了抑郁癥患者的全腦功能網絡,發現患者默認網絡區域表現出功能連接的異常增加,而且這些異常增加與患者的病程和疾病嚴重程度顯著相關。”這些發現為抑郁癥的病情監測和治療評價提供了全新思路。該研究成果以封面論文形式發表在Biological Psychiatry。根據ScienceDirectTop 25 Hottest Articles(2011.7-9)排名,該論文位列Biological Psychiatry雜志最熱門論文排名第一位,并入選ESITop 1%高被引論文。
這些腦疾病應用研究的成功,需要堅實的方法學基礎做后盾。事實上,早在這些臨床應用研究之前,王金輝就開展了多項腦網絡的方法學評價工作,詳盡對比了不同分析策略下腦網絡的可重復性和重測信度。這一系列的方法學評價研究為疾病條件下的腦網絡應用研究奠定了堅實方法學基礎。在此基礎上,他和同事一起開發了腦網絡分析平臺GRETNA。該平臺囊括了當前主流的分析方法,實現了腦網絡分析的自動化流水線作業,大大方便和促進了腦網絡研究的開展。
過去的收獲都是積淀,現在和未來才是王金輝所注重的。基于結構磁共振成像的形態學腦網絡在人腦連接組學研究中發揮著不可或缺的作用。然而,當前的形態學腦網絡研究主要是基于群組水平的形態學共變方法,該方法忽略了解剖結構的個體間變異,嚴重限制了形態學腦網絡的神經生物學意義研究和重大神經精神疾病的生物標記物開發。“鑒于此,我們團隊正致力于開發一套系統,基于結構磁共振圖像的個體形態學腦網絡分析方法,全面評價這些方法的魯棒性和重測穩定性,為其實際應用提供方法學建議和指導。”他說。教學雙“靶點”
身為一名師者,王金輝很重視學生“寫文章”的水平。通過多年的學習和工作,他覺察到科研做得好的人,都是撰寫論文的高手。“他們對科研文獻信手拈來,在不失嚴謹和保證科學嚴肅性的前提下,能夠以一種科學特有的美感帶領讀者迅速進入相關情境,接受新思想、新發現的洗禮。”王金輝贊賞道。在修改學生論文的過程中,他發現了學生們的一個通病,就是冗詞贅句過多,語句間、段落間缺乏銜接。
“這看起來似乎問題不大,但實乃撰寫科研論文的大忌,這樣的論文,只會讓讀者抓不住重點,最后變得讀之無味,棄之可惜。在這個知識爆炸性增長的時代,單刀直入、直奔主題無疑是一個很好的選擇。”他說。在此基礎上,王金輝還要求學生注重語句過渡、行文邏輯,把論文寫得行云流水般優美。“這樣的效果要遠好于用華麗的辭藻堆砌出來的文章。一項研究成果無論有多重要,如果由于我們表達的問題而無法被同行們所理解,最終被束之高閣或者延遲發表,這將是一件多么令人惋惜的事情。”
發揮學生的主動性是王金輝開展教學工作的另一個著重點,他要求學生摒棄一遇困難就求助的習慣。“我經常會遇到學生沒有對問題進行深入思考就提問的情況。這樣的習慣其實并不好。一遇到困難就尋求幫助,會抹殺一個人的主動性,長此以往,學生便會喪失獨立思考、解決問題的能力。而獨立思考是科學研究中必不可少的關鍵。試想,如果人云亦云,跟在別人屁股后面做科研,能產生什么價值?”
那么,遇到問題該怎么辦呢?每當學生向王金輝提問時,他通常先要反問:“你做了什么準備工作?查了什么資料?做了什么樣的嘗試和思考?”然后他會帶著學生把一個看起來很“宏觀”問題分解為多個細節,再去逐一解決。“值得欣慰的是,現在,我的學生在這方面做得已經非常好了,通常任務布置下去后,他們會主動尋找不同的途徑來解決問題,甚至在某些方面他們已經是我的老師了。”王金輝高興地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