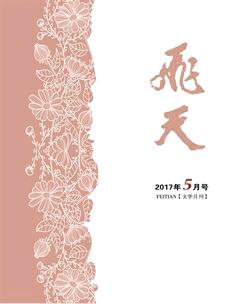在雨天與通渭書家劉小農(nóng)喝茶
爾雅
到達劉小農(nóng)的工作室的時候,是下雨的天氣。從窗戶望出去,可以看見文化廣場上巨大的、鏤空矗立的繁體字:書。雨水讓它顯得濕潤清晰。人們從街道上走過,汽車濺起水花。雨水的聲音密集,行人與車輛逐漸稀少。整個縣城看上去像是一幅靜物水彩畫。
小農(nóng)在工作室里等我,他的笑容帶了些許羞澀,像是鄉(xiāng)村里未曾遠游的少婦。他也從雨中過來,衣服和頭發(fā)被雨水打濕。他在房間里走動,擺茶具、倒水、拿煙卷、找他以前貯存的茶葉。他有很好的茶。然后他說,下雨好,安靜。
我也喜歡雨天。空氣清新濕潤,書架上的器皿和書籍有一種溫婉的光澤。墻壁上懸掛的字畫和字畫里的詩句一樣美好。雨天還有植物、花朵和田野的氣息,令人想起感傷又快樂的少年時光。時間過得好快。我們聽見窗外清晰的雨水聲音,像是某一種美妙的樂器。有時候,我們保持沉默。聽見茶湯漸次沸騰,然后徐緩傾倒在茶杯里。我們都喜歡這種聲音,它們比言語更美妙。
茶具被隨意擺放在一個角落,看上去尋常,其實是非常考究的器物。茶杯和茶壺是柏彩汝窯,釉色如璞玉,紋路如蟬翼。燒水用手工鍛造的生鐵壺。茶臺是一方古老石磨,粗糲拙樸,居然是漢代的文物。是他田野考古時,從民間收購而來。書架上還擺放了若干新石器時代的紅陶和彩陶。它們互相映照,像是舊年閣樓里幽暗處的線裝經(jīng)卷。小農(nóng)曾經(jīng)送我一個新石器時代的陶碗,可惜弄丟了。一張巨大的書桌靠近窗戶。筆墨、紙張、硯臺和書籍散亂地擺放。禿筆與新鋒在一起簇擁。墻角堆放著被丟棄的宣紙,紙上是他的文字。墨汁的氣味彌漫開來,輕盈清晰,像是茶湯經(jīng)過喉嚨之后留下的某種細微的回甘。
有些時刻,恍然覺得置身于古老漫長的舊日時光。在漢代,這里只是一座小小的邑鎮(zhèn)。渭河從河谷里緩緩流過,河水清澈,水里是斑斕溫潤的石頭,魚類在石子間游弋。岸邊是繁花綠樹,蜂飛蝶繞,鳥群飛翔。人們穿著粗布衣裳,在田陌上勞作。邑鎮(zhèn)安靜,道路寬闊,一輛馬車從青石鋪就的路面上緩緩駛過。馬車里是官府的文書,或者是一位盛裝出行的富家少女。整個白天,街道上只有這一輛車子經(jīng)過。那時候在官邸中,一位邑鎮(zhèn)的官員正陷入濃烈的相思。他的妻子因病回鄉(xiāng),不能和他一起吟詩酬唱、虛度時光。他手握筆豪,在柔軟細密的素絹上寫下思念的詩句。他寫道:“省出情凄愴,臨食不能飯。獨坐空房中,誰與相勸勉?”這些詩句被包束整齊,送到他遠方妻子的手里。那時候的信使緩慢,很久之后才能送達。又過了漫長的時日,妻子的回信到來,也是濃烈又憂傷的詩句,寫在發(fā)黃的素絹上。她寫下:“瞻望兮踴躍,佇立兮徘徊。思君兮感結(jié),夢想兮容輝。”邑鎮(zhèn)的人們目睹了他們偉大的愛情,傳唱這些美妙憂郁的詩句。
兩千年過去,世間的繁華苦厄煙消云散,只有這些詩句留了下來。古老的詩句散發(fā)出光芒。它們排列成整齊的文字,在整潔細密的紙張上起舞。在遙遠的年代,這些文字會被書寫到有著植物氣息的絹帛上,它們看起來更美,是熱烈愛情的一部分。那些溫婉哀傷的詩句和書寫詩句的過程,甚至比愛情更長久、更令人懷想,因為它們可以讓愛情不朽。
有時候我就坐在這里。小農(nóng)說。他坐在一把高背的紅木椅子上,正對面是一排書架,書架上擺滿了各種書籍。他凝神看著它們。他說,要是沒有別的事,我就這樣坐著,一個人,很長時間。我在心里想,每天能喝點茶、看看書、寫寫字,不想別的事,我就很滿足了。
他說話的時候,還在看著對面的書籍。他的眼神里有細微的迷離。退守書齋是一種浪漫的期望,在安靜的雨天,這種期待也許更加強烈。但是,作為一個聲名遠播的書法家,他必須與窗外的生活產(chǎn)生聯(lián)系。他需要在閱讀和煙火之間建立平衡。
他的作品出現(xiàn)在各種場合:新開業(yè)的酒店大堂和房間、展覽會、小城居民的客廳和居室、紙質(zhì)媒體的專題報道,以及書畫村中多家畫廊的門匾。人們談?wù)撍淖髌罚埶麑懽郑行┤藦暮苓h的地方來,希望得到他的作品,有些人請他辨認碑帖上生僻的文字,以及一些古舊字畫和器物的鑒定。有兩三年的時光,我經(jīng)常從蘭州驅(qū)車到縣城里。我在寫一部小說,小說里涉及到古代書畫作品的鑒別、流傳、修復(fù)與揭裱問題。這些專門的知識大部分都由他提供。他提到的很多知識很難從網(wǎng)絡(luò)或者普通的書籍上得到。在小說的后記部分,我特別提到故鄉(xiāng)的這位書法家,為的是表達我的敬意與感謝。時代喧嘩,幾乎所有的知識都混同于信息的泡沫,以點擊搜索引擎的方式充斥于紛亂的時空。找到一位擁有專門的甚至生僻知識的人,可以想見有多么艱難!
人們看到他的篆刻與書法作品,看到他的溫和、靦腆和從容,還有人在好奇地揣測書法家的聲名為他帶來的光芒和物質(zhì)回報,正像人們通常對一個成功藝術(shù)家的反應(yīng)。相比于其他的藝術(shù)門類,人們會說:一個書法家的書寫簡單、隨意、自由、輕松。他光鮮體面,回報豐厚。這讓人羨慕。
實際的情形當然并非如此鮮亮。很可能當我們虛度時光的時候,他已經(jīng)開始了隱秘、持久的閱讀。他退守一隅,在昏暗寂靜的燈光下勤奮學(xué)習(xí)、刻苦訓(xùn)練。他隱藏了自己的光芒和野心,謙遜面對日常生活里的人事,對未知的領(lǐng)域和藝術(shù)史上的先賢保持了真誠的敬畏。他準備的時間比我們想象的還要漫長。我仍然記得多年以前,他留守在文化館的一間小屋里的景象。房間狹小,簡樸又凌亂。舊式的辦公桌上凌亂地擺放著書籍、筆墨硯臺和篆刻的刀具,床鋪上也都是書,地上是水桶和煤油爐。他的工作和住宿都在這里。燈光昏暗,他的衣裳樸素。他看上去就像是舊年里寂寥的書生。在暗淡的光芒中,他顯得局促不安,就像我們發(fā)現(xiàn)了他的野心;這野心與他的寂寞、他的狹小的時空并不相配。他謙卑地解釋說,他讀書與學(xué)習(xí)篆刻只是為了打發(fā)時間。那時候我在城市里讀大學(xué)的中文系、寫詩、參加各種聚會,收到漂亮女生的來信,還與她們中間的幾個談?wù)撛姼瑁黄鹑ル娪霸嚎磹矍楣适缕Ec我們熱烈喧鬧的青春比較,他的寂寞與安靜則仿佛是對生活的屈從。也許不久之后,他會成為小城里普通的居民。他娶妻生子,關(guān)心蔬菜糧食和天氣,隔上很長一段時間去一座城市的風(fēng)景區(qū)拍照、購買便宜的旅游紀念品,在擁擠的飯館里排隊用餐。
多年之后,劉小農(nóng)成為小城里最好的篆刻家和書法家。那時候我才意識到,個體的自以為是顯得多么的滑稽。寂寞與安靜對一個藝術(shù)家又有多么重要。
很可能,他最初的篆刻就是為了對抗漫長又深刻的孤獨。小城空曠又寂靜,他獨坐斗室燈光的中心,手執(zhí)刻刀與石頭,在方寸之間構(gòu)建并書寫他豐盈飽滿的精神圖景。刀筆霍霍,發(fā)出響亮的聲音,細微的屑末飛揚起來,雪花一樣晶亮輕盈。那些生僻的象形漢字正在徐徐起舞。石頭溫潤,是遠古年代清揚婉兮的美人。刀筆游走,是舊時玉樹臨風(fēng)的長袖書生。他與古為徒,追慕先賢,只手可握的器物成為最適宜的媒介。它溫潤、堅硬,有金石之響,又能為繞指之柔。它甚至可以與漫長的時空抗衡。在很多時候,石頭上的書寫過程更接近藝術(shù)家豐盈廣闊的內(nèi)心疆域。
小農(nóng)以篆刻成名。其刀法古拙爛漫,多鳥獸象形趣味。他深研戰(zhàn)國古璽之剛健古樸氣象,又取法漢魏碑刻風(fēng)骨,有鏗鏘金石之氣。若以書寫風(fēng)格論,他的篆刻多受明代金石大家浸淫。有明一代是篆刻藝術(shù)最為鼎盛的時期。彼時高手云集,篆刻逐漸成為獨立的藝術(shù)形態(tài)。諸多書家各展才華,在方寸間呈現(xiàn)浪漫美學(xué)趣味。印信成為書寫藝術(shù)中的重要部分。小農(nóng)的諸多篆刻作品也正從此得法。他的鈐印閑章尤其顯得天真浪漫,生動之處,有如孩童一般憨態(tài)可掬,而橫豎刀鋒間隱約可見的剝蝕痕,則表達的是其對古老漢字的敬意。很多古璽文字深埋地下,經(jīng)歷了千年歲月的腐蝕,斑駁殘破,反而更具有厚重樸拙的殘缺之美,深沉典雅、古意盎然,是印章中的極品。明清的大多金石家,也正從中取法。剝裂紋呈現(xiàn)的是物我一體的情懷,書寫者以此印證文字不止是器物的附庸與點綴,它們以爛漫之態(tài),成為自然造化的一部分。小農(nóng)深諳此道,也以此體現(xiàn)他作為篆刻家的美學(xué)趣味和技法上的精致追求。
若干年后,篆刻家劉小農(nóng)成為書法家。他的書法作品突然呈現(xiàn),而且作品的格局之高,一出手便遠超許多同輩書家。這些都令人驚奇。通常意義上的篆刻與書法保持了必要的距離,而一個書法家的成長過程也通常會被人們留意。他似乎在突然之間成為一個書法家。后來有一次我們說到這個問題,也是下雨的天氣,我們坐在畫室里閑聊,聽見窗外雨水的聲音。小農(nóng)說,他勤于治印之時,于書法之道也從未懈怠。治印與墨寫其實一體。他研讀書法流變,細讀碑帖,拜訪書法高手,勤于練習(xí),以期進入書法堂奧。某年他在復(fù)旦大學(xué)進修文博專業(yè),忽一日,他在靜夜時分,獨自觀看徐渭作品,神思恍惚之際,心有所悟。一時醍醐灌頂,心中塊壘釋然而出。徐渭是明代書畫大家,一生經(jīng)歷了人生巨大的悲愴、幻滅、激情與無常。他以水墨為戲,意在形先,藉墨色渲瀉心中的孤獨與生命頓悟。他洞悉世間繽紛色相,解其紛,挫其銳,和光同塵。他的書寫法諸米芾,但能不拘一體而極盡狂放恣肆。徐渭之書,密處不透風(fēng),疏處可走馬,若擔(dān)夫爭道,疾徐有法,又如卷席之勢,筆意連綿而開合有度。
小農(nóng)由此而悟得書道。他書狂草,上追唐時張旭,下逮明清江南狂放之風(fēng),起合結(jié)體有大氣,筆落之際,滿紙云煙。又因他深研篆刻意趣,于是在筆法中引入漢魏古碑之風(fēng),在恣肆連綿中有蒼勁沉著之氣,乃至?xí)r時有意而為破筆、折筆,藉此呈現(xiàn)書家只求意趣與內(nèi)心酣暢之情懷。
他謙和寡言,低調(diào)應(yīng)對日常生活,其書風(fēng)卻激烈張揚,盡顯桀驁不馴之氣。日常圖景中的文弱書生,在紙上構(gòu)建起宏大壯烈的金戈鐵馬、驚濤駭浪。這足以令人驚奇。
他同時要面對另外的問題。他居住在西部的一座縣城。這座人口不足十萬的小城擁有中國數(shù)量最密集的畫廊和書畫家。它被譽為中國最著名的書畫藝術(shù)之鄉(xiāng)。這里最普通的鄉(xiāng)村居民也能寫出一筆好字,也能懂得欣賞一幅書畫作品。書畫就像糧食和蔬菜。在大多數(shù)時候,小城安靜而內(nèi)斂,人們向往古老的詩書傳統(tǒng)。本埠的書法家書寫魏碑、楷隸和行書。這些法度謹嚴、方正妍媚的漢字,表達的是人們對主流書法傳統(tǒng)的敬意。書寫草書的人數(shù)量很少,狂草的書家則幾乎不曾出現(xiàn)。
劉小農(nóng)作品中的獨特氣質(zhì)引人注目。人們送上贊美,很多書界同仁認為他呈現(xiàn)了年輕一代書家的新高度。他的作品在省會城市和一些重要的展會上出現(xiàn)。他改變了人們對書畫之鄉(xiāng)的日常印象:他代表了銳意變革、擺脫舊式的藩籬、自由探索,以及新時代的美學(xué)趣味。但在同時,另一種聲音出現(xiàn),這些聲音里包含了質(zhì)疑和批評,他作品中的異質(zhì)性被認為是對傳統(tǒng)書法美學(xué)的背離與挑釁。相當一部分觀眾和書界同仁并不能體味他作品中的藝術(shù)旨趣。某個藝術(shù)界同行有一次發(fā)問說,他(劉小農(nóng))為什么只有狂草作品?他為什么不能寫一些真書作品出來?發(fā)問的語氣顯得尖刻,尖刻中充滿了懷疑。事實上他的發(fā)問并不具備基本的美學(xué)前提。首先,書法藝術(shù)中的狂草代表了最為謹嚴苛刻的藝術(shù)法度,即使最細微的筆法、構(gòu)圖與層次都要嚴格遵循出處與來歷,需要書法家兀兀窮年的潛心研讀和不懈練習(xí),需要對書法藝術(shù)的流變爛熟于心。這也是為什么在當下的藝術(shù)境況中,狂草書法家少之又少的原因。非不為,乃不能為也。其次,劉小農(nóng)的真書作品數(shù)量不少。他的真書,得鐘繇、顏真卿、蘇東坡、懷素諸書家熏染,又以漢魏碑刻書意為底韻,蒼然大器,既有金石風(fēng)骨,又具婉轉(zhuǎn)游弋之味,其姿態(tài)意趣同樣令人驚嘆。
藝術(shù)界的同行都有如此質(zhì)疑,何況更多的普通藝術(shù)受眾。這其實印證了時代趣味的蕪雜、喧嘩與浮躁。另一個更重要的問題是:一些評論家撰寫關(guān)于他作品的藝術(shù)評論時,可以很明顯地看到,他作品中的獨特性與精神訴求被忽略和遮蔽。在很多評論家的觀點里,他與大多數(shù)成功的書法家一樣,通過勤奮臨習(xí),成為獲得某種獎項、入選某種選本的藝術(shù)家。刻薄點說,很多撰寫藝術(shù)評論的人,對所涉及的藝術(shù)門類其實缺少學(xué)養(yǎng)。姑且引用幾句先賢名句,米芾在其著名的《海岳名言》中說:“歷觀前賢論書,征引迂遠,比況奇巧,如龍?zhí)扉T,虎臥鳳閣,是何等語?或遣辭求工,去法逾遠,無益學(xué)者。”如今的藝術(shù)評論,大多時候正如米芾所說,大而無當,泛泛而談,并不能深入肌理。
在雨天,我來到小城,與書家劉小農(nóng)喝茶。談?wù)摃ā⒆蹋约叭粘I畹脑掝}。雨天讓縣城顯得清新、整潔、安靜。我一直在給小農(nóng)拍攝一部小規(guī)模的紀錄片。每次見面,都要拍一點影像資料。他的鏡頭感不好,在鏡頭里,他的表情會顯得羞澀生硬。我還曾經(jīng)弄丟了一些拍好的影像素材。在給他拍攝素材的時候,我在寫一部關(guān)于藝術(shù)家題材的長篇小說。現(xiàn)在,小說早已寫完并且出版,關(guān)于他的紀錄片仍然沒有完成。我為此感到愧疚。
這個時代太喧囂了,我要應(yīng)對生活里不斷涌現(xiàn)的聚會、講座、觀光和物質(zhì)活動,他也一樣。中國的很多鄉(xiāng)村正在邁向城市化,這座小城也只是在雨天顯得安靜。雨后的縣城鼎沸喧嘩,在某些時候,甚至比更大的城市更顯蕪雜。這里的人們互相認識,很多隱秘的生活與信息被共享,也更容易被談?wù)摗K栽诟鄷r候,退守書齋、品茗讀書也只是一種近于奢侈的期望。作為藝術(shù)家,他也必須面對藝術(shù)書寫的物質(zhì)化訴求。他有一間中等規(guī)模的畫廊,還需要收購價格不一的古舊書畫,要支付大部分日常生活的成本。這些都需要他的書法和篆刻的收益來支撐。小城里的很多人贊美他的作品,來索要他的墨寶,請他篆刻印章,但大部分時候,并沒有意識到每一件作品都需要耗費繁重的精力,需要有基本的物質(zhì)投入。所以,如何維持純粹的藝術(shù)書寫與現(xiàn)實生活的平衡是一個難題。
他坐在那里,許久沒有說話,后來他說,先就這樣過吧。
我是一個小說家。我提出的問題其實也適合我自己。我們面對的問題都一樣。同樣,對我來說,這也是一個很難回答的問題。在已經(jīng)出版的小說《同塵》后記中,我寫道:“藝術(shù)家處于欲望漩渦的中心,但又常常被喧嘩的聲色疏離。他們制造潮流,引領(lǐng)消費,卻又是時代的敵人。他們既安靜又輕浮,寂寞又敏銳,他們既與日常生活對抗,又是自我舞臺上孤獨的舞者。”無論如何,在大部分情境里,懷抱著赤子之心的藝術(shù)家是異質(zhì)又寂寞的人。
我寫下此文,向劉小農(nóng)——一位生活于西部小城、具有天賦異稟氣質(zhì)的藝術(shù)家,表達我真誠的敬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