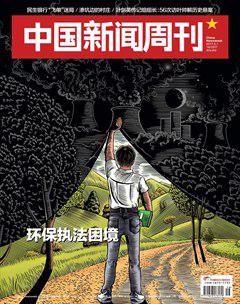二手孤獨和一手自由
康慨
寧愿置之死地,尋找只有憑最銳利的希望才能看到的一線光明,
也不相信祈禱詞和救世主
托妮·莫里森在《最藍的眼睛》里寫了三個好心的妓女, 分別給她們?nèi)∶ㄌm、中國和馬奇諾防線,毫不掩飾地用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的歷史象征黑人被肆意侵犯卻無力自衛(wèi)與反抗的現(xiàn)實。《地下鐵道》里的大部分黑奴也是一樣,他們在一出逆來順受的集體悲劇中各自扮演著下場幾近相同的苦命角色。
女主人公科拉一出生就成了白人的家財,又早早失去了父母的保護,受盡侮辱與虐待。在內(nèi)戰(zhàn)前夕的1850年代,在南方腹地的種植園,如果不逃跑,她的命運幾乎是注定的了:要么慘死于監(jiān)工的九尾鞭下,要么在有毒的環(huán)境里自甘墮落。
“每個奴隸都想著逃跑。”書中寫道,“每個夢都是逃跑的夢,哪怕看上去不像。比如一個關于新鞋子的夢。”但并非每個人都能下定出逃的決心。對大多數(shù)奴隸來說,自由是不可想象的,在種植園里忍辱,好歹還能偷生。
但科拉跑了。16歲那年,她跑出了種植園,借著月色蹚過沼澤,跑過野豬林,藏進糧油店老板的馬車,通過廢奴分子家地板上的活門,進入地下鐵道,登車北行。每到一地,她都將見識種族主義惡行的新貌,她和幫助她的同志們都要為自由付出更大的代價。
“如果想看看這個國家到底是個什么樣子,你們得坐火車。”第一次將她送上火車的站長說,“跑起來以后,你們往外看,就能看到美國的真面貌。”事實終將證明這番話是個殘酷的玩笑,隧道里只有無盡的黑暗。黑暗才是美國。
科拉要逃離的不只是殘暴的奴隸主和充當鷹犬的民防團、巡邏隊、獵奴人,還有她身邊的黑人同胞。罪惡的制度敗壞了集體道德,連最窮苦的群落也不放過。倔強的性格和自衛(wèi)的本能讓科拉在黑人社區(qū)內(nèi)部受到排斥。他們強暴她,然后中傷她——婦人們傳言她溜進樹林,與驢子和公羊通奸。
在莫里森的另一部小說《秀拉》里,女主人公臨死前這樣告訴依附男人又被男人拋棄的另一個黑女人:“我的孤獨是我自己的。而你的孤獨卻是別人的,是由別人制造后送給你的。這難道不能說明什么嗎?一種二手的孤獨。”科拉享有她自己的孤獨,她也不要二手的自由。她不相信祈禱詞和救世主,她全靠自己救自己。她逃出種植園,在途中殺死了一個捉她的白人少年,與強大的獵奴者搏斗,并帶著置之死地而后生的決心走進黑暗的隧道,去尋找只有憑著最銳利的希望才能看到的一線光明。
這是一個有欠豐滿但高度鮮明也十分必要的黑人形象,不同于快樂的黑鬼或順從的傻瓜(《湯姆叔叔的小屋》),不向上帝訴苦(《紫色》),不靠打垮丈夫贏來自由(《他們眼望上蒼》)或殺死女兒給她自由(《寵兒》),甚至不需要別人代自己辯護(《土生子》)。
與莫里森流暢奔放的文學語言不同,懷特黑德使用的是一種斯巴達式的高度儉省和樸素的句子。他忌諱優(yōu)美流暢,正像理查德·賴特視感人為惡一樣。在談到《土生子》的創(chuàng)作動機時,賴特說他此前曾經(jīng)發(fā)誓:“如果再寫小說,我要叫任何人也無法掉淚;小說要寫得冷酷而深刻,讀者必須直面這部書,毫無淚水的慰藉。”
《地下鐵道》有著強烈的政治潛力,但絕非“抗議小說”。事實上,懷特黑德聰明地調(diào)動了多種類型化小說的元素和商業(yè)化寫作的技巧,讓老套的逃奴主題懸念叢生。我在閱讀時完全受著情節(jié)的引領,在翻譯的過程中沉浸于語言的糾纏,只在某一天生出了少許的使命感。
那是今年1月20日,特朗普在華盛頓的霪雨中宣誓就職。我剛好譯到獵奴者里奇韋在田納西的酒館里對科拉大談美國的天命:“我更喜歡咱美國的神明了,是他把我們從舊大陸召喚到新大陸,讓我們征服,建造,推行文明。毀滅需要毀滅的。教化少數(shù)種族。教化不了,就鎮(zhèn)壓。鎮(zhèn)壓不了,就根除。我們的命運是本著天意來的——天降大任于美國。”
“我得去趟茅房。”科拉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