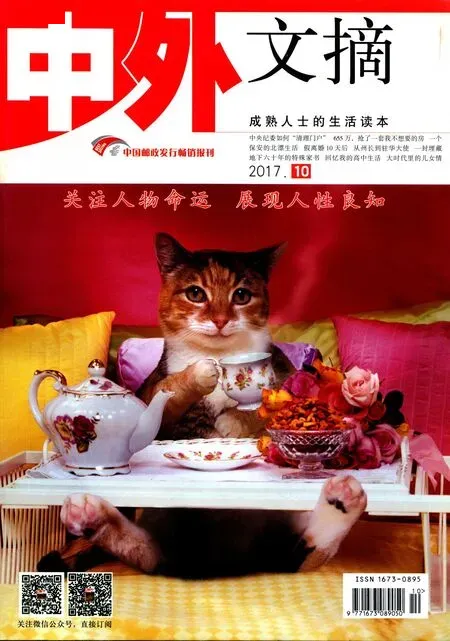回憶我的高中生活
□ 祁玉江
回憶我的高中生活
□ 祁玉江

一
1974年初春的一天,我懷揣沉甸甸的高中錄取通知書,走進澗峪岔高中,繼續進行深造。
澗峪岔高中設在公社所在地的澗峪岔鎮,位于鎮子以東大約兩華里的廟灣坪。我家距學校三十多華里,盡是大山和深溝,交通不暢,需要步行三四個小時才能到達。夏秋和冬季行走還較為方便。而最難走的是初春,冰河融化,滿溝黃水泥濘,還沒等到了學校,鞋襪以及半個褲腿就濕透了。父親將我送到學校后,就趕著毛驢匆匆回去了。
澗峪岔高中是一所混合制學校。我們剛進校時,有小學一至五年級、初中一至二年級,以及高一、高二各一個班。后來小學分出去了,擴大了初中班和高中班的招生,初中班和高中班不再是各一個班了,好像每個年級都變成了兩個班。全校有學生三百多名,教師近三十名。校園規模不大,但比我讀的桑塔中學大多了。院
內橫貫東西三排磚窯,上排二十多孔為校長和后勤人員辦公室及女生宿舍;中排二十多孔是灶房和男生宿舍;與兩排磚窯平行且離兩排磚窯稍遠一些、靠近馬路邊還有一排十幾孔磚窯。為節約用房,這排窯洞中間進行了封隔,即將一孔窯洞一分為二,兩頭開門,南面主要作為教師們的辦公室,北面大部分成了庫房、實驗室、雜物間。校園院落十分簡陋,包括操場全為黃土地,沒有任何磚石鋪設,更沒有花草、樹木;院子、道路坑坑洼洼,高底不平,一下雨,泥濘不堪,走起來十分不便。
二
那時,全國上下正值開展“批林批孔、反擊右傾翻案風”活動,剛剛復蘇的教育又“回潮”了。上面一味強調的是“開門辦學”,以階級斗爭為綱,生怕資產階級占領教育陣地,形勢異常緊張。
好在,有一位好校長和一批好老師。他們深知知識對學生的重要性,壓根不想昧著良心使家長省吃儉用送來學校深造的子弟荒廢學業。但是面對極左路線的干擾,有誰又敢明目張膽地站出來反對呢?在這進退兩難的情況下,他們只能虛張聲勢,避實就輕,明里緊跟形勢,暗里卻緊抓教學不放。
校長袁國祥,雖然僅僅是高小畢業生,但文化底子深厚,加之長期從事基層教育工作,曾經擔任過好幾個小學和初中的校長,管理經驗十分豐富。他每天起早貪黑,在學校里轉來轉去,總怕哪里有安排不到位的地方。他對教師的授課和學生的學習要求很嚴,動不動就黑煞著臉,不僅學生害怕,就連教師也很是敬畏。
老師們多數是“文革”前的老牌大學生,品學兼優,工作兢兢業業,一絲不茍,的確是我們這些山里孩子的福份。例如我們的語文兼班主任老師何希哲,陜西富平縣人。1961年畢業于陜西師范大學中文系,中文基礎扎實,寫得一手漂亮字,文章寫得更好。畢業后,因家庭成份不好,先被分配到偏遠落后的陜北子長縣中學任教,后又充實到更加偏僻、艱苦的澗峪岔中學任教,主要擔任高中班的語文教學。他當時三十七八歲,個頭不高,不到一米六五,瘦瘦的,著一身土布衣服和方口布鞋,臉堂黑紅,前額開闊,頭發花白,走起路來風風火火。他教學很是認真,操一口關中腔,講起課來,不僅聲音洪亮,而且聲情并茂,每節課都講得十分細致生動。起初,我們很難聽懂他的話語,隨著時間的推移,便句句中肯入耳,讓人一下子忘不了。對學生的作業尤其是作文,批改得十分認真,批語定性準確,對我們寫作水平的提高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此外,他對學生要求極嚴,上課隨時提問,不許交頭接耳。自習時間時不時來教室巡查,生怕我們吊兒郎當,荒廢了學業。即便課余時間,也常常叫一些學生到他辦公室,面對面、手把手地給予指導。晚上要求我們按時熄燈休息,決不允許喧嘩吵鬧,否則便會狠狠地批評訓斥一頓。許多同學,包括他很器重的我,都曾挨過不少批評。但同學們都毫無怨言,因為他是真心愛我們的。
再比如數學老師魏振金,本縣玉家灣人。1960年畢業于陜西師范大學數學系。也因家庭成分不好,幾經周折被“刺配”到澗峪岔中學任教。他高高的個兒,背微微有些駝,長方臉,五官棱角分明,尤其是那一雙明亮的眸子,時不時會射出兩道寒光,瞅著你,使你頓覺毛骨悚然。年齡與何希哲老師差不多,頭發烏黑而稠密,留著寸頭,著一身中山裝,顯得精干威嚴。最令人佩服的是,他對數學很是精道,上課從來不拿課本,也不帶教案,只拿兩根粉筆,口若懸河,一邊講解,一邊在黑板上寫寫劃劃,做著試題,不知不覺一節課就上完了。我向來愛好語文,對數理化不感興趣。但是由于魏老師的數學課講得好,對我們要求嚴,使我對數學漸漸產生了一定的興趣,成績不斷攀升。正是魏老師給我打下的堅實基礎,才使恢復高考后進入延安農校學習的我,竟然當上了數學課代表。此外,他心直口快,表里如一,敢于發表自己的觀點和意見。他對教育回潮形勢怎么也看不慣,明確表示反對,認為不抓教育,不培養人才,成天搞“開門辦學”,盡培養些“白卷”先生,我們的“四化”建設怎么能夠實現?這個觀點現在看來不是什么問題,然而在當年那種“政治掛帥”的嚴峻形勢下,需要鼓起多么大的勇氣呀!
再如理化老師林冰,甘肅蘭州市人,1967年畢業于蘭州大學物理系。畢業后,為了支援貧困地區教育事業,幾經周轉,也被指派到了澗峪岔中學,擔任了我們高七五和高七四兩個班級的物理和化學老師。他中等個兒,不胖不瘦,人長得帥氣,鼻梁上架著一副高度近視鏡,穿著打扮很是講究,講一口普通話,顯得很是斯文。他在校就是高材生,對理化很是精道,講起課來滔滔不絕。可惜我們多數同學對理化不感興趣,無心聽講和學習,致使成績一直上不去,這也是我們后來參加高考成績不高、上不了大學的重要原因。
在兩年的高中學習中,校長和老師對我們備加關懷。尤其是語文兼班主任老師何希哲,更是對我格外關心。有一年暑假,何老師沒有回家,專程去我家家訪。記得那天,天晴日朗,火辣辣的太陽炙烤著大地,也炙烤著我們。由于前幾天剛下罷暴雨,溝道里發了山水,泥濘不堪,難以行走。于是師生倆舍近求遠,拄著柴棍,翻山越嶺,徒步五十余華里山路,用了大半天時間才趕到我家。看到我家人口多,生活困難,何老師十分傷感、動情。在我家住了兩天后,在他的要求下,由我領著他,又到附近村子的幾個同學家轉了幾天,使他全面掌握了同學們的家庭生活情況。十余天后他才返回學校。我日后的成長進步、文學創作的成就,與袁國祥校長及各位老師,特別是與語文兼班主任老師何希哲的教誨是分不開的。對此,我將永遠銘記在心!
三
在高中整整兩年學習期間,最大的困惑還是饑餓。上大灶每天兩頓飯,上午是一勺玉米面糊、一個“老黃”(玉米面饃);下午一勺多白菜熬洋芋,同樣一個“老黃”。根本吃不飽。至于白面饃饃很少吃到。因為那時伙食是以粗糧為主,粗細糧比例大約為八比二。那點細糧飯票怎敢放開肚皮吃呢?緊節省慢節省就吃完了。由于頓頓吃不飽,餓得人上頓等不到下頓。還沒有下課,同學們就收拾好了碗筷,做好打飯的準備。下課鈴一響,便箭一般地沖出教室,潮水般地向灶房門口涌去,以便能夠搶在前面,早早打到飯菜,填充饑餓的肚子。打來了便很快離開灶房門口,蹲在院子一角,狼吞虎咽地吃開了。可這點飯對一個正在長身體、且學習任務繁重的年輕人來講,只能是杯水車薪,似乎不吃倒也便罷,而吃了這點飯反倒把餓神引逗起來了,餓得更厲害了。只得再次擠到飯盆前,企盼著沒有打完的飯菜能否再給加上一點,哪怕一口也行!有時還能加上一點,而多數時候是等不來的。這時,大伙又把眼睛聚焦到灶房里那一鍋滾燙燙的面湯上——那是老師煮面剩下的,上面還依稀漂著幾根碎面條。如果能喝上一碗滾燙的面湯,撈到一兩根碎面條,那是多么地幸運呀!一碗熱面湯喝下去,肚子立刻便會鼓起來,身上微微發著汗,滿身地舒服自在!
特別是家住郭家河大隊的侯海川,他中等個兒,著一身補丁衣服,頭發微黃枯焦,臉龐寬闊,有一張大嘴,一雙圓溜溜的眼睛,常常泛著黃色,一看就是個“餓死鬼”。他家人口多,父親侯貴芝,又不務正業,經常耍賭,家中生活十分困難。按理侯海川是很難上得起學的,家里也不支持他上學。可侯海川看到考上的同學都報名了,他不甘心就這樣回家“戳牛屁股”,便死磨硬纏,終于說服了大人,咬著牙來讀高中了。他的飯量很大,在我的印象中,他從來沒有吃飽過。別人吃一份飯就可以湊合,可他吃兩份還不得飽,整日思謀著吃飯。所以,排隊打飯他往往擠在最前頭,遇到加飯他也能夠加上。至于面湯,侯海川肯定是少不了的,不僅能夠滿滿地喝到一大碗,而且有時還能喝到兩碗。遇上“五一”、“十一”、元旦之類的重大節日,學校往往是要會餐的。所謂會餐,就是殺一頭豬,做一大鍋豬肉燴粉條、洋芋、白菜等,美其名曰“大燴菜”。幾百名學生,每人大半勺燴菜,一個白饃,這是多么可口的大餐呀!而眼疾手快的侯海川,不知使了什么伎倆,總能干上幫廚的美差,這可是多少同學羨慕的營生。因為,此活雖然累一點,有時還要向大師傅、管理員低頭哈腰,被人瞧不起,但最起碼能夠放開肚皮美美地吃上一頓。至于別人的冷嘲熱諷,管它呢!反正那些話不能當飯吃。侯海川就是這樣,當別人挖苦他時,他總是嘿嘿一笑,并不反唇相譏,該做什么就做什么。至于我,因為個頭低,力量小,臉皮薄,往往搶不到面湯喝,更找不到幫廚的美差,只能自作清苦,獨自哀嘆了!
四
解決饑餓的辦法,除了開小灶和事先準備的一些所謂的“干糧”填充肚子外,有時還利用月黑風高的夜晚,走出校園偷吃玉米、瓜果之類的東西。
記得學校大門口馬路下邊種植一片玉米,長得很茂盛,玉米棒子掛在桿子中間,吐著纓子,看上去豐滿結實,很是誘人。一天晚上,我實在餓得不行了,而眼下連一點可供吃的東西都沒有了。這可怎么辦呢?我便突然想起那片玉米地,想起了玉米稈子上掛著那一個個胖乎乎的家伙。于是我便約了一位同學,摸黑來到玉米地里,順手掰了兩個玉米棒子,像猴子一樣敏捷地離開玉米地,悄悄溜回學校,乘著灶膛和爐坑里的火焰還沒有熄滅,很快把玉米棒子填進去燒烤起來。一方面怕人發現,另一方面的確餓到了極點,烤了沒多少功夫,還沒有熟,就將玉米棒子挖了出來,餓狼似地將半生不熟的玉米吞下肚去。吃完了,又怕別的同學發現,兩人又跑到水管前,將手上和嘴上留下的“罪證”清洗干凈,裝成若無其事的樣子,心滿意足地回到宿舍睡了。
學校隔壁東北方向兩華里外的塌灣里種植一大片西瓜和小瓜。照瓜的是一個塌鼻、駝背、說話口齒不清、腿腳不很利索的半老頭。這一年正遇上風調雨順,西瓜和小瓜都在瘋長。剛入秋,滿地里都是橫七豎八、明晃晃的西小瓜,惹得人十分嘴饞。有一天晚上,正好沒有月亮,天黑得伸手不見五指。我們幾位同學相互約好,趁著天黑,摸到了瓜地里。在即將抱著瓜離開的時候,那老頭忽然打著手電向我們走了過來。我們一下子完全曝露在看瓜人的眼前。“這下完了!”我們的心在劇烈地跳動著。那老頭一陣大喊大罵,土疙瘩雨點般地向我們砸來。我們慌忙丟下西瓜,拼命地逃跑。可是,上山容易下山難,再加之有梯田圪塄阻攔,跑起來非常吃力。為了不被人作為“賊娃子”捉住,我們便連滾帶跳從塌灣上奔了下來。不僅沒有偷吃到西小瓜,而且有的同學還將褲子撕扯爛了,腳腕也扭傷了,還有的丟了鞋。相互望著對方氣喘吁吁,狼狽不堪的樣子,欲哭無淚,欲笑不能,只好挨了暗肚子氣,灰溜溜地潛回宿舍。
五
整整兩年的高中學習生活就這樣結束了。我們既高興又傷感:高興的是,我們終于完成了艱難困苦的高中學習任務,就要畢業和親人團聚了,最起碼還能有飽飯吃;而傷感的是,我們將要永遠告別親愛的母校,離開敬愛的老師和日夜相伴的同學,從此天各一方,更不知下一步等待我們的命運究竟是什么?
1976年元月9日,在我們即將離校的時候,學校高音喇叭里突然響起低沉悲壯的哀樂。大家一顆心頓時提在了嗓子眼上,都在默默地猜想,是哪一位黨和國家領導人逝世了?但誰也沒想到竟然是周恩來。此刻,全體師生驚呆了,悲痛的淚水盈滿了眼眶。于是師生們自發地在臂膊上戴上了黑紗,在胸前扎上了小白花,在校園的墻壁上掛起了挽帳。
就這樣,我們憂心忡忡地告別了敬愛的老師、親愛的同學,離開了澗峪岔高中。背起鋪蓋卷兒,一步一回頭地返回家鄉,走向了農村。
(摘自《各界》2016年第1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