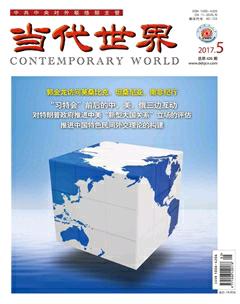民主之“鞋”:質量好壞關鍵看合不合腳
趙雨澤
2017年3月24日,中共中央對外聯絡部“萬壽論壇”系列活動之“危機背景下民主制度的困境和出路”主題對話會在北京萬壽賓館舉行。中聯部研究室主任欒建章、拉美局局長魏強主持了對話活動。來自亞洲、非洲、拉美十國的40余位政要和學者,圍繞發展中國家面臨的治理挑戰與經驗、政黨的角色與責任等問題,與北京大學、中國人民大學、北京林業大學、北京外國語大學等單位專家學者及青年師生深入互動交流。
西式自由民主在不同國家
都出現了問題
20世紀80、90年代,以美國為首的西方世界挾冷戰勝利余威,以“自由民主+市場經濟”的“萬能方程式”和“歷史終結”鳴鑼開道,并在強大軍力的“護衛”下在全球肆無忌憚地推行“自由民主”,結果非但沒有給“受眾”帶來預期的繁榮和穩定,反而造成相關國家持續動蕩和貧窮。對于這種強推民主釀成的苦果,廣大發展中國家的感受十分深刻。
埃塞俄比亞政府政策研究中心新聞處主任賽科·蓋塔丘·提魯內指出,奉行新自由主義理念的美式民主已經陷入危機,導致世界范圍內效仿美式民主的發展中國家普遍陷入“進退兩難”的困境,一系列問題由此產生。
柬埔寨人民黨中央委員、柬司法行政部副國務秘書喬索帕尼認為,目前西式民主遭遇了深層次的結構性危機。即便是美國、英國、德國、法國這樣的“老牌民主國家”,尚且不同程度深陷保護主義、民粹主義等泥潭中難以自拔,遑論印度等不遺余力推行西式民主但收效甚微的發展中國家,西式民主的弊端可見一斑。
黎巴嫩共產黨政治局委員、黎巴嫩美國大學經濟學教授格桑·達伊巴指出,目前西方民主遭遇的困境,與資本主義內生缺陷所產生的周期性經濟危機密不可分,而西方主導的全球化進程所導致的貧富差距更是加大了不同社會階層之間的矛盾沖突。從某種意義上說,“民主危機”的實質是“資本主義危機”。
馬來西亞智庫“誠信之家”創始人、國防部長希沙慕丁顧問阿卜杜拉·拉扎克·艾哈邁德指出,西方民主正在經歷一場“反自由主義”浪潮,而英國脫歐、特朗普當選等“黑天鵝事件”無疑反映出這樣一個事實:全球化進程的利益受損者——那些“被遺棄的人們”已經行動起來,通過選票發出自己的聲音。
南非非國大政策研究室主任斯蒂芬·普拉吉認為,民主從某種意義上來說本身就是一場“危機”。被西方奉為圭臬的自由主義民主模式恰恰斷絕了人民追求自由的可能。
阿根廷創新陣線領袖、國家眾議員賽爾希奧·馬薩指出,阿根廷在實行西式民主的過程中并非一帆風順,歷史上曾經歷十天內政府連續更迭而導致民主制崩潰的窘境。[1]目前,政府將大多數人民排除在公共決策過程之外,且在有效回應民眾訴求方面也并未真正發揮作用。
北京大學國際關系學院教授潘維指出,民主制度的困境在于其未來發展具有巨大“不確定性”,而這種不確定性源于精英左翼、精英右翼、平民左翼、平民右翼這四種力量之間的不斷博弈。對比來看,被西方認為“不民主”的中國反而最具備“確定性”。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政府能夠有效平衡和團結上述四種力量,積極推行“以市場創造財富、以社會主義價值觀分配財富”的發展模式,因而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
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系學院教授楊光斌指出,人民主權從來不可能“自我實現”。對于廣大發展中國家而言,西式民主已淪為“失敗民主”,被資本所控制的民主政治只能導致毫無效率的“否決政治”,于國于民都毫無益處。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在具有廣泛代表性的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致力于真正實現人民的當家作主地位,因此才取得了巨大的發展成就。
北京林業大學人文社會科學學院院長林震指出,目前民主遭遇了“多重危機”,西式民主的弊端也延伸到環境治理領域。“民主”選舉上臺的特朗普宣稱美國退出巴黎協定,使氣候變化談判成果面臨重大挑戰。相反,中國政府將經濟發展和環境保護兩大目標有機結合,注重協調促進環境治理領域的公眾參與,積極回應人民對“綠水青山”的訴求。
民主實質:
程序重要,結果更重要
在政治學里,民主是一個永恒的命題。從柏拉圖、亞里士多德到熊彼特、薩托利,無數大家都嘗試以自己獨特的方式解讀民主的實質,而最關鍵的問題在于“民主是什么,民主為了什么?”。美國著名政治學家羅伯特·達爾曾指出,“理想的民主是選民對政治議程的最終控制”。然而,現實中的“選舉民主”卻很難達到這一理想狀態,亞非拉各國政治精英在本國民主實踐中得出的結論更具有說服力。
賽爾希奧·馬薩指出,我們似乎始終沒有搞清楚一個問題的答案:民主到底是一種值得我們追求的價值觀,還是我們實現某種目的的手段?民主真正的要義,是使政府有能力促進社會經濟發展,從而滿足人民過上更好生活的訴求,使人民擁有“獲得感”。
賽科·蓋塔丘·提魯內指出,發展中國家領導人不應糾纏關于民主“形式”的無謂之爭,而應以求真務實的態度客觀分析國內外形勢,把主要精力集中在解決國內發展問題上。
喬索帕尼認為,民主制度的目的,在于通過實行“善政”促進社會經濟發展,滿足人民的各類需求,確保國家和社會的正常穩定運轉。
阿卜杜拉·拉扎克·艾哈邁德指出,民主是回答“誰決策”和“如何決策”兩大問題的一種制度設計。凡是制度都存在弊端,如果運用不當,民主制度就可能演變為“多數人的暴政”,導致社會矛盾的激化,進一步加劇社會不平等。
尼日利亞博利塔外交與戰略研究中心主任博拉·阿金特林瓦認為,民主是一個過程量也是一個結果量,無論是總統共和制還是議會共和制都只是形式差別,關鍵在于民主模式為人民提供了什么樣的公共物品,而民主的終極價值在于“惠民”。
巴西民運黨眾議院黨團領袖巴雷亞·羅西指出,民主應該被看作是一種“工具”,每個國家使用這種“工具”的最終目的是讓人民生活更加富裕,獲得更好的教育、住房和公共產品。
放之四海而皆準的民主模式
是不存在的
美西方認為西式民主模式是人類政治發展史的“終結”,這種觀點本身就是一種“致命的自負”。發展中國家只有從自身國情出發,在充分學習借鑒其他國家優秀發展經驗的基礎上選擇自己的發展道路和模式,才能實現真正的發展,照抄照搬的“本本主義”注定沒有未來。
賽科·蓋塔丘·提魯內指出,實現民主的道路應該是多樣化的,沒有一種模式能夠同時解決所有國家的所有問題。我們應根據每個國家的具體國情,選擇相應的民主模式。歷史已經證明,相比較西式民主,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就是一種取得巨大成就的“特殊模式”。在過去的25年里,埃塞俄比亞經濟飛速發展,扶貧事業取得顯著成績,其根源就在于實行了具有鮮明埃塞特色的“發展型模式”。
格桑·達伊巴認為,“阿拉伯之春”給中東人民帶來的混亂和失序表明,西方民主尤其是美式民主在阿拉伯世界已經失敗,根本不具有所謂的“普適性”,而美國向伊拉克等中東國家兜售其民主模式的真實目的在于借機謀取私利。
塞內加爾爭取共和聯盟創始成員、該黨干部聯合會外事負責人奧古斯丁·哈馬·恩戈姆指出,西式民主在非洲大陸的推廣進程步履維艱,塞內加爾沒有完全照抄照搬西方民主模式,而是在充分考慮本國國情的基礎上有針對性學習借鑒西方民主的優秀因素,最終形成了“塞內加爾模式”并取得了一定的發展成績。
博拉·阿金特林瓦認為,在非洲和亞洲,不同國家的民主模式具有不同的特點。“中國式民主”就是一種“本土化”的民主模式創新,正是因為其適應了本國國情,才取得了如此巨大的發展成就。
強加于他人的“移植民主”
注定沒有生命力
醫學上器官移植出現的機體排斥現象會威脅到患者的生命安全,而政治領域的“移植民主”帶來的“排斥”也會對接受國的政治、經濟和社會穩定造成巨大負面影響,美西方出于自身戰略和政治利益對外強推或移植“自由民主”,卻選擇性忽視民主移植造成的水土不服和排斥問題,注定了西式民主的對外輸出終究會成為一場歷史的鬧劇。
巴西民運黨眾議院黨團領袖巴雷亞·羅西指出,中國領導人習近平有一句名言:鞋子合不合腳,自己穿著才知道。每個國家都有權利實行適合自身國情的民主模式,對此我們應表示尊重而不是否定和干涉。巴西特色民主模式取得了成功,這并不意味著“巴西民主”就一定適用于其他國家。
賽科指出,埃塞前總理梅萊斯·澤納維認為新自由主義在非洲已經失敗,幫助非洲脫貧致富的唯一途徑是走發展型道路。與新自由主義假設不同,發展型國家對經濟發展的國家干預,對于發展中國家擺脫貧困陷阱至關重要。實踐證明,發展型國家已經成為欠發達國家打破貧困與落后惡性循環的極佳選擇,這種發展模式有利于發展中國家最大限度地發掘利用其人力和自然資源。
喬索帕尼稱,西方民主制度曾被認為是人類歷史上最好的政治設計,可如今,無論是美國入侵之后所建立的“民主樣板”阿富汗和伊拉克,還是“阿拉伯之春”后幾近碎片化的中東,都無情地打碎了西方世界對“民主萬能”不切實際的幻想,我們甚至無法找到一個發展中國家通過實行西方民主制度而真正實現國家穩定、經濟發展的有效范例。
斯蒂芬·普拉吉指出,南非曾是西方國家推行西式民主的樣板,但實行西方民主制度以來,南非人民并沒有真正獲得自由,也沒有真正擺脫貧困,這樣的民主模式何談成功?
在總結發言中,欒建章指出,政黨對于促進民主發展發揮著重要作用,特別是面對日益復雜的內外形勢,政黨和政治家都要有所擔當,都要積極作為,切實為解決目前民主遇到的問題貢獻力量。
(作者單位:中共中央對外聯絡部研究室)
(責任編輯:徐海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