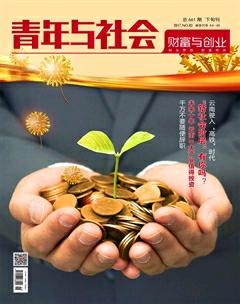“新社會階層”有你嗎?
隨著社會經濟的快速發展,我國社會簡單的“兩個階級一個群體” (工人階級、農民階級、知識分子群體)的社會結構正逐漸被打破,其中,一個不吃財政飯,與黨政機關、國有企事業單位員工完全不同的全新的社會群體——“新社會階層”正在崛起。日前由中國社會科學院、社科文獻出版社共同發布的《2017年社會藍皮書》就明確提出了“新社會階層”的概念,并指出高收入、高消費、工作強度大、生活節奏快是這一群體的主要特征。
什么是新社會階層?
在《2017年社會藍皮書》作者之一、上海大學上海社會科學調查中心常務副主任、上海大學社會學院教授張海東看來,從社會學研究的角度而言,“新社會階層人士”的“新”是指這個群體不在黨政機關、事業單位或公有制企業內就業,相對改革開放前社會群體而言是新生長出來的社會群體;從社會地位來看,“新社會階層人士”并不是一個嚴格意義上的階層概念,其內部階層地位顯然并不一致,或者說并不屬于一個階層。在不嚴格的意義上,可以說大部分“新社會階層人士”的職業地位與收入普遍較高,因此可以將其歸為“體制外的中間階層”。
新的社會階層是隨著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在非公有制經濟領域和社會領域出現的一些新的社會群體。新的社會階層人士主體是知識分子,主要包括民營企業和外商投資企業管理技術人員、中介組織和社會組織從業人員、自由職業人員、新媒體從業人員等。
根據調研統計測算,新的社會階層人士中,各群體規模分別為:民營企業和外商投資企業管理技術人員約4800萬人;中介組織和社會組織從業人員約1400萬人;自由職業人員約1100萬人;新媒體從業人員約1000萬人。由于各類群體間存在人員交叉現象,因而,上述數據直接加總多于7200萬人。
新社會階層的特點
2016年12月,中國社會科學院在京發布《2017社會藍皮書》,其中也提到了新的社會階層。
社科院根據來源于北上廣三地6000多個樣本的調查進行推算,北京、上海、廣州新社會階層人士群體規模分別為8.4%、14.8%、13.6%。藍皮書指出,新社會階層的高收入、高消費特征明顯。
新社會階層特點一:收入高
從個人收入來看,新社會階層在過去一年的平均收入達到166403元,遠高于社會平均收入75184元,是其2.21倍;而在家庭收入層面上,新社會階層過去一年的家庭總收入均值達到288826元,是社會平均收入147573元的1.96倍。
在北京、上海與廣州三地,新社會階層的收入呈現很大的差異。
從家庭總收入來看,上海的新社會階層收入最高,達到369131元;北京次之,為259978元;廣州最少,為201772元。而在工資性收入方面也呈現類似的特征。
在經營性收入和財產性收入方面,廣州排名均為第一,達到38447元。報告稱,“這可能與廣州的非公有制經濟活力更強、重商氛圍濃厚、有更多的人從事經營活動和財產性活動有關。”
新社會階層特點二:消費能力強
在消費水平與消費能力方面,數據顯示,北上廣三地新社會階層在過去一年家庭總支出的平均數達到131459元,是社會平均水平的1.71倍。
在各分項的支出方面,新社會階層的飲食支出為35433元,略高于社會平均水平25832元;服裝配飾支出為14720元,比社會平均水平高92.8%;醫療支出為6778元,高于平均水平38.9%;教育支出與住房支出明顯高于社會平均水平,分別是其1.68倍和1.40倍,說明相對于社會其他階層來說,新社會階層自身的消費能力更強,也擁有更巨大的消費潛力可發掘。
新社會階層特點三:經常換工作,生活節奏快
新社會階層就業穩定性比較低,工作變動非常頻繁。根據社科院的調查結果,三地有53%的人表示以前換過工作崗位,高于社會平均水平的37%;有11%和7%的人表示更換過兩次或者是三次工作;而從未來的職業規劃來看,很多受訪者表示兩年以內打算找一份新工作或者創業。
收入這么高,為什么還很焦慮?
新社會階層的生活聽起來很不錯,但是,值得關注的一點是,盡管收入較高,但這個群體在收入上的自我認同感并不高。上述中國社科院的報告顯示,新社會階層人口中,只有27%認為自己個人是屬于中產階級,64%的受訪者認為他的家庭不屬于中產階層。實際上,從中國普通家庭來看,這一階層的家庭年收入已是相當驚人。但是,64%這個比例的“不認同”值得深思。
這從新的社會階層的支出結構可窺見一斑。實際上,他們的支出結構中,發生在飲食上的支出與社會平均水平差別不大。但是,教育支出與住房支出明顯高于社會平均水平,分別是其1.68倍和1.40倍。可見,教育、住房是其開支的大頭。這其中映射出的中國社會的住房、教育、養老、醫療等民生負擔之重,需要認真對待。這倒不是說這個階層的民生問題就特別重要,而是因為連這樣收入的階層,都缺乏經濟上的安全感,中國的民生保障壓力之大可想而知。
從新的社會階層內部來看,這一點同樣明顯。六成多的受訪者否認自己是中產階層,其中又分別有八成和六成的受訪者,認為自己和家庭的收入不足,以及資產總量不夠。之所以會如此,很大原因在于房價飆漲。這說明,許多大城市的高房價和高消費,不僅普通老百姓承受不起,即便名義收入看起來很高的新的社會階層,同樣不堪重負。高房價在中國已經形成獲利者甚少甚至多方皆輸的局面,這一點值得特別警醒。
同時,頻繁變動的股市,也常對人們的財富進行洗劫,因此許多人都對自己的財富有著很強的不安全感。正如清華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主任李稻葵,中產階層的焦慮,來自高稅負下對個人可支配收入增長的憂慮,來自不斷攀高的房價和教育、醫療、養老的高成本。
從任何一個社會來講,橄欖型社會是最能夠導向持久和諧和穩定的系統。如果中國這一階層的人數能持續不斷擴大,而且其自身真正形成較高的自我認同和經濟、社會安全感,國家和社會的長治久安將迎來福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