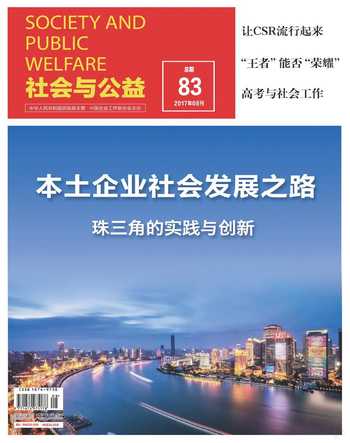本土企業社會工作發展之路珠三角的實踐與創新
關冬生
企業社會工作在我國(除港澳臺之外)的發展,無論是實踐還是理論,無論是行業實務還是專業教育,比社會工作在任何其他領域,都應該強調本土的創新。
如同社會工作源于工業化、城市化、市場化一樣,企業社會工作直接就是工業化、城市化、市場化的產物,與之相關的社會工作領域有工業社會工作、職業社會工作、工會社會工作等,相較于這些叫法,企業社會工作強調的是社會工作的場域,是一個涉及企業組織內外、以內為主的服務。之所以強調“本土的創新”,是因為我國的工業化、城市化、市場化的背景、道路、形式與西方社會的發展歷程有許多的不同。
我國現代企業的形成,主要是三個來源,一是國有企業、集體企業的改革演變;二是民營企業的興起;三是境外企業(含港澳臺)的進入。前者的改革進程中有一個將“單位人”變成“社會人”的銳變,把原有的社會職能以改革的名義去除了,而現在又在新的背景上以“企業社會責任”的名義回過來檢視其社會職能。中者在發展的初期,關注的只是經濟功能和經濟目標,而經過多年的發展,也殊途同歸一樣與國企、集體企業關注了“企業社會責任”。后者則在境外接受了“企業社會責任”的理念,有部分會把其理念與做法引進來,也有些企業進來后并不實施。
在工業化、城市化的進程中,80年代以來,一種叫做“工業園區”的集中發展模式在全國開花,大量企業是集中在一個與原有村鎮、城區有一定距離的,比較純粹自勺經濟功能區里。
在這些變化中,我國社會結構也隨之出現了非常大的變遷,人口從農村向城市、城鎮、工業園區大流動。而建立于戶籍制度基礎上的社會福利、公共服務也遭遇到前所未有的大挑戰。尤其是70、80年代出生的人群代替50、60年代出生人群,成為新型的流動大軍,流動兒童,以及被稱為“小候烏”的留守兒童、被稱為“老候烏”的離家隨遷照顧流動兒童的老人,對公共服務均等化、社會關系重構、社會融合的沖擊之大,恐怕在全球各國的工業化、城市化過程中,都是未曾遇到的一種新型“移民”浪潮。
因此,無論是員工個人與家庭層面,企業層面,還是園區層面與社會層面,我國企業社會工作既覆蓋生產適應、環境協調、企業福利、職業生涯等微觀內容,也涉及如何推動缺乏社會功能的“工業園區”發展為“產業社區”,以及社會福利制度、公共服務等社會政策的改革。無論是微觀的需求,還是中觀的社區建設與宏觀的政策發展,無不關系著不斷變遷著的產業大軍的切身利益和生活質量。因此,在我國開展企業社會工作,應該有新的視野、新的理念、以及新的理論和方法。
珠三角是我國工業化、城市化、市場化發展的前沿之一,對企業社會工作的本土探索,也走在了前列。源于西方的社會工作理念、理論以及個案、小組、社區等工作方法被賦予了許多新的含義。中國特色的由工會推動的企業社會工作。基于“產業社區”的整合型企業社會工作等一些新的形式更是大大豐富了我國企業社會工作的實踐和理論建設,成為推動我國社會工作本土發展的重要組成部分。